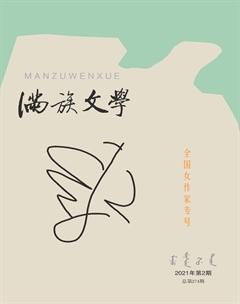潮與蟹
一
多年以前,通常是在暑假或者周末,我和虹莉手拉著手,悄然穿過第四中學寂靜的校園。我們腳下是紅磚鋪就的甬路,頭頂上古槐森森,兩旁佇立著一排排精致莊重的紅磚瓦房——直到成年以后,我才得知這些校舍的前身,竟然是建成于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海口檢疫醫院。繼續往前,拐過一幢哥特式紅磚小樓,從它旁邊的圍墻破洞里鉆出去,一片廣闊的黝黑河床呈現在我們眼前。不遠處帆檣林立,一條大河浩浩湯湯,不時有機動漁船“突突突”地從河面上開過去。
與中國的大部分入海河流不同,這條河的流向是從東往西。在我的整個少年時代,這件事總是讓我深感驚異:這條逆向而行的河,它與課本以及這個約定俗成的世界之間出現了難以說清的縫隙。而在某些時刻,一些河水調頭東流,與西行的同伴迎面相遇——水與水彼此沖撞,激起的浪花拍打著兩岸的河床,唰——唰——,大河漲潮了。
這個城市曾經有過多少道潮溝?沒人知道。潮溝如同血管,蜿蜒進城市的任意角落。大海憤怒的潮汐涌入這些血管,被引流,被稀釋,而后慢慢平息。沒有什么是不會退卻的,即便滿月之夜的大潮也是如此。對于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出生在這座城市里的一茬茬孩子來說,在家門口的潮溝里挖螃蟹,是十歲以前重要的戲碼之一。如今,你若問起這條河潮水漲落的時間,我唯有茫然;但是在多年以前,有一座精密的大鐘埋伏在我的體內,于潮落時分發出響亮的鳴音。
第四中學圍墻外邊的這條潮溝,名叫西潮溝。它或許一度是這座城市與西郊的分野,但在我的小學時代,城市已經擴展到這道界線的外邊。就在不久前,一位從事歷史研究的朋友經過長期考證,終于確認本地區最早的一座老炮臺曾經修筑于此。但在我和虹莉把這片河灘開辟為狩獵場之前,炮臺已片瓦無存。虹莉告訴我,第四中學合并入其他學校之后,這片校址就被廢棄了。當她帶著兒子試圖故地重游,卻只能止步于銹跡斑駁的大鐵門外。隔著鐵門的柵欄,她看見校園里荒草萋萋,她與父母兄姊住過的教師宿舍也已拆毀。她看不到我們倆一次次漫步其間的那條甬路了,它們消逝于時光漫漶的潮水。
但我知道西潮溝仍在那里。潮水退去,露出陡峭溝壁上濕漉漉的淤泥。潮溝的西岸是一片長滿野草與低矮蘆葦的荒坡,而在我們身后十米遠處,是一道與潮溝平行的高大圍墻,南端與四中圍墻相接,并一直向北延伸到河堤上,剛好把這一小塊河灘分割成獨立王國。河灘上密密麻麻布滿手指粗細的小洞,我和虹莉手持一根小木棍,自洞口的一側斜斜插入,藏于洞口附近的小螃蟹被截住退路,只得從洞中飛快逃出,成為我們的俘虜。有的則狡猾一些,或者純粹是嚇得呆住,這時我們將小木棍向上一挑,那只小動物便在一團黑泥中蠕蠕而動。每天供我們狩獵的時間實在有限,很快暮色降臨,河面上濁浪翻滾,河水就要收回它的地盤。
有一次在潮溝邊上挖得太過投入,我腳下一滑,整個人沿著陡峭的潮溝滑溜下去,幸虧被虹莉一把揪住衣領。兩個人在原地僵了好一會兒,這才緩過神來,手腳并用,渾身泥漿地撿回一條小命。
冒險捕獲的戰利品其實并無所用。雖然兩家的大人偶爾都會惋惜地說一句:“等把泥吐干凈了,和點面炸著吃很香呢。”但都只是說說而已,始終沒見他們有所行動。大約我們的收獲總是不夠多;而憑票供應的白面和豆油,怎么能為不值一文的小螃蟹肆意揮霍?
那些個傍晚,我和虹莉坐在她家門前的院子里——其實并沒有“院”,只有一個用碎磚頭壘就的小小的圓形花壇,里面常年種著幾株色彩繽紛的紫茉莉。我們用來囚禁小螃蟹的海螺殼就擱在花壇邊上,而螃蟹們早已蹤跡杳然。舊年的竹椅吱呀作響,我和虹莉開始探討小螃蟹到底去了哪兒。我說它們會不會趁著夜色沿著來路爬回去,反正全程也不過二百米;虹莉說它們也許正在花壇的下面挖洞,這樣完全不需要繞路,挖上幾十米就到了河邊。這支在假想中正在地下向著家園掘進的螃蟹部隊把我們迷住了,許多天里,我們都在猜測它們可能遭逢的奇境和難題。
至今我仍不知道,那些指甲蓋大的小螃蟹到底會不會長大,長大之后它們又去了哪里。或許這片河灘只是蟹族的育嬰場,一旦成長為少年,它們便要分道揚鑣,一部分遷入淡水沼澤,另一部分,奔赴兩公里之外的海洋。
二
黃昏時分,海退到幾百米開外。夕陽將水面鍍亮,成為遠方天際處金光閃爍的一線。夕光沿著潮濕的灘涂蔓延而來,它細如針尖的腳掌,在黝黑松軟的淤泥中一路沉陷。
這是蟹族的晚餐時間。大大小小的螃蟹們揮動大螯,在淤泥間揀選它們的食物——草籽、來歷不明的蛋白質殘渣以及極小極小的單細胞海藻……想起年少無知,竟以殺戮為游戲,我不由得心生愧意。
薄暮的柔光籠罩著它們。淤泥細膩,濾去了塵世的聲響,也將擅長制造聲響的人類阻隔在岸上。有兩三個幼童突破了泥灘的邊界,他們努力向前伸出沾滿泥漿的小手,試圖抓住距離最近的幾只小蟹。他們的父母陪在一旁,臉上掛著溫存的笑容,而螃蟹們埋首就餐,對孩童和他們的家長視而不見。它們之中,有的外形與多年前被我捉到的小蟹一模一樣,通體灰黑,大小只及成人的指甲蓋;有的則大如鴿卵,看上去威風凜凜,是步兵隊列中昂然而立的驃騎將軍。我以為它們會將身形小巧的同類一口吞下,但是錯了,它們彼此相安無事——縱使人世早已習慣了叢林法則,但這些小蟹,卻并非大蟹們的美餐。
在這些靜默的裝甲車隊列里,間或有白光一閃——雄性招潮蟹開始大秀它們的俊美風姿。與色彩低調的雌性不同,雄性招潮蟹擁有鋼藍色的盔甲,除了一只用于進食的小蟹鉗,還配備一只巨大的戰斗器,色澤紅白相間。雖然這些戰士的整個身寬不會超過六厘米,但當它們的招牌大螯伸展開來,尺寸之巨令人驚嘆。夸張的比例絕非僅限于裝飾功用,很快我們就會知曉,這只巨掌將如何替它的主人俘獲愛情。在泥土色的雌蟹中間,這些美男子一邊來回走動,一邊將鮮艷的巨鉗舉過頭頂。白光在鋼藍色的底調上不斷劃過,不僅博得了異性的注目禮,也為男生們贏得了“提琴手”的美名。伴隨著琴身的跌宕起伏,隱形的琴弦彈出悠悠樂音,誘惑之舞隨之跨入高潮時分。
但是白光同時也會吸引掠食者的視線,使性感的舞蹈時刻伴隨著性命之憂。很多海鳥熱衷于品嘗新鮮蟹肉,包括鳶、翠鳥、三趾鷸以及燕鷗。它們從蟹群上方掠過,瞅準時機疾沖而下。鳥羽投下的銳利剪影拉響了空襲警報,蟹們四下奔逃,一頭扎進距離自己最近的某個洞穴。盡管這些地下防空洞個個建造得幽深曲折,但并不足以保障避難者的安全——千萬年來,為了追索這些擅長土遁的獵物,海鳥們進化出了長而彎曲的喙。
因此,在招潮蟹的世界,住宅的價值評判系統與人類異常相似——位于城市中心的樓盤往往最為珍貴——無論空襲從哪個方向降臨,無數只蟹腳驚惶雜沓,危險警報總能迅速傳遞到蟹城的中心。而鳥們棲息的樹木佇立在海濱的外緣,即使靠近海岸的洞穴可以向大樹借取幾分蔭涼,但同性命相比,這一點收益完全可以忽略不計。
每年四月,遷徙的水鳥從北極趕來,途經這一片海濱,在此匯集成陣。近岸處的海面上鳥浪翻滾,極是壯觀。但是鳥潮很快散盡,在這個夏日的黃昏,蟹族享受著它們安恬的晚餐時間。
三
自然界似乎有意要求雄性生物承擔起某些重任,卻又讓它們看起來不務正業游手好閑——在招潮蟹這里,雌性隨身攜帶兩只刀叉用于進食,雄性則硬生生勻出一只用于表演。我疑心它們在一段時間里經常餓著肚子,因為除了兼職演出,它們還有更為重要的事業——與人類一樣,男生們需要整飭住宅,迎娶新娘。這些邋遢的單身漢平日里得過且過,到婚禮前夕突然判若兩蟹,開始忙里忙外,異常勤謹。它們的大螯化身為卷尺,用于丈量房間各處的尺寸;余下的八只腳則充任挖掘機,掘走多余的淤泥。新房的門口也要修整和加固,最后還要四處尋找營養沉積物,并將之團成球狀,逐一搬進新房,做好食物儲備。
并非每一位男生都長得高大健美,倘若不幸天生相貎平平,它們就必須在住房上耗費更多的心血,以期在接下來的愛情競爭中獲取加分。時辰到了,它們恭候在整飭好的新房旁邊,豎起兩只眼睛,向著雌蟹群中翹首張望。一旦視線中出現了意中人,它就開始加速揮舞自己的招牌提琴,頻率由原來的每分鐘五次,陡然提高到兩秒多一次,這樣一邊頻頻打著愛情旗語,一邊直奔意中人,先將自己的背甲展示給對方,并且高舉巨鉗抖動身體,像健美選手秀出鼓凸的背肌,然后推著意中人前往自己的新房。如果這一系列求婚動作有失魯莽,或者有什么地方未能達到對方的擇偶標準,就會遭到無情拒絕。但如果它的熱情表達得恰到好處,同時展現出優雅、力量和風度,新娘就會半推半就,順從地被擁進洞房。然而變故隨時可能發生,在進入新房之前,有可能會斜刺里殺出來一個程咬金,試圖橫刀奪愛。一場戰爭由此展開,雙方廝殺得如火如荼,被撇在一邊的新娘等得不耐煩,索性悻悻走開。直到戰斗分出勝負,兩位男士回過頭來,才發現新娘子已消失在茫茫蟹海。
而旗語也會招來競爭者的注意。看到別人的婚房整飭一新,又處于比自家更好的位置,不僅有利于自身的安全,還可以吸引到更多的意中人——一念及此,這個小強盜就會跑來搶房子。這場住房爭奪戰往往比爭奪新娘更為慘烈,考慮到新房的昂貴成本,雙方均會以命相搏。兩只巨鉗直指對方的要害,在這當兒,螯鉗大小的重要性就顯現出來,武器偏小的一方會選擇退讓。但如果雙方勢均力敵,那么這場相撲賽可能會持續數分鐘。多數時候,新房的主人事先占據了有利地形,牢牢據守在房間門口,而挑戰者失去平衡被扳倒在地,只得俯首認輸。
總之,情場上總是戰火頻仍,從蟹族到人類,概不能免俗。
歷經種種波折,準新娘終于踏入求婚者的家中,如果對新房的各方面條件均感到滿意,它就會留下來。直到此時,候在洞口的新郎才會歡慶勝利,再一次揮舞它的鉗子。隨后,它將一側的四條腿勾成籃子,把早就準備停當的一堆泥土鏟進籃中,僅用另一側的腿腳爬行,用泥土封住洞穴的入口。
眼下,這個密閉的小天地暫時遠離了人世。在這里,新娘和新郎共同完成屬于它們的愛情儀式。作為結晶,攢聚在一起的受精卵看上去就像一串串迷你的紫葡萄,隱藏在母親腹部圍裙狀的肚臍下方。接下來的十天里,這些卵會在母親的臍下孵化,在成熟時轉變為豐腴的灰色卵塊。因為身懷六甲,母親們行動緩慢,只得終日閉門不出。直到某天夜里,海潮再一次來臨,母親們走出房間,費力地爬上淺灘。在清涼的海水里,它們開始擺動身體,卵殼應聲開裂,成團的幼蟹離開母親,投身大海。這個過程進行得如此安靜,沒有誰覺察到,以千萬計的新生命正于此間啟程。
當潮水再次回落,將無數只幼年之蟹帶往外海——這些比針眼還要細小的蟹,它們是否擁有關于世界的清晰認知?在海洋這個偌大的宇宙里,它們中的大多數會很快死去,而幸存者們經過數周的歷險和漂泊,會在某個遙遠的海岸,幸運地登上陸地。在那兒,它們將延續祖輩們的生活,在或沙質或泥質的海灘上建起家園,等待一波又一波的海潮為它們帶來盛宴。
而在它們誕生的那天夜里,月光鍍亮了寂靜的海濱。那是農歷十五的月亮,形狀幾近正圓。
【責任編輯】王雪茜
沙爽,作品散見《詩刊》《散文》《鐘山》《天涯》《大家》等刊。出版有散文集《手語》《春天的自行車》《逆時光》《拈花》,長篇歷史人物傳記《桃花庵主——唐寅傳》,歷史隨筆集《味道東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