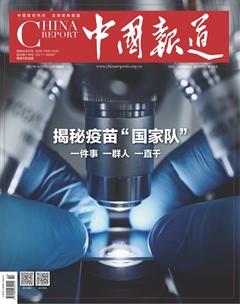中國生物臨床醫學中心副主任楊云凱:“一輩子和活病毒打交道,在心理上已經免疫了”
陳珂
一路跟這個項目,我有責任去,也是最合適的人選之一。

在阿聯酋,每一個參與新冠病毒滅活疫苗Ⅲ期臨床試驗的志愿者的監測手環上,都寫了這樣一行字——為了人類(For Humanitiy)。楊云凱說,這個創意是由合作伙伴提議、長城項目組整體策劃的,以此表明全人類命運與共、共同抗擊病毒的決心。
楊云凱是中國生物臨床醫學中心副主任,有28年疫苗生產研發經驗和18年臨床研究經驗。從2020年7月9日隨項目組來到海外開展新冠病毒滅活疫苗Ⅲ期臨床試驗以來,她已有將近200天沒有見到過家人。“出來的時候,大家奔著要把試驗做成的目標去,一轉眼都過去這么長時間了。只要我們的產品在國內能盡快投入使用,大家都覺得付出是值得的。最艱難的時候已經過去了。”
信心倍增
楊云凱已經記不清哪天開始就忙了起來,她只記得2020年春節一頭扎進新冠項目里后,休息變得格外奢侈。在疫苗研發初期,楊云凱主要負責制定動物安評實驗方案,并在完成實驗后著手申報臨床批件。
動物安評實驗是疫苗研發必不可少的一步。面對龐大的研發需求,實驗動物明顯不夠用。3月初,各地在疫情防控上嚴陣以待,用于實驗的主要動物——猴子進不了京,“實驗動物緊張,下一步就無法進行。”楊云凱克服重重困難跟有關部門聯絡,幫助辦理猴子進京手續,隨后又盯著團隊完成每個實驗環節。“那時候沒有失敗了反復重來的時間,又是個新產品,用多少劑量、走多少程序、能不能在最短時間里得到最好的結果,都是未知數。”
但幸運的是,好消息很快傳來。武漢生物制品研究所2020年3月8日至4月7日開展的動物安全性評價工作研究結果顯示,動物沒有出現任何異常反應和不良反應。這意味著可以開展臨床試驗了,楊云凱立即著手臨床批件申報工作。4月12日,武漢生物制品研究所申報的新型冠狀病毒滅活疫苗獲得國家藥監局臨床試驗許可,成為全球首家獲得臨床試驗批件的新冠病毒滅活疫苗。“那天剛好是我48歲生日,非常開心啊!”半個月后,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也傳來同樣的喜訊。
不容等待片刻,兩家研究所均在獲得臨床試驗批件的當天就開展了新冠滅活疫苗Ⅰ/Ⅱ期臨床試驗,而批準企業同步進行兩期試驗也是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在應急審批上的創新。
“沒有人顧得上休息。”工作28年來,楊云凱經手的十幾項臨床有四五個已經上市,包括OPV、IPV等產品。這次臨床她主要負責制定試驗方案,并在技術上給出指導。在疫情期間完成試驗要克服的困難有很多,而試驗完成后,疫苗有效沒效,揭盲就特別重要:結果好會給大家信心,結果不好又得重新研發。“其實對于疫苗臨床來說,每次揭盲都是這樣,不過大家對這次疫苗的期待太大了。”楊云凱對《中國報道》記者表示。
6月16日和6月28日,武漢所、北京所研制的新冠病毒滅活疫苗Ⅰ/Ⅱ期臨床試驗盲態審核暨階段性揭盲會先后均在北京、河南兩地同步舉行。楊云凱見證了兩次揭盲現場,回憶起來她仍有些激動:“揭盲的結果都顯示,按照兩針間隔28天程序接種兩劑后中和抗體陽轉率達100%,證明了我們的疫苗是安全的。所有人都信心倍增。”
使命當前,絕不退縮
而事實上,完成Ⅲ期臨床試驗是疫苗最終研發成功的關鍵。
“沒有Ⅰ/Ⅱ期的數據開不了Ⅲ期,而Ⅲ期的數據決定了疫苗能否上市。”這也使Ⅲ期臨床試驗與Ⅰ/Ⅱ期有所不同:必須要讓受試者有機會處在病毒存量較多、疫情未受控制的區域,且需要人數眾多的受試者。中國生物積極推進Ⅲ期臨床的海外合作,并在2020年6月23日獲得了阿聯酋關于新冠滅活疫苗國際臨床(Ⅲ期)試驗批準文件,項目團隊組建工作隨即啟動。
接到7月9日出發的通知那天,留給楊云凱的準備時間還有不到一周。其實這一刻對于她來說,是已經在思想上準備好了的。“一路跟這個項目,我有責任去,也是最合適的人選之一。”楊云凱沒有絲毫猶豫。

當地時間2020年8月27日,巴林首都麥納麥,國藥集團新冠疫苗臨床試驗在改造過的會議中心里進行。國藥集團的新冠疫苗最早獲得阿聯酋的三期臨床批件,之后又相繼獲得巴林等臨床批件。
但她不知道怎么告訴將要參加高考的兒子。因為疫情,2020年高考推遲一個月舉行——剛好和出發的時間重合,會不會給孩子增加心理負擔,打亂備考節奏?但讓楊云凱欣慰的是,兒子不但理解她的工作,還說考試不需要她陪,叮囑她在外面保護好自己。
7月9日早上7點,國藥集團生物制品事業部總裁、中國生物黨委書記朱京津率領北京生物所、武漢生物所、中疾控、河南疾控中心等29人組成的“國藥集團中國生物長城項目(Ⅲ期臨床)組”出現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29人中,最大的是“60”后,最小的是“90”后,他們有的從家里起早趕到機場,也有的5點起床先去單位取了實驗器材后再去和大部隊會合,很多人的行李是臨行前抽空收拾的。
“新聞里說病毒蔓延給經濟帶來影響,看到眼前空蕩的機場,這種體會更深了。”楊云凱當時心里只有一種使命感,把疫苗提供給社會——不僅為了保護健康,也為了讓人們回歸原來的生活。臨行前,國藥集團特意舉行了簡短的出征儀式,“更讓我們覺得要把這件事做好。”
“困難只是暫時的”
經過近9小時飛行,項目組抵達阿布扎比,入住當地一家距離接種點二三十分鐘車程的酒店。此后的近200天時間里,在阿聯酋展覽中心開展試驗的成員就這樣每天往返于酒店和接種點之間。
“阿布扎比當時是疫區,包括后來試驗進行過程中,每天也有1000多人確診。試驗要完成,鎧甲也得穿好,所以我們當時是接種了自己研制的疫苗后出來的。”楊云凱告訴《中國報道》記者,自己一直和活病毒打交道,在心理上也免疫了。
抵達后的隔離期間,項目組并沒有閑著——通過線上會議和合作方籌備試驗的前期準備工作,跟當地的研究者、臨床實施機構商量計劃,包括和對方明確需要提前準備什么、怎么招募志愿者,并確定好每項任務的負責人。楊云凱坦言,在境外開展試驗的難度從這時候開始就表現出來了。
“每個國家的研究者都有自己的特點,試驗怎么做、采血流程是什么、怎么處理血清樣本……召開電話會議時,我們不止一次在類似問題上激烈討論。”楊云凱并不覺得語言不通是最大的障礙,不同文化背景下統一方案標準、規范方案執行才是最難的,“只有所有現場的實施標準和實施流程一樣,將來才可評價。”她總結說,最重要的是確保試驗的規范性,雙方一路走來是相互說服的過程。
7月16日,準備工作就緒后,項目組在阿布扎比率先啟動入組。此前一天,阿布扎比衛生部長艾哈邁德作為志愿者接受疫苗接種。“我們在現場見證了這個時刻。”
但這不意味著一切順利。阿布扎比剛啟動入組時,每天的入組量僅有幾十人。“對于臨床試驗來說是正常現象,尤其是疫苗來自別的國家,受試者總會有一個慢慢接受的過程。”盡管對此有所預期,楊云凱依然感到頭上有一座大山壓著。
為此,楊云凱提出了無數條建議,當地電視臺、新媒體也不斷加大宣傳力度,政府官員帶頭參與臨床試驗接種疫苗。8月4日,入組量終于首次突破1000,此后每天也都保持在這個數字以上。
兩個月,45000人
在阿布扎比開展試驗的同時,長城項目團隊在朱京津帶領下積極推動在阿聯酋周邊國家開展聯合試驗,拓展新的臨床試驗現場,并先后在巴林、約旦、埃及等開設了分中心。
8月4日,作為技術負責人,楊云凱前往巴林參與臨床試驗入組工作,并駐場一個月——她要協助做好質量把控和督導,確保所有環節不能出現紕漏。
“每個人都是長城項目團體的一分子,往每個點派人時,我會兼顧到各個方面——負責質量把控的、負責現場接種的、負責數據整理的,這樣才能保證及時解決每個環節遇到的問題,有比較難的共性問題了再反饋到阿布扎比現場。”
有了之前的經驗,5個國家和地區完成所有入組工作僅用了兩個月,共完成約45000人的入組量,為疫苗研發提供了有力支撐。
“不同階段的工作重點也不同。”楊云凱說,入組結束后,試驗以接種、采血為重點,目前主要進行的是病例收集、觀察疫苗保護力。“從知情、體檢、采血、接種再到隨訪,4萬多名受試者把所有流程走一遍,雙方工作人員都付出了巨大努力。”
“阿布扎比的節奏不像我們那么快,剛開始的時候人家到點就要下班,我去溝通讓他們也加班把當天的工作做完,后來慢慢也接受了。入組量平均每天1500的那段時間,至少有20多天我們一起熬到夜里12點,所有人都是連軸轉。其實對于能夠參加臨床,當地的醫生也是與有榮焉。”楊云凱向《中國報道》記者回憶說。
中國和阿布扎比有4小時時差,家人也只能找合適的時間和楊云凱聯系,但經常撲空。
“最大的理解和支持來自家人,但我虧欠兒子太多:沒有陪他參加高考、沒有給他辦18歲成人禮……”為了彌補,楊云凱在兒子生日那天,特意請外國朋友錄了一段阿拉伯語的祝福視頻。“考上大學后就在學校住了,周末回家了我倆就聊聊天,我會問他大學生活怎么樣,他會問我試驗進展到哪兒了。當看到疫苗在阿聯酋上市的新聞時,他會自豪地跟同學講‘這是我媽媽參與的項目,還特意把新聞轉發給我。”
2021年1月10日,長城項目組凱旋歸國。飛機落地后,楊云凱百感交集。“回家的感覺真好!”等隔離期滿后,她打算好好陪陪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