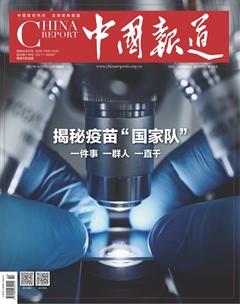讓皮影在“不安分”中生存
陳珂

“一個10分鐘的小節目,5分鐘后開場。”話音剛落,路寶剛已經麻利地坐到音響設備旁,幾個年輕演員隨即走到幕后,打開頭頂上方的一排燈光,將道具緊貼在幕布上。伴著輕松的音樂,一只烏龜和一只仙鶴斗智斗勇的故事被靈活演繹,中間沒有一句臺詞。對北京皮影劇團團長、北京皮影第五代傳承人路寶剛的采訪就從這則寓言故事《龜與鶴》開始。
這出戲中,鶴的動作最多,操作起來難度也最高。路寶剛最開始演是在1981年,那年他17歲,為了觀察鶴是怎么跑的、怎么跳的,他拿著面包往動物園一坐就是一整天。這種越難越要做好的個性伴隨了路寶剛全部的皮影生涯,以至于后來面對“北京皮影該走向何處?”這個難題時,他也在不斷嘗試給出自己的答案。
“一口道盡千古事,雙手對舞百萬兵”
一塊白色幕布加上燈光映出的影子,一個個影人就在光影搖曳中、在藝人們的股掌間鮮活起來。北京皮影到路寶剛這,已經傳承了五代。
1957年,北京皮影劇團在路家德順皮影班社的基礎上組建而成,他的父親任第一任團長。回憶起來,路寶剛覺得自己一生都在與皮影膠著。“給我一個機會讓我證明我是路家人,沒給我父親丟人。”在這股信念的支撐下,路寶剛每天都在別人下班后再練上幾小時、劇團排練時在后臺學習老藝人的表演技巧……當他慢慢意識到皮影的無窮趣味時,他開始敬畏皮影,并在皮影傳承的道路上摸爬滾打至今。
皮影和觀眾的良性互動,是路寶剛樂于提及的過往。2006年,當時的北京市文化局為擴大京郊農村群眾性文化活動范圍,推出“文藝演出星火工程”,北京皮影劇團也受邀參與巡演。路寶剛說,在延慶最多一年演了四十幾場,他帶著劇團每天凌晨4點從市區出發,到演出地點后吃早飯,還要多買一份當午飯吃。“觀眾都等著呢,演完轉場和吃午飯最快40分鐘內全部解決。”“演出服上的汗漬一圈一圈,累得晚飯都吃不下,演出結束后倒頭睡到天亮。沒有人理解我們為什么這么拼,但是大家高興,達到這種程度。”
2008年,北京皮影戲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北京皮影劇團成為傳承保護單位。盡管政府和業界一直在努力,但北京皮影似乎也沒能擺脫被冷落的命運——會耍皮影的人越來越少,愿意拿出一點錢為皮影買單的人也越來越少。在路寶剛看來,其中的原因三兩句話并不足以概括。
北京皮影劇團排練廳位于北京天橋藝術中心地下一層一個不起眼的角落:一張能容下10人左右的辦公桌,上面堆放著雕刻皮影剩下的邊角料,右拐是單獨一間排練廳——既承擔著劇團成員的日常排練,也是存放演出器材的小倉庫。“劇團每年大概承接上百場演出,我們只要沒有演出就來這里。”
“這塊兒蠟板流傳40年了,懸肘撅腕……在蠟板上雕刻不傷刀,下刀處也清爽流暢。”“和陜西皮影刻一個人物用20把刀相比,北京皮影一把執刀,再加上圓規、畫針、剪子等輔助工具,全拿下來了……”向記者介紹時,路寶剛絕不含糊,在他眼里,這些物件和手藝都是頂著光環的寶貝,只是當下它們似乎正不斷褪色。
新人不應當只是一個幫手
皮影喪失觀眾緣,盡管是多元娛樂方式沖擊下難以避免的現象,但路寶剛對此卻有清醒的認識:如果皮影哪一天消亡了,一定是人才沒有及時補位、沒有找對培養方法。
“我們真人沒多少,假人多了去了。”路寶剛掃了一眼堆在地上的影人,滿臉苦笑。目前劇團一共有16個在編皮影戲演員,年輕演員只有7個,“如果哪天走一兩個,我就得上。”因此他要求每個人都掌握表演、雕刻、音樂等本領——既是基本功,也是以備不時之需。
張杰2003年來劇團時剛15歲,現在是北京皮影西城區傳承人,也是兩個孩子的媽媽。“看過皮影,沒學過。那時候的皮影還不太一樣,幾個老頭在一塊白布后面扯著嗓子喊,人影是黑白的,燈是黃的。”張杰告訴記者,進團時,路寶剛還是隊長,他教自己從零開始學表演、學雕刻。
和張杰不同,90后的陳睿科班出身,2013年從北京戲曲藝術職業學院京劇表演專業畢業,并在當年進了北京皮影劇團。她和張杰一起被路寶剛視作劇團未來的希望,采訪期間,每當她倆提出比較新穎的點子時,會引得路寶剛興奮地連拍幾下桌子。
但在路寶剛眼里,張杰和陳睿代表了兩種完全不同的培養方式。他稱張杰是“隨團學員”,“15歲的孩子,中學還沒畢業就到我這兒來了。我教她的只能是有限的表演和雕刻,沒辦法教孩子形體、樂理知識,缺項太多了。”但他也說張杰因皮影而有才,“因為她在18年的皮影學習中做到了有心。”不同的是,“陳睿接觸到了完整的學校教育,有扎實的基本功,京劇表演技巧能夠很好運用到皮影表演中。”
皮影人不應當僅僅是技藝嫻熟的民間藝人,更應該是全面發展的藝術家,對此路寶剛深表認同。“新人今后要走學院派的路子,任何劇團或單位都達不到學院或者學校培養孩子的要求。”路寶剛解釋,后備人才要有充足的基礎知識傍身,包括表演、樂理、形體、造型、化妝、舞美等,否則培養出來的,充其量是一個幫手。“就像一個金字塔,那些在學校學到的知識是金字塔的底座,底座穩了,才能站穩。”
也是在耗費了一定的精力和財力后,路寶剛才逐漸認識到這一點的。“真正的傳承人不是我,是他們。但是目前來看,需要我的時候有‘大師,不需要我的時候一撒手、還沒轉身或許他們就掉地上了。”為了不讓年輕人“掉地上”,路寶剛每年都會請中央戲劇學院、中央美術學院的老師講授形體、聲樂等課程,一個學期大概十四五次。“但事實證明,達不到學校學習的效果。”眼下,路寶剛正在尋求新的培養方案。
《影戲傳奇》只是一個開始
人的因素是一方面,對皮影未來的思考或許還有其他思路。
路寶剛評價自己“是一個不安分的人”,由此也使北京皮影變得“不安分”。“一塊兒白布、燈光照上去映出影子,41年演了多少場我不記得了,不僅我煩,觀眾也早就煩了。”
2005年9月15日,“冀東油田杯”2005中國唐山國際皮影藝術展演拉開帷幕,北京皮影劇團一共捧回5個獎項,其中路寶剛導的《孟姜女》榮獲創意獎——這也是北京皮影在“不安分”中獲得的第一個跨界融合獎。“整臺戲用到了人影、人戲、真人表演,用同比例縮小的城磚做了一個真的烽火臺。孟姜女拿著寒衣到長城腳下尋找萬喜良,最后知道丈夫去世后,她眼淚決堤,然后是長城倒塌。現場掌聲雷動。”
“皮影要不消亡,必須得借助外力,打破舊思路。”這是路寶剛自那以后的最大感受。“傳統表演形式把觀眾吸引到劇場已經不可能了,這一點不用懷疑。未來不僅要研究觀眾想看什么,還要思考皮影怎么重獲新生。”
做一臺影戲,是路寶剛的第二次“不安分”。“5米幕布、8米幕布在1200人的劇場里,從遠處看就一‘屁簾兒。而有光就有影,不管是多大的舞臺,影戲可以占滿整個劇場。”他認為,皮影只是中國影戲當中的一個分支,人影、偶影,每一個單拿出來都是珍珠,但缺少一條線把它們串起來制成珍珠項鏈。“這條線就是把各種影子集中起來,并用它們來演故事的藝術手段。”
2019年7月5日,由北京天橋盛世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出品、北京皮影劇團制作運營的創意影戲親子舞臺劇《影戲傳奇》迎來首演,路寶剛覺得這次演出很成功。
《影戲傳奇》專為孩子們量身打造,時長70分鐘,主要講的是天真頑皮的女孩小小無意間喚醒了2000歲的皮影人“大巴掌”,當燈光照進“大巴掌”的身體,一場講述皮影前世今生的穿越型故事就此展開。
對路寶剛來說,《影戲傳奇》是北京皮影結合影戲的一次成功實踐。將皮影戲藝術和舞臺現實真人表演相結合,融合了人影、皮影、紙影、景影等多種光影藝術,除了呈現《哪吒鬧海》《花果山》等北京皮影戲的經典段落外,整部劇還從舞美、音樂和表演等方面進行了創造性藝術嘗試。“如果孩子們看完戲走出劇場,嘴里叨念著戲里的故事,哼唱著其中的小曲,這就是我們最大的成功了。”路寶剛說。
《影戲傳奇》原本要在2020年演30場,受疫情影響目前一共只演了10場。路寶剛沒有想到的是,場場爆滿,還出現了黃牛倒票。事實上,在路寶剛看來,《影戲傳奇》只是一個開始,它最吸引人的地方還在于勾連起了對北京皮影未來可能性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