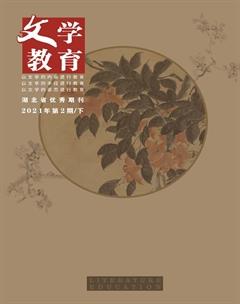方言的隱喻功能在電影中的應用
王海燕
內容摘要:漢語方言涵蓋的不僅是這一地域通用的語言系統,還包括當地的文化風俗、地域特色等。它對電影中塑造人物形象、強化敘事背景等都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方言的恰當運用既構成了電影語言的一個分支,還可以隱喻非語言層面的內容,加強對作品主題的渲染。方言的隱喻功能主要表現在強化人物形象、展現地方文化以及增強文化認同感等幾個方面。
關鍵詞:方言 隱喻 人物形象 地方文化 認同感
方言,俗稱地方話,通行于一定的地域。漢語中存在著多種方言。近年來,電影中運用方言的情況日益增多,也逐漸顯出了方言為熒幕帶來的不一樣的色彩。美國路易斯·賈內梯在《認識電影》中提到:“在電影中,方言包含了許多豐富的意義。”[1]方言的合理運用可以讓作品的人物形象更加鮮明,為電影營造更加別致的氛圍。
隱喻廣泛應用于人們對生活的認知過程中。具體來說,隱喻是“靠喻體將自己外形、特征、結構、行為、功能、價值等的信息,包括它的形態、內在的復雜程度、不規則性等各種特性向本體投射,使得認知主體對二者的感覺是相似的。”[2]漢語方言是集歷史、文化與一體的語言形式,它所涵蓋的不僅是這一地域通用的語言系統,還包括當地的文化風俗、地域特色等。它對塑造人物形象、強化敘事背景等都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方言的恰當運用既構成了電影語言的一個分支,還可以投射出非語言層面的內容,加強對作品主題的豐富、渲染功能。
一.方言對人物形象的隱喻功能
語言可以分為語音、詞匯和語法三個主要部分。人們通過對某一方言的語音、詞匯、語法的感知,往往會自覺地在大腦中對其進行“解讀”。但是通常情況下,人們最直接感知到的是語音、詞匯方面的差異。隋朝陸法言就我國方言的特征做出過這樣的評價,他說:“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為入,梁益則平聲似去。”袁家驊等在《漢語方言概要》中引用了《顏氏家訓》“音辭篇”顏之推對方言的理解:“南方水土柔和,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水深厚,其音沉濁而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3]從語言學研究的角度來看,這些根據地理條件分析方言的解釋或許難免有失偏頗。但這兩種說法更側重描述人們對方言差異的直接感知。從直覺感知本身來說,人們對方言的確有著一種自發的認識,并且會形成一種獨特的判斷。如人們通常認為北京話聽起來是“京油子”的感覺,認定北京人擅長“侃”;天津方言聽起來夠“哏兒”,山東方言給人的感覺為“侉”,而南方方言則是“蠻”。
人們的這種認知能力有時甚至可以很細化。除了在綜合層面上,還能就相鄰的方言進行評價。比如在江蘇省徐州市一帶的人看來,自己的口音和河南、山東等地的口音都是“侉”的,連云港、泗陽一帶的口音是“□(音MAO,陰平調)”的,由此再向南到蘇州等地就是“蠻”了。這種看法與方言學上的畫分其實是很相近的,“侉”的口音就是中原官話,“□(音MAO,陰平調)”的口音是江淮官話,而“蠻”的口音就是吳語。徐州一帶的人認為與“□(音MAO,陰平調)子”是可以交流一些的,但是“蠻子的話咦哩哇啦實在是聽不懂”。這些看法我們都可以從方言學的角度來給出解釋,“侉”和“□(音MAO,陰平調)”都是屬于官話,有一定的共性;而“侉”和“蠻”分屬兩個不同的方言區,自然交際上會存在困難。
當然,這種“土人感”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往往要受到一定的地域限制。人們的這種看法通常是局限于自己周圍的區域,而不能大范圍地擴展。比如蘇州和廣州相距很遠,但是正是因為這兩個地方對于徐州人來說都是遙遠的、陌生的,反而就忽視了其中的差別,把這很長一段距離視為“都是南蠻子”。
對方言的認知往往和評價運用這種方言的人直接相連。這種方言特征的判定自然也會被觀眾應用到電影人物角色的判定當中。聽到電影中的人物說某一地的方言時,觀眾往往就會在心中對其進行“預設”,認定這個角色可能有怎樣的特征,并將其與自己想象中的形象進行比對。如馮小寧導演的《舉起手來》中的郭大叔(郭達飾演),他出場時的一口陜北方言迅速會讓觀眾在腦海中塑造起來一個陜北的農民形象。郭大叔既積極參加抗戰,但是又有著一般老百姓缺乏戰斗經驗的那種“一驚一乍”。但是,觀眾因為有了心理上對這個人物形象的“預設”,所以能夠接受這個人物的表現。影片中方言的使用還隱喻了為了保護自己家園,中國千千萬萬的老百姓自覺地加入到戰爭中,他們拿起武器,用自己獨特的方式進行戰斗。影片中,稚氣未脫的孩子以彈弓做武器,已是古稀之年的老奶奶端起簸箕倒豆子,都是這一隱喻的表現。
張藝謀導演的《一個都不能少》中的臨時代課教師魏敏芝所用的方言則給她增加了一份特有的執著和較真,話語雖然不多,但是很“沖”,只認一個理——就是把學生看住——即便是村長想把學生帶走也不行。為了找回一個跑去打工的孩子,她費盡周折。當她終于坐到電臺的鏡頭前,她也只是簡單的三兩句話,但就是那一句“一個不能少”,足以觸動觀眾的內心。這個“犟得十頭牛拉不回來”的孩子在那一刻讓無數觀眾淚奔。
方言的隱喻功能還在于可以進一步豐富影片中的人物形象,將人物角色的成長發展過程敘述得更加完整。如馮小剛導演的《手機》中,嚴守一的河南話和費默的四川話雖然使用得不多,但是都恰到好處地為兩個角色增添了不一樣的色彩,讓這兩個人物都有了“根”,從而完成了對嚴守一和費默從小到大的成長經歷的交待。小時候的嚴守一正是因為與電話的一次意外接觸,才引導他成年后走上了主持人的道路。這一描述同時也讓觀眾不禁思考一個問題,究竟是什么原因,讓曾經那個純真、善良的少年,變成了現在這副模樣。雖然影片中更多的是集中展現了嚴守一的成長過程,但是觀眾也不難聯想到,費默必定也有著相似的經歷和過往。這種隱性的“補充”對人物角色的性格特征、行事風格等的塑造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使影片的敘事線索得以完善。方言的這種功能是其地域性所賦予的,也是它的獨特性之一。試想,如果僅以普通話作為這部影片的語言的話,可能就會忽略了這些內容。
二.方言對地方文化的隱喻功能
我們國家地廣人多,地理條件多樣,方言復雜且差異性大,有的方言之間甚至無法進行通話。因此從很早時期,人們就開始重視共同語。春秋時期的“雅言”可以算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普通話”,后來歷經兩漢、隋唐,漢語共同語的發展趨于成熟,之后又經過幾百年的演變,語言再次進行華麗轉身,形成現代漢民族的共同語。“漢族共同語的歷史是中國文化史的縮影。”[4]為了加速國家現代化建設的步伐,20世紀50年代,我們確立了普通話的標準,將其定義為: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范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范;2000年10月,我們國家還專門制定了專項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以加強對語言文字應用的規范化、標準化。
在確立普通話、推廣普通話的過程中,我們對方言與普通話之間的關系,一直保持清晰而明確的認識。它們兩者之間既對立又統一。普通話是全國通用的語言,推廣普通話是人們進行語言交際的實際需要。但是,從語言演變的實際情況來說,普通話和方言之間難免會相互影響。普通話會吸收方言中的詞語,方言會向普通話靠攏。一般而言,方言的變化會相對大一些、快一些,甚至會導致一些方言中特殊現象的消亡。這也是方言學研究工作者們比較擔憂的問題。
基于普通話和方言的交際功能和應用范圍的差異,人們對普通話和方言的“地位”認知自然也不同。陳章太提出:“普通話又是文化教養的標志,普通話普及程度是衡量文化教育發達程度的重要標志。”[5]路易斯·賈內梯也說:“在電影中,方言包含了許多豐富的意義(在生活中也是)。因為方言通常流通于低下階級,傳達他們顛覆的意識形態。”[1]普通話在地位上高于方言,但是方言也有其自身不可忽略的特色,它承載的不僅是語言本身的交際功能,還涵蓋其領域中所屬的文化要素。雖然人們或許會“看低”方言的地位,但是方言所承載的文化特色、地域特征等卻是無法忽略的。
周振鶴、游汝杰提出:“語言是文化的產生和發展的關鍵,文化的發展也促使語言更加豐富和細密。”[6]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方言是一個地區重要的文化符號,不同方言可以展現不同的風土人情、文化風俗。方言在電影中的運用可以有效拓展電影作品本身帶給觀眾的信息。觀眾不僅可以直觀地看到影片中的故事、情節、人物等,還可以看到其發生的環境。如寧浩導演的《瘋狂的石頭》為觀眾展現了重慶穿樓而過的輕軌、充滿煙火氣的過江索道纜車、棒棒(挑夫)等;馮鞏導演并主演的《心急吃不了熱豆腐》向觀眾展示了天津大街小巷上一度非常常見的人力三輪車,以及天津人可謂是與生俱來的曲藝細胞;侯孝賢導演的《海上花》在講述故事之余,給觀眾留下印象最深刻的非十里洋場的特殊生活場景莫屬了。
電影,作為一種綜合性的藝術形式,它的創作目的不能僅局限于作品本身,外延同樣重要。如果一部作品上映后,還能夠引發人們對拍攝地及其地方文化,如方言、民俗、建筑、服飾等的興趣,從而帶動相關的文化產業,這應是電影的又一成功之處吧。
三.方言對觀眾認同心理的隱喻功能
觀眾觀看電影不是一個簡單的瀏覽過程,而是處于自覺的互動狀態。大衛·波德維爾曾就觀眾如何與電影的敘事互動做過調查。他發現,觀眾會嘗試將電影的世界進行邏輯組合。路易斯·賈內梯也提出:“大部分時候觀眾看電影前已經有所期待,其對某個時代或某個類型的經驗已經使他期待一組可能的變量。”[1]觀眾對電影的評價過程其實從觀看前就已經開始了。
觀眾選擇觀看電影時,就是對電影評價的第一步。這時他會通過海報、電影名、劇情簡介、演員、導演等進行初步的想象、期待。隨著電影開始,觀眾也開啟自己的判斷過程,他會主動將所看、所聽與自己已知經驗進行比對,判斷電影中的角色、攝影、場面、故事、聲音、表演、剪輯等是否跟自己的已知經驗、想象符合,從而做出判斷。如果影片中輸入的內容跟他的所想不符,甚至大大超過他的預期,但是只要能夠與他的意識形態仍處于同一空間,他就能夠接受,或許還會為之喝彩;反之,如果影片內容讓他感覺完全跟自己了解的世界不符,太過荒謬,他就很難接受。
作為電影語言中的一種形式——方言——也是觀眾衡量作品的要素之一。方言往往是觀眾判定人物角色、故事、情節的一個重要基準點。如電影作品中出現東北話,人們就不由自主地將作品與東北特色文化現象相連,如二人轉、大秧歌等。馮小剛主演的《老炮》用典型的北京話能迅速為觀眾建立起北京文化的即視感。試想電影《舉起手來》中,如果郭大叔也說著一口標準的普通話的話,或許他身上的那股憨厚、樸實的勁兒就會“失真”,面對戰爭中突發情況的張皇失措就會讓觀眾覺得做作。每種方言都是其地區對應的文化符號,脫離了這個符號觀眾就會覺得不真實。
從根本上來說,方言(語言)的選用其實關涉更多的是人們的語言態度。李如龍說:“方言之間沒有優劣之分,但是對于共同語來說,卻有雅俗之別。地方話又稱‘土話,不論是舊時說的‘鄉談、‘俚語,或者至今還在通行的‘平話、‘白話,都是著眼于它的‘俗。”[6]這里所說的“土”、“俗”,恰恰反映了人們對自己方言的態度和心理感受,也是人們放棄方言的一個重要原因。
然而奇妙的是,與此同時,人們又很難抵擋方言的“土”或者“俗”的“誘惑”。如日常交際中,人們使用的詞語恰恰是要關注、追求這種“土味”。看到影片中角色的形象與其所用方言一致時,觀眾又往往為之著迷。如《天下無賊》中的傻根。他一口河北方言與其單純到幾乎透明的人物形象,可以說是瞬間俘獲了觀眾的認同感。如果將劇情中一對竊賊搭檔被一個民工感化的情節單列出來的話,觀眾會覺得這種劇情實在太過單薄,不具可信度。但是,在該影片中,觀眾完全沒有這種感覺,甚至覺得順理成章。這就與觀眾對方言的塑造力量的接受有很大的關系。方言在影片中很容易喚起了觀眾的認同感。
而影片中的方言也常常會在上映后成為人們關注的另一個對象。如《舉起手來》、《秋菊打官司》等作品讓陜北方言的第一人稱“我”(發音如“呃”)“婆姨”一時很風靡;上海方言電影《股瘋》讓觀眾接受了“阿拉”作為第一人稱的說法;《老炮》也為觀眾介紹了一些北京話:茬兒、嘛呢、揍性、局氣、丫等。
結語:方言在電影中的作用自然是不容忽視,但是,在電影中方言也不能濫用,否則同樣會影響觀眾對作品的理解,反而適得其反。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廣播、電影、電視正確使用語言文字的若干規定》(國發〔1986〕64號)中第三條明確規定了:“電影、電視劇(地方戲曲片除外)要使用普通話,不要濫用方言。扮演領袖人物的演員在劇中一般也要講普通話。如因內容需要,要用某些方言,也不能過多。使用方言的電影和電視劇的數量要加以控制。”[7]這里的關鍵詞在于“濫用”“控制”,也就是說,不是禁止使用,而是運用得當、有度。從實際應用來看,這一規定的指導方向是明確的,也是非常科學的。
此外,我國方言種類繁多,特征各異,如何選擇方言,選擇方言中的哪些語音特征、詞匯以及方言在整部作品中的使用比例等都是應該考慮的問題。我國古典名著《紅樓夢》、《西游記》、《水滸傳》、《三國演義》、《儒林外史》等雖以北方話為基礎,但是均具有一定的地方方言色彩。這些地域方言不僅沒有影響讀者對作品的閱讀,反而為其增添了一些別樣的內涵。電影對方言的運用或許可以考慮借鑒。
參考文獻
[1]【美】路易斯·賈內梯.認識電影[M].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7,208;292.
[2]徐盛桓.隱喻喻體的建構——分形論視域下隱喻研究之一[J].外語教學,2020(1),8.
[3]袁家驊等.漢語方言概要[M].語文出版社,2001,20.
[4]李如龍.漢語方言學[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6.
[5]陳章太.關于普通話與方言的幾個問題[J].語文建設,1990(3),28.
[6]周振鶴,游汝杰.方言與中國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
[7]國務院.關于廣播、電影、電視正確使用語言文字的若干規定[Z].國發〔1986〕64號.
基金項目:2018年度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基金項目(編號:2018SJA0701):方言地理學視角下江蘇北部中原官話和江淮官話邊界研究。聯系電話:15850740989
(作者單位:江蘇海事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