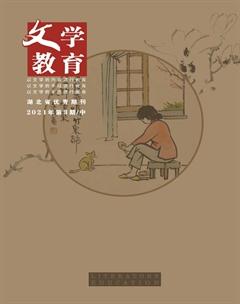當我們談論道德時我們在談論什么
《陪李倫去襄陽看鄒忍之》(以下簡稱《鄒忍之》)是曉蘇今年在《天涯》雜志第6期上推出的一篇小說。小說用第一人稱,寫了“我”陪導師李倫去襄陽看他的學生、我與之曾有過朦朧戀情、但被導師干涉掉了的鄒忍之而不遇的故事。中國古典文學中,有過“尋人不遇”的表達,如唐代詩人賈島《尋隱者不遇》,又如清代詩人蔣蘅有《十五夜尋蘭心不遇獨往貞元閣踏月而歸》。但它們都只是一種簡單的記錄,告訴讀者“我什么時間干了什么事,結果如何”而已,傳達出作者精神的飄逸和閑適。《鄒忍之》卻志存高遠,以輕松的由頭起筆,寫出了一個讓人沉思的故事。
1
馬原曾經說過:“小說最重要的特質是一定要有一個好故事。”曉蘇是個講故事的高手。這篇小說以輕松的事起頭:學校老干處組織的旅游,又是襄陽古隆中這樣的大景點,自然是輕松、放松、人人向往的。同時“我”借著介紹導師,抖出一件件往事,一幅幅生活的畫面便在讀者眼前出現了:鄒忍之“無可奈何”回到原來的單位,師母“見縫插針”地給學生們傳道解惑,李倫“暗暗調查”那個男孩的家庭背景,我只好“背著”李倫到省城找工作,“我剛把雙臂張開,正要和鄒忍之迎面相擁時,教研室的門哐啷一聲打開了”……小說人物逐一登場,各種性格漸漸顯露,之間潛藏的矛盾浮上水面,無不告訴讀者:大戲即將開始。
小說從第三節開始“找人”,作者精心設置的玄念發揮作用,強烈吸引著讀者:鄒忍之一直沒露面。這是為什么?讀者的想象力在此時被調動起來,共同參與到對小說結果的猜測和編織中。這就好比一大陣蜜蜂,伴隨著蜂王,嗡嗡地、浩浩蕩蕩地出行——要一同去看鄒忍之。
曉蘇家鄉有句俗話:生娃的不急抱腰的急。作者在這里就是那個“生娃的”。他把握著文本的節奏,不疾不徐,安排“三看而不得”。煞費苦心請人陪同、風塵仆仆從省城趕到、特意推卻游隆中,滿以為會在大學行政樓里看到鄒忍之,卻被告知鄒忍之早已調到了后勤處,“一看”失敗。再到后勤處,大筆頓一頓,安排了一個熱情好客的科長出來,愣把“我”和導師當成聯系維修業務的,浪費好許筆墨,只讓“一陣抱腰的”急得不行時,才慢慢告訴客人,鄒忍之已經調走了。“二看”又不得,小說的第三節結束。
還找嗎?當然!再往地處城郊張灣的烹飪學院而去,故伎重演。該校招生辦的牟主任,在兜售了一番招生業務后,才說鄒忍之跑招生去了,幫著客人打通了鄒忍之的電話,對方卻拒絕接聽,“三看”又不得。由此我想到馬原說的:“聽故事的人對于你的故事前情,對你故事的結尾有某種期許,對前邊發生的起伏跌宕有某種期待,讓你能夠在你自覺自愿的前提下繼續,讓故事繼續,讓講故事的行為繼續,讓你聽故事的狀態繼續,這個才能讓一個故事真正稱之為好故事”。
行文至此,故事已經講了一大半兒。聰明的讀者已經明白,作者的“幾看”而不得,并非是要寫一個豐富的教育市場,而是要通過環境來展現烘托人。王國維先生有言:“一切境語,皆是情語。”人是環境的產物,只有透過一次比一次糟糕的環境的,我們才能感受到鄒忍之的命運的滑落。滑落的原因,魯科長已告訴讀者:都是離婚惹的禍!“善惡終有報”,鄒忍之后來混成這樣大概無顏見老師吧。
改變鄒忍之命運的是“離婚事件”。妻子余小滿被他“拋棄”后過得怎么樣,李倫非要帶著“我”去鄒忍之的老家去看看。可就是這一看,一個驚人的謎底揭開,不僅李倫“如聞驚雷,頓覺天旋地轉”,連讀者都驚掉了下巴:余小滿親口說出是她背叛了鄒忍之,并提出離婚。為什么這樣做,是因為有一個更適合她的男人——芒種。
2
曉蘇的追求是寫出既有意思又有意義的小說。“有意思”很好理解:好聽的故事、豐滿的人物形象。這篇小說,鄒忍之雖然沒有出面,卻是形象最豐滿的一個。通過他人之口,讀者知道他是位教師,出生農村,有一個農民妻子,后來去省城讀“思想品德”研究生時,和女同學產生感情,被導師干涉掉,畢業時導師不愿幫他留在大都市,只好回母校當了一名高校的思想政治課的老師,卻因為與妻子離婚,成了人們心目中的“陳世美”,被道德審判,被生活拋棄,從高校老師變成修理工,再到技校打雜。
李倫的形象也極其豐滿。在世人眼中,他是個好老師,自律,也嚴格要求學生,始終做品德高尚的人。學校組織旅游,他待在酒店里,跟服務員談心,要人家“愛崗敬業,不斷進步”。到襄陽講課,拒絕對方的豪華宴席,“作為一個研究思想品德的學者,我怎么能讓你們用公款請我大吃大喝呢?”與鄒忍之一起吃襄陽牛肉面,“搶著付錢。”“助人為樂,每當有人求助,總是慷慨解囊,也不問青紅皂白,還經常打腫臉充胖子。”女兒和同事情投意合,他“暗暗調查那個男孩的家庭背景,打聽到他父母都有過兩段婚史。便斷言:上梁不正下梁歪。”逼兩人分手。師母死了,為拒絕上門示愛的女人,“別出心裁地取出師母的遺像,抱在懷里,一邊擦一邊說,哎喲,才兩天沒管,頭上都落灰了。”……這些描寫,把李倫刻畫得栩栩如生。
另外幾個人雖著墨不多,并不影響她們有著各自不同的鮮明性格。“我”對老師又怨又關心;小滿勤勞又勇敢;師母尊夫順夫相夫,擁有被社會普遍認可的、中國傳統女性的“美德”。
曉蘇心中的“有意義”包括三個層面,即:現實意義、歷史意義、哲學意義。這篇小說中,闊別多年師生、同學相見是件令人高興的事,作者借此精心設計出來一個沉重的話題:婚姻是否就該從一而終?再婚是否就是道德有私?我們在教授道德時,又該教授些什么?
李倫是高校老師,在弱勢的學生和女兒面前,他天然擁有裁決的權力。他喝令“我”與鄒忍之分手,導致的結果是:一個“匆匆嫁了”。言外之意,好像沒有感受到愛情的幸福;一個連體面的工作都沒有,也根本不再認老師。他裁決女兒的婚姻,女兒憤然出走,親情斷裂。他極力維護傳統的婚姻,堅決不允許鄒忍之和余小滿離婚,否則就是“陳世美”,卻不知是余小滿拋棄了鄒忍之。這是一張熟悉的面孔,可以說,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到處都可以看到“李倫”“張倫”“王倫”……他們舉著道德的旗幟,振振有詞,殺伐決斷,卻不知葬送了多少人的幸福。
中國在漫長的帝制時代,形成了一套固有的婚姻觀念,其中又以犧牲女性幸福為核心,什么“好女不嫁二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從一而終”等等。這些曾被寫成法律,并在某些朝代以載史冊,豎牌坊等形式高調宣揚。時代進入21世紀,雖然這其中的絕大部分已經被社會拋棄,就連我國的離婚法也以感情破裂為離婚的充分理由,但在某些“道德家”的心中眼里,那些論調依然有生命力,似乎傳統的東西都是寶貝。李倫嘴上就掛著一句“夫妻倆只要志同道合,沒有共同語言可以共同建立嘛。比如你們的師母,她實際上只是一個工人,但我沒有拋棄她,我們不是也很幸福嗎?”他和一些人的判斷:離婚=道德敗壞。這個公式不禁讓人想起20世紀六七十年代,離婚就跟登天一樣難。寫到這里,作品顯然已經打通了歷史。
著名文藝理論家孫紹振說過:“歷史的真,是科學價值;道德的善,是倫理價值;藝術的美,是情感價值。三者是錯位的。”愛情自然是感性的,否則何來“問世間情為何物,只教人生死相許”?我與鄒忍之間,小滿與芒種間,愛慕李倫的女人與李倫間,李楚與男友間,無不如此。李倫試圖用書本上的教條,來解決復雜的人性帶來的相關問題,只能是一敗涂地。正如社會學家李銀河所說:“情是人心的一種感覺,如果它到了需要道德來約束的程度,它還存在嗎?”“后來,李倫就一直沒再說話,從襄陽到武漢,沿途始終一聲不吭,像一個啞巴。”一輩子口吐蓮花、布道后輩的人,經過此事,再無力發聲……這不是哲學層面的意義又是什么?
3
曉蘇給小說人物取名往往隱含深意,耐人尋味。此篇也不例外。李倫即“倫理”,寓意著某些傳統道德;鄒忍之即凡事“忍之”。正是這個忍,讓他一生活成悲劇。鄒忍之與“我”本可以成為幸福的一對,卻因為李倫的主觀臆斷橫加干涉,以及鄒忍之的一味的怕與忍而斷送了幸福。小滿和芒種的名字取自民間二十四節氣。它們來自田野,故而生機勃勃,自由自在。牛肉面作為一條引線,暗喻著人間煙火,是人人都要過的最真實的生活,它的香味那么誘人,不可阻擋,表明人對幸福的渴望如同對美味的渴求,是不可遏制的本能。
在廣闊的文學天地之中,永遠存在著有待塑造的人物。鄒忍之是個悲劇人物,他的幸福是被代表著道德完人的老師,以一些似是而非的道德觀念干涉掉了的。這是一個嶄新的人物形象,在此之前,似乎還沒有出現過。他非常能忍,研三那年,就已離婚,但忍著,并未向外說出妻子出軌又拋棄他的真相,以致于外界誤會;在被生活一次次放逐時,依然“忍之”,一忍再忍,從不為自己辯護,頗有傳統道德欣賞的“儒者之風”。
中國傳統文化對“忍”字頗為推崇。“小不忍則亂大謀”、“艱難困苦,玉汝于成”、“德莫若讓”、“動心忍性”、“退一步海闊天空”等等,無不表達著對“忍”的贊美和訴求。能“忍”,便是君子之風,便能成大事。但細細品味,這是一種自上而下的規則和倡導,在民間,卻有“忍氣吞聲”“含垢忍恥”與之對應。鄒忍之的故事,是活生生的事例。這個沒有出來說一句話的人,像是在用自己的人生,反證著道德干涉和一些古訓的荒唐。這個人,既卑微又高大,既窩囊又勇敢的人,順應生活之變,擔荷所有困苦,在這個意義上,他類似于美國作家辛格筆下的“傻瓜”吉姆佩爾。
著名文學評論家洪治綱說,“曉蘇善于讓人物置身于隱秘的倫理內部,盤旋于人性、情感與倫理之間,東奔西突,左扯右拽,由此凸現人物潛在的心靈氣質,叩問凡俗中的人性光澤。”對于《鄒忍之》這篇,我想大膽地加上一句:“揭開那些虛偽的面紗,直視道德的真相。”
艾子,湖北省作家協會會員,襄陽市作家協會副主席。2008年開始文學創作,曾在《長江文藝》《四川文學》《鴨綠江》《芳草》《當代小說》《西部散文家》《長江叢刊》《金山》《漢水》《南方周末》等刊發表過小說、散文、報告文學多篇,曾獲“《長江文藝》完美散文獎”、“中國金融文學優秀散文獎、小說三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