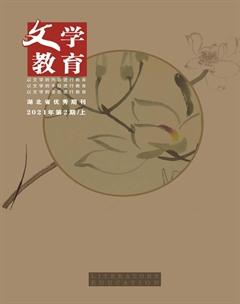汀洲萋萋麋鹿鳴
一
“荊有云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鱉黿鼉為天下富”。這是兩千多年前《墨子·公輸》對古代楚國云夢澤地區麋鹿以及黿鼉等生物生存狀態的描述,可以想象古時長江流域洲灘縱橫、水草豐茂,人與動物和諧共處的自然風景。經過歷史車輪的碾壓,許多原生態景象消失不見,但楚地仍有這樣一處地兒,“汀洲萋萋麋鹿鳴,蒹葭蒼蒼白鷺飛”,那就是石首,一個你來了就想駐足筑夢的地方。
時值初冬,我再次來到石首桃花山。這里依山傍水,綠樹環繞。亭臺樓榭在水一方,怪石嶙峋點綴其間。白墻灰瓦的徽派建筑群一棟棟掩映在青松翠竹之間,與湖光水色交相輝映,別有一番韻味。彼時細雨若絲,天氣微寒,我們沿山路逶迤而上,一抬頭,就看見山頂巨大的白色風車,一排排,慢慢旋轉著,仿佛直升機的螺旋槳,似乎一不小心就要起飛直插云霄,成為山頂一道獨特的風景。聽說,風車是利用風來發電,聰明的石首人將大自然的資源開發運用,通過科學技術將風能轉化為電能,這是現代文明的進步,為石首點贊!
我對石首并不陌生。2017年3月,我和幾位老同學專程從荊州開車到石首欣賞桃花山的美景,當時天公不作美,一過江就飄起了菲菲細雨,我們的車順著導航七彎八拐,竟然迷路了,下車問路邊一位面相憨厚的老農,老農停下手里的活計,說一口地道的石首方言,很熱情地給我們指路,讓人感覺民風淳樸。
到了桃花山腳下,我們被山上一片片粉色的花海迷住了。桃花山北枕長江,東望洞庭,據說由280座大小山峰組成,我們到的只是其中的一座山峰。順著濕滑的水泥小道往上爬 ,但見山巒蜿蜒起伏,山坳里的桃樹成行成片成林。遠遠望去,一樹樹星星點點的粉,交織成一片粉色的海洋。繼續往上走,路邊的桃枝冷不丁地撞入眼簾,只見枝丫上桃花朵朵,或低眉含羞,或昂首吐蕊,那粉嫩粉嫩的花瓣上凝聚著一顆顆晶瑩欲滴的雨珠兒,仿佛美人垂淚,我見猶憐。彼時細雨迷蒙,天氣微寒,空氣里沁出一絲絲清冷的幽香,竟有“桃花山里看桃花,山亦朦朧雨亦奇”的浪漫感覺!
二
除了桃花山,石首最令人神往的當屬天鵝洲。遺憾的是因為天氣原因,探訪天鵝洲未能成行,那撒蹄狂奔的麋鹿自然也未能躍入眼簾。
記得2017年8月,我曾隨友人來石首拍攝一部宣傳片,就是在天鵝洲取景。從大門進去往里走,就是一片茂密的蘆葦蕩,那時蘆葦長得又高又密,鋪天蓋地,比影片《紅高粱》里的高粱地還要令人震撼。別看蘆葦長得壯實,其實它還有個詩意的名字,即蒹葭。蒹,是指沒長穗的荻;葭,是指初生的蘆葦。古代文獻資料如此記載:蒹葭者,蘆葦也,飄零之物,隨風而蕩,卻止于其根,若飄若止,若有若無。思緒無限,恍惚飄搖,而牽掛于根。根者,情也。相思莫不如是。露之為物,瞬息消亡。瞧,多么擬人的解釋!古時文人墨客似乎格外青睞蒹葭,常以之吟詩作賦,最能勾起相思情懷的莫如《詩經》里的“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而彼時,從《詩經》里脫穎而出的蒹葭,經過千年的生生不息,于時光無涯的荒野里,長成一道天然的屏障,將紛紛擾擾的紅塵俗世隔絕在外曠野之外,蒹葭深處,是泥沼,是灘涂,是一方從未被污染的原生態凈土。
三
穿過厚而密的蘆葦叢,便是一片視野開闊的青草地,草地盡頭即延綿的長江故道,如一條蒼茫的玉帶,在夏日的陽光下閃出粼粼波光。“看,麋鹿!”友人驚喜地指向遠處的洲灘,于是大家齊齊望過去,只見洲灘里有十幾頭麋鹿,有的站立,有的俯臥,有的低頭冥思苦想,有的昂首東張西望。或許是天太熱,它們很多都伏在水里,似乎在泡澡,只露出頭和樹杈般的角,雖然因為相距太遠看不清它們的面目和神態,但能感受到它們的愜意和自在!
麋鹿,因其頭臉像馬、角像鹿、蹄像牛、尾像驢,因此得名 “四不像”,是我國特有的世界珍稀物種。兩千多年前,就有麋鹿生活在古代楚國云夢澤地區的記載。過去,由于棲息地被破壞,人為捕殺,還有戰亂、洪水等原因,麋鹿曾一度消失。1991年,國家在石首天鵝洲建立了濕地自然保護區,先后從北京麋鹿苑引進麋鹿自然放養,致力恢復野生麋鹿種群。因為天鵝洲氣候溫和,土地肥沃,水草豐茂,成了麋鹿生命的搖籃。經過20多年的自然繁衍,麋鹿數量倍增。如今,這里已經擁有了世界上最大的麋鹿自然野化種群。
麋鹿其實是很靈性的動物,作為生命力旺盛的的標志,它不僅是先人狩獵的對象,也是宗教儀式中的重要祭物。據考證,古代楚國墓葬里出土的鎮墓獸就是麋鹿。從春秋戰國時期至清朝,古人對麋鹿的記載不絕于書。傳說的姜子牙座騎、“指鹿為馬”、“逐鹿中原”等典故都與麋鹿有關。《孟子》中記述,“孟子見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這說明至少在周朝,皇家的園囿中已有了馴養的麋鹿;蘇東坡有詩曰“我本麋鹿性,諒非伏轅姿”;白居易有詩云“龍蛇隱大澤,麋鹿游豐草。棲鳳安于梧,潛魚樂于藻”等等,可見麋鹿歷史淵源悠久。如今,面對人類,麋鹿是自由的;擁有麋鹿,自然是和諧的。追求自由、構建和諧,才是數千年麋鹿文化的精髓。
正想得入迷,一只蜻蜓從我眼前掠過,它輕輕煽動著比蟬翼還透明的翅膀,忽高忽低地,在我擎著的油紙傘上方盤旋,似乎在與傘面繪著的菡萏嬉戲。同行的攝像師開啟無人機,準備航拍這獨特的風景,卻不小心驚動了蒹葭深處棲息的白鷺。于是乎,又一副壯觀的景象出現:一大片白鷺振翅而起,撲啦啦飛向天際,一會兒排成一字,一會兒排成人字,漸漸成為天邊的小黑點。讓人不由想到王國維的詩句:“白鳥悠悠自去,汀洲外、無限蒹葭。”此時藍天白云,水天合一,人與動物和諧相處,好一副安寧、祥和、生動的原生態畫面!
我想靠近一些,細細觀賞麋鹿的風姿,卻躑躅著不敢貿然向前,一是怕不小心陷入沼澤地,二是怕驚擾了麋鹿們的自由和寧靜。在大自然面前,我始終懷著一顆敬畏之心。我期待,世界多一些像天鵝洲的地方,讓自然更好地回歸自然,讓人類多些悲憫,少些殺戮,成為動物的保護者而非掠殺者;同時也多些胸懷,少些狹隘,成為大自然的守護者而非破壞者。
四
任何一座城市,都不乏悠久的歷史文化底蘊,何況石首這樣一個與長江流域緊密相連的地方,更是有著驚人的探索與發現。
據考證,在東升鎮焦山河鄉走馬嶺村,有座總面積達20萬平方米,屬于屈家嶺文化晚期的古城址,雖歷經5000年風雨滄桑,但走馬嶺古城依然保存其原貌。相傳三國時期關羽曾在此策馬揚鞭,走馬嶺因此而得名。
在石首市調關鎮,有關于俞伯牙鼓琴巧遇鐘子期的調弦亭的傳說。相傳春秋戰國時期,楚國大夫俞伯牙乘舟自楚都(郢城)東下,因避風雨在此地臨時停泊。晚上閑來無事,他不由撫琴而歌,開始一曲意在高山之律,樵夫鐘子期說:“善哉!峨峨兮若泰山(此調仿若雄偉而莊重的高山)”,接著他又彈了一曲意在流水之律,子期則說:“善哉!洋洋兮若江河!(如綿延不斷的長江流水般源遠流長)”,伯牙于是大喜過望,遂與子期結為莫逆之交。民間傳說這里就是俞伯牙撫琴調弦遇子期之地,遂命名為“調弦口”。鐘子期死后,俞伯牙在他墳前為其彈奏一曲《高山流水》,琴音嗚咽,極盡哀思。一曲作罷,俞伯牙斷弦摔琴,發誓終生不復鼓琴。這斷裂的琴弦就成了調弦河。早在宋朝年間,人們就在這里修建了“調弦亭”",不過后來由于年久失修而毀于民國。
在桃花山鎮的鹿角頭,有越國上大夫的范蠡墓,范蠡廟和其隱居飼馬的飲馬池;在城北,有劉備和孫夫人新婚燕爾由吳返荊而留下的繡林亭、錦幘亭、望夫臺、照影橋、劉郎浦;在高陵崗,有后梁孝宣三王墓、孝宣公主墓……等等。
石首歷代名人輩出、聞名遐邇,比如明代有“三閣老(宰輔)”(張壁、袁宗皋、楊溥)、“兩尚書”(王之誥先后任兵部尚書、刑部尚書)、“一太史”(曾可前)。其他歷史名人如大禹、孔子、岳飛等也都在石首留下過許多美好的傳說,著名詩人元稹、杜甫、陸游、黃庭堅等都在石首留下流芳百世的詩文……石首的名勝古跡比比皆是,名人故事更是世代相傳。
其實,石首醉人的不僅是原生態風光和歷史人文風情,還有令人味蕾綻放的特產美食。比如桃花山土雞蛋、天鵝洲荻筍、香辣木瓜絲、糯米團子等,尤其是筆架魚肚堪稱一絕,其形如筆架,其色似白玉,其質嫩如脂。相傳早在明朝年間,筆架魚肚就被列為朝廷貢品,極其珍貴,這次有幸在桃花山品嘗了這道美味。只見雪白的魚肚飄在金色的雞湯里,香味四溢,讓人垂涎欲滴!輕輕舀一勺,魚肚就著濃湯,“吱溜”一聲入口,頓覺香脆爽滑,入口即化,唇齒留香。那滋味,怎一個美字了得!還有天鵝洲荻筍,即蒹葭之荻葦的嫩莖,雪白脆嫩,久煮不爛,食之口感細膩,風味獨特。舌尖得到滿足,讓人不得不感嘆石首物華天寶,人杰地靈,大自然饋贈給它豐富的自然寶庫、悠久的歷史文化底蘊與獨特的珍饈美味!
美麗的石首讓人流連忘返。離開的時候,依然微雨若絲,被迷蒙雨霧浸染的桃花山,草木葳蕤,清新若夢,如一副動人的水墨畫。那山頂的風車,依舊輕輕旋轉著,一如初見時的祥和、寧靜。
(作者介紹:伍美菱,女,湖北荊州人,湖北省作家協會會員,在國內報刊發表小說、散文約300萬字,代表作長篇小說《荊州女人》《你的一生,我只借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