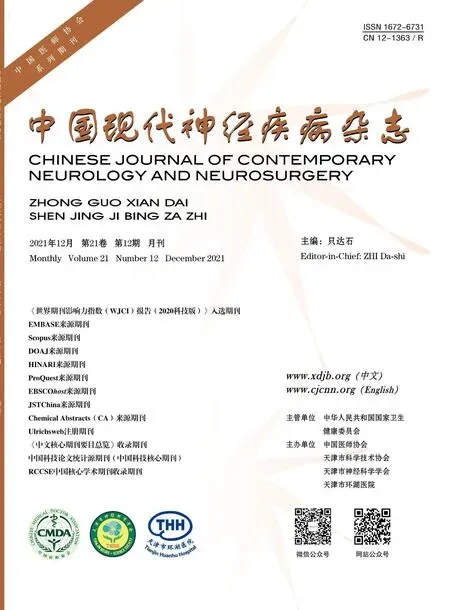非酮癥高血糖伴癲發作一例
高雨田 劉文娟 王克健 黃作義
患者 女性,58歲。因抽搐發作7年,加重3月余,于2021年8月20日入院。患者7年前乘坐電動自行車時突發肢體抽搐,自車上摔下,無意識障礙和嚴重外傷,急診至外院診斷為癲,予奧卡西平0.30 g/次、2次/d和左乙拉西坦0.50 g/次、2次/d口服抗癲治療,發作控制欠佳,每月發作3~4次。3個月前癲發作頻繁,表現為身體后傾,右上肢不自主上舉,左下肢屈曲,口角向左側偏斜,持續3~5秒后自行緩解,每日發作20余次,發作過程中無意識障礙和大小便失禁,于2021年8月13日至我院門診就診,增加藥物劑量為奧卡西平0.60 g/次、2次/d和左乙拉西坦1 g/次、2次/d,癲發作未見明顯改善,發作頻繁且影響日常生活,門診收入院。患者既往有2型糖尿病病史8年,隨餐服用阿卡波糖100 mg/次、3次/d,睡前皮下注射地特胰島素8 U,血糖控制欠佳,其母及其妹罹患2型糖尿病,否認癲家族史,余既往史、個人史及家族史無特殊。入院后體格檢查:體溫36.5℃,心率68次/min,呼吸18次/min,血壓124/74 mm Hg(1 mm Hg=0.133 k Pa),心、肺、腹部查體未見明顯異常;神經系統查體神志清楚,語言流利,腦神經檢查未見異常,四肢肌力、肌張力正常,共濟運動和感覺系統未見明顯異常,生理反射對稱引出,病理反射未引出,腦膜刺激征陰性。實驗室檢查:入院時隨機血糖9.70 mmol/L、入院第2天院第4天早餐前空腹血糖10.81 mmol/L,糖化血紅蛋白(HbA1c)7.20%(4%~6%),尿糖陽性、尿酮體可疑陽性;入院第4天腰椎穿刺腦脊液檢查外觀清亮、透明,壓力120 mm H2O(1 mm H2O=9.81×10-3k Pa,80~180 mm H2O),葡萄糖為4.78 mmol/L(2.50~4.40 mmol/L);血清和腦脊液抗自身免疫性腦炎抗體譜抗N-甲基-D-天冬氨酸受體(NMDAR)抗體、抗接觸蛋白相關蛋白-2受體(CASPR2R)抗體、抗α-氨基-3-羥基-5-甲基-4-異唑丙酸1和2受體(AMPA1R和AMPA2R)抗體、抗富亮氨酸膠質瘤失活基因1受體(LGI1R)抗體、抗γ-氨基丁酸B型受體(GABABR)抗體、抗谷氨酸脫羧酶65受體(GAD65R)抗體均呈陰性,腦脊液抗神經元抗體抗水通道蛋白4(AQP4)-IgG抗體呈陰性。入院即行長程視頻腦電圖(LT-VEEG)監測,記錄到3天共50余次樣發作,表現為右上肢向上抬起,左上肢屈曲,頭部向左側偏轉,痛苦樣表情,無意識障礙;同期腦早餐前空腹血糖為5.66 mmol/L(<6.10 mmol/L)、入電圖顯示發作前1秒左側中央區、頂區、中央中線最先出現棘波節律(圖1),以及發作開始后大量肌電和動作偽跡,持續約20秒。入院第5天(8月24日)頭部MRI檢查顯示,右側基底節區腔隙性梗死灶(圖2)。入院第7天(8月26日)頭部18F-脫氧葡萄糖(18F-FDG)PET顯示,右側頂葉可疑葡萄糖代謝略有減低,右側基底節區軟化灶(圖3)。入院后連續監測3天血糖(7次/d),空腹血糖8.10~11.10 mmol/L、餐后血糖11.80~13.90 mmol/L(<7.80 mmol/L),經內分泌科會診(入院第4天)后調整治療方案,在阿卡波糖100 mg/次、3次/d隨餐口服基礎上,增加格列齊特60 mg/早口服,血糖仍控制欠佳,同時予奧卡西平0.60 g/次、2次/d和左乙拉西坦1 g/次、2次/d,癲發作仍頻繁,每日發作20余次;再次請內分泌科會診(入院后第7天),將治療方案調整為胰島素皮下注射,三餐前6 U、睡前8 U,繼續監測4天血糖(7次/d),空腹血糖為4.90~7.30 mmol/L、餐后血糖8.20~12.20 mmol/L,抗癲治療方案不變,癲發作頻率明顯減少(4次/d),持續時間縮短(1~2 s/次),癥狀明顯減輕,右側肢體無肌強直樣伸直動作。患者共住院15天,出院后遵醫囑規律皮下注射胰島素(三餐前6 U、睡前8 U),同時監測血糖,并根據血糖水平門診復診以調整胰島素劑量;繼續服用奧卡西平0.60 g/次、2次/d和左乙拉西坦1 g/次、2次/d,癲發作好轉之后,門診復診以逐步減停抗癲藥物。出院后2個月隨訪時,患者癲 發作頻率明顯減少(約2次/月),仍采取上述抗癲治療方案。目前仍在隨訪中。

圖1 腦電圖(2021年8月21日)顯示,發作期起始為左側中央區棘波節律Figure 1 EEG showed the onset of a seizure with a spike rhythm in the left central region.
討 論
1965年,Maccario等[5]首次報告高血糖狀態下并發部分性發作,同時具有血糖升高、酮體陰性、意識保留和部分性發作這4個特點。目前,非酮癥高血糖伴癲發作的發生機制尚不明確,單一因素不足以明確解釋這種復雜疾病,分析其原因可能為:(1)高血糖狀態使神經元產生滲透壓梯度,使膜電位去極化[6],蓄積電位引起癲發作。(2)高血糖引起顱內動脈硬化和功能損害,形成的局部缺血性病灶使腦血流量減少,引起腦組織局部代謝狀態改變,導致局灶性發作[7]。本文患者18F-FDG PET顯像結果亦證實這一機制。(3)高血糖導致γ-氨基丁酸(GABA)代謝升高,增加大腦能量消耗[8],導致癲發作閾值降低。而在糖尿病酮癥患者中,細胞內酸中毒使GABA含量增加,使細胞膜電位處于穩定靜息電位水平,防止癲發作。從這一角度可以考慮為酮癥的抗驚厥作用。(4)免疫相關異常,Peltola等[9]發 現,難 治 性 癲患者抗谷氨酸脫羧酶抗體(GADA)呈陽性,與1型糖尿病患者效價相似,說明二者存在某種聯系,提示免疫功能異常很可能參與非酮癥高血糖伴癲發作的發生。(5)近年研究顯示,血-腦屏障破壞也是非酮癥高血糖伴癲發作的重要機制[10],且與其他高血糖相關神經系統癥狀相關,如肌張力障礙、認知功能障礙等[11-12]。(6)非酮癥高血糖伴部分性發作可能是由于長期高血糖引起局部血管異常、缺血,或不同部位神經細胞對高血糖、高滲透壓的敏感性和耐受性不同[13]。

圖2 頭部橫斷面FLAIR成像(2021年8月24日)顯示,右側基底節區腔隙性梗死灶 2a,2b基底節區層面 2c放射冠層面 圖3 18F-FDG PET顯示,右側頂葉葡萄糖代謝略減低(右側綠色區域所示)Figure 2 Brain axial FLAIR showed the lacunar focus in the right basal ganglia region Basal ganglia level(Panel 2a,2b).Radial coronal level(Panel 2c). Figur e 3 18F-FDG PET showed the metabolism of the right parietal lobe decreased slightly(green areas in the right indicate).
本例患者根據其發病年齡、病程、發作特點和頻率,結合既往史和相關輔助檢查等明確診斷為非酮癥高血糖伴癲發作。該例患者中年發病,表現為單純部分性發作且發作頻繁,入院后LT-VEEG監測到反復刻板發作,發作期腦電起始節律支持局灶性發作,由于發作迅速且短暫樣放電快速傳導至對側引起腦電圖改變,完善影像學檢查無結構性病變和腦血管病相關病灶,18F-FDG PET顯示右側頂葉葡萄糖代謝略減低,考慮為頻繁發作致左側代謝略高所致,實驗室腦脊液檢查未提示中樞神經系統感染、免疫性腦炎和神經變性病相關線索,結合首次發作時間和既往史,考慮為血糖相關癲發作。入院后血糖控制過程也體現出癲發作與血糖的相關性。
治療方面,基本治療原則主要為盡早采取有效方法控制血糖[17]和補液等,同時密切監測血糖,糾正水電解質紊亂[18-19]。然而,抗癲藥物對此類發作療效較差,即使應用足量仍無法控制發作,且有些藥物如苯妥英鈉、地西泮等,通過誘導胰島素抵抗和影響離子通道等機制還可加重癲癥狀,故選擇藥物時應考慮此種情況。此外,還應對確診為糖尿病的患者加強健康宣教,指導其堅持服用降糖藥、清淡飲食、保持積極心態,避免因血糖波動過大導致癲發作[20],提高治療效果。血糖控制后無需長期抗癲治療。
綜上所述,本文報告1例非酮癥高血糖致單純部分性發作患者,嚴重影響日常生活、降低生活質量,應早期識別這一臨床綜合征,及時予以有效降糖治療,避免不必要的病因檢查,對患者預后至關重要。
利益沖突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