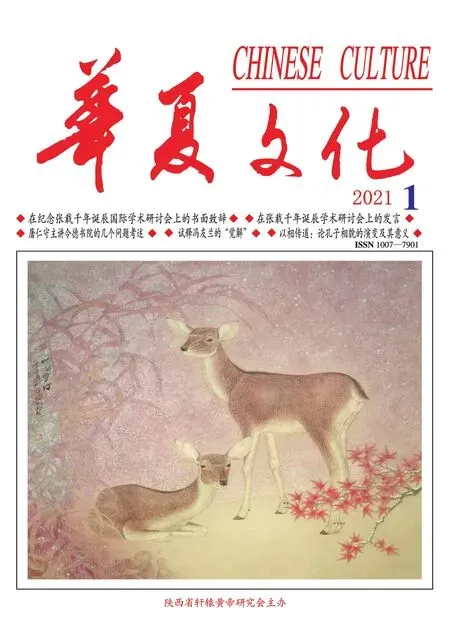唐甄的德育方法論
□柴永昌

唐甄作為明清之際的重要思想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學界的重視。現存《潛書》97篇是研究唐甄思想的主要材料。在《潛書》中,直接或間接談到道德修養的篇章頗多,并涉及德育的諸多方面。唐甄《潛書·誨子》(按:以下引《潛書》原文僅出篇名。另,本文所引《潛書》原文主要依據黃敦兵《潛書校釋(附詩文)》長沙:岳麓書社,2010年版)認為教子應當“修身為上”,強調立“德”的重要性。他還認為“學必得師保”(《得師》),“所貴乎師友者,師道迷而友振惰也”(《無助》),強調師友在人道德品行養成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唐甄認為教師若要充分發揮其德育功能,就要注意方式方法。
第一,要“善講”。“講”是教師道德教育的重要方式。唐甄認為教師“善講”會對受教者的道德成長有很大幫助。《講學》說:“師友善講,則學有成。”何謂“善講”?“講”一般要依據一定的教材或文本,唐甄認為“善講”并不是“辨文析義”,僅把教材或文本的語言文字意思說清楚,這種“講”對幼兒有幫助,但對成人為學幫助不大。如果整天拿著五經四書,以及諸儒語錄講給學生聽,這樣的“講”頂多是教了些思想道德的知識,并不一定能達到德育目的。教師的“講”和教師的德育,說到底是要“淑其身,明其心”(《講學》),即善于教人行為端正、心地明徹,啟發人的自覺。唐甄認為,道德教育并不是教人學知識,《講學》說:“善講者如掘井得水,因其自有而取之,非異水也。……今則求之于已,乃我之自有焉,則善講者之功也。”可見,“善講”不是照本宣科,而是能夠激發受教者內在的道德意識,讓受教者知道“道”在什么地方,并能鼓勵受教者克服求“道”的畏難情緒,讓受學者自覺發明本有之良知。
第二,要“親和”。唐甄對“升五之座”,“環而聽之者百千人”的教學模式提出批評,認為教師講學貴“親”。《講學》說:“教者貴親,親則易知;承教者亦貴親,親則易化。……一室之中不過數人,朝而見,夕而見,侍坐于先生,侍食于先生,非若大眾之不相接也,可以教矣。”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要親近,教師的“教”才有“溫度”,才能感染人。從唐甄的論述來看,所謂“親”首先是空間距離比較近。這在今天仍有現實意義,即教師講學時,人數不能太多,人數過多,上下懸隔,“親”不起來;其次,所謂“親”是經常溝通交流,有共同生活、學習的時間,發揮教師耳濡目染、言傳身教的作用。
第三,要同異結合。唐甄認為在教育過程中要注意普遍性的“教”和有針對性的“教”相結合。《講學》說:“又患教之同也,又患教之易也。一日言智,共此求智之方;一日言勇,共此求勇之方;一日言仁,共此求仁之方,是同也。”根據教學安排,有時候主要是“求智”,有時候主要是“言勇”,有時候主要是“求仁”,對受教者的普遍性教學是必要的;但是,人有千差萬別,性剛性柔不一樣,優點缺點也不一樣,這就要求教師在“同教”的基礎上有所變化,注意受教者的差異,能夠對癥下藥、因材施教。
第四,要以身作則。強調教師德育的表率作用是儒家德育思想的一個重要傳統,現代德育學也認為“榜樣示范法”是道德教學的重要方法之一,唐甄對此亦頗為重視。《太子》說:“凡教太子,有不教之教,天子身自為制,是謂不教之教。”唐甄認為,天子教育太子要發揮以身作則的示范作用。天子只有勇于損其宮室、妃妾、閹奴,做到“去奢守樸”(《尚治》),才能達到對太子“不教之教”的德育目的。
第五,要用好勢位。唐甄認為教師之“教”能否達到預期效果,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勢位”。《太子》說:“自昔有言:教太子必擇賢師傅。其在于今,則為罔上之言。公卿之家,千金之子,且輕師傅,何況太子?使師傅教太子,如使弱羊牽大車。”也就是說,太子有錢有勢,必定輕師傅,師傅要想教好“太子”猶如“使弱羊牽大車”,是不會有好結果的。因此,唐甄主張要把尊貴的太子教育好,只能由“天子自教之”。《太子》說:“太子故尊,必處于卑;……故驕,必納于約。”只有天子的強勢介入,才有可能鎮住“尊”而“驕”的太子,使之被納于“卑”而“約”。
第六,要嚴格規矩。教師在德育過程中要嚴格教學規矩。在《太子》篇,唐甄認為教太子必須使之遵循嚴格的禮義規矩,并且說:“凡教太子,有過必撻。”對太子不遵循禮儀、未完成教學任務、違背教育目的等言行,都要嚴厲體罰,不能手軟。通過體罰使受教者嚴格遵守規矩的做法,在今天已難以被人們接受,但他強調嚴格規矩在德育中的積極作用,仍值得我們借鑒。
第七,要注意實踐教學。唐甄重視實踐教學是基于其“身世一氣”的理論主張。《良功》說:“身之于世,猶龍蛇之有首尾也,猶草樹之有本枝也。”《性功》說:“身世一氣,如生成之絲;身世一治,如織成之帶;不分彼此,豈可斷續!”“身”是自身,“世”是世運,自身與社會(世運)融為一體,不可二分。由此觀點出發,唐甄認為“修身治天下為一帶,取修身,割治天下,不成治天下,亦不成修身。”(《性功》)即“修身”不能脫離社會實踐(“治天下”),如果脫離社會實踐就無所謂“修身”,“舍治世而求盡性”(《性功》)是達不到目的的。因此,在道德教育過程中,要注意將受教者引向社會實踐。《太子》說:“凡教太子,春使視耕,夏使視耘,秋使視獲,冬使視藏。”還說:“凡教太子,過市,則見販鬻之勞;在涂,則見負擔之勞;行道,則見征役之勞;止舍,則見羇旅之勞。”在唐甄看來,教太子不能僅待在深宮講些大道理,專講些書本知識,而應讓他深入生產實踐,親身體會農工商賈的實際生活,知道自身衣食住行的來源,這樣才可能形成正確的價值觀。
第八,要創造好的環境。德育環境對人的發展起著引導作用。唐甄在《太子》篇提出教太子要“先去女蠱”、“必除閹蠱”,即可見其重視環境在德育中的作用。《太子》還說:“艷女賊體,陰寺賊性,眾佞賊智,雖三朝三問,禮嚴文備,如優飾然,何有于教!天子視朝之余,太子事師之余,不離左右,慈以笑語,嚴以誨責,三賊不近,一習常安。”在他看來,要教好太子,就不能給予其太多的自由空間和生活特權,否則只會縱容其恣睢;教太子應該使之常隨天子左右,而不能被“艷女”、“陰寺”、“眾佞”包圍。這給我們的啟示是,在德育過程中教師要有意為受教者創造良好的環境,把不利于受教者品行培養的因素盡量排除在外。
唐甄雖然認為教師在德育中發揮重要的作用,但是,他還講“即心是道,即心得師,破迷起惰,不假外求,誠能精思竭力,必為圣人”(《無助》),強調主體用心、努力對道德養成的重要性。《無助》還說:“茍不憚勞、不恥后,雖無仆馬之助,終亦必至焉。為學無朋,亦若是矣。”在此,唐甄把師友在進學中的作用比作“仆馬”,認為他們不過是“致遠之資”罷了。人走到半路,沒有了“仆馬”,難道就不走了?只要不怕困難,哪怕慢一點,也會達到目標。可見,道德養成的關鍵是“反求諸己”,即充分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