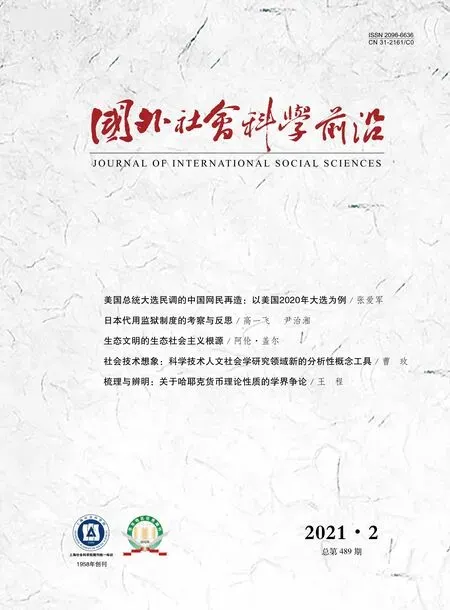生態(tài)文明的生態(tài)社會主義根源 *
阿倫·蓋爾 /文 曲一歌 / 譯
2007年10月,在中國共產(chǎn)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生態(tài)文明”被納入中央委員會的報告,正式成為中央政府的政策目標(biāo)。2012年,中國共產(chǎn)黨將生態(tài)文明的目標(biāo)寫入黨章,并將其納入五年規(guī)劃。2017年,中國共產(chǎn)黨的十九大呼吁加快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生態(tài)文明與循環(huán)經(jīng)濟(jì)的追求相關(guān)聯(lián)。在循環(huán)經(jīng)濟(jì)中,“一個系統(tǒng)設(shè)施所消耗的能源、水、材料和信息等,來源于另一個系統(tǒng)設(shè)施的輸入”。1Geall, Sam and Adrian Ely, Narratives and Pathways Towards an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na Quarterly, vol. 236, 2018, p. 1189.用于改善環(huán)境、減少污染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技術(shù)支出已大幅增加,但環(huán)保人士認(rèn)為,這方面的支出還遠(yuǎn)遠(yuǎn)不夠。鑒于生態(tài)文明在中國政治文化中的中心地位,生態(tài)文明的含義備受爭議。
生態(tài)文明通常被認(rèn)為是工業(yè)文明之后的產(chǎn)物。這可以解釋為中國必須先實現(xiàn)全面工業(yè)化,才具備全面解決生態(tài)問題的能力。它也可以解釋為利用技術(shù)解決方案來處理工業(yè)化所產(chǎn)生的生態(tài)問題,這很像西方的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一個更為激進(jìn)的觀點認(rèn)為,需要挑戰(zhàn)資本主義和工業(yè)化帶來的權(quán)力集中化。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城市發(fā)展與環(huán)境研究所所長潘家華認(rèn)為,生態(tài)文明要求制度要使市場置于從屬地位,并賦予地方政府以權(quán)力。中國人民大學(xué)的張云飛教授從更為廣泛的意義上來定義生態(tài)文明,他認(rèn)為,生態(tài)學(xué)維度在不同程度上貫穿于所有文明之中,那些生態(tài)文明發(fā)展不充分的社會正在破壞它們的存在條件。張云飛教授認(rèn)為,當(dāng)前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相對薄弱,有必要恢復(fù)和推進(jìn)遺失的早期生態(tài)智慧。2Zhang Yunfei, On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vol. 30, 2019, pp. 11-25.與此并不矛盾的是,清華大學(xué)盧風(fēng)教授認(rèn)為,生態(tài)文明已經(jīng)成為人類戰(zhàn)勝當(dāng)前全球生態(tài)危機(jī)和解決局部生態(tài)問題的目標(biāo)。由于資本主義的發(fā)展被認(rèn)為是全球范圍內(nèi)生態(tài)破壞的主要驅(qū)動力,在避免這種破壞力陷于癱瘓的背后,這種更激進(jìn)的觀點往往(雖然并不總是)明確地與作為社會主義生態(tài)文明的生態(tài)社會主義斗爭聯(lián)系在一起。這是原國家環(huán)境保護(hù)總局副局長、北京中央社會主義學(xué)院第一副院長潘岳的觀點,他是政府級生態(tài)文明的主要倡導(dǎo)者,他得到了包括北京大學(xué)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郇慶治在內(nèi)的主要學(xué)者的大力支持。
對這些生態(tài)社會主義者來說,資本邏輯是生態(tài)破壞的罪魁禍?zhǔn)住R虼耍缗嗽浪裕骸拔覀儽仨氂民R克思主義的理論武器來‘反對任何偏離生態(tài)文明的生產(chǎn)方式和生活方式’。”他認(rèn)為,“社會主義更有可能為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提供制度動力和制度保障。”3Wang Zhihe, Huila He and Meijun Fan, The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Debate in China, Monthly Review, vol. 66, 2014, p. 10.據(jù)此,盧風(fēng)教授認(rèn)為,生態(tài)文明及其實踐將否定和超越現(xiàn)代文明和城市文明,并與新型的經(jīng)濟(jì)、社會和文化制度框架相聯(lián)系,人們將通過這些制度框架過上更有意義的生活。4Huan Qingzhi, Socialist Eco-civilisation and Social-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Capitalism Nature Civilisation, vol. 27,2016, p. 55.在這種情況下,生態(tài)文明就等同于一種先進(jìn)的生態(tài)社會主義形式。然而,如前所述,情況并非總是如此。要說明生態(tài)社會主義是生態(tài)文明的基礎(chǔ),并且生態(tài)文明蘊涵著生態(tài)社會主義,就必須理解生態(tài)文明概念發(fā)展的歷史背景。
一、生態(tài)文明的俄羅斯之源:從組織形態(tài)學(xué)到生態(tài)文化
中國的“生態(tài)文明”(ecological civilisation)一詞最早是由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學(xué)家葉謙吉提出的。1984年,他在《莫斯科大學(xué)學(xué)報》上發(fā)表了一篇關(guān)于科學(xué)社會主義的文章。1987年,這篇文章被翻譯成中文發(fā)表在中國的報紙上。1Huan Qingzhi, Socialist Eco-civilisation and Social-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Capitalism Nature Civilisation, vol. 27,2016, p. 52.“ 生態(tài)文明”最初的術(shù)語是“生態(tài)文化”(ecological culture),后被翻譯為“生態(tài)文明”。但在中國,“文化”和“文明”有時被視為同義詞,“文明”一詞在中國的使用方式如同“文化”一詞在俄羅斯的使用。中國將文明分為物質(zhì)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態(tài)文明等組成部分,每一種文明都是其他文明和更廣泛文明的條件,正如不同民族的文化可以有不同的亞文化一樣。“生態(tài)文化”的概念最初是由蘇聯(lián)的馬克思主義者提出的,并在20世紀(jì)70年代以后被廣泛使用。例如,1983年,尤里·伊萬諾維奇·馬寧(Yuri Ivanovitch Manin)在《生態(tài)學(xué)的社會方面》(Social Aspects of Ecology)中發(fā)表的《生態(tài)文化與共產(chǎn)主義》和V. S. 利比茨基(V. S. Lipitsky)在1983發(fā)表的《人格生態(tài)文化及其形成途徑》。接著,一位主要的政府人物伊凡·T. 弗洛洛夫(Ivan T. Frolov)與T. V. 瓦西里瓦(T. V. Vasileva)和V. A. 洛斯(V. A. Los),在蘇聯(lián)的一份出版物《生態(tài)宣傳》(Ecological Propaganda)中提出了“生態(tài)文化”的概念。同年,瓦西里瓦在一篇文章上就這個話題進(jìn)行了辯護(hù)。2這些細(xì)節(jié)是由卡列維·庫爾(Kalevi Kull)提供的,他是當(dāng)時蘇聯(lián)一位活躍的理論生物學(xué)家和生態(tài)學(xué)家。
伊凡·T. 弗洛洛夫(Ivan T. Frolov)是一位專門研究生物學(xué)的科學(xué)哲學(xué)家,也是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bachev)的顧問。他后來成為蘇聯(lián)主要意識形態(tài)雜志《共產(chǎn)黨人》(Kommunist)的編輯,之后又成為主要報紙《真理報》(Pravda)的編輯。1985年,在戈爾巴喬夫成為蘇聯(lián)總書記之前,弗洛洛夫在波士頓大學(xué)哲學(xué)系和科學(xué)史研究中心的一次會議上提出,面對全球生態(tài)危機(jī),能夠而且應(yīng)該將人類團(tuán)結(jié)在一個共同的目標(biāo)上,即戰(zhàn)勝冷戰(zhàn)。他詳細(xì)闡述了這種生態(tài)導(dǎo)向的含義,他認(rèn)為“把生物圈僅僅看作是資源的來源或廢物的‘清除器’是錯誤的”。3D. R.Weiner, A Little Corner of Freedom: Russian Nature Protection from Stalin to Gorbach?v,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p. 399.弗洛洛夫認(rèn)為,把美學(xué)和倫理價值重新整合到我們與世界的關(guān)系和科學(xué)發(fā)展之中是同樣重要的。他呼吁從人類中心主義轉(zhuǎn)向生物圈中心主義(biospherocentrism)。另外,弗洛洛夫反對社會生物學(xué),該學(xué)說認(rèn)為社會行為是由基因決定的,復(fù)興了社會達(dá)爾文主義,并使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合法化。弗洛洛夫援引馬克思將人的特征描述為社會關(guān)系的總和的論斷,他提出人類本質(zhì)上是文化存在者。4Ivan Frolov, Genes or Culture: A Marxist Perspective on Humankind, Biology and Philosophy, vol. 1, 1986, pp. 89-107.
生態(tài)文化的支持者賦予文化以重要地位實際上是源于20世紀(jì)2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tǒng)。這是由布爾什維克前進(jìn)派所倡導(dǎo)的激進(jìn)馬克思主義的一部分,其中包括教育委員阿納托利·盧那察爾斯基(Anatoly Lunacharsky),他被列寧任命負(fù)責(zé)環(huán)境保護(hù)。他拒絕將社會的“經(jīng)濟(jì)基礎(chǔ)—上層建筑”模型(the base-superstructure model)粗劣地解釋為技術(shù)決定論。正是出于反對將馬克思主義進(jìn)行機(jī)械化和教條化理解的考慮,馬克思宣稱,如果他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他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1Friedrich Engels, Engels to C. Schmidt, London, Aug. 5, 1890, Marx Engels: Selected Works, 7th Impression, vol. II.,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62, p. 486.此外,這些激進(jìn)的馬克思主義者認(rèn)為技術(shù)和意識形態(tài)是文化的不同組成部分,創(chuàng)建社會主義社會有必要創(chuàng)建一個新的文化,其中包括一個新形式的科學(xué),以克服資本主義造成的認(rèn)識上的缺陷和扭曲,由此反對資產(chǎn)階級及其管理者的文化霸權(quán)。這在1918年得到了列寧的支持,但他想要一個更為實際的方向。2James D. White, Red Hamlet: The Life and Ideas of Alexander Bogdanov, Leiden: Brill, 2019, p. 392.
新社會主義的文化運動——無產(chǎn)者文化運動(Proletkult),最初是受到亞歷山大·波格丹諾夫(Aleksandr Bogdanov)思想的影響。馬克思在《〈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批判〉序言》中對社會的“經(jīng)濟(jì)基礎(chǔ)—上層建筑”模型進(jìn)行了描述,他認(rèn)為“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3Karl Marx,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S.W. Ryazanskaya,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0, p. 19.在此基礎(chǔ)上,波格丹諾夫指出,社會存在是有意識的存在,并將其納入“文化”范疇。意識涉及文化的技術(shù)成分,也涉及協(xié)調(diào)人的文化意識形態(tài)成分。馬克思批判了資產(chǎn)階級生產(chǎn)方式,說明經(jīng)濟(jì)學(xué)的范疇不是永恒的,而是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在特定歷史形式下的表達(dá),馬克思主要暗示了存在著能夠替代這些范疇的新范疇。波格丹諾夫在《生活經(jīng)驗哲學(xué)》(The Philosophy of Living Experience)和后來的《社會意識科學(xué)》(The Science of Social Consciousness)中試圖探尋新的范疇以作為對經(jīng)濟(jì)學(xué)范疇的替代。他認(rèn)為科學(xué)是人類有組織的集體經(jīng)驗,并且展示了如何通過自然的隱喻表達(dá)在社會生產(chǎn)組織中的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并通過這些隱喻理解、說明和再現(xiàn)這些現(xiàn)有的社會關(guān)系。
在提出這一論點時,波格丹諾夫并沒有否定科學(xué)的成就。然而,他認(rèn)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科學(xué)的新進(jìn)步將受到抑制,因為它們挑戰(zhàn)了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而科學(xué)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將需要進(jìn)行克服資本主義文化的斗爭。無產(chǎn)者的文化運動試圖克服過去所有文化的認(rèn)知缺陷,同時將所有最好的文化納入其中。正如希拉·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所指出的,這種關(guān)于無產(chǎn)者文化的觀點與1928—1931年蘇聯(lián)“文化革命”期間自上而下的觀點非常不同,后者導(dǎo)致了李森科主義(Lysenkoism)的產(chǎn)生。4Sheila Fitzpatrick, Cultural Revolution as Class War, in Sheila Fitzpatrick(e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ssia, 1928-1931,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10.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關(guān)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著重強(qiáng)調(diào)實踐與改變世界。受其影響,波格丹諾夫認(rèn)為,新的文化不僅需要推進(jìn)我們對世界的理解,還需要提供概念。通過這些概念,人們可以重新定義他們在自然中的位置和他們彼此之間的關(guān)系,使他們能夠?qū)崿F(xiàn)自我組織從而創(chuàng)造未來。
這將是一個消除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工人和管理者之間的差別的未來。在這些概念的幫助下,人們將理解他們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工人們將能夠管理他們自己的工作。換句話說,人類將克服與他人、自然、人性以及自身創(chuàng)造力的異化關(guān)系,最終將克服笛卡爾的二元論和機(jī)械論的自然觀。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分化表現(xiàn)為統(tǒng)治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分化。工人階級和自然一起傾向于被物化為為統(tǒng)治階級賺取更大的利潤(剩余價值)而進(jìn)行斗爭的控制工具。科學(xué)家或哲學(xué)科學(xué)家,在他們的工作中已經(jīng)克服了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對立,并且能夠自行組織起來推動科學(xué)的發(fā)展。他們逐漸認(rèn)識到,他們是理解世界的積極行動者,并努力克服他們科學(xué)理論中的二元論。以先進(jìn)的科學(xué)發(fā)展成果尤其是熱力學(xué)和相對論為基礎(chǔ),科學(xué)家們已經(jīng)開始受到人們的贊賞。波格丹諾夫呼吁并著手發(fā)展組織的一般理論——組織形態(tài)學(xué)(Tektology),作為一個完整的世界觀的基礎(chǔ)。從這個角度來看,“整個世界由一個自組織的過程構(gòu)成,它是在相互關(guān)聯(lián)、斗爭或統(tǒng)一中無限發(fā)展的一系列不同形式和不同層次的組織綜合體”。1James D. White, Red Hamlet: The Life and Ideas of Alexander Bogdanov, Leiden: Brill, 2019, p. 289.組織形態(tài)學(xué)關(guān)于世界的自組織過程的創(chuàng)造性闡發(fā)克服了自然科學(xué)和人文科學(xué)之間的對立,同時為人們提供了方法,不僅讓他們了解自己在自然、社會和歷史中的地位,而且讓他們能夠組織和管理自己,而不是被管理者管理。2Arran. Gare, Aleksandr Bogdanov’s History, Soci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31, 2000, pp. 231-248.組織形態(tài)學(xué)啟發(fā)了一般系統(tǒng)理論,是復(fù)雜性理論的先驅(qū)。
二、生態(tài)學(xué)、理論生物學(xué)和生態(tài)符號學(xué)
生物學(xué)在創(chuàng)造一種新文化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最初,在蘇聯(lián)廣受青睞的生物學(xué)是反活力論和反唯心論的,本質(zhì)上是實證主義和還原主義。然而,當(dāng)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開始發(fā)揮影響時,蘇聯(lián)生物學(xué)和心理學(xué)一起成為后來被稱為第三條道路的主要中心——既不是活力論,也不是機(jī)械論,而是一種反還原主義的自然主義。在20世紀(jì)20年代得到盧那察爾斯基的大力支持,他同時還支持弗拉基米爾·伊萬諾維奇·維爾納茨基(Vladimir Ivanovich Vernadsky)的工作以及他的生物圈(biosphere)和智慧圈(noosphere)概念。這些想法與波格丹諾夫的組織形態(tài)學(xué)非常一致。3Arran. Gare, Soviet Environmentalism: The Path not Taken,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vol. 4, 1993, pp. 69-88.甚至在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前,俄羅斯就已經(jīng)是生態(tài)學(xué)和其他地球科學(xué)研究的主要中心,特別關(guān)注生物群落的共生關(guān)系。4Giulia. Rispoli, Between “Biosphere” and “Gaia”, Earth as a Living Organism in Soviet Geo-ecology, Cosmos and History, vol. 10, 2014, pp. 78-91.生態(tài)學(xué)的特點是對生物種群或生物群落的研究,而不是對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研究,其重點是生物之間的關(guān)系,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如何增強(qiáng)它們生存和進(jìn)化的條件。這是彼得·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的民主聯(lián)邦制的基礎(chǔ),這種聯(lián)邦制的基礎(chǔ)是把互助作為生活的基本特征。在20世紀(jì)20年代,蘇聯(lián)的生態(tài)學(xué)研究結(jié)合了熱力學(xué)和恩格斯的思想,是世界上最具原創(chuàng)性、先進(jìn)性的研究。
但是,這并沒有持續(xù)多久。隨著斯大林的勝利和“戰(zhàn)時共產(chǎn)主義”政策的實施,調(diào)查的自由受到嚴(yán)重限制。1929年,盧那察爾斯基辭去教育委員職務(wù),以抗議政府對教育的干預(yù)。雖然他們反對任何聲稱自然不可能被完全控制的主張,并且許多生態(tài)學(xué)家遭到斯大林及其追隨者的迫害,但這種激進(jìn)的科學(xué)運動并沒有完全被摧毀,而是在蘇聯(lián)持續(xù)了下來,正如道格拉斯·R. 韋納(Douglas R. Weiner)在1999年出版的《自由的小角落》(A Little Corner of Freedom)一書的標(biāo)題中所描述的那樣。
然而,這種新文化并不僅僅是在蘇聯(lián)這個自由的小角落里發(fā)展起來的。蘇聯(lián)的工作引起了英國激進(jìn)科學(xué)家尤其是生物學(xué)家的注意。1931年6月,由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布哈林(Nicolai Bukharin)率領(lǐng)的蘇聯(lián)代表團(tuán)參加了在倫敦舉行的一次科學(xué)會議,發(fā)表了蘇聯(lián)關(guān)于科學(xué)與社會關(guān)系的研究成果。俄羅斯對這次會議的貢獻(xiàn),由布哈林編輯并發(fā)表在《十字路口的科學(xué)》(Science at the Crossroads)雜志上。這對一些受到物理學(xué)和馬克思主義進(jìn)步思想啟發(fā)的英國生物學(xué)家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這些進(jìn)步包括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德國和俄羅斯生物學(xué)的發(fā)展,以及懷特海的過程哲學(xué)。1Erik L. Peterson, The Life Organic: The Theoretical Biology Club and the Roots of Epigenetics,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17, p. 55.這些社會主義者致力于發(fā)展生物學(xué)的新思想,主要關(guān)注胚胎學(xué)。其中最著名的是J. D. 貝爾納(J. D. Bernal)、尼達(dá)姆·約瑟夫(Joseph Needham)以及C. H. 沃丁頓(C. H. Waddington),他們參加了1931年的會議,并于1932年成立了理論生物學(xué)俱樂部。由于沃倫·韋弗(Warren Weaver)反對他們的共產(chǎn)主義情懷,2Erik L. Peterson, The Life Organic: The Theoretical Biology Club and the Roots of Epigenetics,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17, p. 119.因而他們未能獲得劍橋大學(xué)和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支持。之后沃丁頓移居愛丁堡大學(xué),并繼續(xù)促進(jìn)其“數(shù)學(xué)—物理—化學(xué)形態(tài)學(xué)”(mathematico-physico-chemical morphology)的發(fā)展。
他們的研究獲得了支持,為活力主義者和分子生物學(xué)家的還原論綱領(lǐng)提供了另一種選擇。分子生物學(xué)家用達(dá)爾文進(jìn)化論綜合了他們的思想以發(fā)展關(guān)于進(jìn)化的綜合理論,并最終發(fā)展了社會生物學(xué)。正如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所說,有機(jī)體是繁殖基因的生存機(jī)器。沃丁頓和他的支持者們建立了一個創(chuàng)新性的關(guān)系過程世界,在人類的發(fā)展過程中,他們在地球上不僅創(chuàng)造了生命,而且創(chuàng)造了新的價值。雖然這整個研究計劃在50年代被忽視和邊緣化,但隨著人們對生態(tài)破壞認(rèn)識的發(fā)展和60年代激進(jìn)主義的興起,他們有可能獲得支持并成功地推廣這些想法。20世紀(jì)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沃丁頓在瑞士貝拉吉奧(Bellagio)組織了理論生物學(xué)方面的世界級會議,由沃丁頓編輯會議記錄,最后出版了4卷本的《走向理論生物學(xué)》(Towards a Theoretical Biology)。由此,這引發(fā)了一場國際范圍的理論生物學(xué)運動,為后來的后還原主義生物學(xué)的發(fā)展提供了一個理論參考點,包括辯證生物學(xué)、突變理論、復(fù)雜性理論和層次理論。3Arran Gare, Chreods, Homeorhesis, and Biofields: Finding the Right Path for Science through Daoism, Progress in Biophysics and Molecular Biology, vol. 131, 2017, pp. 61-91.沃丁頓是讓·皮亞杰(Jean Piaget)遺傳認(rèn)識論的堅定支持者,該認(rèn)識論不僅挑戰(zhàn)了行為主義心理學(xué),而且對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的反實證主義科學(xué)哲學(xué)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
雖然這些理論生物學(xué)家最初關(guān)注的是單個生物體的形態(tài),但他們也關(guān)注發(fā)展中的生態(tài)學(xué)。沃丁頓支持公開馬克思主義辯證生物學(xué)家和生態(tài)學(xué)家理查德·列文斯(Richard Levins)和理查德·列旺丁(Richard Lewontin)的工作。他還支持等級理論家霍華德·帕提(Howard Pattee)。帕提認(rèn)為,生活、人類文化和人類制度的出現(xiàn)是一種新的有利約束問題。這一觀點后來成為與蒂莫西·艾倫(Timothy Allen)和斯坦利·薩特(Stanley Salthe)及其同事的理論生態(tài)學(xué)的核心。沃丁頓還發(fā)表了C.S.霍林(C. S. Holling)關(guān)于生態(tài)系統(tǒng)穩(wěn)定性和恢復(fù)力的著作,霍林是為數(shù)不多獲得諾貝爾生態(tài)學(xué)獎的生態(tài)學(xué)家之一。霍林參與了生態(tài)經(jīng)濟(jì)學(xué)的建立,并創(chuàng)辦了《保護(hù)生態(tài)學(xué)》(Conservation Ecology)雜志,后來改名為《生態(tài)學(xué)與社會》(Ecology and Society)。此外,霍林激發(fā)了“恢復(fù)力聯(lián)盟”(Resilience Alliance)的靈感,這是一項旨在將生態(tài)思維納入公共政策的運動,其理念是維持或創(chuàng)建有恢復(fù)力的生態(tài)系統(tǒng)。總的來說,這些理論家反對達(dá)爾文主義和社會達(dá)爾文主義的簡化形式及其通過競爭斗爭和適者生存取得進(jìn)步的理論教條,強(qiáng)調(diào)約束在進(jìn)化中實現(xiàn)的共生和協(xié)同作用。他們將社會主義的追求合法化,將經(jīng)濟(jì)人的利己主義置于從屬地位,這作為一種進(jìn)化的進(jìn)程,為人們提供充分發(fā)揮其潛能的條件,以促進(jìn)人類生存條件的發(fā)展。沃丁頓本人也越來越關(guān)注全球資本主義帶來的環(huán)境問題。他的最后一部作品《人造的未來》(The Man-Made Future)的開頭是這樣的:“無論未來如何,它都是人類創(chuàng)造的。世界范圍內(nèi)物種所面臨的重大問題本質(zhì)上并且不可避免的是復(fù)雜的。它由一系列主要的世界性問題組成,包括人口、糧食供應(yīng)、能源、自然資源、污染、城市狀況等。這些問題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任何一個問題都不可能孤立地得到妥善解決。”1Conrad. H. Waddington, Man-made Futur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8, p. 9.沃丁頓認(rèn)為,人類將通過了解這一點并采取適當(dāng)?shù)男袆觼韯?chuàng)造未來,而不是讓市場的力量來決定未來。
盡管這些激進(jìn)思想在20世紀(jì)60年代和70年代初得以復(fù)興,但早在1975年沃丁頓去世之前,這些思想就開始被邊緣化。在接下來的30年里,它們被沃丁頓所描述的“COWDUNG”(占統(tǒng)治地位群體的傳統(tǒng)智慧)排擠到了一邊,這就是資本主義賴以建立的“德謨克利特—笛卡爾哲學(xué)”。在這種背景下,沃丁頓與蘇聯(lián)的理論生物學(xué)家和生態(tài)學(xué)家進(jìn)行了交流。在1974—1975年期間,他與愛沙尼亞科學(xué)院動物和植物研究所生態(tài)系的卡列維·庫爾(Kalevi Kull)進(jìn)行了通信,并給他寄去了4卷本的《走向理論生物學(xué)》(Towards a Theoretical Biology)。1976年,理論生物學(xué)集團(tuán)在塔爾圖成立,恢復(fù)了愛沙尼亞生物學(xué)的反機(jī)械傳統(tǒng)。這可以追溯到卡爾·恩斯特·馮·巴爾(Karl Ernst von Baer)和雅各布·馮·埃克斯庫爾(Jakob Von Uexküll),以及最近在生態(tài)學(xué)和理論生物學(xué)方面的工作和有關(guān)理論生物學(xué)的國際會議,都得到了莫斯科科學(xué)家們的高度重視。
塔爾圖和莫斯科的符號學(xué)者共同建立了“塔爾圖—莫斯科符號學(xué)學(xué)派”(Tartu-Moscow School of Semiotics)。該學(xué)派一直延續(xù)到現(xiàn)在。1964年出版的《符號系統(tǒng)研究》(Sign Systems Studies)雜志于1991年以英文出版,成為研究文化與自然的符號學(xué)和符號過程的國際期刊。盡管在某種程度上與西方符號學(xué)的工作相似,并受到索緒爾(Saussure)的影響,該雜志的撰稿人也受到米哈伊爾·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及其圈子的思想的影響,包括在20世紀(jì)20年代興盛起來的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者帕維爾·N. 梅德韋杰夫(P. N. Medvedev)和瓦倫丁·尼古拉耶維奇·沃洛希諾夫(V. N. Volo?inov)。近幾年來,他們更傾向于支持查爾斯·桑德斯·皮爾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而不是索緒爾。這些符號學(xué)家為法國符號學(xué)家及其會說英語的人提供了另一種工作選擇。庫爾加入了這一符號學(xué)派,并且后來成為《符號系統(tǒng)研究》雜志的編輯。他與丹麥的生物符號學(xué)家進(jìn)行了密切接觸,特別是激進(jìn)環(huán)保主義者杰斯帕·霍夫邁爾(Jesper Hoffmeyer),后者提出了符號圈(semiosphere)的概念,符號圈領(lǐng)域起源于生活,并且是生物圈的中心。他們與來自捷克、奧地利和其他地方的生物符號學(xué)家一起,開展了國際生物符號運動,并每年舉行一次集會。從2008年起,他們出版了《生物符號學(xué)》(Biosemiotics)雜志。庫爾使塔爾圖成為國際領(lǐng)先的生物符號學(xué)和生態(tài)符號學(xué)研究中心。
在關(guān)注生態(tài)符號學(xué)的同時,庫爾和他的同事們正致力于重新定義人類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將人類文化解釋為一種更復(fù)雜的符號形式。這促進(jìn)了對馬克思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批判的重新表述,將其直接與生態(tài)問題聯(lián)系起來。正如瑞典人類生態(tài)學(xué)家阿爾夫·霍恩伯格(Alf Hornborg)在1999年出版的《金錢與生態(tài)系統(tǒng)崩潰的符號學(xué)》(Money and the Semiotics of Ecosystem Dissolution)中所指出的,金錢是一種只有一個符號的代碼,或者是一種只有一個音素的語言。它不可能提供適當(dāng)處理復(fù)雜情況所需要的反饋,而且事實上,通過掩蓋人與人之間關(guān)系的本質(zhì)正在驅(qū)使人類走向生態(tài)破壞。霍恩伯格在《生命的跡象:亞馬遜流域人類生態(tài)的生態(tài)符號學(xué)透視》(Vital Signs: An Ecosemiotic Perspective on the Human Ecology of Amazonia)一文中闡述了這一點,并發(fā)表在《符號系統(tǒng)研究》雜志上。2001年,馬克斯·奧爾施萊格(Max Oelschlaeger)在同一份期刊上發(fā)表了《生態(tài)符號學(xué)與可持續(xù)轉(zhuǎn)型》(Ecosemiotics and the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一文。根據(jù)馬克思所說:“哲學(xué)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奧爾施萊格接著論證了生態(tài)符號學(xué)論是如何促進(jìn)國際文化變革的。正如他所說:“如果生態(tài)符號學(xué)不僅僅是一種學(xué)術(shù)娛樂,那么就必須有一個大綱(暫定的或簡略的)概述實用的生態(tài)符號學(xué)在某種程度上如何影響‘生態(tài)符號學(xué)’,即人類生態(tài)與生物物理生態(tài)的重疊,文化主體與自然主體的混亂界面。生物物理生態(tài)或自然與人類生態(tài)或文化的鴻溝威脅著生物物理災(zāi)難性進(jìn)程和不可逆轉(zhuǎn)的變化……主要的文化法則(經(jīng)濟(jì)學(xué)、政治學(xué)、倫理學(xué)、心理學(xué)等)使這種分離永久存在,從而引導(dǎo)人類走向自然選擇的命運。生態(tài)符號學(xué)理論應(yīng)描述可促進(jìn)適應(yīng)性文化變革的過程。”1Max Oelschlaeger, Ecosemiotics and the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 Sign Systems Studies, vol. 29, 2001, p. 226.
生態(tài)符號學(xué),根據(jù)其在人類生態(tài)中的位置(與“經(jīng)濟(jì)人類學(xué)”密切相關(guān)),將人類文化融入其對自然的理解之中,不僅為理解資本主義失敗的原因提供了手段,也通過整合科學(xué)和人文重新思考已被接受的概念并實現(xiàn)社會轉(zhuǎn)型,從而實現(xiàn)一種基于生態(tài)思維的文明。
三、李約瑟與中國的科學(xué)和文明
當(dāng)沃丁頓從事他的理論生物學(xué)工作,并致力于環(huán)境問題和藝術(shù)創(chuàng)作之時,留在劍橋大學(xué)擔(dān)任生物化學(xué)教授的李約瑟卻轉(zhuǎn)向了科學(xué)史。起初,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西方科學(xué)的胚胎學(xué)歷史上,后來受俄羅斯人的啟發(fā),他知曉了西方科學(xué)曾經(jīng)的成就和目前的失敗。由此,他便開始了關(guān)于歐洲和中國的科學(xué)發(fā)展對比的重大研究項目。他后來的歷史著作比蘇聯(lián)的科學(xué)史學(xué)家更詳細(xì)地解釋了17世紀(jì)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和科學(xué)唯物主義的興起之間的關(guān)系。通過利用新發(fā)展的成文法的隱喻性質(zhì),他展示了自然如何被視為運動中的物質(zhì),依據(jù)永恒不變的法則盲目而毫無意義地運動著,從而使資本主義的新興社會秩序合法化。資本主義社會堅持和擴(kuò)展這種自然觀并將其納入經(jīng)濟(jì)理論和其他人類科學(xué)。羅伯特·楊(Robert Young)延續(xù)了李約瑟在科學(xué)史研究上的馬克思主義方法。他在1985年的《達(dá)爾文的隱喻》(Darwin’s Metaphor)中展示了達(dá)爾文主義是如何克服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文化危機(jī)的。在這場危機(jī)中,經(jīng)濟(jì)發(fā)展與工人階級的貧困和帝國主義相聯(lián)系,對殖民地人民造成了毀滅性的后果。人們用以經(jīng)濟(jì)學(xué)為特征的資本主義社會關(guān)系來比喻自然,然后利用它來捍衛(wèi)經(jīng)濟(jì)學(xué)本身以及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殘酷后果。
然而,李約瑟也發(fā)現(xiàn)了一個反傳統(tǒng)思維方式,從萊布尼茨開始,貫穿于赫爾德(Herder)、謝林、黑格爾、馬克思、恩格斯、塞繆爾·亞歷山大(Samuel Alexander)、勞埃德·摩爾根(Lloyd Morgan)和懷特海以及理論生物學(xué)運動的著作中。這些思想家把自然界看作是一個關(guān)系過程或活動模式的領(lǐng)域,能夠產(chǎn)生知覺、意識和精神,而不是運動中的物質(zhì)。李約瑟認(rèn)為,中國思想尤其是12世紀(jì)宋明理學(xué)大師朱熹對萊布尼茨的影響,從根本上改變了這一傳統(tǒng)的思維方式。
李約瑟認(rèn)為,萊布尼茨的獨創(chuàng)性在于反對伽利略、牛頓科學(xué)傳統(tǒng),萊氏認(rèn)為這一科學(xué)傳統(tǒng)的根本原因在于朱熹對他的影響。根據(jù)朱熹的觀點,自然是由能量(“氣”)的形式(“理”)構(gòu)成的,而能量(“氣”)是通過陰陽對立但相互滲透且相互支持的原理或力量相互作用而發(fā)展的。關(guān)于朱熹,李約瑟寫道:“在他的身后,有中國相關(guān)思維的全部背景;在他的前面,有戈特弗里德·威廉·萊布尼茨。”1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2, 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6, p. 291.雖然現(xiàn)代科學(xué)起源于歐洲,但后還原主義科學(xué)吸收了來自中國的思想,超越了還原主義的科學(xué)唯物主義。它吸收了所有文明的精華,現(xiàn)在正成為一門全球科學(xué)。李約瑟認(rèn)為,現(xiàn)在需要的是一種新的社會秩序,以促進(jìn)19世紀(jì)末開始的思想革命的全面發(fā)展,并將這種思想吸收到社會組織中去。從李約瑟的角度看,社會主義生態(tài)文明理念在中國普遍受歡迎也是可以理解的。馬克思主義最初在中國被接受主要是為了借鑒西方社會關(guān)于工業(yè)化的觀念,以克服建國初期的貧困和實現(xiàn)民族解放。而中國傳統(tǒng)文化則保留了儒家所倡導(dǎo)的仁愛思想和民本傳統(tǒng),以及道家所倡導(dǎo)的對自然價值的尊重,儒家價值觀避免了將人當(dāng)作商品化的工具。此外,宋明理學(xué)家張載、周敦頤、程氏兄弟和朱熹將道家宇宙觀融入儒家學(xué)說,主宰中國哲學(xué)長達(dá)700年之久,他們反對接受還原論的科學(xué)唯物主義。李約瑟對中國的研究同沃丁頓在理論生物學(xué)領(lǐng)域的研究相結(jié)合,解釋了為什么中國科學(xué)家在欣賞自己的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李約瑟的研究促進(jìn)了這一傳統(tǒng))的同時,能夠接受并推進(jìn)生態(tài)學(xué)和生態(tài)思維方式。現(xiàn)在,李約瑟的預(yù)言即將成為現(xiàn)實。1Arran Gare, Daoic Philosophy and Process Metaphysics: Overcoming the Nihilism of Western Civilisation, in Guo Yi,Sasa Josifovic and Asuman L?tzer-Lasar (eds.),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Knowledge and Ethics in Chinese and European Philosophy, 2014, pp. 111-136.
四、作為生態(tài)社會主義文化的生態(tài)文明
中國的生態(tài)文明倡議和俄羅斯人對蘇聯(lián)的生態(tài)文化的探索,只是激進(jìn)的科學(xué)家和哲學(xué)家在更廣泛的全球運動中的一部分。這些激進(jìn)的科學(xué)家和哲學(xué)家經(jīng)常與敵對的知識環(huán)境作斗爭,以促進(jìn)其思維方式的發(fā)展,即創(chuàng)造使社會主義合法化所需的意識。在這種社會形式中,人們控制自己的命運,承認(rèn)自己是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參與者。
雖然波格丹諾夫、盧那察爾斯基、維爾納茨基、沃丁頓、李約瑟和庫爾等都未曾提出全球生態(tài)文明的概念,但他們的工作為引出中國及其在理解中國的突出地位提供了理論背景。但是,卻沒有在其確切內(nèi)涵上達(dá)成共識。弗洛洛夫和其他要求生態(tài)文化的俄羅斯人發(fā)揚了波格丹諾夫的文化觀念,認(rèn)為文化是人們在其基礎(chǔ)上生產(chǎn)和組織自己的意識形式。從這個角度看,社會主義要求發(fā)展一種新的文化,既要克服以往文化的缺陷,又要吸收其中的精華。后還原主義科學(xué)對這一發(fā)展至關(guān)重要。波格丹諾夫、盧那察爾斯基、維爾納茨基、沃丁頓、李約瑟和弗洛洛夫都是社會主義者,他們認(rèn)為自己的工作是對資本主義產(chǎn)生的主流科學(xué)的挑戰(zhàn),是創(chuàng)造真正社會主義的核心。換言之,他們所設(shè)想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包括對自然的新認(rèn)識。李約瑟的著作解釋了中國為什么擁護(hù)社會主義,并提供了一個使生態(tài)文明概念不僅能夠被提出,而且能夠被政府接受的文化環(huán)境。生態(tài)文明的基礎(chǔ)是這種激進(jìn)的社會主義傳統(tǒng)。因此,它涉及對資本主義文化及其作為一種自然生命形式的合法性的根本挑戰(zhàn)。相反,它使得為挑戰(zhàn)資本主義而建立的運動、機(jī)構(gòu)和政府的軌跡合法化并保持下去,從而建立社會主義的生命形式以創(chuàng)建社會主義的世界秩序。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參與這場斗爭的每一個人都贊賞他們這一探索的歷史、工作目標(biāo)和成就,或者說,這一探索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并不意味著他們?yōu)閯?chuàng)建社會主義社會鋪平了道路。如果不了解這一歷史背景,不了解激進(jìn)科學(xué)傳統(tǒng)的連貫性及其與社會主義的關(guān)系,人們很容易接受生態(tài)文化或生態(tài)文明的概念,卻無法理解它們的影響以及它們對資本主義的挑戰(zhàn)有多激進(jìn)。如前所述,它們可以被解釋為只不過是主流資本主義對環(huán)境問題的解決辦法,這些問題被視為與工業(yè)化相關(guān)的經(jīng)濟(jì)增長所帶來的邊際副作用,需要通過技術(shù)發(fā)展來解決這些問題,而不是解決一場重大的文明危機(jī)。然而,這場危機(jī)要求人們徹底改變理解自己的方式和他們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以及他們?nèi)绾谓M織經(jīng)濟(jì)、社會和政治生活。因此,生態(tài)文明的斗爭是與文化遺忘癥的斗爭,即失去了過去在認(rèn)識和保持連貫性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這種激進(jìn)思想傳統(tǒng)的激進(jìn)含義。
即使有了這段歷史,大多數(shù)人也可能忽略這些思想的全部含義(至少一開始是這樣)。資本主義越占主導(dǎo)地位,商品形態(tài)就越強(qiáng),人們就越難理解它的歷史相對性,也就越難理解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可能存在的不同關(guān)系,或者關(guān)于世界的不同理解。任何打破舊思維方式的做法都會被邊緣化、被遺忘或者被誤解,然后被重新表述以適應(yīng)主流文化。那些參與發(fā)展可能挑戰(zhàn)資本主義文化思想的人經(jīng)常被壓制,或者他們的努力因缺乏資金而受到削弱。隨著新自由主義的出現(xiàn),人們對主流思想的挑戰(zhàn)逐漸被削弱,他們將大學(xué)轉(zhuǎn)變?yōu)榭鐕虡I(yè)公司,并將其融入經(jīng)濟(jì),將教育、研究和知識商品化,從而只支持為公司帶來利潤的教育和研究。
甚至還有一種對語言的歪曲,使得人們很難表達(dá)激進(jìn)的思想,也很難理解這些思想及其意義。文化和文明的概念就說明了這一點,這些概念最初是為了使人們能夠描述和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并堅持更高的價值觀而發(fā)展起來的。
這些術(shù)語是從資本主義文化的角度來界定的。因此,盡管馬克思作出了努力并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但人們未能認(rèn)識到這一點。正如馬克思在《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批判大綱》中所描述的,經(jīng)濟(jì)學(xué)范疇表達(dá)了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存在形式,它們是一種特定文化和文明的內(nèi)核,是可以被取代的。任何真正的文明人都不能容忍把人和自然的其他部分僅僅當(dāng)作是滿足他們欲望的手段,把知識僅僅當(dāng)作是控制的工具。把文化和文明的概念從它們的瑣碎化中解放出來,使我們能夠?qū)⒖茖W(xué)視為文化和文明的一項重大成就和組成部分,堅持對真理的追求并將它視為對現(xiàn)實的連貫和全面的理解,既與其他文化相互促進(jìn)也相互制約。
由于資本主義是依靠科學(xué)的,所以對資本主義文化霸權(quán)的挑戰(zhàn)可能是最有效的。科學(xué)的進(jìn)步表明,資本主義賴以存在并使之合法化的世界觀正在失效。氣候科學(xué)和生態(tài)學(xué)正帶頭挑戰(zhàn)主流的假設(shè)。這一挑戰(zhàn)有可能將科學(xué)從目前的分裂中拯救出來。羅伯特·尤亞諾維奇(Robert UIanowicz)認(rèn)為,生態(tài)學(xué)應(yīng)該成為定義科學(xué)的參考點,以克服目前阻礙理解進(jìn)化現(xiàn)象、發(fā)展生物學(xué)和其他生命科學(xué)甚至物理學(xué)方面取得進(jìn)展的觀念。1Robert E. Ulanowicz, Ecology: The Ascendent Perspectiv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6.這樣的科學(xué)既有可能揭示控制自然的極限,也有可能揭示如何控制自然,同時也有助于理解自然的內(nèi)在意義。通過發(fā)展一些概念,為如何診斷現(xiàn)代文明的疾病以及如何維護(hù)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健康和創(chuàng)建健康的社會提供指導(dǎo)方針,以人類生態(tài)學(xué)取代經(jīng)濟(jì)學(xué),成為制定公共政策的核心框架。
一旦有了嶄新的思維方式的種子,尤其是當(dāng)它們被包含在定義社區(qū)的敘述中時,它們便可以孕育完全改變社會和文明的創(chuàng)新型系統(tǒng)。把生態(tài)文明作為中國官方的說法,在某些人看來可能像是公關(guān)活動。然而,有了這一點,就以生態(tài)社會主義的形式復(fù)興了社會主義的宏大敘事。正如薩姆·吉爾(Sam Geall)和阿德里安·伊利(Adrian Ely)在《當(dāng)代中國生態(tài)文明的敘述和途徑》(Narratives and Pathways to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中所說,這種敘述可能在未來幾年內(nèi)影響到中國和國際社會走向可持續(xù)性社會秩序的途徑,這一觀點得到了毛里西奧·馬里內(nèi)利(Mauritzio Marinelli)的支持。1Mauritzio Marinelli, How to Build a “Beautiful China” in the Anthropocene,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the Intellectual Debate on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Journal of China Political Science, vol. 23, 2018, p. 375.正在出現(xiàn)的一種新的、重新煥發(fā)活力的社會主義作為生態(tài)文明的宏大敘事,它可以挑戰(zhàn)和取代還原論,后者也可以說是一種社會達(dá)爾文主義的新自由主義宏大敘事,這種宏大敘事在20世紀(jì)70年代推動了資本主義新的重大進(jìn)步。
五、結(jié) 論
本文考察了生態(tài)文明的歷史背景,解釋了它在中國的興起及其多樣性。為了避免被邊緣化,中國不得不接受和吸收大量來自歐洲的文化,這是通過接受馬克思主義來實現(xiàn)的。這促進(jìn)了中國的工業(yè)化,同時也使中國人與歐洲傳統(tǒng)保持著重要的距離。然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一直被混淆和誤解,在某些情況下,這導(dǎo)致了幾乎不加批判地采用西方文化(盡管它存在問題)。在這些情況下,生態(tài)文明可以被理解為與西方社會特有的環(huán)境保護(hù)形式?jīng)]有什么不同。然而,中國仍然存在著強(qiáng)大的文化傳統(tǒng),這些傳統(tǒng)間接地影響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作。這使中國人能夠在不完全了解生態(tài)社會主義概念的根源的情況下,欣賞蘇聯(lián)生態(tài)文化概念與社會主義產(chǎn)生的共鳴。那種認(rèn)為生態(tài)文明貫穿于所有社會形態(tài)中的思想,是恢復(fù)和捍衛(wèi)過去文化(包括中國文化)優(yōu)越性的一種方式。隨著資本主義的發(fā)展,中國文化因商品化、標(biāo)準(zhǔn)化、同質(zhì)化和貶低現(xiàn)實而受到壓制。捍衛(wèi)過去的文化與捍衛(wèi)社會主義生態(tài)文明、呼吁全球生態(tài)文明并不矛盾,這是現(xiàn)在作為全球文化力量出現(xiàn)的宏大敘事。2Arran Gare,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y Civilisation: 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 London: Routledge,2017.即使不涉及生態(tài)社會主義,生態(tài)文明的核心理念在引導(dǎo)人們行動的過程中得以展現(xiàn),也將不可避免地揭示出其生態(tài)社會主義根源。
一旦了解了生態(tài)文明的全部內(nèi)涵,就應(yīng)該清楚地看到,沒有必要再去談?wù)摗吧鐣髁x”的生態(tài)文明,因為在現(xiàn)代世界,生態(tài)文明只能是社會主義的。事實上,生態(tài)文明不僅聚焦于資本主義的最終失敗和資本主義必然被取代的根本原因,它還闡明了什么是社會主義,以及人類應(yīng)該努力創(chuàng)造什么。它可以提供一種替代霸權(quán)文化的選擇,這種文化能夠克服資本主義的文化霸權(quán),而且可以克服科學(xué)和人文之間的對立。文明通常被定義為反對野蠻和墮落,而在晚期資本主義,我們正面臨著高科技野蠻和消費主義墮落的結(jié)合。對于古羅馬人和文藝復(fù)興時期的哲學(xué)家來說,文明人是那些能夠自我管理的人,他們已經(jīng)被培養(yǎng)或教育去這樣做,具有理解、珍視和捍衛(wèi)他們的自由的美德。更廣泛地說,他們是那些能夠理解生命價值的人。在古代的“文明”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口可以被文明化,依靠奴隸、農(nóng)奴或農(nóng)民來做養(yǎng)活他們所需的繁重工作。馬克思意識到,盡管資本主義有種種缺點,但它正在創(chuàng)造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所有這些壓迫性的工作都可以由機(jī)器來完成,所有人都可以文明化,從而充分發(fā)揮他們的潛力,以拓展他們的社會和自然共同體生活。晚期資本主義通過使人們失去文明而使他們變得無能為力,把不負(fù)責(zé)任的自我放縱的生活描繪成自由的,但他們的消費被無產(chǎn)階級化,經(jīng)濟(jì)狀況變得越來越不穩(wěn)定。馬克思還認(rèn)識到資本主義對環(huán)境的災(zāi)難性影響,這種影響不僅在城市和農(nóng)村之間造成裂痕,而且還造成森林的破壞和氣候的改變。1Kohei Saito, Capital, Nature, and the Unfinished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Delhi: Dev Publishers, 2018.生態(tài)學(xué)著眼于包括人在內(nèi)的生物體的“小家”或“大家”系統(tǒng),為研究這些生物體之間或好或壞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條件,從而拓展了這些家庭。生態(tài)學(xué),包括人類生態(tài)學(xué),提供了重塑經(jīng)濟(jì)學(xué)和其他人文科學(xué)、倫理、政治所需的思維形式。馬克思寫道,在未來,每個人的自由發(fā)展將是一切人自由發(fā)展的條件。生態(tài)文明的勝利將涉及創(chuàng)建一種秩序,將這一理念從個人推廣到社區(qū),再推廣到共同體的共同體。“共同體的共同體”(communities of communities)將包括整個人類以及所有生物群落,其中也包括當(dāng)前的全球生態(tài)系統(tǒng)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