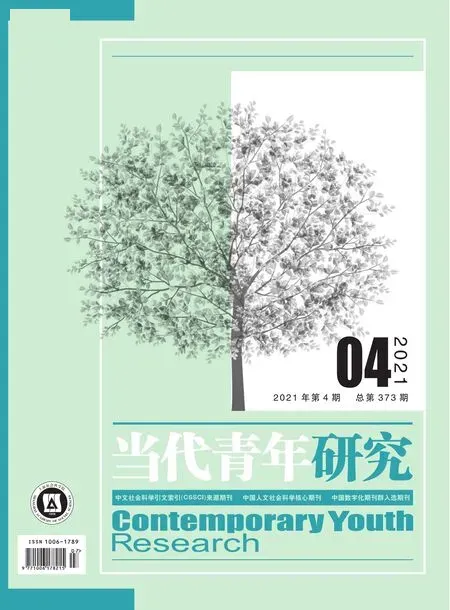家庭文化資本、“影子教育”與文化再生產
——基于縣城兒童和村莊兒童對照的視角
劉騰龍
(華中師范大學社會學院)
一、問題的提出
教育是促進社會流動的重要途徑,已經成為學術界的共識。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的教育不平等和社會階層固化現象愈發嚴重,引發了社會大眾對當前社會流動機制的普遍不滿與擔憂。社會階層地位的獲得越來越依靠教育成就,但是,家庭背景在教育獲得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1]家庭背景對教育成就和階層地位獲得的影響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文化資本這一中介機制發揮作用的,[2]學術界大都是通過這一視角來解釋教育不平等、階級再生產和社會再生產等諸多問題。[3]教育不平等問題已經成為教育學、社會學等學科重點關注的熱點問題,學界就城鄉教育不平等問題已做了大量研究。比如:唐俊超認為,中國社會的教育競爭愈發激烈且不斷“下移”,從重視高等教育的獲得向基礎教育轉移,甚至是向學前教育轉移。在城鄉教育公平問題上,鄉村早早就“輸在起跑線”上了。[4]劉保中認為,教育作為弱勢階層向上流動的重要工具,具有雙重效應,在促進了部分下層階級向上流動的同時,也間接導致了階層再生產,重塑了社會不平等。[5]熊易寒通過對比城市兒童與農民工子女,發現學校教育對于絕大部分處于城市底層的農民工子女而言,并不是其實現社會流動的階梯,而只是邁向階級再生產的驛站。[6]關于教育公平問題,縱觀已有研究,大都是從城市和鄉村二元格局的宏觀視角進行相關探討,而對“縣域”這一層面關注不夠。“縣城”作為城市和鄉村的中間地帶,在城鄉教育公平問題的相關研究方面,它的定位是模糊的,其重要性和價值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屬于研究“缺位”狀態。事實上,隨著教育競爭的不斷“下沉”,縣域內的教育分化和教育不平等問題亦愈發突出,所導致的縣域內階級再生產和階層固化問題也越來越明顯,而這還未引起學術界足夠的關注和重視。
教育公平關乎社會公平,文化再生產會導致社會(或階級)再生產。社會分化不僅只存在于大城市與鄉村之間,縣域內也存在階級分化,而且縣域內不同家庭背景和階層的兒童會具有差異化的文化再生產。從一定意義上來講,縣城和村莊不僅是地理空間上的劃分,還是縣域社會內階層屬性的區隔。基于此,立足縣域社會這一層面,本文對縣域內的縣城兒童家庭和村莊兒童家庭展開了對比研究,以探討縣域社會內的教育公平問題。關于縣城兒童家庭和村莊兒童家庭的界定,本文是以戶籍為核心指標,兼顧收入、職業和教育三個客觀標準。具體來說,縣城兒童家庭是指戶籍為城鎮戶籍,父母雙方一般至少有一方擁有專科及以上學歷,家庭年收入在15萬元及以上的家庭,父母(雙方或一方)大都為縣域內的體制精英(公務員、教師、警察、醫生等)和經濟精英(公司老板、職業經理、個體大戶);而村莊兒童家庭是指戶籍為農村戶籍,父母雙方的學歷一般都在高中及以下,家庭年收入在10萬元以下的家庭,父母雙方大都為農民或農民工。本文試圖探討的核心問題有:縣城兒童和村莊兒童各自具有怎樣的文化再生產圖景?具體表現是怎樣的?兩者差異化的文化再生產又是如何進一步塑造了縣域內的階層再生產?
二、理論視角與研究方法
1986年,布迪厄在《資本的形式》一文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文化資本理論,也被稱為文化再生產理論。布迪厄認為,文化資本有三種存在形態:身體化的形態,如體現在個體身上的知識、技能、教養和品味等文化產物;客觀化的形態,如書籍、字典、書法和繪畫等;制度化的形態,如制度化的文憑、學術資格等。[7]不同階級的家庭在文化資本擁有的質與量是不均等的,因而具有不同資本稟賦的家庭能夠傳承給子代的文化資本也各不相同。布迪厄在《區隔》一書中詳細闡述了文化資本的兩種獲得方式:第一種是家庭濡化,這是主要方式且具有決定性作用;第二種是學校教育[8]。也就是說,家庭和學校是文化資本兩個主要的再生產場域。但是,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影子教育”(或補習教育)在我國得到迅速發展,并且呈現愈演愈烈的態勢,開始由一、二線大城市向三、四線中小城市和縣域城市蔓延發展。[9]有研究指出,“影子教育”作為學校教育的補充,已經成為繼家庭和學校之外的“第三重”文化資本再生產機制。[10]換句話說,在教育市場化的背景下,教育培訓機構成為文化再生產的一個重要空間場域。在城鄉教育一體化的背景下,村莊兒童和縣城兒童在學校教育方面的差距在逐漸縮小,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兩者之間的教育鴻溝在逐漸彌合,相反卻有逐漸擴大的態勢,原因是縣域社會內的教育競爭已經從校內延伸到了校外、從課內擴展到了課外。因此,本文以家庭和教育培訓機構兩個關鍵的文化再生產場域為邏輯起點,闡釋縣城兒童和村莊兒童差異化的文化再生產圖景,進而說明縣域社會內的教育分化和不平等問題。
Y縣是位于鄂東北部的一個農業大縣,該縣大部分村民選擇進城務工經商來作為謀生手段,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農民工輸出大縣。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探討縣城兒童與村莊兒童差異化的文化再生產,故選取了Y縣內的一所縣城中心實驗小學A和一所鄉鎮中心小學B為田野個案,A小學和B小學在軟件和硬件方面的水平大致相同。從兩所小學中分別抽取了15戶學生家庭為研究對象。這30戶家庭的父母、老師以及小學生本人進行了面對面或線上(電話、微信、QQ)交流和訪談,并對訪談資料進行整理和編碼。
三、家庭教育:縣城兒童與村莊兒童異質性的家庭文化資本
家庭是孩子獲得文化資本的第一個場域,家庭濡化是一個更具隱蔽性的文化資本傳承方式。在家庭這一狹窄的空間場域內,孩子通過早期家庭社會化過程積累的文化資本對他們日后教育成就的獲得和人生發展具有關鍵性影響。縣城兒童家庭與村莊兒童家庭在家庭文化資本的數量和質量上具有較大懸殊。
(一)父母的文化教育程度
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與子女在學校的學業表現之間具有重要關聯。縣城和村莊不僅具有地理邊界上的分野,還具有社會階層和文化邊界上的分野。從訪談得知,15戶縣城兒童家庭的父母學歷大都在專科及以上,超過一半擁有大學本科學歷;相反,15戶村莊兒童家庭的父母學歷大都在高中及以下,其中還有5戶只擁有初中文化程度。父輩受教育程度的懸殊導致他們在子女學業輔導以及學校教育參與方面表現出明顯的分野:縣城兒童的父母表現出“全程參與,精準指導”;而村莊兒童的父母卻表現出明顯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和“缺場”。正如一位縣城兒童的母親所言:“孩子的學習是家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我自己也是一位小學老師,孩子的學習成績自然是我最關心的了,我也有能力輔導他。我經常和孩子的老師溝通,做到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的精準對接,以便高效且有針對性地幫助孩子提高學業成績。”(BRM-20170801)縣城兒童的父母多是縣域社會內的文化精英,有足夠的能力和充分的時間來參與和輔導孩子的學習。與此形成鮮明對比,一位村莊兒童的父親言道:“關于孩子的學習問題,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無助感,我家孩子的作業我根本就看不懂。我和妻子進城打工,孩子在老家和爺爺奶奶一起生活,老人們就更沒有能力輔導孩子的作業了。我也想孩子好好學習,考個好大學,日后吃個文化飯,不要像我們這樣辛苦。但確實客觀條件不允許,只能努力賺錢,爭取為孩子創造好一點的物質生活。”(NAP-20170801)村莊兒童的父母大都由于缺乏文化資本,導致在就業市場上缺乏競爭力。在鄉村勞動力過剩的背景下,為了生計,只能背井離鄉選擇進城務工經商,將孩子留守鄉村。所以他們在主觀和客觀上都沒有條件全程參與子女的學習輔導,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是“不在場”的。因此,擁有較多制度化文化資本的縣城兒童父母使其子女在學校教育體系中占據競爭優勢地位,而缺乏制度化文化資本的村莊兒童父母使其子女在學校教育體系中處于競爭弱勢地位。
(二)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投資態度和動機
父母對子女教育投資的態度和動機與其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具有重要關聯,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子女的學業成就。教育不僅可以傳授人知識和技能,還能形塑人的思維模式。正如貧困文化容易導致貧困延續和重復再生產一樣,受教育程度低的底層群體不但缺乏制度化的文化資本,更缺乏身體化的文化資本,容易形成一種底層思維模式,導致他們在子代的教育問題上容易采取一種急功近利的、消極狹隘的教育觀念。據訪談得知,在縣城兒童父母眼里,他們將子女的教育投資視為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或者視為父母應盡的責任和義務,這一點與城市中產階級父母的教育觀念相一致。在對子女的教育投資動機上,縣城兒童父母具有明顯的雙重動機:“最高動機”是希望子代超過父輩,實現向上社會流動;“保底動機”是要維持父輩在縣域內原有的優勢階層地位。正如一位縣城兒童的父親所言:“我是一名公務員,是靠讀書才能吃這碗‘國家飯’,在孩子的教育投資上我是毫不猶豫的,因為我認為這個社會不讀書是不行的,希望他們向更高的平臺去發展,起碼不能比我們這一代差吧。”(GXL-20170802)村莊兒童父母在子女教育投資態度上普遍遵循著嚴格的“成本—收益”原則,關注教育投資是否能帶來可預期的收益,而且片面追求經濟收益。孩子值不值得教育投資,關鍵的評判標準就是看孩子是否是“讀書的料”。值得一提的是,在城鄉二元分化的背景下,優質教育資源日益向城市聚集,導致鄉村兒童在與城市兒童的教育競爭上日益處于弱勢地位,進入重點大學的概率也在降低,靠讀書來獲得好工作的可能性越來越低,進而壓低了普通農民的教育投資回報率,從而動搖了他們“知識改變命運”的教育信仰。正如一位村莊兒童的父親說到:“我也知道讀書的重要性,但是現在靠讀書來找個好工作越來越難了,現在孩子讀書也讀不贏城里孩子了,我們村已經十幾年沒有重點大學的大學生了。如果他確實是‘那塊料’,我也會好好供他讀的,如果他確實不是‘讀書的料’,有那錢還不如攢著給他在縣城買個房實在,書嘛,讀個差不多就行了。”(WHY-20170802)父母對孩子教育的重視程度無疑會影響子女的學業表現和教育獲得。
(三)父母的教育期望
20世紀60年代末,在研究家庭背景對子女教育成就和職業獲得的影響方面,威斯康星學派最早將“教育期望”作為一個重要指標納入其中。[11]通常而言,父輩的受教育程度和社會經濟地位越高,對子代的教育期望就越高,從而會影響子女自身的教育期望以及學業成績和教育獲得。[12]縣城兒童父母和村莊兒童父母分屬縣域社會內的優勢階層家庭與弱勢階層家庭,無論在文化資本還是經濟資本方面都存在較大懸殊,從而導致他們對子女擁有截然不同的教育期望。縣城兒童父母對其子女普遍抱有高教育期望,正如一位縣城兒童的母親說道:“教育都是環環相扣的,上重點小學才更有可能上重點中學,上重點中學才更有可能考上重點大學,這樣才更有可能找到好工作。我要盡我最大的努力讓孩子上最好的基礎教育,每一個教育階段都不能落后。而且現在學歷升級了,光上大學還不行,要上重點大學才有用,單單本科學歷也不行,還需要研究生學歷。”(MAY-20170803)與此不同的是,村莊兒童父母的教育期望卻很低,正如一位村莊兒童的母親這樣說:“我沒有上過大學,當然希望孩子能上大學,本科專科都無所謂,只要是能考上大學我就已經很開心了,我們家族都沒幾個大學生,不過關鍵還是要看孩子自己爭不爭氣,我們也幫不了啥,主要靠他們自己。”(HFN-20170803)。
(四)父母自身的閱讀習慣和興趣愛好
父輩的閱讀習慣和興趣愛好是家庭文化資本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父母會通過身體力行的閱讀慣習以“潤物細無聲”的形式向子代傳承著文化資本。縣城兒童的父母大都受過良好的教育,屬于縣域社會內的“文化貴族”,他們一般擁有良好的閱讀習慣。父輩的這一閱讀習慣有意或無意地培養了子女的閱讀習慣。縣城兒童在“尊重知識、崇尚閱讀”的家庭氛圍的濡化下,會逐漸地積累身體化形態的文化資本。“我的媽媽是一位初中語文老師,她經常會在家閱讀一些文學和古詩詞方面的書籍,我也養成了良好的閱讀習慣。爸爸媽媽每天都有固定的時間陪我閱讀。語文是我的強勢科目,也是我最喜歡的科目。”(KXG-20170804)“我的爸爸在縣政府上班,他空閑時間喜歡看報紙和新聞,他書房里有很多政治和歷史方面的書籍,我經常去他書房找書看,爸爸有時候也會和我聊天,講給我聽。我很崇拜爸爸,受他影響,我從小就喜歡歷史和政治。”(WDP-20170804)除了閱讀以外,縣城兒童父母閑暇時間的興趣愛好如運動、看電影、旅游等,這些都有助于縣城兒童形塑良好慣習、增長知識和開拓眼界。相反,村莊兒童的父母大都文化程度較低,幾乎沒有什么閱讀習慣,即使是閱讀,也只是用手機瀏覽一些碎片化的信息,閑暇娛樂活動主要是玩手機、打牌、看電視、睡覺和閑聊等。“我爸爸書讀的不多,我認識的漢字都比他多。他閑的時候也就是玩手機、看電視或者打打牌啥的。平時的家庭娛樂也是各玩各的,相互聊的不多。”(WLG-20170804)更為關鍵的是,村莊兒童父母身上的這些“壞習慣”在榜樣力量的持續教化下被村莊兒童所身體化和結構化,成為村莊兒童與學校道德規范之間文化沖突的結構性根源。
(五)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投入,主要包括時間和金錢
布迪厄說過,家庭文化資本的有效傳承取決于兩個關鍵因素:一是家庭文化資本的存量,另一個是父輩(尤其是母親)的閑暇時間。[13]縣城兒童家長大都屬于縣域社會內的“有閑階級”。他們有充足的時間投入到子女的教育中去,包括輔導和檢查孩子的作業、陪伴孩子一起閱讀、為孩子安排和規劃課外補習等。村莊兒童大都屬于留守兒童,他們的父輩從事勞動和時間密集型的工作,工作強度大,持續時間長,而收入卻很微薄。負重前行的他們根本沒有時間和精力投入到子女的教育中去,在陪伴和教育子女方面表現出明顯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和“愧疚感”。“我的爸爸媽媽都進城打工去了,我留在老家和爺爺奶奶一起生活。我每個星期都會和爸爸媽媽打電話,雖然他們也會在電話里叮囑我要好好學習,但跟陪在我身邊時時刻刻督促我學習是沒法比的。爺爺奶奶年紀大了,指望他們輔導我學習那是更不可能了。”(FGW-20170805)研究表明,親子陪伴在孩子的學業成就、心理健康和慣習形塑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影響。[14]由于父母在孩子的童年成長中的“不在場”,勢必會影響村莊兒童在主流教育體系中的學業表現。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之間可相互轉換,文化資本的獲取離不開經濟資本的投資。顯而易見,縣城兒童父母會在子女的教育上有更多的資金投入,包括購買客觀化文化資本(書籍、電腦、文化用品等)、購買課外輔導、游學旅游等。相反,村莊兒童的父母在面對子女的教育投資上,普遍表現得“理性”和“精打細算”,一般只能滿足子女最基本的學習投資,并且遵循嚴格的“成本—收益”原則。
(六)父母與子女的代際互動
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不同會導致他們擁有不同的育兒理念,具體體現在與子女差異性的溝通方式上,進而會形成不同的親子互動模式。縣城兒童的父母一般會以一種更加平等的姿態與子女進行互動,在與子代的溝通中表現得更為平等和更具耐心,講究采用正向激勵(表現好會增加獎勵)和反向激勵(表現不好會減少獎勵)的方法;會充分尊重孩子內心的想法,凡事“商量著來辦”,有助于子女發揮自身的主體性和能動性,體現的是一種民主型的親子互動模式。“我爸爸媽媽從來不會打罵我,當我做錯了事情,他們會給我講道理,更多是一種說教的方式,而當我做的好的時候,他們會毫不吝嗇地獎勵我。”(PWH-20170806)相反,村莊兒童的父母在與子女的互動中容易走向兩個極端:一種是專制型親子互動模式,這類家長依舊奉行“棍棒出孝子”的傳統育兒理念,管教孩子具有明顯的限制性特點(說“不”)和強制性特點(粗暴對待);以個人的主觀意志安排孩子的一切,孩子沒有平等表達自我的話語權,當孩子與自己的意志相悖逆的時候,可能還會出現體罰;另外,這類家長在表揚自家孩子方面也表現的格外吝嗇。“我是過來人,聽我的肯定沒有錯,再說他們那么小,能懂個啥。我從來不當面夸獎自己的孩子,小孩子不經夸,容易驕傲。”(WKH-20170806)另一種是放任型親子互動模式,類似于“放養”的模式,對子女的教育采取自然成長、放任不管的方式,在親子陪伴和教育上表現出明顯的“缺場”。“我爸爸媽媽都進城打工去了,我從小就在家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我們平時打電話聊的最多的就是錢,家里沒錢了,他們就會打錢回來,幾乎不怎么關心我的學習情況和心理狀況。”(YDK-20170806)相關研究表明,民主的家庭氛圍、親子陪伴和科學的育兒方法等都有助于孩子的學業表現、身心健康和人格發展。毫無疑問,縣城兒童比村莊兒童擁有更好的家庭環境。
(七)父母與學校教育的互動
家庭文化資本的差異也會體現在父母與學校教育互動的頻率和質量上。一般來說,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和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傾向于主動參與到子女的學校教育中去。縣城兒童的父母在與學校教育的互動上表現得更加積極主動,而且溝通過程更精準和高效。“我會積極參加孩子學校舉辦的家長會等活動,這是增進對孩子學習情況了解的好機會,也是作為父母的責任和義務。我平時也會通過QQ和微信等經常和孩子的班主任和任課老師溝通。有時候接送孩子上學時,也會和孩子的老師聊聊。”(WGQ-20170807)村莊兒童的父母在與學校教育的互動上表現得更為被動,互動頻率很低,普遍存在著客觀“不在場”、工作繁忙、參與能力有限、主觀重視程度不夠等現實困境。“我常年在外面打工,沒有陪在孩子身邊,孩子留在老家上學。確實沒有和老師溝通的這個習慣和意識,有時候還是孩子的老師打電話跟我主動溝通,向我反映孩子在學校的情況,在這方面我確實感到挺慚愧的。”(FLP-20170807)學校教育的高效開展離不開家庭的密切配合,父母越頻繁地參與到孩子的學校教育中去,就對孩子在學校的學習和生活情況了解得越全面和清晰,家庭教育才能與學校教育更好地銜接,這樣更有利于孩子的學業表現和身心發展。
綜上所述,縣城兒童家庭屬于縣域社會內的優勢階層,家庭文化資本雄厚,從小在家庭場域內受到良好的觀念、慣習和品味等的濡化和熏陶,從而形塑了其與社會主流價值體系相吻合的文化慣習和價值認同,這樣他們在生產社會主流精英文化的學校場域內就很“如魚得水”,更能獲得“認可”。學校場域將他們的這種文化慣習予以合法化,使得他們在主流教育體系中獲得了競爭優勢地位。換句話說,由于身體化形態的文化資本方面的先賦性優勢,使得縣城兒童更容易在學校場域內獲得制度化形態的文化資本。擁有這種“象征性權力”使得縣城兒童在未來的人生發展中擁有更優勢的機會結構和發展預期,而村莊兒童的情況則剛好相反。
四、“影子教育”:縣城兒童與村莊兒童區隔的課余生活世界
隨著“影子教育”的盛行,教育競爭從課堂擴展到了課外,補習教育成為繼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之外的“第三重”文化資本再生產機制。調研發現,縣城兒童和村莊兒童具有區隔的課余生活世界。
(一)縣城兒童:“圈養”的課余生活世界
縣城兒童的課余生活大都是在教育培訓機構中度過,體現的是一種被“規訓”的童年。隨著各級教育部門關于中小學生“減負”政策的落地實施,孩子們的課余時間越來越充裕。因而安排和規劃好孩子的課余生活世界,讓他們度過一個充實而有意義的課余生活,成為縣城兒童父母一個重要的日常任務。為了讓自己的孩子在今后的教育和社會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不輸在起跑線上”,教育競爭的“戰線”從課堂延伸到了課外。家長(一般為母親)成為了縣城兒童課余生活世界的“經紀人”,替他們安排和規劃課余生活。縣城兒童家庭的日常生活圖景可以描繪為:一端是“忙碌而焦慮的家長”,另一端是“累并快樂著的兒童”。縣城兒童的父母一邊忙著自己的工作,一邊忙于為孩子甄別、挑選各種輔導機構和家教,忙于接送孩子于各個輔導機構之間,他們既焦慮又無奈,這儼然成為了縣城中一種流行的家長文化。“我也想讓孩子和自己都輕松點,可是為了孩子的未來那也是沒辦法的事情。其他可以耽誤,孩子的教育不能耽誤。這個社會競爭太激烈了,我周圍同事的孩子沒有不參加培訓班和找家教的,小時候吃點苦,長大了就可能少受點罪。再說現在孩子假那么多,不上培訓班,他就光玩手機和電腦了。”(YKD-20170810)縣城兒童的童年是脫離“自然”和“野蠻成長”的,他們絕大部分是在教育培訓機構及課外補習中度過了自己的童年課余生活。課外補習的方式主要有三種:參加教育輔導機構、請大學生家教和在職教師有償輔導。縣城兒童參加課外補習有利有弊:一方面他們被剝奪了自由發揮主體精神和“自然野蠻生長”的機會,“忙碌的童年”取代了“快樂的童年”;另一方面卻保證了他們課余生活的利用效率,積累了文化資本,提高了學習成績,有利于在學校主流教育系統和未來的社會競爭中獲得比較優勢地位。“每年暑假,我媽媽都會讓她單位同事的女兒給我補課,幫我補習數學和英語,姐姐是個大學生,我媽媽經常囑咐我要向姐姐學習,說姐姐是某985高校的研究生。”(PBW-20170810)“每到周末我都會去參加培訓班,剛開始的時候很反感。后來在那里交到了好朋友,主要是我的同學都去參加輔導班了,也沒有朋友陪我玩。還有,通過參加輔導班,我的英語成績確實提高不少,老師在學校還表揚我了,讓我找到了成就感。雖然有點累,但總體來說還是挺開心的。”(FBH-20170810)
(二)村莊兒童:“散養”的課余生活世界
由于有限的家庭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村莊兒童家庭屬于縣域社會內的底層群體。與縣城兒童被“規訓”的童年不同,村莊兒童度過的是一個“游戲”的童年。與縣城兒童“圈養”的課余生活世界不同,村莊兒童擁有的是“散養”的課余生活世界,其家庭呈現出迥然不同的日常生活鏡像:一面是“背井離鄉的忙碌家長”,一面是“留守和散養的兒童”。在訪談中得知,15戶村莊兒童家庭沒有一戶的孩子參加過任何形式的課外補習。這其中當然有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教育觀念的原因,但一個關鍵原因就是他們“匱乏”的家境、微薄的生活收入無法承擔不菲的課外輔導費用。“我和孩子他媽都是干苦力的,收入不高,哪能承擔得起孩子參加培訓班的費用,一個課時就要上百元,都快趕上我一天的收入了。我們還有兩個老人要養,開銷也很大,這方面確實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真是負擔不起。”(YLG-20170811)“放養”的村莊兒童的課余生活世界是在“游戲”中度過的。一方面,大自然成為了他們的“游樂場”,鄉土游戲陪伴他們度過了一個“快樂的童年”;另一方面,手機和電視成為了他們的“精神保姆”,虛擬世界為他們提供了一個新的“娛樂場域”,網絡游戲已經成為他們新的“精神家園”。對村莊兒童而言,鄉土大自然和電子產品有著特殊的社會價值和符號意義,它們承載了村莊兒童在課余生活中的社會互動和嬉戲方式,體現了一種特殊的社會化。“我放假可以做的事情可多了,我會叫上塆的幾個小伙伴一起去釣魚、捉蝦、摘梨子,還可以在家玩桌牌、丟沙包、斗雞啥的,好玩的多得很。”(GKY-20170811)“我有點宅,就喜歡在家看電視和玩游戲。最喜歡玩游戲了,我的游戲玩得可好了,現在玩的這個‘吃雞’游戲,已經玩到了王者。”(YKW-20170811)相對而言,村莊兒童雖然擁有了安排自己課余生活的自主權,能盡情釋放自己孩子般的天性,過一個“快樂的童年”,但也導致了自己在教育競爭中的弱勢累積,喪失了更多向上階層流動的渠道和機會預期。
綜上所述,受家庭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狀況的限制,村莊兒童被排斥在了課外輔導的場域之外,在客觀上維持和強化了縣城兒童和村莊兒童獲取教育資源的不平等現象。課余生活世界的區隔使得縣城兒童在獲得優質教育資源上有優勢疊加效應。“影子教育”將未參加課外補習的村莊兒童排斥在階層流動的上升渠道之外,使得課外補習行為具有了隱匿性的階層再生產特征。縣城兒童和村莊兒童區隔的課余生活世界在相當程度上導致了縣域內階層流動功能的弱化。換句話說,對于在家庭教育中已經處于競爭弱勢地位的村莊兒童來說,缺乏“影子教育”這一有效工具使得他們在各級升學考試中節節敗退,最終難免被“淘汰出局”。
五、小結與討論
階層再生產主要是通過文化再生產來實現的。[15]家庭和教育培訓機構是除學校之外兩個重要的文化再生產空間場域,體現了文化資本的“雙重”再生產機制。由于縣城兒童與村莊兒童在家庭教育和“影子教育”上“雙重”不平等的文化再生產圖景,造成了縣域社會內的階層再生產。具體來說:一方面,由于家庭教育的先賦性弱勢和“影子教育”的區隔,使得村莊兒童在縣域教育競爭中紛紛以中途退學、升學考試分流等方式被“淘汰出局”,進而被排斥在縣域內優勢的社會地位和工作崗位之外,只能過早地進入了次級勞動力市場,延續著父輩的底層生活,成為“農民工二代”等;另一方面,由于縣城兒童在家庭教育和“影子教育”上“雙重”文化再生產方面的絕對優勢,他們成為了縣域主流教育體系競爭中的“勝利者”,更有可能獲得高教育成就,從而擁有較高的制度化文化資本。這種“象征性權利”使得他們順理成章地占據了縣域內優勢的社會地位及工作崗位,從而維持了父輩在縣域內原有的階層地位,成為“公務員二代”“教師二代”等“公家二代”。因此,縣城兒童和村莊兒童在家庭教育和“影子教育”上不平等的“雙重”文化再生產機制阻礙了縣域社會內良性、有序的階層流動,使得縣域內的社會階層趨于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