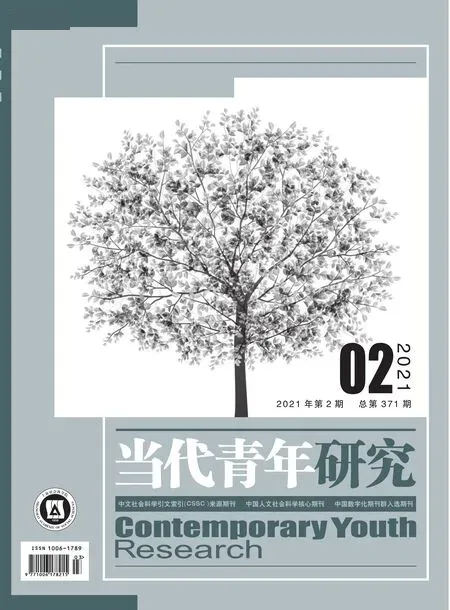家庭經營策略下的農村年輕女性家庭權力與角色嬗變
石 偉
(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女性社會地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引發長者權威與父權結構的動搖甚至瓦解。[1]在主流敘事話語中,年輕女性的角色和地位凸顯社會化的面向,家庭角色減弱。然而,家庭不僅是夫妻生活的私密空間,也是個體融入社會的基本單元。如何在主流話語中找回家庭敘事,理解年輕女性在家庭權力關系中的角色與地位,是性別研究的應有之意,也是厘清當前家庭發展動力與發展策略的有效路徑。
一、重回家庭:年輕女性家庭權力的再思考
(一)社會參與中的年輕女性社會地位建構研究
社會與家庭中的女性狀況是相互關聯的。女性的社會行為受家庭環境的影響,同時受到社會中的文化標簽、制度安排、資源稟賦塑造。[2]家庭對女性具有雙重功能,它既是女性自由喪失、地位失落的現實載體,又是女性追求平等、自由和發展的重要依靠。[3]已婚年輕女性脫離原生家庭,需要在家庭與社會的雙重領域中重新建構自己的角色與身份。從既有研究看,學界對年輕女性的家庭權力分析有兩種視角:家庭權力建構性研究與家庭權力嵌入性研究。
家庭權力建構性研究是在現代化進程中,年輕女性參與到社會結構和市場體系中,利用社會關系網絡建構起社會資本,以外在性力量支撐家庭地位。在研究路徑方面,主要集中在農業生產勞動參與、市場經濟參與和政治參與三方面。從農業生產勞動參與看,有研究通過考察南稻北麥的農業種植活動認為,不同的農業種植方式影響女性在家庭生產中的勞動參與,進而影響女性的經濟價值和家庭議價能力。[4]轉型期的被動介入特征使女性在家庭農業傳承中地位脆弱,新時代的女性對農業經營貢獻提出新訴求,營造了農業生產男女平等的追求。[5]進入有機農業生產后,女性勞動者經濟收入進一步提升,獲得部分家庭決策權,增加其社會資本。[6]從市場經濟參與看,在資源決定論的解釋下,女性非農化就業提升女性的經濟獨立能力,在家庭權力關系中獲得議價權。[7]此外,政治參與亦是女性建構社會地位的有效路徑。宏觀層面,“婦女能頂半邊天”已成為女性政治參與的現實表征。[8]微觀層面,農村女性政治參與制度化、渠道多元化,提升女性村莊地位。[9]故而,女性通過尋求社會資源獲得經濟地位,提升在家庭中的話語權,形成資源主導的家庭權力關系。
(二)家庭結構中的年輕女性家庭權力嵌入性研究
家庭權力嵌入性研究強調在傳統文化習俗、村莊道德規范和家庭倫理的束縛下,女性社會身份缺失,以依附于男性獲得家庭角色與身份認同。在研究路徑方面,主要分為性別說與文化說。首先,性別視角形成女性的社會認知和社會性別。瓊·W·斯科特將社會性別定義為:基于性別差異基礎之上的社會關系集合,是權力關系的表現形式。[10]受社會性別理論影響,部分女性試圖建構反向依賴性,即在夫妻親密關系中女性不借助男性親人的幫助獲得事業成功,成為家庭經濟的主要擔負者,改變了家庭的親密關系。[11]其次,文化說。中國傳統倫理觀念為女性建立了“三從四德”的道德要求,女性被捆綁在家庭之中。[12]農村女性遵循“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亡從子”的倫理,過得安然、從容、有意義,獲得人生意義。[13]一旦進入夫家關系網絡,年輕女性需要嵌入新的社會關系與家庭關系。返鄉年輕女性憑借承擔的家庭責任、為家庭作出的貢獻,獲得婚姻主導權。[14]空間的流動與變化,使傳統社會賦予的女性角色在資本市場中經歷著沖突與抗爭,沖擊著我們的女性認知。回歸“宿命”,女性個體的流動性被消解于鄉村社會,并未對父權形成根本性沖擊。[15]單系父權觀念對女性的影響是深遠的,女性依靠自身的依附性角色嵌入家庭結構。家庭權力嵌入式視角沿襲西方自由平等觀念和公民社會的民主理念,主張女性的獨立自主與權力平等。
(三)返回家庭:年輕女性家庭角色與權力嬗變的研究進路
建構性研究視角主張女性的社會參與,在市場參與中建構經濟資本,從而獲得家庭中的談判權與話語權。嵌入性研究視角是基于家庭結構的文化基礎,強調女性對父權的遵從,以其家庭角色的依附贏得社會認同。這兩種研究導向是二元對立的,皆以女性的角色沖突為基礎,旨在回答年輕女性通過何種方式獲得身份與地位的問題。但是這面臨兩個問題:一是側重性別角色和經濟資源稟賦,缺少對女性參與的主動性認知;二是缺少生命歷程視角,未注意到個體生命發展周期中的角色與任務的階段性。
年輕女性家庭權力是指其在家庭結構中的權力位置。這需以家庭為研究對象,在家庭成員互動的結構性關系中展現。本研究的問題意識是為何年輕女性婚后其社會性角色和社會關系退化并轉向家庭角色時,反而在家庭權力結構中擁有很高的位置。筆者試圖從家庭經營策略視角,為年輕女性的這一轉向及其家庭權力作出解讀。探究在家庭目標、家庭分工以及代際關系等方面,年輕女性行為策略背后的個體、家庭與社會意蘊,以此理解年輕女性的社會地位。筆者以皖南P 村、蘇南G 村、鄂北L 村和川西Q 村的田野調研為經驗支撐。4 個村莊分散在全國各地,其村莊社會結構、人地關系、距市場距離與經濟發展水平不一,村莊中大量的年輕女性婚后在家生活不工作,或選擇顧家就近的簡單工作,為本研究提供了一致性的經驗基礎。
二、面向家庭:年輕女性家庭權力的實踐表征
(一)年輕女性社會地位與家庭角色的關聯悖論
從經驗特征看,年輕女性返回家庭有雙層蘊含。第一層是年輕女性從外地打工回到村莊生活,失去經濟獨立的能力;既有私人性社會關系不再維系,出現社會身份“死亡”。第二層是年輕女性全面回歸家庭,以家庭生活為主,個人嵌入家庭結構。陳鋒認為,農村女性賦閑在家經濟上依附男性群體,卻獲得很高家庭地位是悖論現象。[16]誠如所指,當年輕女性失去獨立能力,嵌入到家庭結構之后,失去話語主導權和談判權。但是,當年輕女性婚后選擇主動退出社會交往回到家庭時,其承擔的只是家庭角色,并未承擔過多家庭任務與家庭工作。如安徽蕪湖P 村王某,女,26 歲,嫁到P 村育有2 子。2012 年結婚前,王某在外地打工,結婚后在家帶孩子,沒有外出務工。丈夫楊某為P 村治保主任,是家中獨子。公公婆婆在家承包土地,從事農業種植。丈夫的工資僅夠兩人日常生活性開支,公婆也會日常給予一部分支持。王某認為,婚后生活很幸福。自己只需在家帶孩子,不用上班,老公和公婆都順著自己的意,也不管家中和村里的事情。同樣,在鄂北L 村二組,全組30 歲以下的男性青年14 人,已婚男性10 人,其中8 人妻子在家全職帶孩子,其余兩戶一戶離婚,一戶在縣城生活。皖南P 村四組,已婚年輕家庭6 對,婚后在家的年輕女子有5 人。
常規意義上,我們認為,家庭地位是通過社會角色和社會地位獲取,實現家庭地位提升。但悖論之處在于,雖然女性社會角色與社會地位缺失,但是家庭地位和家庭身份反而提高。在調研中,問起年輕女性的婚后生活,她們普遍感覺幸福指數高。父輩們也認為年輕女性生活幸福。“什么活都不用做,只在家帶孩子,家庭地位很高。”這背后表現的是年輕女性社會身份缺失,社會角色被家庭角色覆蓋,社會地位以家庭地位的方式展演,個體性角色被吸納進家庭結構性角色之中。在從社會角色到家庭角色轉換的過程中,女性失去社會關系網絡,獲得家庭地位。在家庭中,年輕女性以“無壓力的生活”和“家庭成員的尊重”展現其家庭權力。
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是其對社會地位的放棄。通過退出的姿態,女性家庭中其他成員家庭權力的讓渡,實現個人與家庭的耦合,從而形成耦合性權力。值得指出的是,耦合性權力的形成并不意味著年輕女性自主性的缺失。這種耦合到家庭結構中的家庭權力是家庭發展壓力下的經營策略,是年輕女性的自主選擇,結果形成家庭經營的“合作社模式”。合作社模式是在理性主義支配下,家庭是重視經濟理性的經濟核算單位,家庭共有財產成為制約家庭成員的途徑。[17]在倫理主義范式的研究者看來,中國農村家庭是一個道德共同體,其中道德倫理與利他主義是支配和約束個體行為的核心且有力的規范。[18]年輕女性的家庭角色選擇則是受到個體理性與利他導向的融合作用,既關涉個體生活觀念和價值追求,又依托家庭倫理與共同財產的積累。
(二)年輕女性家庭角色的耦合性支配與權力重構
社會性角色的退化并不代表著家庭角色能夠獲得支配性地位。但社會性角色退化為年輕女性的家庭參與和生活轉向提供了空間與機會。在傳統父權制度下,年輕女性結婚后面臨同樣的社會角色退化問題。在父權制主導的家庭結構中,年輕女性的家庭地位是較低的,故而有“小媳婦”的貶義性稱謂。傳統時期,年輕女性嫁入到婆家后會經營自己與兒子的小圈子,培育與兒子的緊密關系,以使自己在家庭結構中有嵌入性地位,這種家庭關系也被稱為“子宮家庭”。[19]如今,年輕女性家庭權力獲得的必要條件是耦合進家庭,包括縱向的父子軸家庭結構與橫向的夫妻軸親密關系。雙系立體耦合為年輕女性獲得家庭立足的社會資本,同時,耦合性體現出年輕女性社會角色退化的主動性,即出于家庭生活考量下的自我抉擇。這時,作為自我發展主體,年輕女性的階段性目標就已發生改變。經濟資源已經不再是年輕女性追求的目標,社會地位也不再吸引年輕女性的注意力,反而家庭的生活性與情感性成為年輕女性的追求,如川西Q 村張某。張某與丈夫在2017 年結婚。婚前,她在區里大型商場做化妝品銷售員。婚后,她暫時未出去工作,其丈夫在街道上供電部門工作。當筆者詢問其為何不再工作時,張某認為:“在家里可以和家里人生活在一起,公婆在附近廠里上班且收入不低,家庭收入足夠基本生活,不用愁。”
縱向家庭結構的耦合為年輕女性承擔家庭角色提供經濟資本的支持,但是,年輕女性嵌入到父子軸的聯合家庭結構時,年輕夫妻小家庭的角色和地位是被聯合家庭包裹的。以鄂北L 村九組為例。全組35戶145 人,年輕夫妻結婚后與父代未分家的有31 戶,村內的人情往來以聯合家庭為單位,隨禮金也是以父輩的名義為主,子代不會參與社會關系的建構。子代小夫妻之間的朋趣關系網絡也以男性為主,女性不會刻意維護或建構新的社會關系網絡。由此可知,雖然是家庭成員的一份子,年輕女性在村莊社會中的生活面向已然發生轉變,不再參與社會性關系網的編織與建構。因此,年輕女性表現出先天性社會資本弱化,后天建構性關系缺失。
橫向家庭耦合為年輕女性的家庭參與提供情感支持與經濟保障。現代家庭更加注重情感性需求,家庭鏈接紐帶是多面性的,不再是以往的道德維系與經濟扶持的單向度面向。[20]在橫向夫妻軸中,家庭分工不再是傳統的“內外有別”父權制,而是趨向“男主內,女主外,平等分工”的新形式。在男女社會分工平等參與的情況下,女性失去了參與市場經濟活動的機會。沒有經濟自主能力,女性無法獲得經濟收入,在經濟上需要依靠丈夫。但是,在當下的少子家庭結構中,經濟上女性對男性的依附是較弱的,娘家也平等地參與到對小家庭的經濟支持中,女性的經濟依附是多元的。因此,男女兩性之間的經濟地位不僅依靠自身的經濟收入能力,而且依靠著其原生家庭或多種途徑的經濟輸送能力。
三、經營家庭:年輕女性家庭權力建構的動力機制
根據《農業大辭典》定義,家庭經營是指以家庭為單位,運用自己的生產資料,為達到一定經濟目的,組織生產經營活動,承擔經濟風險和責任的經營方式。[21]家庭經營策略是家庭經營的行為策略。筆者認為,理解家庭經營策略有三層蘊含:一是它以家庭為經濟和社會活動的基本單元。以家庭為單位就需要配置家庭勞動力和利用家庭資源。二是它建立在經營性的目的之上,經營性目的就意味著家庭經濟或社會行為是以再生產為目的的,強調利用家庭資源實現家庭積累,提升家庭再生產能力。三是它強調行為的策略性,即追求家庭資源配置的優化,實現家庭效益最大化。
其一,家庭發展壓力成為年輕女性回歸家庭的需求動力。在家庭經營策略行為指向下,為追求家庭再生產和家庭積累,作為家庭資源組成部分的年輕女性,根據家庭目標、家庭任務調適自己的行為。面對城市化進程中的發展壓力,如進城買房、子代教育、父母養老,子代家庭能夠調適家庭結構,依靠家庭內部成員的合作,實現家庭多重發展目標,展示家庭的活力與韌性。[22]年輕女性回歸家庭是家庭經營的策略化行為選擇,以經營聯合家庭經營的方式實現家庭成員內部有序分工。
其二,家庭資源優化配置與家庭經營策略最大化成為年輕女性回歸家庭的經濟動力。家庭經營策略是以家庭統合為基礎的家庭分工。在鄂北L 村,當地形成規模化的西瓜種植產業,同時衍生出諸多西瓜代辦群體(即西瓜中間商)。因為牽涉信任問題,代辦的運作是以家庭規模為限度的。通常情況需要父子在外聯系瓜源、照顧西瓜裝車,中年婦女負責在家燒飯處理瓜販子的飲食生活。單靠中年女性即婆婆是難以完成農忙時的日常生活,需要年輕女性參與家庭勞動,比如照料家庭其他事務。在其他地區,一般的農村家庭中父母兩人相對年輕,他們需要完成農業生產或者參與市場勞動,這時年輕女性需要擔任照料小孩的任務。年輕女性是家庭資源社會化運作的載體,也是社會關系的有效聯結紐帶。關系資源的利用與女性家庭角色是相輔相成的,需要女性在社會交往中充分展現其家庭角色面向,以“婆家人”的身份動員和利用自己的先天性關系資本。在家庭資源效率最大化配置的驅動下,年輕女性參與村莊社會活動時,不是以個體角色出現的,而是以家庭角色的身份參與。家庭統合式經營其經營單位不是個體的小家庭,而是聯合家庭。它強調家庭代際和代內的雙重聯合,形成家庭結構擴大化。
其三,年輕女性身份特質為家庭再生產合力經營體系提供資源補充。在經營家庭經營策略行為中,年輕女性以其自身的性別特征和身份特征參與到家庭再生產的合力經營體系中。在家庭結構方面,家庭經營策略的耦合機制核心在于代際間的資源合力與夫妻間的情感連接。縱向代際間的資源合力,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父代家庭以強有力的收入為子代家庭提供經濟支持,從資源上將年輕女性吸附為依賴家庭,依賴婆家;二是娘家資源的輸送亦成為女性在婆家以休閑姿態生活的關系資本。橫向層面的夫妻親密關系創造了心理的依賴和情感的歸屬。在現代社會復雜再生產的家庭發展壓力下,經營家庭的策略行為,為每位家庭成員提供家庭參與的機會,年輕女性有了平等參與機會與空間。家庭合力的達成,需要家庭成員的相互配合。在以解決家庭事務、助力家庭發展的行為與互動中,年輕女性即使賦閑在家,也可以為家庭貢獻力量。
四、年輕女性家庭權力重塑的社會基礎
年輕女性以賦閑性和生活性的姿態在家庭中獲得家庭權力,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它離不開當前女性在婚姻市場的優勢地位、農業的排斥、家庭與村莊的保護。具體而言:一是雙系婚姻、獨生子女家庭結構與女性占優勢的婚配市場是年輕女性在家庭中能以休閑性姿態生活的根本保障;二是農業生產對年輕女性的排斥減輕女性家庭責任;三是村莊社會結構漸趨松散為女性的“不作為”提供保護性話語。
(一)雙系婚姻模式為年輕女性回歸家庭提供保護性力量
提起女性社會地位和家庭地位首先受到婚配市場的結構性壓力影響。在男多女少的婚配市場中,女性有天然的優勢。特別是處在農村地區的年輕男性群體,處于婚姻的低洼地帶,受到來自全國性婚配市場的擠壓,能接觸到的女性資源相對緊缺。在農村年輕人的婚姻關系中,女性處于婚配主導權,決定著婚變。[23]在鄂北L 村二組,30 歲適婚男性青年未找到女朋友的占到40%;在川西Q 村三組,年輕夫妻離婚有4 對。離婚成為女性主導自己家庭地位的否決權。當年輕女性在家庭中地位不高時,或得不到很好對待時,便會以離婚為要挾。
婚姻的另外一種保障則是母系家庭進行的資源輸送和資源傳遞。受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當前結婚的年輕人多為獨生子女。獨子化或者少子化家庭結構下,年輕女性成為家庭資源的傳遞者,擁有與男性同等的代際繼替地位,在婚姻方式上演變為“并家”的雙系婚姻。新的婚配形態減弱傳統單系嫁娶婚姻下的倫理性和規則性約束,弱化家庭結構的規則面向,強化了女性在家庭傳承中的重要性。在并婚式的新家庭形態中,橫向的夫妻關系是主軸,縱向的親屬網絡則需雙系并重。[24]雙系的親屬關系,從表面上看是提升小家庭在家庭結構中的地位,但從家庭資源等方面看,實際上小家庭缺乏自我維持的能力,還必須依賴于雙系的父代家庭。一旦小家庭并入到其中一方的父代家庭結構中,那么另一方的家庭資源則成為聯合家庭的重要親緣資本。這時,夫妻中作為連接紐帶的一方便是資源鏈接的主導者,在家庭結構中享有相應的優勢地位。雖然近些年婚姻觀念有所改善,但是既有的婚姻形式仍是以男性單系家庭結構為主導,女性代際聯合實則是以平等話語和資源體量與男性代際聯合進行抗爭。抗爭的結果就是女性角色回歸家庭,女性在父權結構的家庭地位中有所提升。
(二)現代農業種植對年輕女性產生排斥性力量
通過文獻梳理可知,農業種植中的女性分工是衡量女性家庭地位的重要變量。[25]據筆者田野觀察,現代農業生產對年輕女性是排斥性的,具體表現在生產工具、種植結構與種植感官。恩格斯認為,導致男女地位不平等的起源是農耕文明中鐵犁的使用,它極大提高了男性地位。[26]牲畜、鐵犁等農業生產工具的駕馭需要足夠的力量,而女性在力量上是天然弱勢的。時至今日,農業生產工具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機械化和現代化的工具大規模使用,極大地解放了人力。但實際上,機械化的生產工具仍然對女性是排斥的,一方面農業生產的傳統文化觀念深入人心,對女性的農業生產參與是排斥的。另一方面現代的機械化操作,在機械操作的掌控能力、靈活性上,男性是優于女性的。在辛勞的農業種植和打工賺錢話語的比較之下,年輕女性對農業種植是排斥的。不僅如此,大部分年輕女性從學校到社會的生活經歷中就缺少務農的體驗,所以年輕女性自身對農業生產也是排斥的。
在農村家庭經營中,農業生產是重要的一環,年輕女性又是家庭成員結構的一極。傳統女性的依附性家庭地位,旨在配合丈夫完成農業生產,以自我剝削式的農業參與為其在家庭結構中贏得微弱的話語和地位。現代年輕女性則是以不參與的形式否定其農業生產附屬者的身份,在男女關系上趨向于平等地對話與溝通,農業生產成為基于男女性別特質的家庭分工。在農業生產上摒棄女性的附屬性地位,這其中有農業生產的各環節對年輕女性的排斥,也有年輕女性自身對農業的排斥。無疑,年輕女性的不參與特性為其家庭回歸提供了平等對話的空間與機會。
(三)社會結構的松散化為年輕女性提供寬松的村莊環境
隨著行政村一級單元的擴大化與人口外流的加劇,村莊社會結構已不再是原來彼此相互了解的熟人社會,而是成為了帶有區隔的半熟人社會。[27]半熟人社會內,村民們雖然生活在共同的物理空間,人與人之間彼此認識,但是互動交流趨向于工具理性,社區整合結構松散,村莊氛圍寬松。半熟人社會中社會結構的松散化,意味著村莊社會內部村民之間的連接紐帶沒有那么緊密,家庭之間保持著相對理性,家庭內部保持著生活的私密性和個體性。在相對松散的環境中,即使女性退出村莊生活,村莊社會內部也不會產生非議和排斥性話語。這種社會結構為年輕女性社會性退化和家庭賦閑提供寬松的輿論環境,年輕女性可以自主退出建構型關系網絡。甚至在家庭的保護性結構中,年輕女性不用為了獲得村莊社會資本和道德話語而在村莊公共舞臺中表現出符合社會需求的“賢妻良母”角色。在松散的社會結構中,村莊社會趨向個體化,公共性較弱,個體與村莊社會勾連方式較為單一,個體通過家庭獲得生命的價值與意義。所以,在松散的社會結構下,年輕女性家庭權力的塑造既缺少來自村莊結構性張力的束縛,又有村莊參與環境中家庭的紐帶式吸納。
家庭是社會活力的微觀基礎,家庭的能動性在于家庭為個體提供的價值支撐和倫理支撐。[28]在經營家庭的策略行為驅使下,年輕女性選擇回歸家庭角色,淡化社會角色。婚后回歸家庭的行為,是年輕女性放棄其社會身份和社會性參與,轉而參與家庭經營,參與村莊社會交往的行為。這既不同于年輕女性為獲得家庭權力而利用社會資本和經濟能力構建社會地位的行為,也不同于年輕女性嵌入到父權家庭結構中的依附式家庭地位的行為。年輕女性承擔家庭角色、回歸到家庭生活的行為,旨在說明年輕女性在家庭統合型經營形成合力的策略下,形成家庭發展的代際合力。年輕女性主動性放棄其經濟發展權力,看似從自主發展走向被家庭約束,實則是獲得新的家庭權力和社會身份,成為“地位很高的人”。對女性個體而言,年輕女性開始追求家庭結構的完整與家庭生活的情感滿足,是個人能動性的表現。對于家庭結構而言,年輕女性的家庭轉向是單系的父權式聯合家庭走向雙系聯合家庭,在雙系父代資源的支持下,小家庭被裹挾進父代家庭結構中,失去發展的自主性和能動性。值得注意的是,年輕女性的耦合性家庭權力是暫時性的,它是家庭特定生命周期中年輕女性家庭權力的社會展演。一旦當子代能夠托管,此時年輕女性則面臨兩種路徑抉擇,繼續以家庭角色的身份追求生活性和家庭性面向,或走向社會追求個體發展,建構社會地位。無論哪種抉擇,都將對家庭結構與家庭關系產生新的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