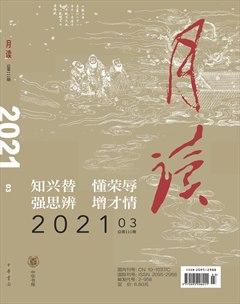《孔叢子》選讀
2021-04-16 15:57:16
月讀 2021年3期
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于察。察之之術,歸于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言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刑論》)
曾子問審理獄訟的方法。孔子說:“大的原則有三個方面:治理百姓一定要寬宏,對待百姓寬厚的方法在于體察民情,體察民情的根本在于義。因此,聽取訴訟卻不寬容是擾亂法紀;有寬容之心卻不體察民情是輕慢法紀;體察民情卻不合乎道義,斷案就不公正;裁決不公,百姓就會有怨恨。所以,善于裁斷的人審理訴訟時不會偏離訟辭,詳察訟辭而不脫離實情,以實情決訟而不違背道義。《尚書》說:‘(定罪的時候)要上下比照其罪行,但不能錯亂訟辭。”
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為之奈何?”對曰:“茍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矣。”(《公儀》)
魯穆公問子思說:“我們魯國可以興旺發達起來嗎?”子思回答:“能啊。”魯穆公又問:“那該怎么做才行呢?”子思回答:“如果您與大夫們能夠仰慕周公、伯禽的治國方針,推行他們的政治教化,大開惠民之門,杜絕個人的私利,對百姓施行恩惠,以禮結交鄰國,那么國家很快就會興盛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