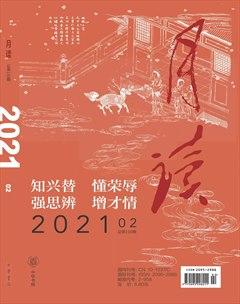牛年話牛
孫麗麗

小時(shí)候生活在農(nóng)村,對牛再熟悉不過了。牛是兒時(shí)的伙伴,牛是大人勞作的幫手,牛總能喚起我們對童年美好的回憶。牛是一種能與人進(jìn)行心靈溝通的動(dòng)物,它見過人間冷暖,感受過人類真情,它會流眼淚,有靈性又有情感。
“朝耕及露下,暮耕連月出”,老牛一生是辛勤的象征。“牛”是個(gè)象形字。早期的牛字就是牛頭,突出了牛角、牛耳的特征。牛是六畜之一。我國早在五六千年前就開始馴養(yǎng)牛了,它是中華民族農(nóng)耕文明不可缺少的角色。
牛,詞典中的解釋為身體大、力氣大、供役使。除此之外,它給人的印象是老實(shí)、忠誠、聽話、賣力、能吃苦。這種本性是絕大多數(shù)動(dòng)物都無法相比的。魯迅曾在詩中贊揚(yáng)那些鞠躬盡瘁的人是“俯首甘為孺子牛”。
牛有溫順的一面,也有倔強(qiáng)的一面。形容一個(gè)人忠于職守、兢兢業(yè)業(yè)是“老黃牛”;形容一個(gè)人固執(zhí),則說他有“牛性子”“牛脾氣”。
《左傳·哀公十七年》說:“諸侯盟,誰執(zhí)牛耳。”后來,人們把“執(zhí)牛耳”引申為在某一方面居于領(lǐng)導(dǎo)地位。
牛還被用于戰(zhàn)爭,如史籍中所記之“火牛陣”。火牛陣是戰(zhàn)國時(shí)期齊將田單發(fā)明的戰(zhàn)術(shù)。燕昭王時(shí),燕將樂毅破齊,田單堅(jiān)守即墨。公元前279年,燕惠王即位,齊將田單派人向燕軍詐降,使其麻痹大意,隨后在夜間用千余頭牛,角上縛兵刃,尾上縛葦灌油,以火點(diǎn)燃,火牛前沖,其后是五千齊國勇士,最終燕軍大敗,田單陸續(xù)收復(fù)七十余座城池。
牛在古代中國,一則用于耕田,二則用于祭祀,而耕田和祭祀恰恰是古人物質(zhì)生活和精神信仰的核心內(nèi)容。《漢書·魏相丙吉傳》中記載了_一則“丙吉問牛”的故事。西漢宣帝時(shí)期,丞相丙吉外出,遇到行人斗毆,路邊躺著死傷的人。然而,他卻不聞不問,驅(qū)車而過;屬下感到很奇怪,但沒有追問。過了一會兒,丙吉看到老農(nóng)趕的牛步履蹣跚、氣喘吁吁,立刻讓車夫停下,并上前詢問緣由。下屬更加不解,便問丙吉為何如此重畜輕人。丙吉回答說:“行人斗毆,有京兆尹等地方官處理即可,我只要適時(shí)考察其政績,有功則賞,有罪則罰,這樣就可以了。丞相是國家的高級官員,所關(guān)心的應(yīng)當(dāng)是國家大事。如今是春天,天氣還不太熱,如果那頭牛是因?yàn)樘鞖馓珶岫ⅲ敲淳驼f明現(xiàn)在的氣候不正常,如此則與國計(jì)民生有關(guān)的農(nóng)事勢必會受到影響。所以,我問了牛的事。”這個(gè)故事既表明了丙吉的為官之道,又從側(cè)面反映了牛對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重要性。
《禮記·曲禮》中說:“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脂肥,羊日柔毛,雞曰翰音,犬日羹獻(xiàn)……”可見在古代祭祀中,牛的品級最高。《曲禮》又記載“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所以,在古代社會,只有天子、諸侯和大夫才有資格享用牛牲。
《詩經(jīng)·小雅·大東》:“維天有漢,監(jiān)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bào)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出現(xiàn)了有關(guān)織女、牽牛星宿的記載,這也就形成了后來的牛郎織女的傳說。
《后漢書·臧官傳》中有“奉牛酒以勞軍營”的記載,牛酒不是一種酒的名字,而是古代用牛和酒作為賞賜、慰勞和饋贈(zèng)的物品。司馬遷《報(bào)任安書》開篇便說“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牛馬走”是指“奔走于牛馬之間”掌管牛馬的仆人,以后便用作自謙之詞,如同說“敝人”“鄙人”。
牛,確實(shí)造福了百姓,人們也忘不了牛。弘一大師詩云:“憶昔襁褓時(shí),嘗啜老牛乳。……念此養(yǎng)育恩,何忍相忘汝。”《南史》中記述了陶弘景畫牛明志的故事:南齊永明十年(492),陶弘景脫朝服于神武門,上表辭謝。梁武帝時(shí),屢次下詔禮聘,陶弘景都不肯出山,并畫了兩頭牛:一牛散放于水草間,自由自在;一牛頭戴金籠頭,被人拉著韁繩,又用棍子驅(qū)趕。梁武帝看到畫后笑著說,此人是不會出來幫我做事了,我豈能強(qiáng)人所難。
著名畫家李可染先生的畫齋稱為“師牛堂”,他畫了許多關(guān)于牛的精品佳作,比如《牧牛圖》,圖中牧童騎著老牛在春天里緩緩行走,背景是煙雨遠(yuǎn)山。說起畫牛,傳說東晉王獻(xiàn)之應(yīng)桓溫之請畫扇,因落筆有誤,就勢畫成一頭牛,并題《檸牛賦》于扇。我國流傳至今最具代表性的牛畜圖,當(dāng)數(shù)唐代宰相韓混的《五牛圖》,這也是他僅存的一件畫牛真跡。五頭牛神態(tài)各異,呼之欲出,充滿著濃郁的鄉(xiāng)土氣息,被譽(yù)為“神氣磊落,希世名筆也”。清乾隆御題曰:“一牛絡(luò)首四牛閑,弘景商隋想像間。舐齙詎惟夸曲肖,要因問喘識民艱。”
說起“牛年大吉”一詞,也是頗有淵源。《周易》中有許多有關(guān)“牛”的卜辭,凡是得“牛”的便是“吉”,如“童牛之牿,元吉”(用木架架住公牛的角,大吉大利)、“畜牝牛,吉”(飼養(yǎng)母牛,必獲吉祥)。
2021年是辛丑年,正所謂“丑時(shí)春到戶,牛歲福臨門”,讓我們在牛年勤勤懇懇做事,踏踏實(shí)實(shí)做人;多一分耕耘,就會多一分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