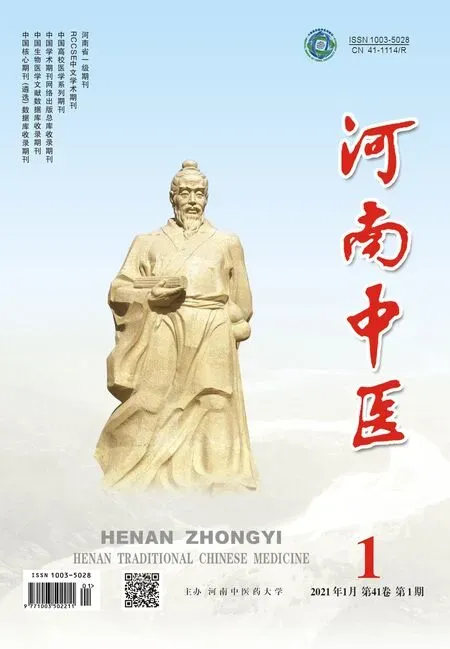和法在糖尿病中的運用
周雨桐,倪青,索文棟
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北京 100053
和法為中醫八法之一,張仲景所作《傷寒雜病論》雖未明言和法,然其所制之方、所用之法多陰陽互調、寒溫并用、補瀉兼施,將和法貫穿其中。糖尿病證候復雜,與張仲景和法作用機理相應。筆者不揣淺陋,從糖尿病常見證型出發,探析張仲景和法在糖尿病治療中的運用。
1 和法求源
和之提出始于西周,“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說文解字》言:“‘和’者,平穩、和緩;協調,關系好,均衡;和,相應也。”傳統和文化以儒家為主體,強調事物之間的協調與統一[1]。隨著社會的進步,《黃帝內經》等醫學著作相繼問世,中醫學理論形成。《黃帝內經》認為,百病皆生于陰陽不和,“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兩者不和,若春無秋,若冬無夏,因而和之……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故而提出了“損其有余,補其不足”的治療大法,以期恢復“陰陽和合”的平衡狀態,為和法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礎。至東漢張仲景所著《傷寒雜病論》,對和法進行了發展和充實,將其應用于臨床。后世醫家對于張仲景所述和法的內容認識不同[2]。清代程鐘齡在前人基礎上,提出了“汗、吐、下、和、溫、清、消、補”八法,認為“傷寒在表可汗,在里可下,其在半表半里者,唯有和之一法,張仲景小柴胡湯是也。”即為“和解”之法,屬于“狹義和法。”用于治療邪在半表半里、臟腑氣血不和之證。也有一些醫家認為,張仲景六經辨證以陰陽為總綱,認為疾病的本質為陰陽失衡,治療疾病為恢復陰陽協調與平衡,如戴北山所說:“寒熱并用之謂和,補瀉合用之謂和,表里雙解之謂和,平其亢厲之謂和。”即“調和”之法,屬于“廣義和法”。“廣義和法”提綱挈領,“狹義和法”提出了具體的治則治法[3],兩者互為補充,應全面看待。
2 糖尿病病機
“糖尿病”一詞在古籍中并無論述,按其臨床癥狀,可歸為“脾癉”“消渴”“消癉”等范疇[4]。《素問·奇病論》言:“有病口甘者,病名為何?何以得之?岐伯曰:此五氣之溢也,名曰脾癉。夫五味入口,藏與胃,脾為之行其精氣,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此肥美之所發也,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內熱,甘者令人中滿,故其氣上溢,轉為消渴,治之以蘭,除陳氣也。”《靈樞·五變》言:“五臟皆柔弱者,善病消癉。”先天稟賦不足、臟腑功能低下或房事不節、勞欲過度,導致腎陰虧虛、燥熱內生;后天飲食不節,嗜食肥甘厚味,脾氣虧虛,脾不散精,清濁失司,聚濕成痰,氣機不暢,中滿日久,郁而化熱,導致絡脈郁滯;“百病皆生于氣”,長期情志不遂,肝郁氣滯,肝失疏泄,氣血津液不能正常輸布,聚濕成痰,化瘀阻絡。先天腎陰不足,后天脾胃失養,肝氣不疏,產生氣滯、郁熱、濕濁、痰瘀等病理產物。臟腑功能失常,病理產物堆積,機體功能紊亂為糖尿病形成的重要原因,臨床常見濕熱蘊脾證、肝郁氣滯證、肝胃郁熱證、胃熱陰虛證、腸道濕熱證、血脈瘀滯證等證型[5]。
3 和法在糖尿病中的應用
《素問·調經論》言:“血氣不和,百病乃變化而生。”張仲景在繼承《黃帝內經》理論基礎上,認為“陰陽失和,疾病乃起。”如“脈不和”“睛不和”“胃不和”“衛氣不共營氣諧和”“太過”“不及”等皆為“失和”所致,陰陽氣血失衡是疾病產生的重要原因。糖尿病亦是由于陰虛、氣虛導致燥熱、氣滯、痰濕、瘀血積于體內的一種“失和”狀態,臨床以濕熱蘊脾、肝郁氣滯、肝胃郁熱、陰虛燥熱、血脈瘀滯最為常見,治療應“觀其脈證,知犯何逆”,辨證運用和法治療。通過運用具有陰陽偏性的藥物,組成具有“調和”功效的方劑,調節人體的“失和”狀態,使機體“陰平陽秘”。
3.1 辛開苦降和脾胃《素問·生氣通天論》言:“味過于甘,脾氣不滿,胃氣乃厚。”過食肥甘厚味,影響脾胃運化,精微物質郁于血內,則血糖升高。可見,脾失健運是糖尿病形成的重要因素,濕熱蘊脾為糖尿病常見證候。脾胃同居于中焦,“太陰濕土,得陽始運,陽明燥土,得陰自安。”脾胃納化相得,燥濕相濟,中焦氣機調暢。對于肥胖型糖尿病患者來說,由于飲食不節致使脾胃升降失調,脾失運化,精微不化,聚為濁邪,“中氣失和,上下不通,陰陽錯位,水火失序,由此形成‘心下痞’。”癥見體型肥胖、腹型肥胖為主,口黏口甜等,治宜和中降逆,散結消痞,方選辛開苦降之半夏瀉心湯類[6]。半夏瀉心湯由張仲景所創,為治療“傷寒下后,心下滿而不痛”之痞,“氣味辛甘發散為陽,酸苦涌泄為陰。”“微苦以清降,微辛以宣通。”方中干姜味辛性溫助半夏散結消痞、溫中散寒;黃連、黃芩味苦性寒,瀉熱燥濕,順應胃腑通降。辛散陽藥與苦泄陰藥相合為用,調和脾胃升降,氣機和則諸癥消。口渴者加石斛、天花粉;困倦乏力者加黃芪;肥胖者加二陳湯。現代研究表明,半夏瀉心湯能夠均衡胃腸內分泌激素,改善胰島素抵抗,降低血糖[7]。
3.2 疏肝理氣和氣血《靈樞·本臟》言:“肝脆則善病消癉易傷。”《臨證指南醫案》言:“心境愁郁,內火自燃,乃消癥大病。”《醫學真傳》言:“消證生于厥陰風木主氣……風火相煽,故生消渴諸癥。”肝主疏泄,氣機調暢,推動營衛氣血運行,生命活動生生不息。“憂愁者,氣閉塞而不行”,若長期情志抑郁、大怒導致五志過極,肝失疏泄,氣機郁滯則見胸脅疼痛,津血不能正常輸布則血糖升高。治宜疏肝理氣,方選四逆散加減。四逆散原為《傷寒論》治療少陰陽氣郁遏,不能布達四肢之厥證。“調氣之藥,首重疏肝。”方中柴胡疏肝理氣、透達郁陽;枳實行氣破滯,芍藥苦泄通絡;甘草和中。柴胡升散為陽藥,枳實、芍藥苦泄為陰藥;柴胡、甘草辛甘化陽,助肝之用,芍藥、甘草酸甘化陰,補肝之體,苦溫相配、體用相協、陰陽相合,氣機調暢,津液運行恢復正常,則諸癥自消。臨床運用時可加香櫞、佛手增強疏肝理氣之功;若平素脾氣急躁、咽干口苦者,加梔子、牡丹皮、黃芩清熱瀉火;肝氣犯胃,噯氣反酸者,可加柿蒂、浙貝母、烏賊骨。四逆散為調肝理氣之方,后世在其基礎上所創的逍遙散、柴胡疏肝散也廣泛應用于糖尿病的治療中。
3.3 清瀉熱結和肝胃張景岳言:“肥者,味厚助陽,故能生熱;甘者,性緩不散,故能留中。熱留不去,久必傷陰,其氣上溢,故轉變為消渴之病。”平素陽盛,脾氣急躁之人,飲食不節,損傷脾胃,從陽化熱,而見肝胃郁熱。《素問釋義》言:“食肥則氣滯而不達故內熱,食甘則中氣緩而善留,故中滿。”內熱中滿則水谷精微郁積、血糖升高。胃熱亢盛者選大黃黃連瀉心湯,肝胃郁熱者宜用大柴胡湯清瀉熱結。《傷寒雜病論》曰:“胃中有熱,則消谷引食。”飲食失節,火毒內生,治以瀉火解毒,如《活法機要》言:“消中者胃也,熱能消谷,如其熱在中焦也,宜下之。”方選大黃黃連瀉心湯,大黃、黃芩、黃連苦寒,清瀉三焦火毒。大便不通者加芒硝;失眠、心煩者加梔子;肝郁者合柴胡疏肝散;濕熱內盛,胸脘痞悶者合厚樸三物湯、平胃散。現代藥理研究證實,大黃黃連瀉心湯能調節糖脂代謝,改善胰島素分泌,減少糖尿病并發癥的發生[8]。
素體脾氣急躁,肝火旺盛者,過食肥膩,釀生痰熱,中焦氣機不通則可見心煩、胃脘痞硬、嘔吐、下利或者便秘。宜以大柴胡湯清肝瀉熱,柴胡辛散疏肝理氣、半夏散結消痞;黃芩苦寒清瀉郁火,大黃、枳實蕩滌實熱;芍藥、甘草緩解止痛。辛開苦降,升降出入,無器不有。中焦熱結得清,氣機通暢,諸癥得愈。若熱邪盛,則減柴胡用量,加黃連、赤芍、牡丹皮清熱瀉火;“久病入絡”,可加三七粉、水蛭粉、丹參活血通絡,預防糖尿病并發癥的發生。現代研究表明,大柴胡湯能改善胰島素抵抗,對于肥胖型糖尿病患者效果較好[9]。
3.4 滋陰清熱和肺腎《靈樞·師傳》言:“胃中熱則消谷,令人懸心,善饑。”《癥因脈治》言:“多食易饑,不為肌肉,此燥火傷于胃,即中消癥也。”胃中燥熱,上灼于肺,肺氣不能通調水道,則口渴欲飲;胃火熾盛,飲食入于胃,食隨火化,消谷善饑;熱耗陰精,下焦不固,則小便頻數。肺胃熱盛,腎陰虧虛,方選白虎加人參湯、玉女煎加減。
白虎加人參湯為張仲景治療陽明熱盛津傷所設,石膏辛寒散熱,知母苦寒清熱滋陰,人參、甘草、粳米益氣生津,諸藥合用,清熱生津,使肺胃熱清,恢復正常通調水道、運化水液的功能。若津傷明顯,可加生地黃、麥冬、玉竹、天花粉滋陰生津,陰陽互根,滋陰亦可益氣。有研究證實,白虎加人參湯能提高胰島素敏感性,對于空腹血糖、餐后血糖、糖化血紅蛋白均具有良好的控制作用[10]。
若熱盛腎陰虧虛,則宜采用玉女煎加減。玉女煎是張景岳在《傷寒論》白虎湯基礎上加減所得,張仲景所立白虎湯治療陽明有熱之證,清熱以和胃。“熱邪不燥胃津,必耗腎液。”胃熱日久,耗傷腎水,水虧不能上濡則見口渴,故張景岳在此基礎上加滋養腎陰之熟地黃,配伍甘寒益胃之麥冬,金水相生;懷牛膝苦平,引熱與藥下行,諸藥配伍,以寒瀉熱,以甘滋陰,瀉火而不傷陰,滋陰而不留邪,補瀉相宜,陰陽恢復平衡。現代藥理證實,玉女煎能夠改善機體氧化應激,調節免疫功能,穩定各類糖代謝指標[11]。
3.5 清熱利濕和腸胃《素問·痹論》言:“飲食自倍,腸胃乃傷。”過食肥甘厚膩、膏粱之品,脾胃運化不及,甘者滿,肥者膩,肥甘之品釀生痰濁,日久濕熱互結,濕性重濁黏滯,下注大腸,則大便黏滯不爽,臭穢難聞;水谷精微不化,聚于體內則血糖升高,形體肥胖。治宜清熱燥濕,方選葛根芩連湯加減。葛根芩連湯為治療太陽表邪不解,濕熱之邪內陷陽明之下利。葛根為陽明經藥,辛涼清熱,《傷寒藥性賦》曰:“陽明之的藥,脾渴可解而胃熱能消。”黃芩苦寒,苦燥堅腸胃,寒涼清實熱;黃連“味極苦濃,療渴為最。”兩者清熱燥濕最宜。葛根與黃芩、黃連相伍,辛開苦降,清濁有序,使中焦氣機恢復調暢。若大便干燥難解,加大黃、芒硝、厚樸;便溏者加白術、茯苓、陳皮、澤瀉。研究證實,葛根芩連湯能降低血清炎性因子水平,改善胰島素抵抗,降低血糖[12]。
3.6 活血化瘀和血脈《金匱要略·驚悸吐衄下血胸滿瘀血病脈證治》言:“病人胸滿,唇痿舌青,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為有瘀血也。”《血證論》曰:“瘀血在里,則口渴,所以然者,血與氣本不相離,內有瘀血,故氣不得通,不能載水津上升。”瘀血是糖尿病發病過程中的重要產物。肝失疏泄,氣機阻滯,則血脈不通;脾主運化,過食肥膩,運化失司,痰濁內生,痰氣阻結,瘀血內生;“陰虛必血滯”,久病氣虛不能行氣,可致血行不暢成瘀。消渴日久,瘀血阻滯,則會產生一系列并發癥,若阻遏心脈,則胸痹心痛;上阻腦絡、眼絡則易中風、視物昏花;瘀血阻滯,精微不能布達四肢,則肢體麻木涼痛;瘀血日久,蘊毒成膿則發癰疽。治以活血化瘀以和血脈,方用張仲景桃核承氣湯加減。方中桃仁破血逐瘀;大黃、芒硝推陳致新;“血得溫則行”,桂枝辛溫,伍入大隊寒涼藥中,助桃仁活血化瘀;甘草和中、緩和藥性,諸藥寒溫并用,峻緩兼顧,共奏破血逐瘀之效。血糖控制不佳者加黃連;血瘀明顯者加牡丹皮、赤芍、鬼箭羽;以肥胖為主者加紅曲、荷葉;口苦、腹脹者可合大柴胡湯。現代藥理研究證實,桃核承氣湯能促進胰島素分泌,減輕胰島素抵抗,改善胰腺微循環[13]。
3.7 調暢身心和陰陽“一陰一陽謂之道,偏陰偏陽謂之疾。”糖尿病前期為糖尿病的未病階段,但其陰陽已失去平衡,在辨證治療的同時,應注重調和身心。《素問·上古天真論》言:“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張仲景在其基礎上提出“五臟元真通暢,人即安和。”平素心情舒暢,則臟腑氣機通暢,五臟安和,身體康健。《金匱要略·禽獸魚蟲禁忌并治》曰:“凡飲食滋味,以養于生,食之有妨,反能為害。”糖尿病多為飲食不節引起脾胃運化失司,臟腑功能紊亂,故應謹和五味,少食厚膩之品[14]。“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調和身心,才能恢復胰島功能,改善胰島素抵抗,做到“陰陽自和者,必自愈”。
4 小結
和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觀,也是中醫治法的精髓。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中對和法進行了完善,提出了“和合”“調和”的學術思想。糖尿病病機寒熱錯雜、虛實兼夾,分為濕熱蘊脾證、肝郁氣滯證、肝胃郁熱證、胃熱陰虛證、腸道濕熱證、血脈瘀滯證等證型,治療當運用和法辛開苦降、疏肝理氣、清瀉熱結、滋陰清熱、清熱利濕、活血化瘀,選用半夏瀉心湯、四逆散、大黃黃連瀉心湯、大柴胡湯、白虎加人參湯、葛根芩連湯、桃核承氣湯調整氣機、平調寒熱、補虛瀉實,并在藥物治療的基礎上注重飲食、運動,調和身心。謹和糖尿病病機,調整陰陽,使機體恢復“陰平陽秘”的狀態,“陰陽自和者必自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