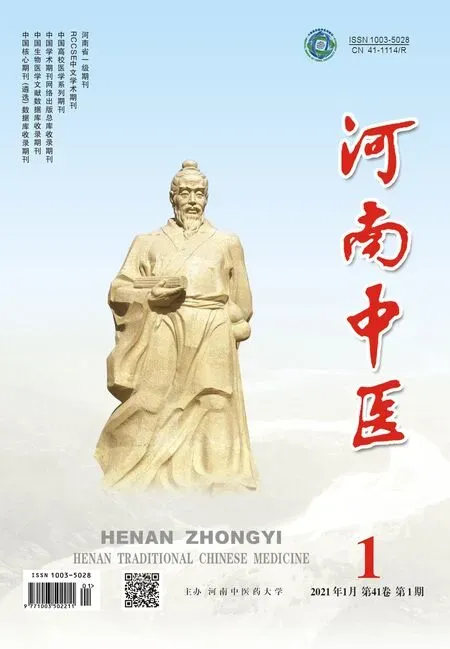腸道微生態與多囊卵巢綜合征發病機制的相關性*
安潔,周琴,薛毅芳
昆山市中醫醫院,江蘇昆山 215300
多囊卵巢綜合征(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PCOS)是一種發病多因性、臨床異質性、不可治愈性、進展性發展的內分泌紊亂綜合征,在育齡期婦女中PCOS的總體發病率為5%~10%[1],而在我國漢族育齡期女性中的發病率為5.6%[2]。在無排卵性不孕癥患者中的發病率高達30%~60%[3]。PCOS除了會造成生殖激素紊亂,還具有影響較大的遠期并發癥,且病因尚不十分明確,是女性生殖障礙疾病研究的重點及難點。
近年來,腸道菌群與多種內分泌疾病發病相關性研究不斷深入,證實了腸道菌群失調參與介導PCOS小鼠的慢性炎癥、胰島素抵抗、肥胖、高雄激素血癥等過程[4-6],有數據表明約41.7%的PCOS的患者常見有胃腸功能紊亂先于月經失調,其中一項臨床病例對照研究也發現,PCOS患者(包括肥胖、非肥胖)的腸道菌群失調率高于正常人群[7]。歷代醫家有云:“內傷脾胃,百病由生”“諸病不愈,必尋到脾胃之中”“百病皆生于氣”“升降出入,無器不有”“萬物之生殺,莫不以陰陽為本始也”等等,溯源PCOS的中醫病證、病因病機,無不與脾胃氣機升降失調、臟腑陰陽氣血失衡密切相關,治療上也賴于健運脾胃,燮理陰陽,而腸道微生態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中醫學的“中土思想”,以及“整體觀、系統觀、平衡觀、恒動觀”,二者理論內涵一致[8]。本文將從中西醫方面對其進行分述。
1 病因病機
PCOS病因復雜、高度異質,中醫認為其根本病機為本虛標實,脾腎虧虛,致臟腑功能失常、氣血失調,化生痰濁、血瘀等,引起生殖功能障礙。近年來,腸道微生態在中醫證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脾虛證、腎陽虛衰證、濕熱證、脾虛濕盛證等[9]。其中與腸道菌群密切相關的胰島素抵抗、代謝綜合征的中醫病機證候與PCOS的病機本質不謀而合[10]。研究者根據中醫理論,通過益氣健脾、化痰祛濕、補腎疏肝等理法,運用中藥復方或單體,改善患者的腸道菌群,修復受損的腸黏膜,調節胰島素的敏感性,促進代謝。可見二者共調共榮,共損共衰,現就其共性闡釋如下。
1.1 陰陽失衡,同為發病根本陰陽學說是中醫學基礎理論之一,不僅是自然界的根本規律,亦是萬物生長壯老已之根源。誠如“生之本,本于陰陽”“陰陽者,萬物之能始也”“人身病損,必先陰陽致偏”“人有陰陽,即為血氣……人生所賴,唯斯而已”“陰陽交則物生,陰陽格則物死”,理論種種,古圣先賢,百病千方,無不遵循“四時-五臟-陰陽-氣血”以調治之。月經病,亦如此。月經,常候也,調候其一身之陰陽愆伏,知其安危,故每月一至,太過或不及,皆為不調。如陽太過則經水先期而至,陰不及則經水后期而來,亦有乍多乍少,斷絕不行者,崩漏不止也,此皆由陰陽盛衰所致。PCOS臨床多態表現之根是腎陰陽失衡,累及他臟,變生多癥[11]。夏桂成[12]臨癥常言“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為期”,治療PCOS常于靜中求動,降中求升,以燮理陰陽為關鍵。腸道微生態之穩態是涵蓋物質、能量、基因間的動態平衡,也體現了陰陽消長、互根轉化理論。一般情況下與宿主、環境相互依賴、相互作用,保持“互利共生”的相對平衡狀態。若平衡被打破,腸道中有益菌、有害菌之間制約、消長失衡,則出現腸道菌群結構或數量、種類異常,致使微生態失衡,代謝性疾病產生。研究證實,陰陽失衡患者與正常人的腸道菌群存在顯著的差異[13]。由此可見,二者陰陽內涵是一致的,所以從腸道陰陽失衡角度來研究PCOS,也可以更好地認識疾病[14]。
1.2 “腦-腸”理論貫穿其中現代研究發現,與食欲、食物攝入量、能量平衡、糖脂代謝和體質量相關的“腦-腸軸”(其以神經-內分泌-免疫調節網絡為核心)對PCOS的發病、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15]。被稱為“成人的第二大腦”的腸道菌群是“腦-腸軸”信息交流的主要介導者[16]。中醫雖無“腦-腸軸”這一概念,但在眾多中醫理論及臨床實踐中不難發現,此概念深含于各方面,絕非單純的器官層面認識,文獻研究發現,醫家多從“氣機升降、臟腑和養、經絡相通”角度來闡釋中醫理論對“腦-腸”關系的認識。
其一,氣機升降相因。生命活動的本真,源于氣的“始-散-布-終”,并通過“升-出-沖-降-入”的形式完成“生-長-化-收-藏”之氣化圓通的結果。誠如《素問·六微旨大論》所云:“故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流通有序,循環有常,則“流行為氣,凝聚為精,妙用為神”,以灌溉四肢百骸、充養腦髓。升降失衡,則氣、血、精、津液無以化,濕停為痰,血阻為瘀,久致臟腑痰濁瘀毒形成,壅塞沖任,血海不能按時滿溢,而致月經失調、肥胖、不孕。“氣病”日久而致“形病”,如PCOS臨癥多見肥胖、痤瘡、多毛等。有學者提出,氣機郁滯是PCOS最基本的病理變化。女性常處于“血常不足,氣常有余”的生理狀態,故婦人氣機樞轉的正常與否更為重要。旺建偉等[17]研究證實,情志因素(大腦)-肝郁-脾虛-肝旺乘脾理論與“腦-腸軸”(神經-內分泌-免疫體系)學說有相重疊之處。甚則有學者提出“腦-腸軸”學說,其失衡的實質是氣機紊亂[18]。故而氣機調暢,升降相因,乃是調病根本。
其二,臟腑和養。此理論基礎源于臟腑之間經絡相通、五行相聯、功能相關。五臟平和,則百骸皆潤澤而經候如常[19]。
從“心胃相關”出發,本(脾)胃賴于心陽宣發溫煦、心氣氣化以運化水谷,化生精微物質,心為君主之官,又賴于精微之涵養,以主“五臟六腑”。且“胃足陽明脈,正別上至脾,入腹里,屬胃,散而之脾,上通于心”,又“胃與心,母子也”,若陽明發病,則心脾二臟無所稟受,神機、樞機失常;反之,心脾病者,胃腸受累。故“月經之本,所重在沖脈,所重在胃氣,所重在心脾生化之源耳”[20]。周惠芳教授遵于此理,辨治PCOS首從健脾胃、寧心神出發,療效顯著。
從“脾腎相關”而言[21],該理論溯源于《黃帝內經》,經后世醫家發展論述至今,二者在生理上相互滋生,病理上互相影響,但何以與“腦-腸”相關?唐宗海在《中西匯通醫經精義·全體總論》中曰:“腎系貫脊,通于脊髓,腎精足,則入脊化髓,上循入腦而為腦髓,是髓者精氣之所會也。”可見“腎通于腦”,經絡功能相通,又“五谷之津液,和合而為膏者,內滲入于骨空,補益腦髓”,榮養之源根于脾胃,脾胃乃“后天之本”,運化精微以充養腦髓。如恣食肥甘厚味,損傷脾胃,則濕邪內生,內蘊腸腑,氣滯血瘀,久則脂膜血絡受損,而至腸病;或腎陽虛,脾陽失于溫煦,脾腎兩虛,水失運化,濕聚成痰,而成“痰瀉”,多數研究證實,PCOS患者腸道菌群紊亂,易見腸道病癥。痰濕上擾,阻滯清竅,神機失用,精神失常,國內外研究也證實,PCOS較正常人群更容易患精神障礙[22],但該研究有其局限性。
從“膏脂”論。膏脂轉輸體現臟腑功能,若如常,則病邪難生。“膏,脂也。”膏脂來源有二。其一,多食肥甘厚味之品;其二,水谷精微轉化而來[23]。“三焦氣化”為膏脂主要運動形式,布散精微至周身臟腑。若臟腑功能失調,膏脂過剩,即“脂凝、脂結”,不歸正化,久成痰瘀阻絡之勢;溢余經脈之外,則積于皮下,積于臟腑,導致肥胖、不孕、代謝綜合征等疾病的產生[24]。誠如《素問·通評虛實論》說:“肥貴人則高粱之疾也。”或曰“肥人多痰,乃氣虛也,虛則氣不運行,故痰生之”“婦人有身體肥胖,痰涎甚多,不能受孕”。數據表明,PCOS肥胖患者比例為20%~60%,其中,肥胖型PCOS患者高胰島素血癥的發生率高達75%。而腸道微生物的“內穩態”不僅是臟腑協調的重要體現,又是脂質代謝的重要前提。賈連群等[25]通過全轉錄組技術對造模小鼠(脾虛痰濁型)的肝臟進行基因表達譜分析,初步發現造模小鼠的腸道微生物是通過驅動TMA/FMO3/TMAO信號通路影響膏脂的轉輸。有研究表明,腸道微生態失衡是膏脂轉輸障礙的關鍵環節,可能是通過腸道多種信號分子,影響機體膽汁酸、肝臟脂質的代謝來影響雌激素代謝、胰島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IR)的產生和腸道細菌的過度增生,尤其凸顯于對膽固醇逆向轉運途徑進行調控,這些均被證實參與PCOS的發病過程[26-28]。所以可以通過調腸道,轉輸膏脂,來治療PCOS。
其三,經絡相通。“腦-腸”間存在廣泛的經絡聯系,經絡具有運行氣血、聯系臟腑、溝通內外的作用。從循行看,“大腸手陽明之脈……絡肺,下膈,屬大腸,其支抵胃,屬小腸;其支者……至目內眥,斜絡于顴”“胃氣上注于肺……上走空竅,循眼系,入絡腦”,又“人頭者,諸陽之會也”;從絡屬臟腑功能看,“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更虛更滿,故氣得上下,五臟安定,血脈和利,精神乃居”“五味入口,藏于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可見二者存在堅實的生理聯系。若經絡病,神機失常,變生多病,故而有醫者通過針灸來調“腦-腸”,治療代謝性疾病及腦病,現代研究也證實“腦-腸”軸發揮作用的基礎包括神經內分泌信號傳導、免疫傳導等方面。
從中醫學理論出發,并無“腸道菌群”這一說法,但腸道微生態的生理功能卻敏銳地反映在周身臟腑、氣血津液、精氣神等諸多方面,尤其是脾胃功能[29]。五臟之病,俱能生痰,但脾胃樞機失常乃為核心。因脾胃地處五臟六腑之中樞,內寓升降浮沉、寒熱燥濕之功,人體之精髓、氣血、津液、營衛皆由其化生而來,濡養灌溉五臟六腑、四肢百骸。脾胃樞機順暢,可下滋腎水、上濟心火,以維持臟腑功能正常運行。轉運失常則至痰濁瘀,“壅滯中焦,傷及腸腑”“閉阻胞宮”等[30],這與PCOS的根本病機也是一致的,故而臨床上許多醫家提出,治療PCOS以健運脾胃為要,杜絕病理產物。脾氣升則腎肝之氣升,胃氣降則心肺之氣降,故而中土旺,氣機升降得疏,水精四布,五精并行,微生態自然內穩[31]。現代“組學”類技術(如宏基因組學、蛋白質組學、轉錄組學、代謝組學等)也已經有力佐證,中醫藥可通過多信號通路、多環節、多臟器靶點與腸道微生態相互作用,治療代謝性疾病。通過中醫藥調節腸道微生態角度來治療PCOS可能是個新靶點[32]。
2 現代作用機制
早在2012年,Tremellen等[33]提出PCOS發病機制的“DOGMA”(dysbiosis of gut microbiota)假說,可總結為:①長期暴露于高糖高脂或低膳食纖維飲食、肥胖型的PCOS患者群,均存在腸道菌群紊亂狀態,腸道上皮細胞間連接遭到破壞,腸壁黏膜通透性增加,形成所謂的“泄漏腸道”。②腸道細菌胞壁上的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進一步滲入血液,產生慢性炎癥反應,誘導IR產生。③IR促進高雄激素血癥,干擾卵泡發育,致PCOS患者不孕。隨后多項研究也證實了其假說的成立,發現PCOS患者腸道微生態及通透性確有改變,且腸道菌群紊亂與相關臨床癥狀密切相關。
2.1 高雄激素血癥高雄激素血癥作為PCOS的重要臨床表現之一,也是疾病診療的核心點,其導致卵巢基質增生、卵巢包膜增厚,加速了卵泡的閉鎖,抑制性激素結合球蛋白合成,進而促使外周血轉化增高,導致女性多毛、痤瘡、排卵障礙等。已有動物實驗發現,腸道菌群的改變會影響動物血液中睪酮(testosterore,T)的含量。Poutahidis等[34]發現,喂食過羅伊氏乳桿菌小鼠血液中的T水平確有升高。Kelley等[35]對來曲唑誘導的PCOS高雄激素血癥小鼠模型進行研究發現,小鼠大腸中細菌的種類及數量確有減少,且小鼠的體質量、脂肪量及血糖水平較對照組升高,說明高雄激素血癥導致了腸道菌群的改變。Guo等[36]對PCOS造模大鼠灌喂了健康大鼠的糞便提取物后發現,大鼠的雄激素水平顯著降低。說明在PCOS中,二者均參與疾病的發生發展,但二者間的關系、機理有待深入研究證實。
2.2 胰島素抵抗通過對PCOS患者血清和卵泡液組分的研究發現,腸道菌群可通過LPS、支鏈氨基酸、短鏈脂肪酸(引起肥胖的關鍵因素)和膽汁酸等介導炎癥反應,從而影響胰島素的敏感性。
腸道菌群能夠破壞腸黏膜的屏障作用,使LPS滲入血液[37]。LPS又通過血中的脂多糖結合蛋白結合運輸,與免疫細胞表面CD14(一種白細胞分化抗原,可介導LPS性細胞反應)結合,并被Toll樣受體4(Toll-like receptors 4,參與LPS信號傳導的重要受體)識別,進一步作用于脂肪細胞及巨噬細胞,從而產生多種炎癥因子(例如腫瘤壞死因子-α、白細胞介素-1、白細胞介素-6等)介導炎癥反應的發生,來誘導胰島素受體底物-1的絲氨酸磷酸化,發揮干擾正常酪氨酸的磷酸化的作用,減弱胰島素信號的轉導,致胰島素的敏感性下降,引起胰島素抵抗[38]。Cani等研究發現通過添加益生元,增加雙歧桿菌的總含量,能夠促進結腸細胞對胰高血糖素樣肽-1的分泌,促進胰島素分泌釋放,改善IR等代謝異常[39]。Zheng等[40]通過幾項前瞻性隊列研究發現,人體攝取越多的支鏈氨基酸(人腸道內的一種普氏菌參與支鏈氨基酸的合成),罹患糖尿病的概率就越高,分析機制可能是因為纈氨酸的分解代謝產物3-羥基異丁酸鹽,刺激了肌肉組織對脂肪酸的攝取途徑,從而引起了脂肪堆積和IR,但還需進一步研究。
膽汁酸作為重要的細胞信號轉導因子之一,可激活多個信號通路來調節生物學過程,其中包括脂類、碳水化合物的代謝和介導炎癥反應等。徐運杰等[41]研究發現,膽汁酸降脂機制有:①乳化脂肪,擴大與脂肪酶的接觸面積;②調控胰脂肪酶和脂蛋白酯酶的活性,提高其對脂肪的水解代謝;③在腸道內轉運脂肪,來促進脂肪的吸收。Li等[42]研究發現,膽汁酸可以通過腸神經內分泌細胞,激活G蛋白偶聯受體,刺激胰島素的分泌,增加胰高血糖素樣肽-1的分泌,調節機體能量代謝。
膽汁鹽作為膽固醇分泌的輔助分子,經研究證實,其可以促進腸中營養物質的吸收,進而刺激胰腺分泌足量的胰島素,并抑制小腸中細菌的增生,促進小腸對脂類的吸收,降低IR的發生[43]。
上述成分在雌激素代謝、胰島素抵抗和小腸細菌過度增生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均參與PCOS發生發展。
2.3 肥胖肥胖與PCOS并非一類疾病,且不是PCOS的致病原因,但肥胖卻是PCOS的常見表現。據統計,PCOS中肥胖患者比例高達20% ~60%,肥胖是公認發生胰島素抵抗最常見的危險因素之一[44]。腸道菌群的改變參與肥胖、代謝異常等發病機制。Cani等發現,腸道菌群產生的LPS會改變腸道通透性,引起機體慢性炎癥反應,最終導致肥胖的發生。Bkhed等[45]發現,B6自交系無菌小鼠腸道植入正常菌群后,小鼠的脂肪量增加了57%,但進食量反而減少27%。NMRI用自交系小鼠做了同樣的實驗,發現有菌小鼠的總脂肪含量增加了90%,進食量卻減少了31%。這兩項研究證實,腸腔內腸道微生物可以促進單糖的吸收,誘導肝臟脂肪的重新合成,導致脂肪堆積。佐證了腸道菌群可以影響腸道中能量的獲取、貯存,并促進脂肪累積。研究者從肥胖者中采集腸道菌群并移植到無菌小鼠,發現小鼠身體脂肪含量會明顯增加,并出現IR。LPS被證實是形成IR的主要原因之一。Cani等[46]給無菌小鼠連續皮下注射4周LPS后,小鼠出現慢性低度炎癥,并導致肥胖和IR。可見腸道菌群失調,腸壁通透性增加,緊密連接蛋白表達減少,引發的內毒素血癥加重慢性低度炎癥,并參與肥胖的發病過程。腸道菌群可能是通過影響能量代謝、慢性炎癥反應、免疫系統調節、腸道激素等多種途徑參與疾病的發生、發展。但目前具體機制尚未完全明了,如腸道菌群結構、代謝機理等諸多方面,所以有待更深入、更精確的研究[47]。
3 結語
綜上所述,隨著對免疫機制、微小RNA、微生態、脂肪代謝組學等層面與多囊卵巢綜合征的發病相關性的深入研究,對多囊卵巢綜合征的病因及發病機制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但仍不十分明了。目前,多囊卵巢綜合征的治療仍集中在針對特定癥狀,還無法達到患者內環境穩態、子代健康的理想結果。腸道菌群作為內環境因素,可與宿主相互作用,多項研究已經證實,腸道菌群可能通過多種途徑、多種因素參與PCOS的病理生理過程的發生和發展,但究竟誰是機理的引導者,尚未知曉。由于PCOS疾病的特殊性、終身性,治療上并非短期可以速效,中醫藥在治療PCOS中體現出了顯著的優勢。目前,關于中醫藥干預治療對多囊卵巢綜合征患者腸道微生態影響的臨床研究報道較少,尚需進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