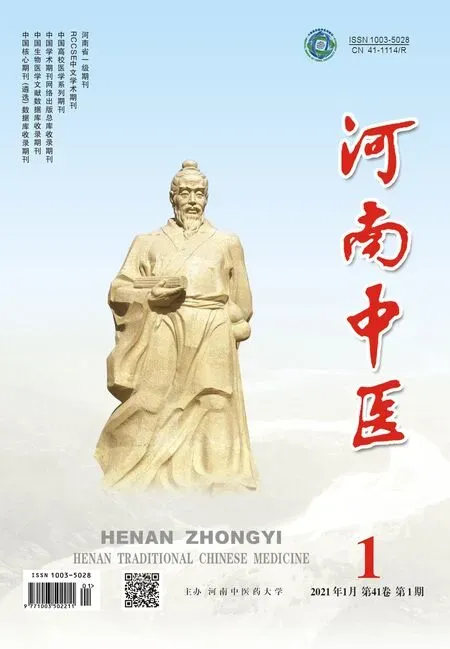李中梓痿證診療思想探微*
金子開,郭子為,張思雅,吳可,馬文軒,姚長風
安徽中醫藥大學,安徽合肥 230038
李中梓,字士材,江蘇云間南匯人,明清時著名醫家,著有《內經知要》《醫宗必讀》等。李中梓治學嚴謹尚實,注重中醫理論的研究,兼取眾家之長,勤于探索,不僅能汲取前人思想的精華,又有自己新的見解,其重視脾腎,擅長“別癥、知機、明治”,注重養生、三因制宜,重視醫風醫德。
痿證是指肢體筋脈遲緩、軟弱無力,日久不能隨意運動而致肌肉萎縮的一種病證。李中梓對于痿證的認知,在《黃帝內經》所述“五臟因肺熱葉焦,發為痿蹩”的基礎上做了進一步發揮,認為“五臟之痿,皆因肺熱最高”。在治則治法上,李中梓認為,“不獨取陽明而何取哉”,并在張仲景、李東垣、朱丹溪等的治療方法上進行了發揮與補充,倡導三因制宜,溫補為善,標本擇治,其學術思想具體體現如下。
1 博采眾長,遍取各家
李中梓在《醫宗必讀》中博采眾家理法,尤其對于痿證的理法方藥,李中梓更是上承《黃帝內經》,下發各家,遍取諸家學術之長,而不偏執,可謂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
1.1 悟各家之理李中梓在《醫宗必讀》中闡述了痿證的病因病機與治療大法。如“五臟因肺熱葉焦,發為痿蹩”“論痿者獨取陽明何也?陽明者,五臟六腑之海,主潤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關節也[1]。”在大段引用《素問·痿論》原文之余,李中梓更是發揮經義,詳盡注解,如“肺者,臟之長也,為心之蓋也”,李中梓注:“此言五臟之痿,皆因肺熱最高,故為臟長,覆于心上,故為心蓋。”[1]因五臟痿證皆先責肺熱,次傳諸臟,故可知肺為臟之先受邪者,必居高位,為諸臟之長,且覆蓋心上。李中梓以后文釋前文,真正從整體把握經文,融會貫通。其又下發各家,吸取李東垣、朱丹溪之學。李中梓在闡述痿證病機時,多從李東垣《內外傷辨惑論》“內傷飲食勞役者,心肺之氣先損,為熱所傷”[2],并由此著重發揮痿證的內傷病因,“失亡,不得,則悲哀動中而傷肺,氣郁生火……故熱而葉焦。”[1]闡述痿證治療方法方面,李中梓援引朱丹溪瀉南補北法:“瀉南方則肺金清,而東方不實,何胃傷之有?補北方則心火降,而西方不虛,何肺熱之有?”[3]李中梓認為,瀉南補北法實際就是用藥攻中寓補,間接顧護了在痿證診療中有特殊意義的肺脾二臟,此法足以治療大部分內傷致痿。由此可見,李中梓不拘于時,真正透悟各家學說。
1.2 集諸師之方在痿證附方中,可見李中梓對于張仲景、李東垣、朱丹溪等的方藥比較推崇,且尤為重視張仲景和朱丹溪的方藥。李中梓善用張仲景之大承氣湯論治痿證可謂創見,大承氣湯本陽明腑實證主方,蓋痿證多內傷勞役,體虛不堪攻伐,然李中梓辨治此痿案,認為痿證雖以實熱壅體為標,內傷為本,然可用此方先下,后予以補虛即可,其大膽活用經方,足見其透讀《傷寒論》,從病機角度理解經方,異病同治,運用于后世證治。論及朱丹溪方藥時,則多理法結合,多處化用《丹溪心法·痿》的內容,如“挾濕熱,健步丸加黃柏、蒼術、黃芩或清燥湯。濕痰,二陳、二妙、竹瀝、姜汁[4]。”且對丹溪治痿名方之虎潛丸、補陰丸多有收錄并臨證化裁之,不拘一家,不泥成方之見,如此足以應對臨證病情之千變萬化,更能有效指導臨床。
2 病機明晰,理法善備
李中梓在痿證論治過程中思路明晰,理法明確,最崇《黃帝內經》之言,發皇古義,下采各家,在痿證病因病機與治療方法等方面對以后的臨床應用具有指導意義。
2.1 病因病機李中梓對于痿證病因病機的闡述,多有發明。李中梓法宗《黃帝內經》“五臟因肺熱葉焦,發為痿蹩”之論,認為五臟雖各有痿證,然需獨重手太陰肺經。手太陰肺經,為五臟之長,位居最高,故“言五臟之痿,皆因肺熱最高”[1]。李中梓認為痿證多由七情六淫等內傷因素所致,內傷氣熱是痿證的重要病機,有所失亡、不得等皆可致使氣郁生火,故“氣熱則五臟之陰皆不足,此痿蹩所以生于肺也。五臟雖異,總名痿蹩”。
2.2 治療方法李中梓秉承《黃帝內經》“治痿獨取陽明”的治療原則之余,進一步闡述,五臟雖各有痿,然應分而治之,但分治之余,不應遺忘足陽明胃經之固護。胃居中焦而運化水谷,胃受邪則血氣少,難以潤養宗筋,故宗筋縱弛,體痿不用。五臟痿皆因肺熱,而肺金受邪,肝木無所制必侮其所勝,中焦脾胃皆受其克。《醫宗必讀·腎為先天本脾為后天本論》云:“胃氣一敗,百藥難施。”[1]李中梓論治痿證尤其注重胃氣的固護,其法同丹溪“瀉南補北”之法,在間接調治脾胃之余,更附言“若胃虛減食者,當以芳香辛溫之劑治之,若拘于瀉南之說,則胃愈傷矣”。筆者認為,李中梓論治痿證理法尤其明晰,其進一步闡釋了《黃帝內經》中手太陰肺、足陽明胃在痿證中扮演的特殊角色,環環相扣,不失古法之余博采后賢之說,堪為治痿之典范。
3 臨證診療,獨具匠心
3.1 不泥成方,三因制宜李中梓治療痿證臨證多有神效,最重要的原因是其注重臨證辨治,不泥成方。如《里中醫案》載:“蘇淞道萬玄圃,神氣不充,兩足酸軟。服安神壯骨,服補腎養陰,服清熱祛濕,卒不效也[5]。”蓋此案所載痿證,時醫不經辨證,直予成方,故三易而無效也。李中梓辨治后云:“六脈沖和,獨有中州澀而無力[5]。”遂與補中益氣湯加蒼術,即日而愈。李中梓認為,臨證病機千變萬化,不能以一定之法、一定之方應無窮之變,而應著眼病機,臨證具體分析,活用前人之妙方,加減化裁,從這個角度來看,古方今用是可實現的。故此,李中梓對五臟痿的具體論治不予成方,而只給予此證相類之藥,如“心氣熱則脈痿,鐵粉、銀箔、黃連……犀角之類”。先經辨證,再以此證相類之藥組方并酌情加減化裁之,由此圓機活法,因病而制方,真正體現了中醫的辨證論治精神。
李中梓臨證亦極具宏觀格局,注重三因制宜,其中尤以因人制宜、因時制宜而出彩。因人制宜:《醫宗必讀·富貴貧賤治病有別論》云:“大抵富貴之人多勞心,貧賤之人多勞力。”[1]李中梓論治“崇明文學倪君儔”案中,四診合參后予以十全大補湯加秦艽、熟附子,蓋文學者,古之通儒典而仕者,其必勞心甚于勞力,故宜于補正,不宜妄加攻伐。此外,李中梓亦注重患者先天體質,《醫宗必讀·不失人情論》云:“陽臟者宜涼,陰臟者宜熱,耐毒者緩劑無功,不耐毒者峻劑有害。”[1]患者先天體質不同,易致之病亦不同,對于藥物的耐受力亦不同,臨證只有宏觀考慮,充分掌握個體差異,才能有所成效。因時制宜:《醫宗必讀·痿》云:“若痿發為夏天,俗稱疰夏,其原因有二,一為腎與膀胱,治宜清暑益氣湯,一為脾濕傷腎,癥見目昏花、耳聾鳴、腰膝無力,治宜當歸、生地黃……”李中梓因時制宜,將夏日之痿責之于腎、脾、膀胱,而不死守“肺熱葉焦”之說,多從外感立論,夏日暑濕困重犯體,唯清暑益氣湯之升陽固表、當歸、生地黃屬滋陰活血藥,堪治此夏日之痿,若一味補益陽明,不顧濕阻中焦,則愈補愈膩,易成痰飲,更重其病。此處足見李中梓對于痿證病機把握之靈活,考慮之周全。
3.2 溫補為善,共治脾腎自元代朱丹溪學派“滋陰論”興起,延至明代,世醫未全解朱丹溪之意,舉世皆用,逐漸發展成濫用苦寒傷脾的局面,為矯枉過正,以薛己為首的溫補學派興起。朱丹溪以“陽常有余,陰常不足”的陰陽對立論為滋陰派立論,而實際上,從朱丹溪學派至溫補學派思想的發展歷程來看,是從陰陽對立論逐漸走向陰陽一體論[6]。李中梓作為明代溫補學派的代表,雖然注重陰陽一體的平衡,指出陰陽“宜平不宜偏”,然在陰陽關系中更強調陽氣的重要性。《內經知要·陰陽》云:“陽氣生旺,則陰血賴以長養;陽氣衰殺,則陰血無由和調,此陰從陽之至理也。”[7]陰血長養需得陽氣煦旺推動,而陽氣生發又需陰血滋養,由此陰陽方可平調、氣血方可生發,人體陰平陽秘,得氣血生養,則痿從何來?而在陰陽、氣血兩對矛盾中,李中梓更加注重氣、陽,《醫宗必讀·水火陰陽論》云:“故氣血俱要,而補氣在補血之先;陰陽并需,而養陽在滋陰之上。”[1]陽氣為人身至寶,陽生則長,旺則壯,衰則病則老,敗則夭則亡。故無論防病治病均應以養陽為主,補氣為要[8]。在痿證的臨床用藥中,李中梓亦貫穿其重陽思想。李中梓極通藥理,將藥物的性味與自然界現象聯系起來,《醫宗必讀·藥性合四時論》云:“藥性之溫者,于時為春,所以生萬物者也,藥性之熱者,于時為夏,所以長萬物者也。”[1]春夏是一年中陽氣最旺盛的季節,故溫熱之藥最助長一身陽氣,陽氣得行,生機自發,則一身元氣來復,雖大虛之證亦可回也。其藿香養胃湯重用藿香為君,白術、人參為臣,藿香甘溫合中,芳香醒脾;白術、人參俱溫和君子,燥濕健脾,大補元氣,君臣相伍,中陽自可上升下降,充養一身,輔以溫熱之半夏、烏藥、砂仁散寒降逆,其品皆以炒制,其火助溫成熱,使和中補虛之功更加顯著,中州得固,氣血生發無虞,痿不復存。
李中梓治療痿證臨證用藥除注重溫煦脾陽外,亦注重腎陽的固攝。在脾腎這對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的補養中,李中梓并重之,《醫宗必讀·虛癆》云:“脾腎者,水為萬物之元,土為萬物之母,兩臟安和,一身皆治,百疾不生。夫脾具土德,脾安則腎愈安也。腎兼水火,腎安則水不挾肝上泛而凌土濕,火能益土運行而化精微,故腎安則脾愈安也。”[1]除此之外,李中梓進一步提出理脾不拘于辛燥升提,治腎不泥于滋膩呆滯[5]。查其治療骨痿諸方,溫補腎陽不濫用桂枝、附子,而多以補陽益精之肉蓯蓉、助陽堅骨之菟絲子等為主藥。其自創之神龜滋陰丸由丹溪之大補陰丸加減化裁而來,去滋補膩滯之熟地黃,仍以四兩龜板為君,而僅加一兩鎖陽、枸杞子,半兩干姜,法同六味丸加少量桂枝、附子為八味丸,意不在補火,而在生火,最具少火生氣之妙。蓋如吳謙云:“且形不足者,溫之以氣,則脾胃因虛寒而致病者固痊,即虛火不歸其原者,亦納之而歸封蟄之本矣”。
3.3 標本擇治,按施三法《醫宗必讀·辨治大法論》云:“標本先后者,受病為本,見證為標;五虛為本,五邪為標。”于痿證論治方面,李中梓極具出彩的一點便是以痿證為本,而以其余伴隨癥狀為標,根據具體情況靈活標本擇治。在“太學朱修之”案中,李中梓診后查其“八年廢痿,然六脈有力,飲食若常,此實熱內蒸,心陽獨亢。”急則治其標,當急瀉心火、除內熱也。《刪補頤生微論·明治論》云:“三法者,初中末也。一曰初法,當用峻猛,緣病新暴,感之輕,發之重,以峻猛之藥亟去之。二日中法,當用寬猛相濟,緣病非新非久,須緩急得中,養正去邪,相兼治之。三日末法,當用寬緩,藥性乎善,廣服無毒,取其安中補益,緣病久邪去,正氣日微也。”于此案的論治中,李中梓充分運用了三法:先以峻猛重劑承氣湯攻下熱結,救陰瀉熱,下六七服后,患者左足已能伸縮;次以承氣湯合人參湯,并服黃連、黃芩、大黃共制之蜜丸,攻補并行,且于攻中寓補,一月之內,則數年之積滯盡去,四肢可舒展也;末以天門冬、生地黃、人參之三才膏益肺脾腎,補氣生津。蓋雖因實熱積滯成疾,且實熱已祛,而久病必虛,積滯已去而內里空虛,當以藥助長正氣,善養調服,如此方可邪去正安。李中梓這種標本擇治、臨證明機并且分階段靈活施治的痿證診療思路,是對痿證更深層次地理解,大大拓寬了補陽明的治療方法,對當代痿證的臨床治療多有指導意義。
4 結語
李中梓作為明代溫補學派大家,論治痿證法宗《黃帝內經》《難經》,下啟諸家,其臨證尤重發揮辨證論治精神,不妄投成方,注重因時、因地、因人三因制宜。此外,李中梓針對痿證虛損的性質,以溫補為善,善用溫藥補陽,并注重先后天之本脾腎的顧護。最具價值的是,李中梓論治痿證極具宏觀格局,以痿證為本,其余伴隨癥狀為標,標本擇治,或以初法攻伐、中法既濟、末法寬補三法分階段論治痿證,此更是對痿證深層次的把握。李中梓集諸家理論與經驗之大成思想,對于既往醫家思想又有更深層次地解讀與創新,圓機活法,古法新用,由此對后世痿證診療產生了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