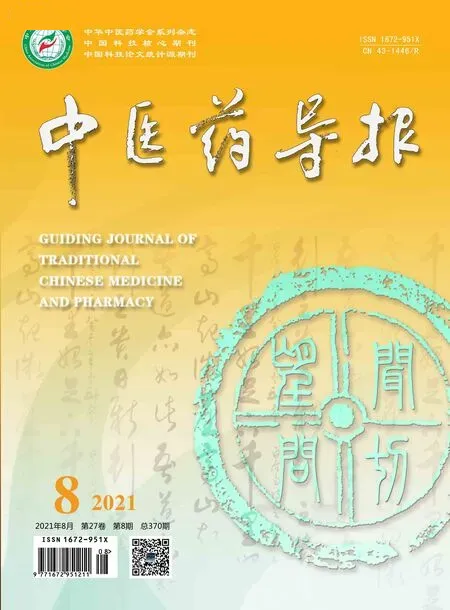丘和明從少陽論治淋巴瘤經驗
歐海濤,胡莉文
(1.廣州中醫藥大學,廣東 廣州 510405;2.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血液科,廣東 廣州 510405)
淋巴瘤是起源于淋巴結和(或)結外淋巴組織的惡性腫瘤,無痛性、進行性淋巴結腫大和局部腫塊是其特征性表現,還可能伴有發熱、盜汗、乏力、消瘦、皮疹、瘙癢等全身癥狀[1]。2014年中國惡性腫瘤發病和死亡分析報告中表明,淋巴瘤的死亡率排在中國所有惡性腫瘤中的第10位[2]。近年來,國內淋巴瘤的發病率呈上升趨勢[3]。西醫主要采用放療、化療、靶向治療、造血干細胞移植等療法。中醫學并無“淋巴瘤”病名的記載,但對于淋巴結腫大的闡述和證治的記載頗多,現代中醫學根據其淋巴結腫大的癥候,將淋巴瘤歸屬于“瘰疬”“筋瘤”“痰核”“惡核”或“陰疽”的范疇。丘和明教授(以下尊稱丘老)是全國著名中醫血液病專家,全國中醫師帶徒名老中醫,廣東省名老中醫,廣州中醫藥大學首席教授,從事血液內科臨床、教學和科研50余年,具有深厚的理論造詣和豐富的臨床經驗,對于中醫藥治療淋巴瘤有著獨到的見解。丘老認為,在選擇合適的西醫治療方案的同時,運用中醫藥,從少陽辨治淋巴瘤,臨床療效顯著。筆者有幸隨丘老侍診兩年余,學習并總結了丘老從少陽論治淋巴瘤的學術經驗,現將其論述如下,以饗同道。
1 少陽經絡臟腑與淋巴組織的聯系
丘老認為,少陽經絡臟腑與淋巴組織解剖生理聯系密切。《素問·陰陽離合論篇》曰:“是故三陽之離合也,太陽為開,陽明為合,少陽為樞。”[4]少陽的基本功能為樞轉氣機,開合表里內外,使得氣機升降出入正常,維持氣血津液的正常運行。少陽經位于半表半里之間,包含足少陽膽經和手少陽三焦經,連接膽與三焦。《靈樞·經脈》:“膽足少陽之脈,起于目銳眥……下耳后……下頸,合缺盆,從缺盆下腋……循脅里,出氣街……;三焦手少陽之脈……其之者,從膻中上缺盆,上項,系耳后直上……從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5]。少陽經位于半表半里,經絡循行經過耳前、耳后、頸部、鎖骨上窩、腋下、腹股溝等部位。現代醫學所言的淺表淋巴組織主要分布于耳前、耳后、頸部、鎖骨上窩、腋下、腹股溝、腘窩等部位,這與少陽經循行路線大致相同。現代名老中醫劉邵武研究《傷寒論》,認為半表半里類似于血液循環系統及結締組織系統[6],張天洪等[7]根據三焦的功能屬性、結合現代醫學解剖學,認為三焦即網膜、腸系膜、輸尿管及腹腔淋巴系統。手、足少陽之經脈臟腑與淋巴組織關系密切,若病變出現在少陽經脈或臟腑,則會通過經絡循行影響到淋巴組織,出現以淋巴結腫大為主癥的病證。如:《靈樞·經脈》言病在足少陽之脈,“腋下腫,馬刀挾癭”[4]。《四圣心源·瘰疬根原》云:“瘰疬者,足少陽之病也。”[8]
2 少陽病與淋巴瘤
樞機不利為少陽病的基本病機。邪犯少陽,樞機不利,疏泄失職,條達失司,或累及膽腑,或致三焦不利,或他經臟腑合病傳變,以致氣機升降出入、氣血津液運化失常。氣機升降失常是疾病發生的重要因素,而腫瘤的形成亦是氣血津液失調的結果[9]。丘老認為淋巴瘤的發病與痰、瘀、熱、毒密切相關,從中醫整體觀念出發,此與少陽關系密切。少陽樞機不利,氣機升降出入失常,氣血津液運行不暢,繼而出現痰濁、瘀血、熱毒內生,痰瘀毒搏結于體內發為淋巴瘤。
2.1 樞機不利,痰濁內生 丘老指出,三焦的氣機升降出入異常是產生水濕痰濁的根本原因。《類經·藏象類》:“三焦氣治,則脈絡通而水道利”[10]。樞機不利,三焦氣化失司,水液代謝失常,水液停聚,痰濁內生。《雜病源流犀燭·痰飲源流》中談到:“其為物則流動不測,故其為害”[11]。痰飲一旦產生,可隨氣流竄全身,外而肌膚、經絡、筋骨,內至臟腑、全身各處。正所謂“無痰不成核”[12],痰濁隨少陽經氣走三焦道路可到達全身各臟腑,停于耳周、頸項、腋下、臟腑等部位,久則出現局部痰核。丘老認為“痰”不僅是淋巴瘤形成過程中的病理產物,痰濁內聚更是該病的致病因素。
2.2樞機不利,氣滯血瘀 少陽為氣之道路,樞調氣機,主導氣之運行,從而調節血、津液之運行。故而三焦暢通,膽疏泄失常,氣機才能調暢。《血證論·便膿》載:“血者陰之質也,隨其運行……氣滯則血瘀……故血之運,其主之。”[13]正所謂氣為血之帥,氣行則血行,氣機暢達則血行無阻。少陽樞機不利,以少陽氣機郁滯為主,而氣機郁滯則血行不暢而瘀。氣機失常,水道不利,氣血津液運行不利而產生氣郁、血郁,留滯于人體,日久形成瘤。
2.3 樞機不利,熱毒內生 明代《慎齋遺書·痰核》載:“痰核,即瘰疬也,少陽經郁火所結。”[14]少陽膽經內寄相火,所以一旦足少陽膽經經氣郁滯,極易化熱化火。丘老以為,少陽樞機不利,少陽經氣郁滯,相火逆行,郁久化熱傷津成毒,熱毒內結,客于經絡,瘤可成矣。有學者從信號傳導角度研究認為,少陽相火乃生發之源,人體的正常的生長發育及細胞的分化、成熟依賴少陽相火功能的正常發揮,少陽相火妄動離位,可誘發細胞異常分化、增殖,在局部表現為新生命的開始,與腫瘤的發生相似,少陽相火異常可引起癌癥[15-16]。
少陽樞機不利,肝膽疏泄失常,三焦功能失司,痰瘀既成,留于體內,與熱毒相搏結,留而不去,日久形成痰核,日益腫大,又耗傷氣血,久則表現為失榮,發為敗證。淋巴瘤病性屬虛實夾雜,病之初起以實證為主,痰瘀熱局限于局部,表現為淺表淋巴結進行性腫大,腫大的淋巴結表面光滑、活動可,質地韌、飽滿、均勻,隨著病情的進展,熱毒內結,耗灼津液,正氣漸虛,傷及其他臟腑,可出現體內腫塊,腫大的淋巴結堅硬如石、發生粘連并且互相融合,甚致形成難愈合的潰瘍,且出現發熱、盜汗、皮膚瘙癢等全身癥狀,病至晚期,痰瘀毒凝結,乃致邪毒內盛,耗傷氣血,日漸正氣空虛,正不勝邪,癌毒內陷,臟腑功能衰竭,出現進行性消瘦、大骨枯槁、大肉陷下等癥狀。
3 從少陽論治淋巴瘤的臨床應用
丘老認為少陽樞機不利為淋巴瘤的核心病機,貫穿淋巴瘤發生發展的全過程。因此,臨床上治療淋巴瘤以調暢少陽樞機為基本治療原則,常以小柴胡湯為主方加減。小柴胡湯乃和解少陽第一方,由柴胡、黃芩、半夏、生姜、大棗、人參、甘草共7味藥物組成,諸藥合用,少陽暢達,樞機得運,氣血津液運行輸布正常,痰瘀不成,乃治[17]。李達[18]在治療淋巴瘤時也常輔以和解之柴胡類方藥,臨證效果頗佳。更有臨床研究表明,小柴胡湯可影響通過影響NK細胞、巨噬細胞、淋巴細胞和細胞因子等,實現抗炎、免疫調節作用,還可通過阻斷細胞周期、抑制增殖和誘導細胞凋亡以達到抗腫瘤作用[19-22]。隨著病情的進展,淋巴瘤在早期、中期和晚期的疾病特點各異,丘老提倡分期綜合治療,臨床治療在和解少陽的基礎上,結合辨證論治,隨證加減,分期而治,以達“立竿見影”之效。
3.1 初期 在和解少陽的基礎上,輔以理氣化痰、祛瘀散結。淋巴瘤早期,少陽樞機不利,痰、瘀初現,痰核初起,其不在臟腑,不變形軀,正氣尚足。此期屬邪實而正氣未虛,辨證多見氣郁痰凝、痰瘀互結之實證,臨床上多出現規則、質地不硬、局部不紅不痛之痰核,常伴隨口干口苦、頭暈目眩、胸脅苦滿、心煩易怒、時有身熱、不欲飲食、舌質淡或紅、苔白或微黃、脈弦滑或弦數等少陽失樞之癥。治療當以祛邪為主,在小柴胡湯的基礎上加減,此時正氣尚旺,常易大補之人參為平和之黨參,輔以理氣化痰、祛瘀散結之藥物,常用陳皮、半夏、天南星、瓜蔞、薤白、白芥子、海藻、昆布、川芎、香附、當歸、玄參、芍藥、牡丹皮等。丘老指出,臨證用藥當辨清痰瘀之輕重。偏于痰結者重用陳皮、半夏、天南星、白芥子之品,陳皮、半夏最掃痰涎,白芥子善祛皮里膜外之痰,配合天南星增強化痰散結之功。偏于血結者重用川芎、玄參、牡丹皮、赤芍之類,川芎為血中氣藥,可散滯氣、破瘀血,與玄參、牡丹皮、赤芍等祛瘀散結以消瘰疬。
3.2 中期 在和解少陽的基礎上,輔以清熱解毒、軟堅散結,少佐益氣養陰之品。淋巴瘤中期,隨著病情的進展,少陽膽經郁而化火,火毒內生,熱毒與氣血痰瘀相搏,痰瘀毒滯留不散,交結成塊,可耗傷氣血津液。此期邪毒漸盛,邪毒入里,耗氣傷津,正氣漸虛,辨證多見瘀毒互結、熱毒壅盛,臨床上多出現頸項部痰核累累或如串珠、堅硬如石,常伴隨肝脾腫大、胸脅疼痛、心悸氣短、急躁易怒、煩熱盜汗、皮膚瘙癢、舌質紅或暗或有瘀點、苔薄白或黃、脈弦澀或弦數等瘀毒內盛津虧之象。治療當以祛邪與扶正并舉,在和解少陽的基礎上,守小柴胡湯為主方,輔以清熱解毒、軟堅散結之品,并少佐益氣養陰藥物。常用夏枯草、白花蛇舌草、貝母、三棱、莪術、蒲黃、五靈脂、丹參、牡蠣、鱉甲、白術、黨參、麥冬、太子參、石斛、沙參、玉竹等。丘老在此期常重用夏枯草、白花蛇舌草、貝母。有研究表明,夏枯草提取物可增強紫杉醇、多柔比星對淋巴瘤細胞的抑制作用[23];白花蛇舌草具有抗腫瘤、調節免疫的作用[24];浙貝母具有清熱化痰、散結消癰功效,《本草經集注》記載:“安五臟,利骨髓”[25]。重用三藥,消癥散結之效益彰。
3.3 晚期 在和解少陽的基礎上,輔以滋補肝腎、補益氣血。病至晚期,痰瘀毒凝結,阻滯氣血,又產生痰瘀等病理產物,形成惡性循環,邪毒內盛,則可耗傷大量氣血津液,氣血愈虛,乃至正氣空虛,正不勝邪,虛證日漸明顯。辨證多見肝腎陰虛、氣血虧虛。臨床上多出現頸項部、腋下及腹股溝等處串珠累累、堅硬如石、推之不移,常伴隨進行性消瘦、神疲乏力、頭暈眼花、心悸失眠、耳鳴、五心煩熱、脅痛、少氣懶言、食欲不振、面色晦暗或晄白、舌紅少苔或舌淡、苔薄白、脈細數或脈沉細無力等臟腑功能衰敗之象。治療當以扶正固本為主,此時以小柴胡湯為主方加減,此期正氣虧虛,顧護脾胃尤為重要,正所謂“留得一分胃氣,便得一分生機”,苦寒之黃芩用量當減少,一般6~10 g為宜,并輔以滋補肝腎、補益氣血的藥物。常用骨碎補、桑寄生、墨旱蓮、菟絲子、女貞子、枸杞子、黃精、熟地黃、山茱萸、白芍、鹿角膠、黃芪、白術、當歸、人參等藥物。丘老在臨證配伍用藥時不忘辨氣血陰陽虧虛之偏重。偏于肝腎陰虛者,重用熟地黃滋腎陰、益精髓,枸杞子、白芍柔肝養肝平肝,若陰虛火旺、五心煩熱可加知母、黃柏以清泄肝腎之火。偏于氣血虧虛者,重用黃芪、白芍、當歸、熟地黃、鹿角膠,黃芪補氣生血,白芍、當歸、熟地黃滋養心肝,補而不滯,鹿角膠乃血肉有情之品可填精補髓以養血,共奏氣血雙補之效。
4 驗案舉隅
4.1 驗案1患者,男,39歲,2018年7月10日初診。主訴:口干、口苦1個月余。患者于2018年3月6日因“發現左側頸部腫物9個月余”就診,查頸部CT考慮淋巴來源病變,淋巴瘤可能。2018年3月10日行“頸部腫物切除術”,術后冰凍切片病理檢查考慮為(頸部淋巴結)霍奇金淋巴瘤。病理活檢示:(頸部淋巴結)淋巴細胞豐富型經典型霍奇金淋巴瘤;免疫組化示:CD20(-)、Pax-5(-)、CD3(-)、CD5(-)、CD30(+)、CD15(-)、Ki-67(+);原位雜交示:EBER(-)。2018年3月12日PET-CT示:左側頸部(Ⅱ、Ⅲ、Ⅳ、Ⅴ區)、左側鎖骨上及縱膈(1組)多發結節狀及團塊狀高代謝腫大淋巴結,考慮為淋巴瘤;脾臟體積增大,并右后部結節狀高代謝病灶,考慮為淋巴瘤浸潤。2018年3月17日至2018年7月9日行4程ABVD方案化療。患者近1個月出現口干、口苦等不適,遂至丘老門診就診。刻診:神清,精神一般,口干、口苦,心煩易怒,兩脅痛,納呆,眠差,難入睡,大便偏干,小便正常。查體:左側頸部觸及一腫大淋巴結,直徑約0.8 cm,腫大淋巴結邊界清晰,質硬,無壓痛,活動度可;舌質紅,苔微黃膩,脈弦滑。平素性情急躁。西醫診斷:淋巴細胞豐富性經典型霍奇金病(Ⅲ期)。中醫診斷:惡核(氣郁痰結)。治法:和解少陽、理氣化痰散結。處方:北柴胡12 g,黃芩15 g,法半夏15 g,陳皮10 g,黨參15 g,生姜10 g,大棗10 g,竹茹10 g,浙貝母15 g,赤芍15 g,枳殼10 g,甘草6 g。14劑,1劑/d,水煎至250 mL,復煎1次,分2次溫服。中成藥:溫膽片(院內制劑,組成保密),口服,4片/次,3次/d。
2診:2018年7月25日,患者神清,精神可,無口干、口苦,無脅痛,睡眠稍改善,仍有心煩易怒,胃納可,大便仍偏干,小便正常;舌質紅,苔薄微黃,脈弦滑。予前方加梔子10 g,郁金10 g。14劑,1劑/d,水煎至250 mL,復煎1次,分2次溫服。續服溫膽片。
3診:2018年8月10日,患者神清,精神可,諸癥明顯改善,偶有口干,余無不適。淋巴結查體基本同前,舌淡紅,苔薄白,脈弦。處方:柴胡12 g,黃芩15 g,法半夏15 g,白芥子10 g,天南星10 g,赤芍10 g,牡丹皮10 g,浙貝母15 g,夏枯草15 g,太子參15 g,麥冬15 g,甘草6 g。30劑,1劑/d,水煎至250 mL,復煎1次,分2次溫服。停服溫膽片。
4診:2018年9月12日,患者神清,精神可,未訴特殊不適,二便正常。查體:左側頸部觸腫大淋巴結較前稍縮小,直徑約0.5 cm;舌淡紅,苔薄白,脈弦。予3診處方30劑,1劑/d,水煎至250 mL,復煎1次,分2次溫服。此后患者數次復診,未見上述癥狀。
按語:患者為中年男性,為霍奇金淋巴瘤化療后就診。本例患者初診主要表現為時有身熱,口干、口苦,心煩易怒,兩脅痛,納呆,眠差,難入睡,大便偏干,結合舌質紅、苔微黃膩、脈弦滑等舌脈表現,四診合參,辨病為“惡核”,辨證當屬“氣郁痰結”。由于少陽樞機不利,氣血津液運行失常,痰瘀內生,發為痰核。而患者中年得病,郁郁不得志,日久情緒不佳,肝氣郁結,乃至少陽樞機失調更甚。少陽膽腑氣機郁滯,膽汁不循其道,上泛至口,故見口苦;郁久膽火內盛,耗傷津液則口干、大便干,膽火擾心則心煩、眠差;足少陽經循脅肋部走行,故見脅痛;少陽樞機失調,陽明氣機受阻,故見納呆。舌質紅、苔微黃膩、脈弦滑均為氣郁痰結之佐證。本病屬淋巴瘤早期,邪氣實而正氣尚足,治宜祛邪為主,以和解少陽、理氣化痰散結為法,方以小柴胡湯為主方加減,輔以化痰散結之品。丘老在運用小柴胡湯治療淋巴瘤患者,柴胡劑量一般在10~15 g,方中柴胡苦平升散,透解郁熱,疏達經氣,黃元御《長沙藥解》載:“瘰疬之證因足少陽之逆,宜柴胡”[26];而黃芩苦寒,清瀉郁熱,實乃和解少陽之要藥,黃芩用量不宜過大,苦寒易傷脾胃,6~15 g為宜;半夏化痰散結;陳皮燥濕化痰;丘老考慮患者正氣尚足,遂易大補之人參為平和之黨參,取其補中益氣生津之效;甘草、大棗調和胃氣。諸藥合用,邪氣可解,少陽得和,樞機開合得利。再配合竹茹清熱解渴除煩,浙貝母清熱化痰散結,赤芍清熱涼血活血,枳殼理氣消痰。另外加服用院內制劑溫膽片清膽和胃,理氣化痰,中藥湯劑與中成藥相輔相成。2診時,患者大部分癥狀改善,治療有效,但患者仍心煩易怒,考慮患者久病肝氣郁結、氣郁化火較甚,予前方基礎上加梔子清心火除煩郁,郁金清肝泄熱,行氣解郁。3診時,患者癥狀基本改善,局部有小淋巴結腫大,考慮患者此時少陽氣機已恢復,但局部痰瘀仍未除去,治療上仍應攻邪。在原方基礎上去補益之黨參、生姜、大棗,予白芥子祛除皮里膜外之痰,天南星加強半夏化痰散結之功,赤芍、牡丹皮涼血活血以消瘀,浙貝母、夏枯草清熱化痰散結,患者仍偶有口干,予太子參、麥冬益氣生津止渴。患者少陽氣機乃復,癥狀基本改善,本次處方已強化化痰散結之功,故停用溫膽片。4診時,患者未訴特殊不適,局部小淋巴結有縮小趨勢,繼續予前方治療。患者期間行放療,后定期門診中醫藥調理,無再訴上述癥狀。
4.2 驗案2患者,女,76歲,2019年7月26日初診。主訴:頭暈、乏力2個月余。患者于2019年4月洗澡時發現左側頸部可觸摸不規則腫塊,2019年5月20日就診,查頸部彩超:左側頸部及鎖骨上窩多發實性結節,考慮異常淋巴結,建議穿刺檢查。2019年5月29日性左頸淋巴結穿刺活檢,病理提示:濾泡性淋巴瘤,Ⅰ級;免疫組化示:瘤細胞CD20(+)、CD79a(+)、CD3(-)、CD5(-)、CD21(+)、CD10(+)、Bcl-2(+)。2019年6月18日PET-CT:左側頸部(Ⅰ-Ⅴ區)、左側腮腺深部、右側頸部(Ⅰb、Ⅱ區)、頸部(Ⅵ區)、右肩三角肌后間隙、雙側腋窩、雙側胸小肌后間隙、雙側鎖骨上區、縱膈(3A)、右側背闊肌深面、右膈上、雙側膈肌角后間隙、雙側腎門區、肝門區、左側腎周、腹膜后、大網膜、腸系膜間、右側髂窩、雙側髂血管旁及雙側腹股溝見多發結節狀及不規則團塊狀放射性攝取異常增高影,最大范圍9.9 cm×5.3 cm×10.1 cm。CT于上述部位見腫大淋巴結及軟組織腫塊影,邊界不清,部分相互融合成團塊,其后腹膜后及腸系膜間病灶包繞臨近血管,與之邊界不清,全身多發結節狀及團塊狀不同程度高代謝病灶,考慮為淋巴瘤多發浸潤;右腎結節狀高代謝病灶,大小約2.0 cm×3.1 cm×3.6 cm,考慮為淋巴瘤浸潤。2019年6月19日骨髓涂片示:骨髓增生活躍,偶見原幼淋細胞;骨髓流式細胞免疫熒光分析報告:粒系、單核細胞表達未見明顯異常;骨髓活檢:增生性骨髓象,造血面積占40%,三系造血細胞數量大致正常,細胞分化良好;免疫組化示:MPO(+)、CD61(+)、CD71(+)。診斷為“濾泡性淋巴瘤(1級ⅣBX期FLIPI-2 4分 高危組)”,交代病情及預后,建議患者行R-CHOP方案治療,患者拒絕行化療。患者遂至丘老門診尋求中醫藥治療。刻診:神清,精神疲倦,頭暈,肢體乏力,少氣懶言,心悸失眠,自汗怕冷,食欲不振,胃納差,大便二日一行,小便正常。近1個月體質量下降2.5 kg。查體:雙側頸部、腋下、腹股溝可觸及不規則腫塊,質硬如石,推之不移;舌淡暗,苔薄白,脈沉細。西醫診斷:濾泡性淋巴瘤(1級ⅣBX期FIPI-2 4分高危組)。中醫診斷:惡核(氣血虧虛)。治法:益氣養血。處方:北柴胡12 g,黃芩10 g,法半夏15 g,人參15 g,生姜10 g,大棗10 g,黃芪15 g,白術15 g,當歸10 g,白芍15 g,煅牡蠣20 g,甘草6 g。14劑,1劑/d,水煎至250 mL,復煎1次,分2次溫服。
2診:2019年8月13日,患者神清,精神改善,頭暈、肢體乏力、睡眠情況、自汗較前稍改善,偶有心悸,怕冷,食欲、胃納改善不明顯,大便二日一行,小便正常;舌淡暗,苔薄白,脈沉細。予前方基礎上加山藥20 g,砂仁10 g,川芎10 g,黃芪增至30 g,白術增至20 g。14劑,1劑/d,水煎至250 mL,復煎1次,分2次溫服。
3診:2019年8月28日,患者神清,精神一般,諸癥較前好轉;舌淡暗,苔薄白,脈沉弦。守2診方鞏固2個月。服藥后患者自覺癥狀明顯改善,堅持門診中醫藥治療,基本予小柴胡湯為主方加減以調和少陽氣機,輔以扶正化痰、祛瘀散結等治療方法,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質量及免疫功能,隨訪至2020年8月20日,患者生活如常人,實現“帶瘤生存”的目標。
按語:患者老年女性,確診為濾泡性淋巴瘤,未經系統抗腫瘤治療。患者初診時主要表現為神疲、頭暈、乏力、少氣懶言等一派虛象,結合患者舌淡暗、苔薄白、脈沉細等舌脈表現,四診合參,辨病為“惡核”,辨證當屬氣血虧虛。由于少陽樞機不利,氣血津液運化失常,痰瘀毒始生,交結體內,發為惡核。緣于患者年事已高,正氣不足,氣血化生不足,罹患此難,正氣愈虛,痰瘀毒內盛,阻滯氣血,耗傷大量氣血津液,以致氣血虧虛。氣血不足,不能上榮頭目,故見神疲、頭暈;不能濡養四肢,故見肢體乏力;不能滋養心脈,故見心悸失眠。患者年老體弱,脾腎之氣漸衰,腎乃先天之本,腎氣不足,固攝失司,故見怕冷自汗,脾乃后天之本,脾氣虧虛,運化水谷無力,故見食欲不振、胃納差。舌脈均為氣血虧虛之佐證。本例患者屬淋巴瘤晚期,邪毒內盛,臟氣虛損,正氣虧虛,抗邪無力,故治療當以扶正固本為主,以補益氣血為法。治病求本,以和解少陽為其基本治療則。方以小柴胡湯為主方加補益氣血之品。方中柴胡、黃芩和解少陽以調達少陽樞機,半夏、生姜化痰消飲以暢達三焦水道,少陽樞機得復,氣血津液輸布得當,痰瘀不成,痰核不長;人參、大棗、甘草扶助少陽正氣;黃芪甘溫,補氣生血而益肌表以止汗;白術益脾精、養胃氣以生氣血;當歸養血活血;白芍酸甘,滋養心肝以調和陰陽;牡蠣咸平軟堅,性澀能斂心神而止驚悸。丘老以為,患者初診之時,一派虛弱之象,不可過補,補益之品劑量不可過大,故在使用補益之藥物時,用藥劑量在10~15 g,需循序漸進,徐徐圖之。2診時,患者精神、頭暈、乏力等較前緩解,考慮此法有效,繼續沿用前方,稍微加大黃芪、白術用量以補益正氣,并加血中氣藥之川芎以理氣行血;另外,患者食欲、胃納仍欠佳,予加用甘平之山藥以補中益脾和胃,砂仁和中調滯以復脾胃之升清降濁。3診時,患者諸癥明顯改善,初見成效,繼續予前方鞏固。患者門診隨診,未見上述癥狀再發。
兩案同為淋巴瘤,其治法、用藥雖不盡相同,但都以和解少陽為基本治療原則。丘老強調,少陽樞機不利為淋巴瘤的核心病機,貫穿淋巴瘤發病進展的全過程,因此當謹守病機,從少陽入手,以調暢少陽樞機為基本治療原則,有提綱挈領之效,是淋巴瘤治療的根本大法。臨證時需辨清早中晚期、辨清虛實,辨證用藥上以小柴胡湯為基礎方靈活運用加減,可使得氣機暢、三焦通、痰瘀去、熱毒清,正氣復來,提高臨床療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