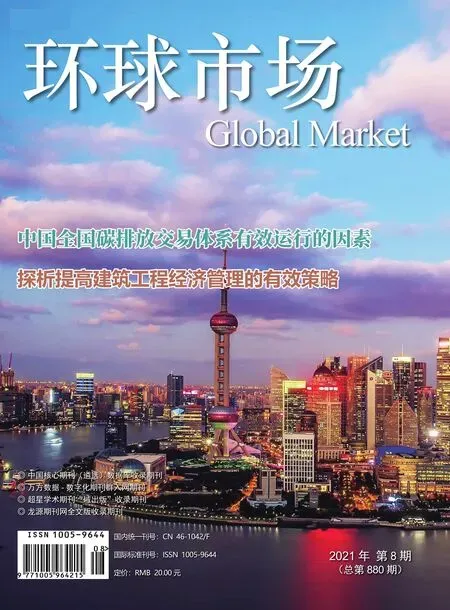貸款集中度對我國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的影響
余慧倫 華南理工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
當前背景下,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密切交織,金融體系的穩定與否直接關系到經濟發展、工人就業以及人民生活等方方面面。而在我國,商業銀行在金融市場中仍處于主體地位,在金融體系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商業銀行的風險問題尤為需要關注。
今年新冠疫情之下,全球一度停工停產,生產消費停滯,實體經濟受挫,在此背景下,實體企業貸款可能爆發大規模違約,于是商業銀行面臨的信用風險成為備受關注的問題。信用風險是銀行自誕生起就面臨的最大風險。2011 年以來,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一路上行,增長翻番,商業銀行面臨的信用風險正嚴重加劇。而銀行習慣性“壘大戶”的做法往往使其出現大額風險暴露,最終可能加劇銀行面臨的信用風險。本文擬針對貸款集中度對我國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的影響進行探究,以期為銀行信用風險管理提供建議。
一、文獻綜述和研究假設
關于貸款集中度對銀行信用風險的影響,學術界大多認為貸款集中度的提高會通過強化風險聚集,進而加大銀行面臨的信用風險。美國經濟學家馬克維茨(Markowitz)1952 年提出的投資組合理論中,強調了分散投資的重要性。發放貸款是商業銀行的一種投資行為,集中的貸款投放與集中的投資組合一樣,不利于消解個體風險。在貸款集中的情況下,一旦重要客戶因經營不善出現清償困難,銀行的不良貸款就會顯著增多,此時相對貸款分散的情形,貸款集中會讓銀行面臨更加難以承受的信用風險。巴曙松等(2010[1])認為銀行在授信時存在“壘大戶”現象,一旦出現經濟下滑,大型企業的財務困境會對未分散風險的銀行造成巨大沖擊。周春喜等(2018[2])基于我國城市商業銀行的數據,研究發現貸款集中度對資產質量具有負面影響,其中客戶集中度的影響比較顯著。
此外,也有學者持相反觀點,認為貸款集中度的提高會帶來專業化效益,從而減小銀行面臨的信用風險。針對貸款集中帶來的專家效應和信息優勢,Berger 等(2017[3])進行了精準深入的探究。其基于風險管理協會(RMA)提供的銀行級別數據集,檢驗銀行的貸款集中度與其索要的財務信息之間的關系,發現貸款集中度較高的銀行,收集經審計的借款人財務報表的傾向較小,這意味著銀行貸款集中度與銀行專業知識緊密相關,這種專業知識替代了高質量的信息,如經審計的財務報表。Winton(1999[4])發現,貸款集中度與不良貸款之間呈負相關關系,其內在機制在于貸款集中化可以有效增強銀行的信息獲取能力,提高銀行的專業化水平和信貸管理能力,從而優化貸款質量。基于以上分析,針對貸款集中度與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的關系,本文提出如下對立假設:
假設1a:貸款集中度的提高會提升不良貸款率,增大商業銀行面臨的信用風險。
假設1b:貸款集中度的提高會降低不良貸款率,減小商業銀行面臨的信用風險。
二、模型構建和實證分析
本文研究的主題是貸款集中度對我國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的影響。被解釋變量是反映銀行信用風險的不良貸款率,核心解釋變量是反映銀行貸款集中度的單一最大客戶貸款比率和最大十家客戶貸款比率。此外,本文還控制了時間效應,并加入了銀行個體層面的一些控制變量。本文銀行個體層面控制變量選取的是反映商業銀行個體規模的總資產,反映商業銀行風險抵御及償債能力的資本充足率,反映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水平的貸存比,反映商業銀行周轉和營運情況的資產周轉率,反映商業銀行凈利息收入水平的凈利差,反映商業銀行股東投資收益情況的ROE。其中,當期的凈利差和ROE 在不同維度上反映了商業銀行當期的盈利能力,而當期的不良貸款率通常會比較直接地影響到商業銀行當期的收益,因此為規避反向因果導致的模型內生性問題,對于這兩個變量,本文選用滯后一期的形式加入模型。本文構建了如下所示的控制了時間效應的固定效應面板數據模型:

其中,NPLit代表的是銀行i 在t 期的不良貸款率,LCit代表的是銀行i 在t 期的貸款集中度,Xit代表的是控制變量向量集,ai代表的是銀行虛擬變量向量集,ut代表的是時間虛擬變量向量集。本文研究的樣本區間是2007-2018 年。變量選取和相關說明如表1 所示。
本文的貸款集中度數據是Wind 數據庫和國泰安數據庫中相關數據互補得到的結果,不良貸款率數據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銀行個體層面控制變量數據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Wind 數據庫和BankScope 數據庫。
表2 展示的是單一最大客戶貸款比率對不良貸款率的影響,表3 展示的是最大十家客戶貸款比率對不良貸款率的影響。從中可看到,逐步加入控制變量之后,貸款集中度對不良貸款率的影響始終顯著為正,于是假設1a 得到了驗證。貸款集中度的提高確實會顯著增大商業銀行面臨的信用風險,商業銀行不應采取“壘大戶”的做法,在貸款客戶投向維度,應盡量分散化放貸。
由上文可知貸款集中度的提高會提升不良貸款率,下面對這一影響進行不同銀行類別的異質性分析,方法是加入銀行類別變量以及客戶集中度和銀行類別變量的交乘項。同時,為保留不同類別間的個體特征差異,采用了控制時間效應的面板數據混合OLS模型。除了控制時間效應之外,還控制了基礎回歸模型中所控制的銀行個體層面變量。本文將我國商業銀行劃分為大型銀行、中小型銀行和外資銀行。其中,大型銀行包括國有行和股份行這兩類全國性大型銀行,中小型銀行包括城商行和農商行這兩類區域性中小型銀行。從表4 中模型(3)可看出,外資行的不良貸款率相對較低。從模型(1)、模型(2)可看出,相對于其他銀行,大型銀行的單一最大客戶貸款比率對不良貸款率的影響更小,而中小型銀行的單一最大客戶貸款比率對不良貸款率的影響更大,因此中小型銀行更應警惕由于客戶集中度過高而帶來的信用風險。以上結論對于以最大十家客戶貸款比率代表的客戶集中度而言,盡管顯著程度不高,但仍然適用。

表1 變量選取與說明

表2 單一最大客戶貸款比率對NPL 的影響

表3 最大十家客戶貸款比率對NPL 的影響
探究完貸款客戶集中度對不良貸款率影響的銀行間異質性后,本文接著探究這一影響是否存在門限效應,即當某一變量突破某一閾值之后,這一影響是否將發生結構性突變。本文利用Stata 的xthreg 命令來檢驗門限效應是否存在。xthreg 命令要求所使用的數據為平衡面板數據,本文對年度數和截面樣本數進行綜合考慮后,決定選用2009-2018 年期間各變量數據完整的樣本進行門限回歸。同時為使樣本量盡可能大,門限模型的控制變量中不加入L.凈利差和L.ROE。從表5 門限值檢驗中看到,單一最大客戶貸款比率門限模型的門限效應不顯著,因此下文僅對最大十家客戶貸款比率門限模型進行門限回歸,結果如表6 所示。從表6 中看到,當最大十家客戶貸款比率超過門限值41.42%時,其對不良貸款率將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而低于這一門限值時該影響不顯著。因此,商業銀行和監管當局應警惕41.42%這一臨界值,當最大十家客戶貸款比率超過這一臨界值時,需要適當加以干預,分散對客戶的貸款,以減少聚集性違約風險的發生。另外還可看到,考慮門限效應后,模型的擬合優度大大提升,從表3 模型(3)的0.224 大幅提升至表6 的0.632。
最后,本文對主要模型進行穩健性檢驗。穩健性檢驗方法之一是采用替換被解釋變量的方法,用同樣象征商業銀行信用風險的“撥備覆蓋率”替換原先的“不良貸款率”進行探究;穩健性檢驗方法之二是采用替換某一控制變量的方法,用象征銀行杠桿倍數和償債能力的“權益乘數”代替象征銀行風險抵御和償債能力的“資本充足率”進行探究。經過上述檢驗,發現本文的主要結論“貸款集中度的提升會提高商業銀行信用風險”是非常穩健的。同時,經過豪斯曼內生性檢驗,發現本文的主要模型不存在內生性問題。因此,本文的研究成果具備較高的可信度。

表4 貸款集中度對NPL 影響的異質性分析

表5 門限值個數及其顯著性檢驗

表6 最大十家客戶貸款比率對NPL 影響的門限效應
三、結語
本文通過實證研究,發現貸款客戶集中度的提高會提升不良貸款率,加大商業銀行的信用風險。相對于其他銀行,大型銀行的客戶集中度對不良貸款率的影響更小,而中小型銀行的客戶集中度對不良貸款率的影響更大,因此中小型銀行更應警惕由于客戶集中度過高而帶來的信用風險。另外,最大十家客戶貸款比率影響不良貸款率的模型存在顯著的門限效應,當最大十家客戶貸款比率未超過門限值41.42%時,其對不良貸款率不產生顯著影響,而當最大十家客戶貸款比率超過門限值41.42%時,其對不良貸款率將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因此,建議監管部門重點關注商業銀行最大十家客戶貸款比率是否超過41.42%,并對超過這一閾值的銀行加強監管,以防范其出現嚴重的信用違約風險。
注釋
① 指銀行個體層面的總資產、資本充足率、貸存比、資產周轉率、L.凈利差、L.ROE 六個變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