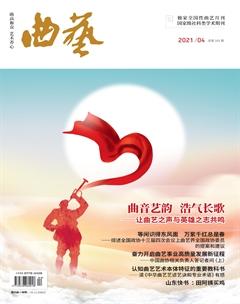視角
吳新伯
曲藝作品歷來講求人物塑造,而境遇、抱負、才能、成就殊異常人者更是描畫的重點,在長篇蘇州評話《水滸》中,力殺四虎的李逵、倒拔垂楊柳的魯智深、能手托千斤石的武松等就可以視為代表。
藝術不能脫離時代需要而單獨存在,曲藝亦是如此。長期以來,曲藝作為不入流的什樣雜耍,在內容展現方面就必然會有意無意地導入當時底層群眾的心理需求。如《七劍十三俠》第一回稱貪官污吏、惡勢土豪、假仁假義等3種人為“王法治他不得”的“極惡之人”,所以需要“那異人、俠士、劍客之流去收拾他”。反觀中國漫長的帝制時代,黎民黔首遭遇的不公正,絕大多數都源于“極惡之人”,在投告無門的絕望情境下,他們只能祈求俠士劍客以英雄之姿匡正扶弱,所以《醒世恒言·李汧公窮邸遇俠客》中才有“安得劍仙床下士,人間遍取不平人”之語。但既是“安得劍仙床下士”,可見人間不平常有而英雄不常有,所以龔自珍才會感嘆“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俠骨恐無多”。就此而言,傳統英雄類型曲藝作品,可以看作是底層百姓“英雄夢”的藝術投影。
悉尼·胡克在論及公眾對英雄人物感興趣的心理根源時認為,首先這是一種“心理安全的需要”,“時代不太混亂,特別是教育又有利于啟發成熟的批判能力,而不把人們的注意力固定在無條件服從的幼稚反應上,在這種情況下,尋找父親替身的需要就相應地減弱了。”反之,公眾將努力地尋找、祈求精神上的“父母”,以獲得安全感和情緒上的穩定。帝制時代的中國,長期缺乏啟蒙與教育的土壤,在治亂興衰、朝代興替的歷史螺旋中掙扎的底層群眾,會將自身的安全與正義寄托在能“以武犯禁”的“劍仙床下士”上,并可能在藝術領域構筑起狹隘的帝王將相或者超人異士英雄史觀,進而導致傳統英雄類型作品的出現。
此類作品寄托著群眾的理想,逸散出的敢于斗爭不屈不撓的氣質和精神是值得我們繼承的。但身處一個偉大的時代,我們觀照英雄的視角必須要有改變。列寧認為,“歷史早已證明,偉大的革命斗爭會造就偉大人物,使過去不可能發揮的天才發揮出來”,這事實上是用歷史唯物主義為狹隘的帝王將相英雄史觀祛魅,回答了英雄從哪里來的重要問題。毛澤東同志更是旗幟鮮明地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英雄不是高踞神座的神靈,不是降生塵世的彌賽亞,更不是離群索居的獨行俠,而是從人民中來,到人民中去,為人民服務,與人民有深厚“魚水”情的杰出奉獻者。任何一位英雄,一旦脫離人民群眾,就如同雙腳離開大地的巨神安泰,終將失去所有。曲藝工作者應該積極改變觀察英雄的視角和尋找英雄的方式,掙脫帝王將相英雄史觀的桎梏,用心發現人民中英雄的感人事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歌頌時代歌頌當代英雄的作品不斷涌現,單在蘇州評話中,就有《橋隆飆》《林海雪原》《江南紅》《紅日》等多部長篇書目及為數眾多的中短篇作品問世。但在強大藝術慣性的作用下,我們在描畫人民英雄時,還是在自覺不自覺中或多或少地使用了一些套路,部分作品中的英雄能感動人卻帶著“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的疏離感。所以,在現代曲藝作品中如何適度摒棄將英雄塑造為“超人”的觀念,讓英雄回到生活中,長出豐滿的肌肉和真實的骨骼,這應該是我們思考的一個課題。
在近年的創演實踐中,我總結出了一些經驗,不敢稱為標準,謹在此提出,請各位方家品評。
從“仰視”到“平視”,彰顯英雄的人民本質。鄧稼先是我創作的短篇評話《往事不如煙》的主角,是“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我國核武器理論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是當之無愧的國家脊梁、民族英雄。如果用傳統的創作視角去觀摩鄧稼先,就可能會將之描畫為一個具備“高大全”特質的“樣板戲”式的人物,故事的走向會越來越不接地氣。因為在之前的創作中有過類似的感受,所以創作《往事不如煙》時,在“鄧稼先舍身入沙漠拾撿未能爆炸的原子彈摔裂的碎片”這一足能彰顯他“許身國威壯河山”英雄氣質的情節后,整個作品趨向平緩,直至結尾時。
今天是1986年5月2日,直腸癌晚期的鄧稼先已經相當虛弱,他躺在床上只能打針才能止痛,病魔正折磨著他。“小許,給我把床頭柜里的那個紫紅色的盒子拿來。”“嗯。”
小許叫許鹿希,是鄧稼先的愛人,她拿過了盒子交到俚手里。鄧稼先慢慢地打開盒子,露出了一枚金光閃閃的全國勞模獎章,這是昨天在床上收到的,他反反復復看了好幾十遍。“鹿希啊,這是國家授予我的榮譽,我鄧稼先這一輩子活得值了,值了!對國家我盡力了,可是對家里我照顧得實在太少太少,讓你一個人受累了。如果有來生,我一定支持你去做一番大事業,我來照顧你和孩子,只是不知道下輩子你還愿不愿意嫁給我喔?”“愿意、愿意!”許鹿希緊緊抓住了老鄧的手,越抓越緊,越抓越緊。
對榮譽的珍視是對自我的肯定,對妻子的愧疚基于對家庭的眷戀。無情未必真豪杰,憐子如何不丈夫,“許國”“許家”于斯統一,極大豐滿了鄧稼先的人物形象。這不但不會損害“兩彈元勛”的光輝形象,反而會在光芒之下營造出更有現實效果的“血肉”,讓人物變得更有觸感,更富靈性。
從“平視”到“仰視”,發掘普通人的英雄潛質。英雄事跡可以壯懷激烈,也可以平實感人。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為實現民族獨立、國家發展、社會進步、人民和諧安居而作出真實貢獻之人,都可以被稱為英雄。短篇評話《青花瓷》就講述了一個“平民彰顯英雄氣”的故事。
一次文物展覽會展出了一只離開祖國近80年的青花瓷瓶。這瓷瓶是當年隱居上海的潘家母女盡全力保護下來的。抗日戰爭時期,倭奴侵略者聞聽潘家有這樣一只乾隆時期的寶物,上門索取。這是一場力量完全失衡的絕望的斗爭,潘家母女用什么來反抗倭奴的刺刀呢?
故事似乎已成定局,但在青花瓷瓶將被侵略者搶走時,一段情節就這樣展開了。
女兒潘汝楨舉起手里的青花瓷瓶準備與敵人同歸于盡,母親見此情景急忙阻止,“女兒啊,你把這個瓶給他們吧。”
“不!我不給!我情愿摔了,也不能給強盜拿去。”“聽媽的話,你給他們。”“不,爹爹臨終前,我答應他,絕不讓日本人拿去,我不給!”“汝楨啊,你聽娘的話,如果你今天把它摔了,這些人可是什么都干得出的。整個潘家灣全村老小都要遭殃,你就讓他們拿去吧。這么好的東西,摔成碎片也太可惜。你講得不錯,他們是強盜,我們碰到強盜有啥辦法呢?”“這個……”“你放心,你爹爹不會怪我們的。”
汝楨娘一邊說一邊從女兒手里接過這個瓷瓶,轉過身來:“青木,你拿去吧。”
青木怎么也想不到潘老太會說服女兒把瓷瓶交給自己,果然姜還是老的辣,我的這點心思老太全看穿了。青木起手將瓷瓶接到手里:“潘太太,好!青木佩服!今天看在潘太太的份上,我就放過你們!走!”青木集合獸群,轉身正要離開。
“慢!青木你聽著,這只瓷瓶雖然給了你們,但是它上面繪的是我們中國人的青花,底下寫的是我們乾隆皇帝的款。現在我們國力衰弱,保護不了它,只能看著它流落天涯。不過總有一天中國會強盛起來,到這個時候,它一定會回來,回到自己祖國來的!”
說完潘老太縱身一躍投井而去!
“媽媽!”
這段書不但把之前略顯平穩的書情推向了高潮,也在峰回路轉中將潘家母女的愛國之情和精神力量描寫到了極致。
弱國無外交,落后就要挨打。古老的中國是帶著首都被外敵攻破兩次的恥辱走過20世紀前50年的,積貧積弱的國家不可能成為民眾自豪的源泉,更不可能為民眾提供有尊嚴的庇護。獻出生命這最后最寶貴的東西,將靈魂與希望寄托于未來必將刺破黑暗天幕的光芒中,這是在那個特殊的歷史背景下,普通人最悲壯但最決絕的舉動。由此噴薄出的英雄之氣,會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形成震撼天地的巨大共鳴。
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一個半個恥臣戎。萬里腥膻如許,千古英靈安在,磅礴幾時通。胡運何須問,赫日自當中。
一般來說,以上兩種視角常用于短篇作品中。而在創作中長篇作品時,因其篇幅較大,內容較多,一種“廣角人物塑造法”可能更為適用。
中篇蘇州評話《我愛這藍色的海洋》梳理了中國航母從無到有的過程。一個剛登上“遼寧”號航空母艦的年輕女兵在中秋月圓之時,給身為中國海軍老兵的爺爺在視頻中唱起了《我愛這藍色的海洋》,故事于斯展開,爺爺的思緒變成了一個廣角鏡頭,把中國航母誕生過程中的風風雨雨和英雄人物都囊括了進來。
“瓦良格”號歸國變成“遼寧”號的曲折歷程,“飛鯊”騰空一躍的歡欣鼓舞,“山東”號國產航母下水時的舉國歡慶,中國海軍由淺藍走向深藍,作品情節一路前行,殷殷期盼的劉華清將軍、堅守崗位的“飛鯊”總設計師羅陽、在刀鋒上起舞的“航母戰斗機英雄試飛員”戴明盟、為保護戰機犧牲自己的飛行員張超、航母女通信兵燕子、身為海軍老兵的爺爺,當年泰州海軍基地的送菜小姑娘等形象一一閃過,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群像。通過中國航母從無到有的故事,一群為強國強軍無私奉獻的英雄躍然而出。就此而言,“廣角人物塑造法”所能展現的,是一種英雄的氣場。
英雄的故事在我們腦海中縈繞,英雄的聲音在山川間回蕩,英雄的精神在我們血液中流淌。什么都可以沒有,但不能沒有夢;什么都可以沒有,但不能沒有英雄。在新時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歷史征程中,我們需要英雄補足精神之鈣、騰躍信仰之火、筑牢前進之基。人民創造了歷史,英雄從人民中誕生,曲藝工作者所要做的,就是從不同的視角出發,用不同的方式實現一個共同的目的——
將這一股人間的英雄氣鍛造為作品的筋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