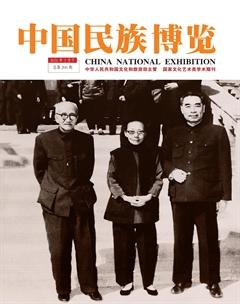文人畫“以書入畫”摭論
吳亞賓 黃新黎
【摘要】“以書入畫”乃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提出的關于人物畫的繪畫理論。宋代文人畫理論得以興起,以蘇軾、米芾等為代表的文人畫家對“以書入畫”進行了初步探索;直至元代,文人畫理論進入盛行時期,由人物、山水推之于竹石花卉等題材,且對“以書入畫”作了理論總結與實踐推進。本文筆者旨在對文人畫“以書入畫”的發(fā)展脈絡進行條分縷析,進而廓清“以書入畫”對文人畫成熟發(fā)展的重要影響,以及其對當代繪畫創(chuàng)作的鑒誡意義。
【關鍵詞】文人畫;以書入畫;意義
【中圖分類號】J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198(2021)04-172-03
【本文著錄格式】吳亞賓,黃新黎.文人畫“以書入畫”摭論[J].中國民族博覽,2021,02(04):172-174.
一、“以書入畫”的起源
在中國畫史上,據(jù)傳陸探微最早將東漢張芝的草書體運用到繪畫中,可惜今已難再見到其畫跡。然而,關于書畫用筆問題,張彥遠曾舉例說明:
“昔張芝學崔瑗、杜度草書之法,因而變之,以成今草。書之體勢,一筆而成,氣脈通連,隔行不斷,唯王子敬明其深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繼其前行,世上謂之一筆書;其后陸探微亦作一筆畫,連綿不斷,故知書畫用筆同法。陸探微精利潤媚,新奇妙絕,名高宋代,時無等倫;張僧繇點曳斫拂,依衛(wèi)夫人《筆陣圖》,一點一畫,別是一巧,鉤戟利劍森森然,又知書畫用筆同矣;國朝吳道玄,古今獨步,前不見顧陸,后無來者,授筆法于張旭,此又知書畫用筆同矣”。[1]
由此可見,繪畫與書法在用筆上有共通之處,也從側面闡明“以書入畫”的合理性。此外,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亦記載:
“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于立意而歸乎用筆,故工畫者多善書”。[2]
從這句話中足以看出繪畫的形似要靠骨氣,而骨氣來源于用筆,可見用筆對繪畫的重要性。筆者認為,其實質是對南朝謝赫六法論中“骨法用筆”的強化。而“骨法用筆”本意即指由線條帶來的力量感,筆路清晰而線質遒勁有力,達到“力透紙背”的效果,而這正是書法用筆的追求。可見,“以書入畫”對于繪畫本身線條質量的提升是大有裨益的。
自古以來,中國畫著重象征地表達方式,以自然論道,以山水寄情,以梅蘭竹菊隱喻君子,這些皆是文人畫家借具象事物來抒情達意。而書法和中國畫有一個最本質的共性,即筆墨工具。筆墨工具材料使用的一致性為“以書入畫”提供了物質基礎,然僅僅有物質基礎對于“以書入畫”是遠遠不夠的,書法與中國畫還有著相似地表達方式。眾所周知,中國畫以點、線、面為表現(xiàn)語言,而書法也不外乎如此,我們分析一件書法作品,無外乎“點畫結字,空間布白”,即筆法、字法、章法諸方面。此外,中國畫講究含蓄美,筆不周而意周,正如張彥遠評顧愷之繪畫為“意存筆先,畫盡意在”,而這正與書法上“意在筆先”“筆斷意連”有異曲同工之妙。可見“以書入畫”不僅要以書法用筆入畫,也要以書法的美學意蘊入畫。
二、“以書入畫”的發(fā)展
(一)以書入畫,重意輕法
文人畫始于唐代王維,其有別于院體畫和民間繪畫,講究筆墨情趣,重神韻。至宋代,在“重文抑武”的社會背景下,再加上統(tǒng)治者對繪畫藝術的青睞以及大量文人階層的積極參與,以繪畫抒發(fā)性情,沖破傳統(tǒng)繪畫規(guī)則的束縛,從而促進了文人畫理論的興起。而蘇軾、米芾等人作為當時極具影響力的文人書畫家,其書畫藝術主張在當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蘇軾在題畫詩《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中提道:“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3]米芾《畫史》亦記載:“山水古今相師,少有出塵格者,因信筆作之,多煙云掩映,樹石不取細,意似便已”。[4]足見蘇、米二人對繪畫“神似”的強調。然在書法上亦有相關論述,南朝書家王僧虔《筆意贊》云:“書之妙道,神采為上,形質次之,兼之者方可紹于古人”。[5]虞世南《筆髓論》亦云:“書道玄妙,必資神遇,不可以力求也。機巧必須心悟,不可以目取也。字形者,如目之視也。……假筆轉心,妙非毫端之妙。必在澄心運思至微妙之間,神應思徹”。[6]由此可見,書法與繪畫的“重神似”使其有著美學意蘊上的聯(lián)系。
此外,關于“以書入畫”,蘇軾進行了實踐性探索,從黃山谷評蘇軾《枯木圖》“出入顏(真卿)楊凝式”足以窺見。郭熙在《林泉高致》中也提道:
“故說者謂王右軍喜鵝,意在取其轉項,如人之執(zhí)筆轉腕以結字,此正與論畫用筆同。故世之人多謂善書者,往往善畫,蓋由其轉腕用筆之不滯也”。[7]
可見書法技法已巧妙運用至繪畫實踐中。郭熙所言“善書者,往往善畫”即擅長書法的人往往有助于繪畫的學習,而蘇軾、文同、米芾等人的繪畫實踐正是其有力的見證。例如,文同在對月光下竹影認真觀察后,以行草書筆意進行“寫”竹,“以書入畫”在其墨竹畫中被詮釋得淋漓盡致;米芾作為宋四家之一,其在晚年行書作品《珊瑚帖》中隨筆畫出一枝珊瑚,用筆率意自然,線條沉著痛快,不求形似,真正達到“無意于佳乃佳”的精神境界。這種“以書入畫”與“以畫入書”的完美契合實為相得益彰。然而,這亦是一種“重意輕法”的體現(xiàn)。
綜上所述,無論文同的“寫”竹,抑或米芾的“墨戲”,皆是對宋代“繁瑣寫實”院體畫的間接性反抗,這是文人畫家的審美情懷,也是繪畫化繁為簡、重意輕法的寫意體現(xiàn)。然而,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宋代院體畫依然占據(jù)主導地位,其與統(tǒng)治者的主張有關,正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由于蘇軾、米芾等畫家對文人畫理論的探索,才有了文人畫理論的興起,同時也為元代文人畫的成熟發(fā)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以書入畫,揮寫逸氣
到了元代,統(tǒng)治階級的文化素養(yǎng)雖然不能與宋代相比,但是其提倡文人“士氣”,極力反對媚俗之作,以此來彰顯獨立之人格,而其代表人物當屬趙孟頫。趙孟頫是個全能型書畫家,集詩、書、畫于一身,有極高的藝術修養(yǎng)。關于“以書入畫”,趙孟頫有其獨到的見解,他在《秀石疏竹圖》卷中題詩道:
“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還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會此,方知書畫本來同”。[8]
這首詩中的“飛白”指的是書法中的一種特殊筆法,筆畫中夾雜絲絲白痕,類似于枯筆,相傳由蔡邕提出;“籀”有篆籀之意,又稱大篆,《石鼓文》乃其代表作,其多以中鋒用筆;“八法”指用筆八法,即側(點)、勒(橫)、努(直)、趯(鉤)、策(仰橫)、掠(長撇)、啄(短撇)、磔(捺)。顯而易見,這就是典型的“以書入畫”。
從趙孟頫《秀石疏竹圖》這幅作品亦足以看出,其書法用筆比比皆是。例如“飛白”“篆籀筆意”“行草書筆意”等等。畫中用墨濃淡相間,用筆時而頓挫,時而靈動;時而含蓄,時而張揚。實乃“如見其揮運之時”[9]也!再細的線條、再小的筆畫在趙孟頫的筆下皆表現(xiàn)得遒勁有力、形態(tài)多姿。正如蔡邕《九勢》所云:“惟筆軟則奇怪生焉”。[10]此外,趙孟頫曾提道:“今人但知用筆纖細,傅色濃艷,便自謂能手。殊不知古意既虧,百病橫生,豈可觀也?吾所作畫,似乎簡率,然識者知其近古,故以為佳。此可為知者道,不為不知者說也”。[11]可見趙孟頫對院體畫“用筆纖細,傅色濃艷”的強烈批判,進而凸顯出其對文人畫“以書入畫”的重視程度。總之,由于趙孟頫對“以書入畫”理論與實踐的全面開拓,促進了“以書入畫”在元代的成熟發(fā)展,且從一定程度上確立了后世文人畫審美方式的新趨勢。
然而,關于趙孟頫提倡的“以書入畫”,錢選的“士氣”說與其亦有相似之處,從二人的談論中可以窺見:
趙文敏問畫道于錢舜舉,何以稱士氣?錢曰:“隸體耳。畫史能辨之,即可無翼而飛,不爾便落邪道,愈工愈遠;然又有關棙,要得無求于世,不以贊毀撓懷”。[12]
趙子昂問錢舜舉曰:“如何是士夫畫?”舜舉答曰:“隸家畫也”。子昂曰:“然觀之王維、李成、徐熙、李伯時,皆士夫之高尚,所畫蓋與物傳神,盡其妙也。近世作士夫畫者,其謬甚矣”。[13]
錢選所言“隸體”“隸家畫”有兩層含義:其一,書法體;其二,有別于畫匠的“外行畫”[14]。筆者認為,無論理解成何種含義,其主旨意蘊皆凸顯了文人畫“以書入畫”的重要性。而趙孟頫所言“近世作士夫畫者,其謬甚矣”中的“近世作士夫畫者”應指宋代蘇軾等文人畫家,從中可見趙孟頫的批判具有一定的客觀性,其是站在文人畫“以書入畫”基礎之上,對繪畫本身技法提出的高要求,糾正了以蘇軾為代表的文人畫家盲目貶低院體畫,標榜文人畫重意輕法的偏執(zhí)觀念,進一步推進了文人畫理論的成熟發(fā)展。
雖然趙孟頫對文人畫“以書入畫”進行了完善發(fā)展,但是真正以實踐全面踐行文人畫“以書入畫”,開創(chuàng)文人畫新局面的當屬元四家,即黃公望、倪云林、王蒙、吳鎮(zhèn)。此四人超脫世俗,頗有隱士風范,其在繪畫中多以反映“隱逸”山水和象征高尚人格精神的梅、蘭、竹、菊、松、石等為題材,極力強調脫俗,講究揮寫“逸氣”,以達到弘揚文人畫風氣,同時也進一步提升了文人畫“以書入畫”的高度。
關于“逸”的話題,歷來皆有評論,莫衷一是。宋鄧椿《畫繼雜說》提道:“自昔鑒賞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獨唐朱景真撰唐賢畫錄,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后黃休復作益州名畫記,乃以逸為先而以神妙能次之。景真雖云:‘逸格不拘常法,用表賢愚,然逸之高,豈得附于三品之末?未若休復首推之為當也”。[15]除此之外,黃休復還將“逸”詮釋為“拙規(guī)矩于方圓,鄙精研于彩繪”,此論極為精辟,至今仍被廣泛沿用。元黃公望亦云:“畫一窠一石,當逸墨撇脫,有士人家風,纔多便入畫工之流矣”。[16]以及倪云林的“逸筆草草”“聊以寫胸中逸氣”等等,可見他們對“逸”的重視程度。筆者認為,“逸”是一種忌繪尚寫、忌工尚意的審美追求,“工”“繪”皆有用筆千篇一律、繁瑣枯燥,缺乏生動變化之感,而要改變這一現(xiàn)狀,即需加入豐富的書法用筆為其畫面增添筆墨意趣。正如柯九思《丹邱題跋》云:“寫竹干用篆法,枝用草書法,寫葉用八分法,或用魯公撇筆法,木石用折釵股、屋漏痕之遺意”。[17]清代蔣驥《讀畫紀聞》亦有相關論述:“書畫一體,為其有筆氣也。此語為士大夫言之,如工人軟弱之筆,雖布置縝密,設色鮮明,終近乎俗。……古人皴法不同,如書家之各立門戶。其自成一體,亦可于書法中求之。如解索皴則有篆意,亂麻皴則有草意,雨點皴則有楷意,折帶皴可用銳穎,斧劈皴可用退筆”。[18]
此外,以元四家為代表的文人畫還有一個較為明顯的特征,即題款內容占據(jù)整個畫面較大比重,乃整個畫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與整個畫面存在著一種相互依托、相輔相成的內在聯(lián)系,而不再只是標識性作用。由此可見,元代文人畫的題款不僅強調畫家的書法功底,更注重畫家文學素養(yǎng)與個人性情的綜合體現(xiàn)。正如李澤厚所言:“所謂‘文人畫,當然有其基本特征。這首先是文學趣味的異常突出”。[19]筆者認為,這是對“以書入畫”的進一步升華,其對后世畫家重書法、重文學素養(yǎng)的觀念樹立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三、“以書入畫”的影響
文人畫“以書入畫”雖然在宋元時期得以興起與成熟發(fā)展,但是在后期依然從不同程度上影響著眾多文人畫家。例如,徐渭在“以書入畫”基礎上對用墨的重視,其所“寫”花卉筆暢墨酣,氣韻生動,極具創(chuàng)新精神;莫是龍、董其昌、陳繼儒及沈顥提出“南北宗論”,在“以書入畫”上喻以禪宗思想;石濤的“字與畫者,其具兩端,其功一體”書畫觀,以及“不似之似”之畫理,正如其詩云:“名山許游未許畫,畫必似之山必怪。變幻神奇懵懂間,不似之似當下拜”。[20]可見石濤的“不似之似”是對蘇軾、米芾等人文人畫“重神似”的進一步深化。而石濤的繪畫亦不再僅僅局限于抒發(fā)個人性情,其是借筆墨書寫天地萬物,實乃“重筆墨,輕丘壑”,有師古而不泥古之境界;以及近現(xiàn)代畫家白蕉的蘭草“葉葉出草法,瓣瓣入楷意”等等。可見他們皆是在“以書入畫”基礎上進行自我發(fā)揮,從而創(chuàng)造出獨屬于自己的繪畫審美主見。筆者認為,他們的這種革新精神從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以書入畫”在后世的良性發(fā)展,然而我們也要學會以辯證的思維看待“以書入畫”,不能一味盲目地追求“以書入畫”,而過分地強調書法用筆,忽視繪畫本身對技法提出的高要求。這是當代書畫家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
四、結語
自張彥遠提出“以書入畫”以來,宋代在蘇軾、米芾等文人畫家的初步探索下,形成了“以書入畫,重意輕法”的繪畫審美原則。直到元代,趙孟頫、元四家對“以書入畫”進行了理論與實踐的全面開拓,其在“以書入畫”基礎上加以揮寫“逸氣”,確立了后世文人畫審美方式的新趨勢,也從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后世眾多文人畫家。整個過程促使文人畫“以書入畫”由具體的書法用筆范疇逐漸上升至抽象的美學意蘊。總之,文人畫“以書入畫”促進了繪畫藝術的良性發(fā)展,亦對當代繪畫創(chuàng)作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1][2]張彥遠.歷代名畫記[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13-24.
[3][11][12][20]葛路.中國畫論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90-196.
[4]殷曉蕾.古代山水畫論備要[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0:41.
[5][6][9][10]上海書畫出版社,華東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歷代書法論文選[C].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4:6-394.
[7] 郭熙.林泉高致[M].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0:77.
[8] 鄭春元.中國名畫品鑒[M].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216.
[13] 王原祁.佩文齋書畫譜[M].北京:中國書店,1984:308.
[14] 啟功.戾家考——談繪畫史上的一個問題[J].文物,1963(4):44-47.
[15][17][18]俞劍華.中國古代畫論類編[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75-1070.
[16] 饒自然,黃公望.繪宗十二忌·寫山水訣[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63:5.
[19] 李澤厚.美的歷程[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9:183.
作者簡介:吳亞賓(1992-),男,河南焦作人,碩士研究生,講師,研究方向為書法理論與創(chuàng)作研究;黃新黎(1992-),女,福建泉州人,本科,青年教師,研究方向為山水畫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