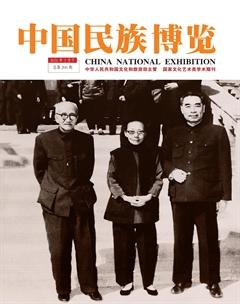地之子的苦難與新生
【摘要】“地之子”是新文化運動時創作者創造出來地表達方式,用來指稱與土地有著精神血脈聯系的鄉土文學作家,農民是最親近的大地之子,趙樹理的小說以講述農民的故事為主,講述大地之子的深重苦難,并將新政權下的新生希望提供給農村人,引導他們走向新生。
【關鍵詞】地之子;苦難;新生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198(2021)04-199-03
【本文著錄格式】閆衛芳.地之子的苦難與新生——趙樹理小說的農村書寫[J].中國民族博覽,2021,02(04):199-201.
基金項目:本文為長治學院太行山生態與旅游研究中心校級基地項目“抗戰時期趙樹理文本的社會動員機制研究”(項目編號:XJ2020000601)成果。
作為晉東南地區的代表作家,趙樹理的小說寫到晉東南農村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生存的人的苦難,當新的政權組織,新的制度政策進入到這片土地,他看到新生的希望,所以試圖用自己接受到的新文化新思想為這片古老的土地以求“變”的可能,對這片土地及其上生活的人們的生活心理的深刻了解使得他求“變”、求“更新”的希望成為可能。
一、趙樹理與“地之子”的身份
李廣田在他的詩歌《地之子》中寫道:我是生自土中,來自田間的,我對她有著作為人子的深情,我愛著這地面上的沙壤,濕軟軟的。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世世代代在土地上生活的人們對土地有著極其深厚的感情。臺靜農將他的鄉土小說合集命名為“地之子”,用小說的形式展現農村人生活的艱辛與農村的各種風俗習慣。晉東南農村這片土地與廣大的中國大地一樣,也滋養著一群勤勞樸實的人。
于大多數的新文學知識分子而言,“地之子”或許只是一種生命氣質、一種理想狀態的追求,但趙樹理是真正生養于土地之上的農民,他立志做“文攤作家”,他所想表達的是大地之子的生活,是靠土地而生存的農民真實的生活敘寫。孫犁說:我認為他是一個典型的農民作家。
知識分子通常是從啟蒙者的立場對農村進行思考的,但農民是真正地面向于土地的。正是知識分子對鄉村文化與鄉村生活的思考,才有鄉村轉變與新生的可能,而擁有農民與知識分子雙重身份的趙樹理,既面向土地生活,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向地而生的農民,又是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豐富的生活經歷與深刻的生命體驗是造就一個作家的根本條件,生養于晉東南這片土地之上的趙樹理,在他成長的年齡階段參與了農村大地上的耕種勞作,他切身體會到勞作的艱辛與被迫勞作卻不得溫飽的殘酷現實,骨子里背負著地地道道的農民身上所背負的沉重的身體負累,當他走進農村之外的世界,被新的文化所洗禮之時,更是深切地體驗到故鄉農村土地上生活的人的不幸與悲哀,而這悲哀的來源不只是身體的負荷之重,還包括長久受欺辱與受壓迫即“精神奴役”之下留下的無法撫平的創傷。趙樹理用簡單的語言,簡單的結構,簡單的故事情節,以一個民間說書人的身份,將晉東南這片土地上生活的農民大眾的生活鮮活地講述出來,他帶著對農村土地上生活的人的苦難,懷著深切的同情,并懷著大地之子對土地母親的深情,為這里的人民展現一條又新又活的出路。
二、地之子的雙重苦難
長久以來,深重的苦難是書寫中國農村大地上所生活的人不變的主題,悠久的農業文明影響之下農民成為鄉土中國一個重要的書寫對象。40年代解放區的新生活、新政策召喚一批青年作家參與其中,農村土改等政治運動的開展更是促使很多新文學作家親身參與到農村實踐中。趙樹理是解放區的代表作家,因其寫作內容以農民為主體,符合了當時解放區政治生活的需要,一度被樹立為典型,被標榜為“方向”。
新文學知識分子會感慨鄉村土地的遼闊、生活的質樸,亦會批判舊習的毒害,嘲諷思想的落后,他們大多站在啟蒙者的立場上俯視自己所構造出來的農村社會。但趙樹理的鄉村是豐富、真實的農村人和沉重負累的生活現實所構成的。
首先是身體上的困難,趙樹理小說中的農民大都是在沉重的生活負擔之下生活的,終年四季汗流浹背卻可能仍不足以糊口,長期的農耕與勞作使得農村人在身體上有著極重的負累,甚至很多孩子從小就承擔著極重的家庭任務,《豆葉菜》寫一家老小吃不上米,只能靠吃豆葉菜為生,小說《毛驢和鞋子》中寫農民王老頭五十多歲了,有個十六歲小孩,敵人占了縣城,他打發孩子去馱煤,孩子小小年紀就開始承擔起家庭的重擔,但最終維持會的人為了搶他的毛驢,把他害死。小說《放羊老漢談“招呼”》中寫一個苦命的放羊老漢,七歲爹去世,八歲娘染了病,天天被二嬸當勞力使喚,給二嬸家放牛割草,還是被打,最終自己出來放羊為生。《催糧差》中劉老漢自己日子本來就過得很清貧,小說寫他穿著破布衣服,頭戴一頂草帽,應該是剛從地里勞作回來,但還是要因為上兩輩的欠債被催交錢糧,東湊西湊還湊不夠。趙樹理在這些故事中展現了艱苦的生活重壓對農民的身體造成的苦難,對物質生活條件極其匱乏的農村人給予了深切的理解與同情。
除此之外,趙樹理在小說中寫了很多農村人痛苦的現實遭遇,在幾組對立關系中寫出農民受欺負、受壓迫的現實處境,與受奴役、不自由的精神狀況。首先是侵略者與被侵略者之間的關系,這是趙樹理小說中最常出現的對立關系,由于當時的歷史環境正處于中國全面抗戰的時期,需要廣大人民認識自己所處的環境并自覺加入到反抗與戰斗中,其次是地主與貧農的對立關系,包括以地主為代表的地方惡勢力與農民的對立關系。在這些關系中農民大都有上千年封建社會所遺留下來的根深蒂固的上下等人關系,在被欺壓下往往表現出無奈情狀。小說《陪黑鬼打牌記》是趙樹理早期的作品,作品中來順屬于地方在日本憲司令當“黑鬼”,逼著村長老旦等人陪打牌,作為貧苦農民的老旦不會打,跪地哀求,來順一聲呵斥,老旦連跪也不敢再跪,小說接著寫道:爬起來站到門邊,眼巴巴守著他閨女。一直熬到黑,老旦站在門口一天沒動,來順一個人玩兩個人的牌贏了村長錢,又直接拉走了老旦不滿十五歲的小閨女。小說沒有使用任何的修辭語言,也沒有可以使用高級的藝術手法,就簡簡單單將這個聽來的故事講述出來,我們就已經可以看到一個被壓迫到毫無尊嚴也毫無反抗能力的底層農民形象,并會隨作者一起為他所經歷的事情痛心,這是真實的文字所發出來的難以言說的生命感染力量。趙樹理很多小說寫到類似的情形,《照像》中寫日本人借照相名義欺辱十六歲的芝妮,《聞風而逃》中開篇講三個鬼子大白天在農村尋開心等,這些小說都表達了在這種關系中農民受欺壓而不敢言的悲慘境遇。
另一方面趙樹理注意到受教育程度低,長期生活于精神奴役之下的很多農村人安逸于平安與溫飽,不能認識自己的實際處境,甚至成為敵人的工具,敵人在各個地方設立了“維持會”等漢奸組織,并且精心編造了很多謊言美化其真實目的。《幫助》中多次重復“皇軍是來幫助中國的”,《“紅紅”和“黑黑”》中維持會的漢奸不分“紅黑”好壞,逼著農民黑白顛倒的說,《二木匠》開篇就提到王木匠弟兄兩個被日軍拉了差,每天修碉堡。這些小說寫出了在敵人體力和精神的雙重利用之下農民不自知的悲劇狀態。
除了外在的,趙樹理還注意到本民族文化對農民精神的壓迫,最明顯的就是民間宗教迷信的精神殘害,民間宗教迷信的束縛。《假關公》中老秀才的年輕老婆被一個無賴假裝的關公推倒,圍觀者不止沒有半點同情,還評價她一定不正派,《小二黑結婚》中的兩個神仙“二孔明”、“三仙姑”兩個人就是裝神弄鬼以八字相克、前世姻緣由天定等理由反對小二黑與小芹的婚姻。二諸葛為了救小二黑,跪在興旺面前求,跪求區長恩典恩典等行為都是長期精神奴役下的自然反應。
透過趙樹理的小說故事,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承受著身體與精神雙重重壓的勞苦大眾,常常在這種生存境況下被任意擺布,甚至被折磨致死,但最為可悲的是他們幾乎絲毫沒有真正認識到自己作為被壓迫者的身份,缺乏對自己生存現狀真實情況的認知,更缺乏奮起反抗的勇氣與覺悟。趙樹理所寫農民的這種苦難并非用深重二字可以去形容,作家也沒有悲觀、絕望的情緒籠罩,相反卻以積極樂觀的態度將新的政策、新的制度之下勝利的結局展示與人,像個負責任的村干部做農村動員一樣,鼓勵大家懷著新生的盼望一同為光明的未來努力。
三、從苦難走向新生
趙樹理小說中新生的希望與力量也無關乎作為個體的“人”的覺醒,人的精神力量的覺醒,而在于外在的政權制度、組織團體的建立,現實的需求不是解決精神的空虛與彷徨,而僅只需要解決物質的飽足,這一切不是啟蒙者所能給予的,只有新的政權力量借著有效的措施及農村社會動員的各種方式所能真正達到的。
趙樹理的小說大都與那個歷史時期的國家政權的政策相結合來講述,將廣大人民命運地改變與地方政策的變化以及廣闊的社會變革背景聯系在一起,以政策施行前后農村社會生活狀況做鮮明對比,以極富激情與說服力的語調描繪新生活的美好,鼓勵生活尚未實現變革的農村與尚未覺醒的農村人積極主動參與到新世界的建造當中。新的民族文化的建立,新的生活條件的維持,需要“群體意識”的覺醒與“群體認同”的建立,而這個群體是由眾多的具有集體意識與生命意識的鮮活個體所組成,這些人可以感受到新時代所帶來的巨大改變,可以為大眾實現“新生”做努力與嘗試。
小說《探女》中馬大娘看女兒外孫,通過兩人的談話對比兩個村的現實情況,馬大娘村里被日本兵占據,要錢要糧要牲口要人,但根據地新景象,抗日軍幫助他們犁地擔糞,兵好官清。在對比中將新的生活景象展現給閱讀者,引導他們認識新的政權力量是于他們的現實生活有益的,可以主動選擇接受新的政權力量。小說《孟祥英翻身》講的是在傳統生產關系不平等的男尊女卑的農村社會中,主人公在新的土地政策之下擺脫原有生產關系中只能被動接受的命運,成為一個擁有獨立自主生活能力的新女性,并且帶領著整個村子里的其他婦女不再依附男性而生存,而是開啟自力更生的新生活篇章。
趙樹理的獨特之處在于他沒有一味地將農民的苦難來源放在敵軍的擾亂,他注意到了農村真實的情況有部分原因是自己同胞乘機發國難財,且有一部分同胞為求生存被敵人利用成為管制欺壓自己鄰里的工具。新的政權組織所提供的不只是外在的幫助,而且要提升所有人的思想意識,要清除的也不只是外來侵略者的暴行,還有本民族中那些惡勢力的壓制。小說《再生錄》采用了傳統章回體小說的形式,講了楊二牛到張村時看到家家封門閉戶,燈火不舉,一片死寂,老百姓都不敢出門,本地沒有日本兵的騷擾,卻有地方散兵土匪的擾亂,逃兵土匪乘機作亂,鬧得家家戶戶不得安生。游擊隊槍斃了地主惡霸,換來了太平世界。小說通過游擊隊進村前后村里情況的對比,將黨領導的新的政權是為人民構建一個平和的、安穩的、民主的世界這一主題講述給民眾,鼓勵他們主動迎接真正的代表人民的力量。在《小二黑結婚》中,趙樹理將小二黑與小芹的自由戀愛放在多重困難之下,有金旺、興旺這種村里地方勢力的破壞,也有二諸葛三仙姑作為封建迷信家長的阻撓,還有無形卻根深蒂固的傳統孝悌禮教文化的影響,困難越大,越能顯示出新政權是在多方面改變著農村人的生活,新的婚姻政策的實施,不止使得小二黑與小芹最終走向自由戀愛與婚姻,而且清除了地方惡勢力與壞分子,更重要的是改變了老農民面對強權、面對偶像時深埋在骨子里的卑躬屈膝的奴性思想,小說將自由與平等的新思想透過生動的故事講述給農民大眾,使他們在眾多的阻攔與壓迫中走向自覺的新生活的追求。
“趙樹理是農民作家,農民作家是民族文學的‘鹽”。趙樹理寫的鄉村可能沒有上升到新文學作家所表現的人性、文化的高度與生命精神哲理的超越性思想深度,他所表達的只是生活、故事與道理,在情理之間講述簡單的故事,喚起農民的意識上的認同與行動上的支持,這些人是沒有受過文化教育的,但他們心底存留有不約而同的是非觀念,這是不止是世代口耳相傳,約定俗成所形成的,也是最真實簡單的人性中普遍存在的。作品內容也無關乎廣闊歷史,無關乎深刻人性,唯關注的就是當下的現實需要,這也是真實的農村人所在乎的,在新的條件下苦難的現實被新生的希望所代替,作品內容簡單卻充滿力量。
參考文獻:
[1]孫犁.讀趙樹理[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79.
[2]董大中.張成德等.趙樹理全集[M].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86.
[3][日]萩野脩二,[美]馬若芬等.外國學者論趙樹理[M].中國趙樹理研究會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
[4]余岱宗.人民的鏡像:從苦難走向新生[J].文藝理論與批評,2005(3).
[5]李相銀.鄉村政治生態與中國當代文學[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1(7).
[6]朱慶華.趙樹理小說中的魯迅因子[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7).
[7]趙勇.在文學場域內外——趙樹理三重身份的認同、撕裂與縫合[J].文藝爭鳴,2017(4).
[8]白杰.趙樹理:在民間立場上統合啟蒙與革命[J].中國語言文學研究,2016(2).
[9]李剛,錢振綱.消融的“歷史實踐主體”——趙樹理小說中農民的政治化生存[J].文藝爭鳴,2016(5).
[10]龔自強.文學與意識形態的糾葛——論趙樹理的文學世界[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2016(3).
作者簡介:閆衛芳(1993-),女,漢族,山西晉城人,助教,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