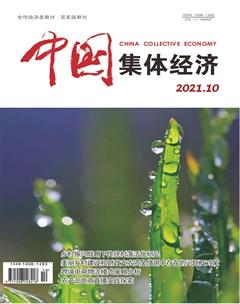“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OFDI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影響
羅華麗 徐夢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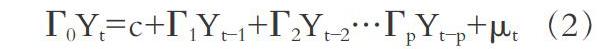
摘要:隨著中國金融市場的進一步改革開放和經濟實力的日益增強,中國OFDI和人民幣國際影響力逐漸成為社會熱點話題。文章理論與實證分析相契合,先探討了OFDI對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影響路徑,隨后基于貨幣交易媒介、記賬單位和價值儲蓄三大職能和貨幣錨模型,初步構建貨幣國際化指標體系,測算出SDR貨幣籃子中五種錨貨幣的國際化指數,再建立SVAR模型,深入分析中國OFDI如何影響人民幣國際進程。實證結果表明,中國OFDI對人民幣國際化水平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并且針對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的路徑選擇提出相應的建議:抓緊“一帶一路”建設機遇,增大對外投融資渠道,優化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布局,多方位深化金融改革,進而穩妥有序地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關鍵詞:“一帶一路”;對外直接投資;人民幣國際化;SVAR模型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一)選題背景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讓學者認識到亞洲經濟區存在著貨幣原罪,即貨幣錯配、結構錯配和期限錯配。由于貨幣錯配受美元波動影響較大且容易招致風險,伴隨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襲來,貨幣原罪加劇,再一次警醒人們過度依賴于美元的國際貿易和貨幣市場存在極高的流動性風險;而在跨境貿易和金融活動中,采用本幣計價和結算,可降低非本地區貨幣波動造成的負面影響,以及緩解貨幣原罪問題。因此,提議國際貨幣體系變革的呼聲再一次成為世界焦點。與此同時,亞洲地區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基礎建設普遍非常落后,從IMF、世界銀行和亞投行等金融機構獲得投融資也絕非易事,這些發展中國家面臨著棘手的融資約束問題。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存在諸多不足和弊端,并且儲備貨幣發行國的貿易逆差壓力日益加劇,為了合理配置全球外匯儲備降低匯率風險,推動國際貨幣體系的多元化建設成為重要任務。同時中國作為亞洲第一大經濟體,近些年與亞洲區域進出口中保持貿易逆差地位,具備穩定的資本輸出能力。中國目前處于經濟轉型期,即由高速增長時期邁向高質量發展時期,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人民幣國際化的加速也成為必然趨勢。自“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走出去”戰略的頒布和推進、以及亞投行的興起,中國OFDI不斷迎來新的機遇和挑戰,人民幣也逐漸成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首選的貿易計價結算貨幣,這便是人民幣國際化的背景。
(二)有關研究的文獻綜述
本文研究“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OFDI對人民幣國際化的作用機制,對有關文獻進行梳理,相關研究大致為可以歸納為以下兩個方面。
關于人民幣國際化水平的衡量方法。一是基于貨幣國際化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如李稻葵和劉霖林(2008)運用三個指標,即國際儲備貨幣結構、跨境結算貨幣權重和國際債券貨幣份額,構建計量模型測度了人民幣國際化程度。二是構建人民幣國際化指數,通過對影響人民幣國際化水平的關鍵指標賦予權重從而測算人民幣國際化指數。彭紅楓、譚小玉(2017)基于國際貨幣交易媒介、記賬單位和價值貯藏的三大職能,通過主成分分析法選取關鍵指標從而測算人民幣國際化指數。徐偉呈、王暢、郭越(2019)運用貨幣錨模型,并構建了貨幣國際化指標體系。
關于中國OFDI與人民幣國際化的關系,我國學者也進行了相關研究和探討。張敬之(2014)認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從國際貿易和國內金融業的發展兩種渠道推進了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前者有助于提高本幣的國際結算權重,后者促進了本幣的計價和流通,為海外投融資提供保障。倪亞芬、李子聯(2016)以境外人民幣存款規模作為人民幣國際化程度的度量指標,利用Granger因果檢驗等計量分析方法來考察人民幣國際化與OFDI的動態關系,證明OFDI對人民幣國際化水平有更為明顯持續的推動作用。姚山、古廣東、楊繼瑞(2016)研究OFDI對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推動機制,提出OFDI主要通過跨國企業來擴展人民幣在全球的使用范圍,減少離岸人民幣的兌換成本和穩定人民幣的內在價值,實現人民幣的高效流通。林樂芬、王少楠(2016)提出對外直接投資對產業鏈上下游帶動效應明顯,從而刺激被投資境外實體經濟對人民幣的黏性需求。付韶軍(2018)構建固定效應模型,分別從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兩個層面分析在“一帶一路”建設背景下人民幣國際化對中國OFDI的影響,分析結果表明人民幣國際化對中國OFDI有顯著的推進作用。
以往學者的研究重心是關于中國OFDI與人民幣國際化關系的規范分析,或者是人民幣國際化對中國OFDI影響的實證分析,但關于中國OFDI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影響分析的文獻較少,這便是本文的研究方向。本文在以往相關研究的基礎上,基于貨幣三大基本職能,通過建立貨幣國際化指標體系測算人民幣國際化指數,并深入分析中國OFDI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影響,最后針對提升人民幣國際影響力方面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即如何在“一帶一路”建設背景下改善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從而加速人民幣的國際進程。
二、“一帶一路”建設背景下中國OFDI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影響路徑
“一帶一路”建設背景下,對外直接投資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影響主要是以下三條路徑。
第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經濟主體——跨國企業,其在境外經營擴大和資產擴張的進程中,投資偏好使用本國貨幣,以人民幣作為最終的計價或結算貨幣在公司內部清償,推動了人民幣的跨境結算進程和國際計價功能。在長期持續性的投資活動影響下,跨國公司使得本國貨幣的路徑隨著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與成熟而不斷強化,拓展了人民幣在國際經濟社會的使用范圍,刺激了東道主國家的官方機構和企業對人民幣的需求粘性。同時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需要龐大的資金支撐,主要依靠于國內的金融機構所提供服務和支持,因此跨國公司的海外擴張促進了本國金融機構在境外的設立和發展,拓寬了本國金融機構在全球發展業務和提供服務的范圍,也為人民幣的全球流通和人民幣金融產品的發行奠定了基礎。
第二,對外直接投資直接影響了資本項目和資本項目的規模,從而有效調節我國的國際收支平衡。隨著中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的全面推進,我國國際收支的經常賬戶(包括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等賬戶)和資本與金融賬戶持續多年“雙順差”;而中國OFDI規模的增長有利于形成項目資本逆差,其與經常項目順差的組合可以保障人民幣內在價值的穩定,有效降低持有人民幣的匯率風險,改善國際收支平衡有助于穩定提高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
第三,伴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全面實施,與沿線國家交流合作的逐步加強,為我國開辟了巨大的經濟增長空間,同時也是我國擴大對外開放和深化改革的重要戰略和途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水平建設十分落后,且國內缺乏資金投資基礎建設,因此需要從外部引入資金援助;但從國際金融平臺獲得的資金杯水車薪,無法彌補巨大的資金缺口,因此中國的海外投融資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人民幣在沿線國家基礎建設、貿易活動、區域經濟合作各方面發揮核心作用。中國實施“一帶一路”戰略,借助亞投行投融資平臺對海外進行投融資,推動其他國家的經濟建設,不僅豐富了人民幣的輸出路徑,還刺激了人民幣的海外需求和使用粘性。我國政策性銀行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建設提供貸款,境外人民幣通過購買人民幣債券等方式回到國內,形成了閉合的人民幣國際循環鏈,建立良好的流通機制,進而推進了人民幣的計價和結算職能。“一帶一路”建設也有利于海外人民幣債權的擴張和人民幣的輸出、海外儲備量的增加,成為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重要推力。
三、“一帶一路”建設背景下人民幣國際化水平的測度方法
本文通過構建貨幣錨模型,確定一國貨幣匯率受主要國際化貨幣匯率的影響程度,反映雙邊層面上某國際貨幣在該國的國際化程度,以此彌補以單一金融指標反映貨幣國際化水平的局限性;并將貨幣錨程度指標納入貨幣國際化指標體系中,豐富測算維度。
(一)基于貨幣錨模型人民幣國際化水平的測算
1. 貨幣錨模型建立
本文的貨幣國際化水平的測算方法借鑒徐偉呈、王暢和郭越(2019)的貨幣錨模型。該模型假設一國貨幣匯率是由SDR貨幣籃子中各貨幣加權平均后計算得出,其中該國貨幣的匯率波動與籃子中某一錨貨幣匯率波動的相關程度,體現了錨貨幣作為該國貨幣匯率浮動的影響因素權重。在下文的模型中選用瑞士法郎為基準貨幣,貨幣錨模型可以整理為以下形式:
ΔlogCURRENCY=α1ΔlogUSD+α2 ΔlogEUR+α3ΔlogGBP+α4ΔlogJPY+α5Δlog CNY(1)
其中,USD、EUR、GBP、JYP和CNY分別表示美元、歐元、英鎊、日元和人民幣兌瑞士法郎匯率。
2. 貨幣國際化水平的測算
從Pacific Exchange Rate Service數據庫中隨機選取選擇58個國家和地區貨幣匯率在2009~2019年期間的月度數據作為研究樣本,運用SPSS軟件,計算出樣本中不同貨幣與貨幣籃子中五種國際貨幣之間的雙邊匯率相關系數,并統計出相關關系顯著(即P<0.05)且為正數的國家和地區的數量,從而確定錨定五種國際貨幣的國家數量占比,如表 1所示。
由表1可知,在2009~2019年期間,貨幣匯率錨定美元的國家或地區比例常年最高,即美元匯率波動對世界貨幣市場具有巨大的影響力,盡管比例有所下降,但不影響美元在國際貨幣市場的領導地位。歐元也是主流的錨貨幣,然而它對其他國家或地區貨幣匯率的影響力大幅下降,占比降幅高達32.08%。錨定日元的國家或地區數量小幅增長,錨定英鎊的國家比例相對而言比較穩定。國家或地區貨幣錨定人民幣的比重先上升后小幅回落,略微下降至2019年的13.24%,但人民幣匯率的整體影響力高于日元和英鎊。在分析過程中發現,“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錨定人民幣的數量呈上升趨勢,說明“一帶一路”建設不僅促進了中國與亞洲發展中國家的經貿往來和金融合作,推進了人民幣的認可度、穩定性和影響力;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改善了周邊國家的基礎經濟建設和市場環境,以及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的進一步融合,通過加快人民幣區域一體化的進程從而提高了人民幣國際水平。
(二)基于貨幣國際化指標體系人民幣國際化水平的測算
1. 貨幣國際化指標體系的指標選取
單一的貨幣職能指標難以客觀衡量一國貨幣國際化水平,所以本文從貨幣的交易媒介、記賬單位、價值儲藏三大職能中選取多個關鍵指標構建貨幣國際化指標體系,使得貨幣國際化指數評估范圍更廣,測算結果更具科學性和說服力。本文將參考彭紅楓、譚小玉(2016)建立的人民幣國際化指標體系(如表 2所示)。采用2009~2019年的季度數據,指標數據來源于BIS、World Bank、SWIFT 、IMF等數據庫。
2. 基于熵權法的貨幣國際化體系的建立
由于貨幣履行各職能對貨幣國際化水平的影響程度不同,因此需要對不同職能下的衡量指標賦予不同的權重,使測算結果更具可信度。本文將參考徐偉呈、王暢、郭越(2019)貨幣國際化各項指標權重的測算方式,利用熵權法,基于數據的離散程度客觀賦予指標相應權重。通過MATLAB R2020a計算得到貨幣國際化體系各指標的權重如表3所示。
3. 貨幣國際化指數的測算
基于上述的貨幣國際化指標體系,分別測算出五種錨定貨幣的國際化水平,具體指數情況如表4所示。
從國際化指數的數值變化可以看出,美元一直牢牢占據全球貨幣市場的霸主地位,其國際化指數只有小幅波動。受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和2009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連續影響,歐元區經濟在近十年一直處于低迷狀態,歐元的國際化指數也從2009年的35.18%下滑至2019年的25.10%,跌幅高達9.78%,其國際化地位明顯呈下降趨勢。英鎊的國際化指數常年保持穩定,占全球貨幣市場份額在6%左右。相比之下,日元和人民幣的國際化水平呈穩步上升趨勢,其中人民幣的國際化指數累計增長了2.22%。自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和2016年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我國積極推進了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金融合作,人民幣在官方外匯儲備的份額迅速提升,貨幣市場和全球外儲管理者對人民幣的信心不斷增強。中國OFDI占全球直接投資的比重從3.25%迅速上升至11.89%,通過拓寬資本輸出、對亞洲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信貸支持等方式,穩步推進人民幣的國際流通渠道。人民幣在國際社會的認可度和接受度與日俱增,其在國際貨幣流通量和跨境貿易結算的貨幣比重也日益增強,人民幣的國際化水平持續提升。
四、中國OFDI對人民幣國際化影響的實證分析
(一)模型建立
本文數據均為時間序列數據,由于變量之間存在動態影響,選擇模型時考慮結構向量自回歸(SVAR)模型,其優化了向量自回歸(VAR)模型,涵蓋了模型體系內各變量之間即時的結構性關系,通過對模型施加約束條件,能將隱藏在誤差項中變量間的當期相關關系顯示出來。這樣能更有助于解釋系統受到隨機擾動的動態沖擊,使模型更具有經濟指導意義。SVAR模型的表達式如下:
Γ0Yt=c+Γ1Yt-1+Γ2Yt-2…ΓpYt-p+μt(2)
(二)變量選擇與數據處理
模型中選用兩個變量:OFDI即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單位為億美元;RII表示人民幣國際化指數。采用2009~2019年的季度數據,變量數據來自于國研網統計數據庫的中國OFDI規模總額和基于貨幣國際化體系測算得到的人民幣國際化水平指數。為了消除通貨膨脹因素的影響,采用定基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進行價格平減,CPI(1978=100)來自國家統計局。
(三)描述統計分析
1. ADF單位根檢驗
在建立SVAR模型前,各變量需要先通過時間序列的平穩性檢驗,保證模型的穩定性。本文采用ADF做單位根的平穩性檢驗,原假設為存在單位根,結果如表5所示。OFDI、RII均為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接受了原假設,即存在單位根,不是平穩變量。而一階差分后的變量均拒絕原假設,即OFDI和RII的一階單整序列,符合向量自回歸模型建設的前提條件。
2. JOHANSEN協整關系檢驗
基于AIC和SC信息準則,確定SVAR模型的滯后階數。模型的最大階數的選取不僅要考慮足夠的滯后項,也要保證自由度。通常采用LR法則,基于表6的運算結果,將最優滯后階數定義為1階。
接下來通過Johansen檢驗法來確定OFDI和RII之間的協整關系,即兩個平穩時間序列之間是否具有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防止偽回歸現象出現。如表 7所示,在5%顯著性水平下,OFDI和RII的一階單整序列的協整檢驗接受了協整方程的駕駛,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中國OFD I對人民幣國際化水平有顯著的正向作用。同時對SVAR模型進行穩定性檢驗,由圖1可知,AR特征方程的根的倒數絕對值均落于單位圓內,表明模型通過平穩性檢驗。
3. 廣義脈沖響應函數分
脈沖響應分析函數可以研究時間序列模型中變量之間的影響,即解釋變量的沖擊對被解釋變量造成的影響,反映了變量間的動態關系。模擬結果如圖2所示,在OFDI一個標準差單位的正向沖擊后,RII當期沒有響應,在滯后大約一期后開始出現向上波動,在第2期攀升至峰值后一直呈正向影響且逐漸衰弱,長期收斂。說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短期內有助于提升人民幣國際化水平,且從長遠看來,對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有直接的正面積極影響。
4. 方差分解分析
方差分解是根據各個方程隨機誤差項的關聯情況,將SVAR模型中內生變量的波動按其成因進行分解,以此確定各個變量波動的重要性。因此結合方差分解,可以對脈沖響應函分析的結果進行補充和完善。方差分解的結果如圖3所示,在預測第1期時,RII的預測方差完全是由于自身的沖擊,隨后RII的波動受OFDI沖擊影響的比重逐漸增大。在第4期,OFDI 對隨著時間的推移,RII受自身擾動項的沖擊影響逐漸穩定在80%左右,OFDI對人民幣國際化指數波動的貢獻比重不斷上升,其貢獻率保持在18%上下。分析結果表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通過構建貨幣錨模型確定2009~2019年期間錨定五種國際貨幣的國家數量比例,并基于貨幣三大職能建立貨幣國際化指標體系,分別測算出五種錨定貨幣的國際化指數,從而進一步驗證中國OFDI對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推動機制和促進作用。根據2019年Q1~2019年Q4的季度數據,建立SVAR模型。在脈沖響應分析中,發現OFDI對RII具有長期正向影響;在方差分解分析中,明確指出OFDI對RII波動的貢獻程度有18%,說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人民幣國際化水平具有顯著的積極影響。
基于以上實證分析結果,為了進一步提高人民幣在貨幣市場的國際影響力、刺激海外對人民幣的需求和使用,本文針對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深入推進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金融合作,在跨境投融資活動中充分發揮人民幣的作用。通過提供資金幫助亞洲發展中國家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或著國內金融結構向海外發放貸款的路徑,主動推進人民幣的跨境流通和循環機制。同時借助亞投行、絲路基金和金磚國家等國際金融平臺,以及建立人民幣海外投資基金,積極擴大人民幣對外投融資渠道,逐步增強沿線國家對人民幣的依賴和粘性需求。
第二,基于中國巨額的大宗商品成交量,增強人民幣貿易計價功能。根據SWIFT《人民幣追蹤報告》的數據顯示,人民幣的國際結算功能近些年來迅速發展,但其計價功能仍未能有效發揮;我國大部分跨國公司在國際貿易中以“美元計價、人民幣結算”的方式為主,美元作為計價貨幣的使用慣性其實阻礙了人民幣計價的發展,不利于增強人民幣的定價話語權。對此,推動大宗商品采取人民幣計價的方式是解決此問題的有效路徑。在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資源要素往來中,比如我國占有市場份額優勢的稀缺原油、鐵礦石等,簽訂雙邊自貿協定與人民幣匯率掛鉤,有利于增強人民幣計價職能的競爭力。以及鼓勵跨國公司在對外貿易中采用人民幣計價,不僅有助于規避匯率風險,也能提高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計價權重。
第三,我國應繼續完善金融合作平臺和創新多邊合作機制,改善金融市場環境,才能有效規避國際市場的金融風險,進而增強人民幣的穩定性和認同度。政府應在對外投融資、跨境貿易等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勵企業“走出去”;深化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比如積極參與和構筑區域貨幣合作,加強中國經濟的對外滲透力;推進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簽訂貨幣互換協議,有助于提升人民幣在官方外匯儲備的權重。與此同時,完善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的建設,擴展國內金融機構的海外業務,合理規劃我國對外金融發展格局。抓緊“一帶一路”建設機遇,多方位深化金融改革,加快中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的腳步,優化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布局,進而穩妥有序地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參考文獻:
[1]李稻葵,劉霖林.人民幣國際化:計量研究及政策分析[J].金融研究,2008(11):1-16.
[2]彭紅楓,譚小玉.人民幣國際化研究:程度測算與影響因素分析[J].經濟研究,2017,52(02):125-139.
[3]徐偉呈,王暢,郭越.人民幣國際化水平測算及影響因素分析——基于貨幣錨模型的經驗研究[J].亞太經濟,2019(06):26-36+144-145.
[4]張敬之.人民幣國際化與人民幣對外直接投資的相關性研究[J].上海金融,2014(11):24-26.
[5]倪亞芬,李子聯.人民幣國際化與對外直接投資的互動分析[J].金融與經濟,2016(02):45-49+75.
[6]姚山,古廣東,楊繼瑞.對外直接投資:促進人民幣國際化機理與優化路徑探討[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6,37(12):142-147.
[7]林樂芬,王少楠.“一帶一路”進程中人民幣國際化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J].國際金融研究,2016(02):75-83.
[8]付韶軍.“一帶一路”背景下人民幣國際化對中國OFDI的影響研究——基于SVAR模型的實證檢驗[J].工業技術經濟,2018,37(12):147-155.
(作者單位:深圳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