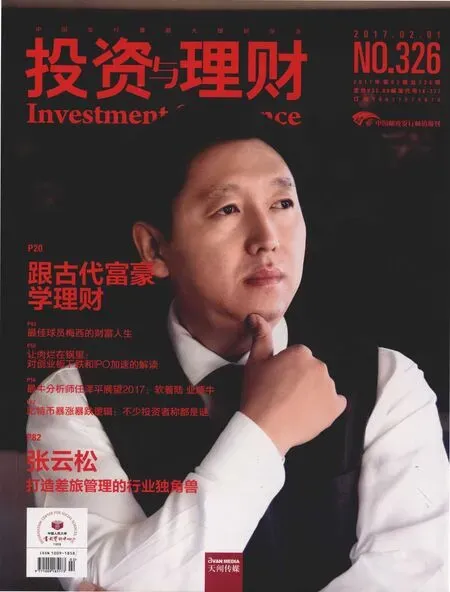新規再現,銀行理財只能銀行買?
粟小牛
1月15日,銀保監會、央行發布了《關于規范商業銀行通過互聯網開展個人存款業務有關事項的通知》,規定商業銀行不得通過非自營網絡平臺開展定期存款和定活兩便存款業務,包括但不限于由非自營網絡平臺提供營銷宣傳、產品展示、信息傳輸、購買入口、利息補貼等服務。
就在前不久,支付寶、理財通、京東金融等多家互聯網平臺紛紛下架互聯網存款產品,此次新規出臺正式明確了監管要求。這也是繼上月底銀保監會發布《商業銀行理財子公司理財產品銷售管理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之后,針對規范銀行理財業務的又一重要文件。
互聯網平臺過去曾是中小銀行吸收存款的主要渠道
互聯網平臺的銀行存款,其實就是銀行委托互聯網平臺進行銷售的各類存款產品。銀行提供產品,支付寶、理財通、螞蟻財富等互聯網平臺負責提供購買入口,并展示產品信息。
我們都知道,銀行的主要業務之一就是吸收存款。像中農工建交這樣的大型國有銀行,網點遍布全國各地,是個人和機構存放資金的優先選擇對象,所以它們不用怎么操心存款資金來源的問題。
但我國銀行體系里還有上千家地方性商業銀行,它們網點少、品牌知名度低、營銷力量薄弱,對它們來講,吸引存款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所以要提高獲客效率,除了提高存款產品利息,另一條非常重要的途徑就是尋找線上平臺增加曝光度。
因為互聯網渠道的銀行存款產品具備門檻低、利息高的特征,受到了廣大投資者的青睞,后面更多地區的城商行、農商行也紛紛開始效仿觸網。地方性中小銀行在某種程度上享受到了這幾年互聯網的流量紅利,存款業務規模成倍增長。
比如浙江紹興恒信農村商業銀行存款總額從132.91億元到181.05億元,長安銀從168.64億元到203.36億元,2019年吉林億聯銀行的存款余額從86.56億元增至250.58億元,山東藍海銀行的存款余額從108.85億元增至225.43億元。
如今為何要禁止互聯網平臺賣銀行存款產品?
1、不符合監管規則的要求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修改建議稿)》規定,區域性商業銀行就應當在住所地范圍內依法開展經營活動,未經批準,不得跨區域展業。
這是因為地方性銀行往往在資本充足率、貸款質量、盈利能力、流動性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
而借助互聯網平臺,地方性銀行把存款業務做到了全國,從地方性銀行變成全國性銀行,不符合監管要求。這類似于僅限于國內航線的客機飛國際長途,存在安全隱患。
2、互聯網渠道的穩定性不高,對中小銀行的流動性管理造成挑戰
投資者可以通過互聯網渠道購買銀行存款產品,同樣也能在互聯網渠道賣出。如果某家中小銀行的存款全部依靠互聯網渠道,一旦出現大批線上投資者同時贖回,這家銀行很可能會經受一次擠兌危機。
央行金融穩定局局長孫天琦在《線上平臺存款:數字金融和金融監管的一個產品案例》這份報告中曾提到過,個別銀行的互聯網渠道存款占各項存款的比例高達83%。
3、互聯網渠道存款利率過高,會對銀行造成一定的經營壓力
我們知道,貸款和存款業務間的息差收益是銀行的主要利潤來源之一。2014年以來,央行開始推進市場利率化改革,放開銀行存款的利率浮動上限,但銀行業協會的自律機制仍然會為銀行存款利率設置一定的上浮限制。

舉例來說,目前1年期、3年期的存款基準利率分別為1.50%、2.75%。對于金額20萬以上的大額存單利率,國有行、股份及城商行、農商行的定價上限分別為基準利率上浮50%、52%和55%,所以1年期和3年期大額存單的最高利率是2.36%和4.26%。
對于小額普通存款,通常上限為基準利率上浮50%,1年期和3年期的存款利率2.25%和4.13%。
而部分中小銀行發行的1年期與3年期互聯網渠道存款,利率已經觸及自律定價機制上限,如果再加上某些銀行給新用戶的加息福利,則直接超過了上限。
競爭之下,不僅僅是地方性中小銀行,整個銀行體系為互聯網渠道支付的存款利息也會隨之水漲船高,這無疑提升了整個金融體系的潛在經營成本。
而在貸款端,去年受疫情影響,6月17日國務院提出要推動金融系統全年向各類企業合理讓利1.5萬億元,降低企業融資成本;一年期LPR(貸款基準利率)也從1月份的4.15%降至如今的3.85%。
存款利率提升而貸款利率又面臨收縮壓力,一增一減,銀行經營壓力陡然上升。
對于普通投資者,如何重新定位我們的理財規劃?
從兩年前銀行理財打破剛性兌付,到限制貨幣基金的整體規模以及當日T+0申贖上限,再到三方平臺禁售銀行存款,監管層的接連發聲,其實也是讓廣大投資者盡早轉變思維,打破過往對銀行理財產品高收益、低風險的路徑依賴。
“欲戴皇冠,必受其重”,想要獲得超額收益,就必須承擔相應的風險。因此,未來投資理財權益化、居民儲蓄搬家進入資本市場或許是一大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