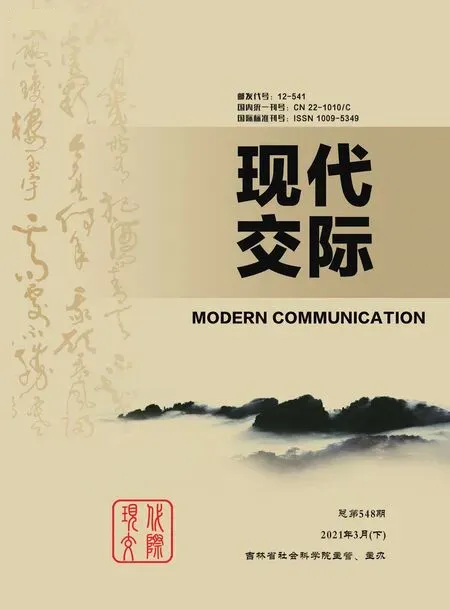基于弗蘭德斯互動分析系統的在線教學分析
周 霈
(湖南科技大學教育學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發對中國乃至世界的教育業產生了巨大影響,為保障諸多學子有學可上,教育部發出“利用網絡平臺,停課不停學”的號召。[1]隨著“停課不停學”工作深入推進,在線教學無可避免地被推到舞臺中央。
在線教學沒有面對面的約束,“學生智能終端在線,人不在線”的現象時有發生,在線課堂依然重復著傳統課堂中教師“滿堂灌”的老路子,改進在線教學質量日漸成為各校關注的話題。從本體論的角度看,課堂教學存在的根本在于師生互動[2];同理,互動也應當成為在線課堂教學的靈魂。師生、生生、人與技術之間的互動效果是檢驗和評價在線教學質量的重要指標。基于此,以改進型的弗蘭德斯互動分析系統為工具,分析在線教學互動的特征,以期為促進在線環境下的教學與學習實踐創新提供參考。
一、弗蘭德斯互動分析系統及其改進
美國學者弗蘭德提出的弗蘭德斯互動分析系統(FIAS)能夠對師生互動事件進行編碼和量化解讀[3],其結構化、定量化等特點使課堂教學評價更科學、客觀,受到國內外諸多學者的青睞。
隨著教學環境不斷變化,課堂教學互動行為日益豐富,在多年的教學實踐應用中,FIAS逐漸暴露出一些局限性:對學生言語的劃分不夠全面;將沉寂單一地概括為沉默或混亂;缺少信息技術應用于課堂教學的分析等。為了分析課堂教學中愈發復雜的交互行為,不少學者對FIAS做出了一些改進。綜合來看,國內對FIAS的改進可分為三個類型:一是從結構上對其加以改進,如寧虹等[4]結合定量與定性研究對FIAS加以改進;二是在原來的基礎上增加技術維度[5](顧小清等);三是基于“以學為中心”的理念進行改進[6]。
縱觀國內外對于利用FIAS分析課堂教學互動特征的研究,大多是針對線下的課堂,鮮有將線上課堂作為研究對象的例子。因此,設計一套適用于在線環境下的教學互動編碼系統成為研究主題之一。
二、在線教學互動分析系統設計
基于網絡的視頻會議系統可實現共享桌面、電子文檔及其他學習資源,便于用戶之間的實時交互,為在線教學提供了新途徑。以FIAS及其改進等研究為基礎,結合以騰訊會議為代表的視頻會議軟件自身特性和功能,設計了改進型的弗蘭德斯互動分析系統,即在線教學互動分析系統(Online Teaching Interaction Analysis System,OTIAS),如表1所示。

表1 OTIAS編碼表
OTIAS對FIAS的優化和調整主要表現在:(1)將教師提問細分成教師提出開放式問題及教師提出封閉式問題兩項;(2)將教師講授細分為教師直接講授和利用PPT等多媒體呈現教學內容;(3)在學生言語中增加同伴討論一項,強調虛擬課堂上的主動交互行為;(4)增加兩個操作交互編碼,即教師操作與學生操作,強調技術與課堂教學的整合;(5)將沉寂細分為學生思考和無助于教學的沉寂。
三、在線教學互動分析
以湖南X高校的《現代遠程教育研究與實踐》在線課程為對象,對一節課堂教學實錄視頻進行編碼,該視頻時長近50分鐘,編碼總量約973個,依次將相連的兩個編碼組成坐標,得到972個編碼組合,并生成互動分析矩陣。

表2 《現代遠程教育研究與實踐》在線課程的教學交互行為比率統計表
1.課堂教學結構分析
對表2編碼進行數量統計,得到《現代遠程教育研究與實踐》課程的教學交互行為比率統計表。從表中數據可以得出以下信息:第一,在線環境中,教師言語比率為81.79%,其中教師講授占教師行為的88.55%;學生言語比率為4.84%,整個課堂中教師行為遠超于學生行為。說明在該環境下,教師處于主導地位,主要通過語言向學生講授知識,學生作為受眾參與課堂,在教學中的互動積極性不高,教學主體地位未能實現。第二,課堂沉寂的比率為7.41%,說明該教師對課堂的掌控力較強,整堂課的教學利用率較高。其中學生思考所占比重為22.22%,教師在提問后給予了學生一定的思考時間;無意義沉寂占比較大,結合課堂觀察可知,這主要是教學過程中偶爾出現網絡卡頓的情況造成的。
2.課堂教學活動分析
課堂中,教師的間接語言行為出現次數為83,而直接語言行為次數為712,明顯高于間接語言行為。結合各編碼在矩陣中的分布,從“穩態格”可看出,序對(5,5)有密集分布,表明教師持續講授時間較長。由于OTIAS中的教師講授可分為直接講授與結合PPT投屏等媒體講授兩類,進一步分析二者頻次,發現教師大部分時間是直接講授(占比約為65.06%)。由此可見,該教師對教學內容的把控較強,在課堂上善于引經據典、發散思維,如利用“你有一個蘋果,我有一個蘋果,互相交換還是一個蘋果;你有一個想法,我有一個想法,互相交換就能得到兩個想法”等語言來鼓勵學生積極發言、同伴討論。序對(8,8)出現頻次為31,說明學生被動回答問題的傾向較高,該教師側重直接教學風格。除此之外,在互動分析矩陣中,“積極格”的記錄次數占總次數的2.26%,“缺陷格”的記錄次數占比為0,說明該教師利用言語行為打造了相對和諧共振的師生交互的心理環境,在教學上傾向于積極強化。
3.課堂互動行為分析
教學過程中,教師有3.81%的時間用于提出問題,其中封閉式問題與開放式問題的比率分別為51.35%和48.65%,兩者占比相當。從課堂實錄視頻中可以看到,教師給學生提供發揮想象的機會較多,多數教學活動由“提問—回答”組成,說明教師注重用問題引導學生學習,從而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及創造性思維能力。另外,騰訊會議支持“彈幕”功能,當學生人數較多時,大部分學習者會采用發送彈幕的方法來表達觀點。與之相對應的,教師為了確保自己所提的問題能夠被所有學生接收到,也會利用彈幕與學生交流,或者發送“點贊”“鼓勵”等表情來激勵學生回答。如表3所示,操作交互中學生操作技術的比率達到55.17%,其中大部分是學生發送彈幕的行為,這與課堂觀察結果一致。
四、在線教學互動的特征
1.多樣性
互聯網的出現,推動了人與人之間交往方式的變化,作為“互聯網+教育”的具體表現,在線教學使課堂中的師生互動突破時空壁壘,延伸到虛擬空間。師生可以靈活選擇一對一、一對多、多對多的交流形式,對交流主題、對象的選擇亦呈現出多樣性的特征,形成如“個別交互學習”“同伴協作學習”等學習模式。另外,在保留傳統教學環境下的師生互動、生生互動等人際交互的同時,在線環境中的教學互動還包含了學習者與網絡學習資源的人機互動和以遠程技術為中介的人際互動,即“人—機—人”互動過程。
2.矛盾性
網絡環境下,數字化符號的內涵和外延發生變化,師生們以符號或表情代表自己的言行與情感,使交談變得更為輕易、便捷。伴隨著情感投入的增強,師生們在教學中的心理期望也不斷上升,認為以超時空虛擬情景作為公共互動空間會使學生、教師、內容三者之間的交互取得較好的成效。在觀察在線教學活動時,發現師生們的互動過程中往往存在高心理期望與現實間的矛盾,具體表現為:以為網絡中的互動能弱化師生的身份界限,體驗平等對話的喜悅,卻常常出現互動話語迷航,無關話題泛濫的現象,難以達到互動的真正目的;以為教師精心設計的多媒體課件會引發學生的興趣,然而課堂中的“沉寂”現象大量存在,學生的信息反饋極為匱乏;以為網絡的匿名性、自發性會產生不同特色的非正式群體(社區),卻發現互動主體以“熟人”為主,課堂中僅有經常活躍的一兩個學生與教師進行互動,同伴之間的、更大范圍的交互基本沒有發生。
3.不平衡性
就本質而言,師生互動的過程,就是師生對話的過程。通過對課堂實錄視頻的內容分析,在言語互動方面,教師引導成分較少,講授成分更多,師生話語比例呈現出明顯的不平衡性。在線課堂中師生互動的突出表現是“教師居中心,學生處邊緣”,教師的言語和非言語行為占據了課堂80%以上的時間,而學生的課堂話語時間明顯不足。此外,技術的引進在豐富教師與媒體、學生與媒體互動方式的同時,也使互動數量與互動質量逐漸失衡。從統計數據來看,學生在課上發布彈幕的次數高于言語表達的次數,最長持續時間為6分鐘左右;從彈幕內容來看,多數是泛泛而談,以信息交流為主,缺乏深度討論,大部分彈幕是回答教師的封閉式問題,主動提問者很少。
五、結語
弗蘭德斯定量分析方法的改進和應用,為在線教學互動特征、互動質量研究提供了寶貴資源與借鑒。研究設計了改進型的弗蘭德斯互動分析系統——在線教學互動分析系統(OTIAS),并對高校的一節在線課程進行編碼分析,發現在線教學互動具有多樣性、矛盾性、不平衡性的特征。疫情使在線教學進入中國教育的舞臺,但它的“舞姿”不夠優美,離我們理想的目標還有一定的差距。教學交互是在線教育基本理論研究的核心問題,也是在線和傳統教育教學改革中必須深入探討的問題。[7]如何避免“照搬傳統課堂”,利用在線教學的互動特征幫助一線教師進行教學實踐,并總結解決問題的方法和策略,是研究者的下一步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