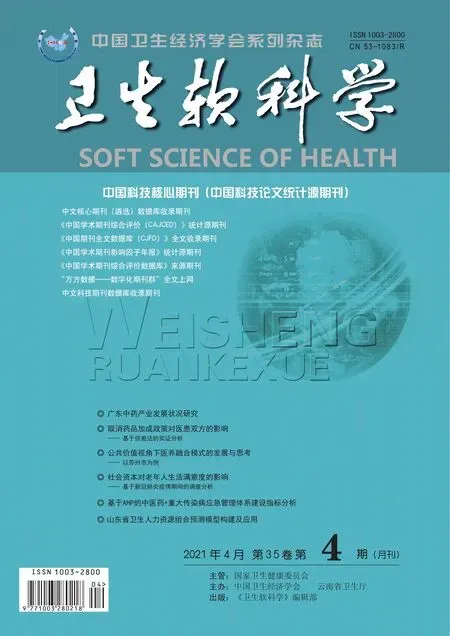我國分級診療制度建設效果評價
周明華,何思長,譚 紅,馮 瀟
(1.瀘州市人民醫院重點工作推進辦公室,四川 瀘州 646000;2.西南醫科大學附屬醫院信息與統計部,四川 瀘州 646000;3.西南醫科大學口腔頜面修復重建與再生實驗室/西南醫科大學附屬口腔醫院牙周粘膜病科,四川 瀘州 646000)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醫療資源由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向城市公立醫院流動,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服務能力被不斷削弱,逐級就診的有序就醫格局被打破[1]。為了切實緩解“看病難、看病貴”問題,重塑逐級診療的有序就醫格局,2009年以來,國家將分級診療制度納入醫藥衛生體系改革,逐步完善頂層設計、實施路徑和評價標準[2]。2015年,我國所有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城市和綜合醫改試點省份都陸續開展了分級診療的試點[3],《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推進分級診療制度建設的指導意見》(國辦發〔2015〕70號)提出了分級診療試點工作評價標準。逐步完善分級診療制度建設,落實分級診療預定目標,提升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服務能力,有利于推動人民群眾合理有序的就醫、構建分級診療有序就醫的秩序。本文依據分級診療試點工作評價標準,對我國分級診療制度建設效果進行評價,為進一步完善分級診療制度提供科學的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我國分級診療制度建設中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鄉鎮衛生院和村衛生室)、全科醫生相關數據來源于2015-2019年《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選取醫療衛生機構數、診療人次數、全科醫生數、提供中醫服務的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占同類機構的比例和改善醫療服務等指標作為評價指標。
1.2 研究方法
采用對比分析法對分級診療制度建設效果與評價標準進行比較分析。按照《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推進分級診療制度建設的指導意見》(國辦發〔2015〕70號)規定的分級診療試點工作評價標準,本文采用的評價標準為:(1)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建設達標率≥95%;(2)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量占總診療量比例≥65%;(3)城鄉每萬名居民有2~3名合格的全科醫生(每萬名城市居民擁有2名以上全科醫生,每個鄉鎮衛生院擁有1名以上全科醫生);(4)提供中醫藥服務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鄉鎮衛生院、社區衛生服務站、村衛生室占同類機構之比分別達到100%、100%、85%、70%;(5)遠程醫療服務覆蓋試點地區50%以上的縣(市、區)。
2 結果
2.1 我國基層醫療機構建設情況
我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總數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數量緩慢增長,鄉鎮衛生院和村衛生室數量有所減少,平均每個街道、鄉鎮和行政村至少有1家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見表1)。

表1 我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建設情況
2.2 我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人次
我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總診療人次以3.17%的年均增長率緩慢增長,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人次占總診療人次比例從2015年的56.36%下降到了2019年的51.95%,未達到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量占總診療量比例≥65%的目標。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站)和鄉鎮衛生院診療人次有所增長,但是鄉鎮衛生院診療人次占總診療人次比例呈下降趨勢(見表2)。

表2 我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人次情況
2.3 我國全科醫生發展情況
我國全科醫生以17.96%的年均增長率迅速增加,每萬人口擁有量從2015年的1.38人上升到了2018年的2.22人,每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站)和鄉鎮衛生院全科醫生擁有量從2015年起超過了2人,達到了城鄉每萬名居民有2~3名合格的全科醫生的目標(見表3)。

表 3 我國全科醫生發展情況 單位:人
2.4 提供中醫藥服務的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占同類機構比例
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和鄉鎮衛生院提供中醫藥服務占同類機構的比例超過了97%以上,但是離100%的目標還有一定差距。社區衛生服務站提供中醫藥服務占同類機構比例在2017年提升到了85%以上,達到了85%的目標。村衛生室提供中醫藥服務占同類機構比例從2015年的60.30%提升到了2019年的71.30%,達到了70%的目標(見表4)。

表4 提供中醫藥服務的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占同類機構的比例 單位:%
2.5 二級及以上公立醫院改善醫療服務
二級及以上公立醫院開展遠程醫療服務占比自2018年起超過了50%,基本達到了遠程醫療服務覆蓋50%的目標。2019年,開展預約診療服務占比為46.10%,臨床路徑管理占比為91.60%,同級檢查結果互認占比為86.10%,優質護理服務占比為93.90%(見表5)。

表5 二級及以上公立醫院改善醫療服務占比情況 單位:%
3 討論
3.1 基層醫療服務能力不足
推進分級診療制度建設以來,我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緩慢增長,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隨著街道數的增加而增加、鄉鎮衛生院隨著鄉鎮數的減少而減少,總體來說,平均每個街道、鄉鎮和行政村至少有1家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從醫療機構數量上來講,基本滿足了分級診療制度中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建設情況;從全科醫生數量上來講,也達到了城鄉每萬名居民有2~3名合格的全科醫生的目標;但是,長期以來形成的優質醫療資源集中在大醫院,基層醫療機構資源匱乏致使其能力不足,成為分級診療制度順利推進的障礙[4]。一是基層衛生人才嚴重缺乏。2019年《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鑒》數據顯示,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衛生技術人員學歷以大專為主、職稱以初級為主,其中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研究生學歷為1.5%、高級職稱為5.0%,鄉鎮衛生院研究生學歷為0.1%、高級職稱為2.1%,人才隊伍整體素質制約了醫療服務水平。二是基層衛生人才隊伍不穩定。工作壓力大、技能提升困難、收入待遇較差等造成基層衛生人才流失嚴重。三是基層衛生財政投入不足。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財政補助收入占總收入的32.29%,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承擔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財政投入不足導致基本藥物配置不齊全、收治病人的能力不足,患者對基層醫療機構的診療能力缺乏信心[5]。居民對基層醫療技術不信任,使其不愿意向下轉診而出現“上轉容易、下轉難”的現象[6]。落實“基層首診”的關鍵在于提升基層醫療服務能力及人才培養,加強對基層醫療機構專項資金的投入,對偏遠、貧困地區制定傾斜政策引進基層衛生人才,完善以轉崗培訓和全科醫生規范化培訓為主的培養體系[7],加強基層人員的繼續技能技術培訓,完善基層醫療機構基本藥物配置,以提高基層醫療服務能力。
3.2 基層醫療機構診療人次呈下降趨勢
我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總診療人次以3.17%的年均增長率緩慢增長,但是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診療人次占總診療人次比例從2015年的56.36%下降到了2019年的51.95%,分級診療政策實踐效果并不理想,醫療服務并沒有下沉到基層醫療機構。一是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整體服務效率不高。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當前投入的衛生資源未得到充分利用,沒有達到最佳投入產出狀態[8]。近年來公共衛生得到重視,大量的公共衛生工作擠占了提供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時間,導致基層人員疲于應付各種檢查,基本醫療服務積極性不高[9]。二是雙向轉診通道不暢。醫聯體或雙向轉診協議雖然明確了上轉、下轉的權利和義務,但是醫療機構間缺少有效的分工協作[10],轉診標準不明確,上轉優先檢查、優先住院的綠色通道不暢通,基層醫療機構藥品目錄不能滿足患者需求,又導致了下轉困難。三是我國的醫保報銷政策對就醫選擇幾乎沒有限制。雖然等級越高報銷比例越低,但是不通過分級診療、雙向轉診的患者也能夠得到醫保報銷,因此居民就醫選擇不容易受到制約,影響了分級診療的效果[11]。因此,在基層衛生機構要積極增加公共衛生人員以減輕醫療服務的壓力,推動基本醫療服務整體效率的提高;要暢通雙向轉診通道,推動醫聯體建設上級醫院幫扶基層,促進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合理完善醫保政策的引導,改革醫療支付方式推動上級醫院積極下轉,合理拉開醫保報銷差距引導患者積極參與基層首診,逐步提升基層醫療機構的醫療服務利用。
3.3 基層醫療機構提供中醫藥服務不足
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和鄉鎮衛生院提供中醫藥服務占同類機構的比例未達到100%,相關研究表明2015-2018年基層中醫診療量逐年減少,占總診療量的比重呈下降趨勢,其中村衛生室的機構數和服務量萎縮是主要影響因素[12],基層醫療機構中醫藥服務能力建設有待提升。一是基層醫療機構中醫人才缺乏,學歷層次較低。2019年《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鑒》數據顯示,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中醫類別占同類機構執業(助理)醫師總數的19.7%、鄉鎮衛生院中醫類別占同類機構執業(助理)醫師總數的16.3%;基層中醫全科醫生的學歷以專科為主,大部分沒有經過全科培訓,整體素質偏低[13]。二是基層醫療機構醫務人員中醫適宜技術掌握程度并不理想。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工作繁重,不愿意花費精力學習中醫適宜技術;中醫適宜技術有賴于經驗積累,缺乏專家指導不利于臨床實踐[14]。要逐步加強基層醫療機構中醫人才培養,通過中醫全科醫生培訓和中醫“師帶徒”促進基層醫療機構醫務人員學習中醫技術,引進中醫藥專業的醫學院校畢業生,通過上級醫院專家坐診、中醫醫院對口支援等充實基層醫療機構中的中醫人才力量。積極探索中醫適宜技術在基層醫療機構的應用,在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中納入群眾容易接受、副作用小的中醫藥特色療法,發揮中醫藥的作用[15]。積極探索社會辦中醫門診部和中醫診所納入基層醫療機構統一管理,發揮其基層中醫藥服務網底的作用[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