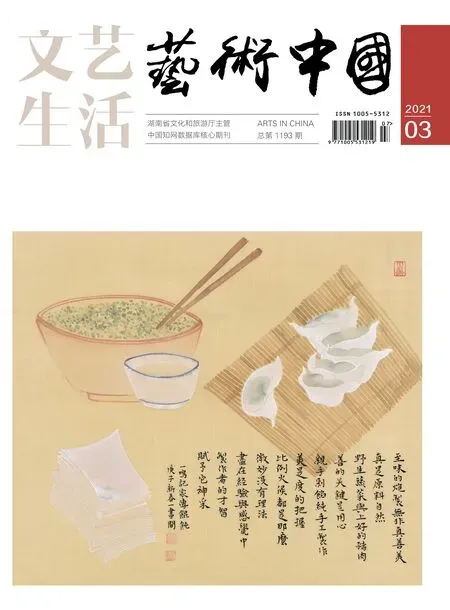直觀而抽象的呈現
——塔皮埃斯作品淺析
◆陳昱(中國美術學院綜合材料繪畫系)
塔皮埃斯的創作思想和繪畫靈感深受二十世紀早期涌現的許多藝術思潮的影響,如達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畫派等現代藝術的發展,引發了塔皮埃斯對人的存在本身和世界本源的深刻思考。這些思考影響了藝術家晚年的世界觀,并進而影響了他的藝術創作。研究一個藝術家,既要從作品本身來研究,還要結合其生長環境中的各類影響因素,尤其要結合藝術家本人的思想發展歷程來研究。藝術與哲學都是在揭示真理,對任何藝術作品的深刻挖掘,必會通向哲學層面的表達與思考,尤其在對塔皮埃斯這位哲
學藝術家或詩人藝術家的研究中更要重視這一點。
西班牙前衛畫家安東尼·塔皮埃斯,是二十世紀歐洲先鋒藝術的先驅,他以繪畫材料和抽象藝術的大膽運用聞名于世,是具有世界代表性的抽象藝術大師。他的創作范圍包括平面作品、拼貼畫和油畫等。他的創作過程與日常創作方式不同,給予附屬品或容易被忽視的物像以關注,大眾在欣賞其作品時,往往面對的是樸素的物品或者幾乎空無一物的灰色畫布上隨意的標志。但就是這種極簡的形式構成,賦予了他作品極大的辨識度。
一、現成物品符號的巧妙運用,極大地拓展了繪畫材料的藝術感知功能。硬紙板、紙張、畫布、清漆和黏土等材料強烈的視覺沖擊力,看似沒有任何形式的統一,但這些物象所呈現出來的看似隨意且浪漫的線條符號,在欣賞者看來卻極具詩意。塔皮埃斯通過這些詩意手法的重復,在陌生與熟悉之間來回穿梭,設法使不熟悉的事物變得容易被人們接受,這與我們平常的認知概念明顯不同。塔皮埃斯的藝術為觀眾提供“感知”而不是定型了的“品味”。從哲學意義上說,也許最終無法直觀表達真理,他卻堅持追求這一個也許虛無縹緲的目標。而且,藝術家堅信,隨著某些形式符號一次又一次的出現,最終真理一定程度上在其作品中被解蔽出來。如圖一作品《石板》和圖二作品《雙足》,塔皮埃斯大膽使用黏土等混合材料,將其塑造成方碑與雙腳的形狀,簡單地在其表面繪制其標志性的十字,黏土燒制后的特殊肌理與涂抹、雕刻的十字,體現了西方語境當中的東方美學,給予了觀眾不一樣的情緒感知。塔皮埃斯常常通過畫面語言的變化來極大拓展材料的一般功能,讓大家從熟知的物品中產生出不一樣的“感知”。

圖一 石板(局部) 黏土混合材料

圖二 雙足 熱黏土和釉
二、繪畫材質肌理變化和疊加技法運用,讓人感受到作品潛在的藝術情緒。通過對塔皮埃斯作品的觀察能夠得出一種感受:如果我們下意識地用與直覺方法相反的觀看方式,你就一定會陷入視覺與作品的對抗中。很多藝術欣賞者和藝術評論家都感覺到了這一困惑。所以,我們很難將通常的欣賞方式和標準的分析方法應用于塔皮埃斯的藝術,否則必然會使觀眾陷入直接翻譯作品的誤區。比如,觀者可能僅僅從塔皮埃斯的作品中感悟到沉默——一種聽不到的、不可言說的語言。但筆者認為塔皮埃斯作品的“沉默”是一種無聲的表達,呈現出了某種能說之外的存在。海德格爾認為:“自持的器具之寧靜就在可靠性之中。只有在可靠性里,我們才能發現器具實際上是什么。”塔皮埃斯的話語是從所選材料的沉默中提取出來的,伴隨著作品材質肌理微妙的變化和技法的重復疊加,讓人感受到某種潛在的情緒沖動。如圖三。

圖三 象征性藍天 模板混合技法
三、繪畫材料與“痕跡簽名”的技法運用,象征人類起源的某種神秘通道。一般來說作品里刻意的痕跡都可看作藝術家的簽名,這些簽名代表了藝術家的創作意圖。但塔皮埃斯作品里的痕跡與簽名的概念渾然一體,正是因為其作品中呈現了它們脆弱、退化、不完整的狀態,才給觀賞者留下某種特別神秘的印象。我們想知道:這雙樸素老舊的鞋子(圖四)是指人類的存在還是指向遺棄?我認為他似乎在尋找著一般人類的痕跡,尋找他們的普遍存在。梵高畫過《農鞋》,盡管有些類似,但相較于梵高畫中農婦因每日勞作而變形嚴重、顯得疲軟無力的農鞋,在我看來,塔皮埃斯的這雙鞋更像是一位經歷了風塵的學者之鞋。鞋型樸素卻挺拔,意味著職業的嚴肅性;鞋面上的十字代表著他對真理的真摯信仰;鞋子表面的老舊肌理,以及鞋底的邊緣變形和塌陷,象征著物主的身體勞績。他是一位思考者,然而與養尊處優的學者不同,他的身體也同樣“操勞于世”,行走在世間,為求得一點真理而歡欣,并將其成果作為痕跡遺留在世。這讓我想起了荷爾德林的詩:“人充滿勞績,但詩意地棲居于大地之上。”在塔皮埃斯看來,盡管人類的起源跡象是多種多樣的:遺物、筆跡、足跡,盡管它們可能提供偶然的或是有意的線索,但他們不能導致起源問題的解決,因為我們無法僅僅從觀察所得出的任何關系中,還原本來的環境。

圖四 鞋 泥土、清漆
四、多層墨跡涂鴉重寫畫面技法運用,藝術地再現人類歷史時間流逝和時代變遷。一個人可能確實是帶著“簽名”出現在這個世上的,但這似乎并不能說明什么。古人遺留下來的涂鴉符號只剩一組組痕跡,它們是由一個個匿名作者留下的語言和視覺景象,它們沒有版權,但屬于每一個人,它們可以出現在每一塊公共墻壁上,可以出現在任何地方。人們涂鴉的無限重復往往源于一種情緒,這種情緒能夠從匿名的藝術家傳遞給匿名的觀眾,畫家會與那些能夠理解他作品的觀眾產生共鳴,這種過程便是來自精神力量的沖擊。涂鴉和重寫帶來了時間的觀念,它們暗示著時間流逝和時代變遷。在多數情況下觀眾都受制于過去,涂鴉把我們的注意力吸引到畫作表面的銘文上,而這些墨跡則暗示了多個圖層:它們的轉移、消失、腐蝕。層疊的墨跡展現了作畫的進程以及思緒的疊加,被刮去的墨跡屬于過去和現在。在塔皮埃斯作品中,涂鴉和隱約的符號文字指向了一種語言,這種語言不是由說話者個人表達出來的,而是一種通用的語言。(如圖五)

圖五 灰與黑 木板繪畫
結語
“墻”在西班牙語中與塔皮埃斯的名字同音,所以他后來索性將作品制作成“墻”。墻的厚重基調承載著藝術家的一切,但藝術家和觀賞者都無法與墻完全的連接在一起,他們無法彌合彼此之間的感知隔閡,他們也不能摧毀“墻”的概念,盡管會有出入,但看到塔皮埃斯作品時大家都能感受到不全然相同但近似的體驗。盡管如此,人們只需要耐心和等待,終能從他作品中得出什么。他的藝術反映了特定的歷史和政治條件,它們反映了在弗朗奎斯特政權下的加泰羅尼亞人的經歷,1936-1939年的西班牙內戰以及弗朗哥政權的暴政,當時政府對加泰羅尼亞人的殘忍鎮壓在青年塔皮埃斯的心里留下了苦痛創傷,這對他今后的審美走向和表達意愿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塔皮埃斯一直認為自己是西班牙人民的游吟詩人。誠如瓦爾特比梅爾在《當代藝術的哲學分析》里表示過對藝術作品用哲學表述方式的存疑:“通過一種哲學的解說,藝術是否疏離了自身,被置入一個它不再能存活的環境中了,就像神奇的閃光的深海魚,一旦被拖到海面上就變得毫無光彩”。的確,任何理性的言語對藝術之感性表現,都有可能誤解,使文章偏離作品的本原。所以,本文只能以作者非常局限的思考,來對塔皮埃斯藝術做一些膚淺的描述和賞析,作品最終的解析還得留給每一個觀者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