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guó)外政府董事制度考察及其啟示
蔣科 付金
基金項(xiàng)目:國(guó)家社會(huì)科學(xué)基金項(xiàng)目(15BFX169)
作者簡(jiǎn)介:蔣 科(1970—),男,湖南洪江人,博士,湖南工商大學(xué)法學(xué)院教授,碩士生導(dǎo)師,研究方向:民商法。
摘 要:政府董事即政府委派或推選至公司董事會(huì)中履行公務(wù)職責(zé)的董事,其功能在于實(shí)現(xiàn)政府的政策目標(biāo)或其他經(jīng)濟(jì)目標(biāo)。國(guó)外基于政府董事的公職身份或其承擔(dān)的公務(wù)職責(zé),對(duì)其考評(píng)、激勵(lì)、監(jiān)督及法律責(zé)任等均體現(xiàn)了強(qiáng)烈的公法性。我國(guó)的國(guó)有股權(quán)董事類似于國(guó)外的政府董事,但現(xiàn)行法律僅承認(rèn)其董事的私法身份而否認(rèn)其公法定位。這使得其在公司獨(dú)立法人地位的保護(hù)下,與公司內(nèi)部人形成了利益同盟,削弱了其作為政府董事的基本功能。我國(guó)可借鑒國(guó)外有益經(jīng)驗(yàn),將國(guó)有股權(quán)董事定位為承擔(dān)公務(wù)職責(zé)的政府董事,以適應(yīng)我國(guó)國(guó)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需要。
關(guān)鍵詞:政府董事;雙重人格;制度借鑒
中圖分類號(hào):DF411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3-7217(2021)06-0154-08
在國(guó)外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國(guó)家,政府對(duì)其出資企業(yè)或涉及某種公共利益的私人企業(yè),往往委派公職人員或聘請(qǐng)專業(yè)人士擔(dān)任公司董事,同時(shí)賦予其特定的公務(wù)職責(zé)并代表公共利益,該類董事即“政府董事”。在我國(guó),國(guó)資委等代表政府履行出資人職責(zé)的機(jī)構(gòu)(以下簡(jiǎn)稱國(guó)資委),同樣向公司制國(guó)企委派或推選其國(guó)有股權(quán)董事,該類董事均具潛在的行政級(jí)別并承擔(dān)著國(guó)資經(jīng)營(yíng)監(jiān)督之公務(wù)職責(zé),事實(shí)上為我國(guó)的政府董事。但我國(guó)的國(guó)有股權(quán)董事雖具政府董事的實(shí)質(zhì)內(nèi)核卻僅具董事的私法身份,這使得其在公司獨(dú)立法人“外殼”的保護(hù)下,利用公司法上“合法”的職權(quán),逐漸擺脫了應(yīng)有的公務(wù)約束,與其作為董事會(huì)中國(guó)家代表的身份漸行漸遠(yuǎn)。本文擬通過(guò)考察國(guó)外政府董事的起源與發(fā)展,明晰其功能定位及其法律地位,并通過(guò)深入考察其具體制度,發(fā)現(xiàn)各國(guó)政府董事的共性和差異,以期借鑒其有益成分建立適合我國(guó)國(guó)情的政府董事制度,為當(dāng)前國(guó)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制度保障。
一、國(guó)外政府董事制度的基礎(chǔ)性考察
(一)政府董事的緣起與發(fā)展
據(jù)現(xiàn)有文獻(xiàn)考察,政府董事制度起源于美國(guó)。1833年1月8日,吉爾平(H.D.Gilpin)、約翰·沙利文(John T. Sullivan)等人根據(jù)美國(guó)銀行章程,被時(shí)任美國(guó)總統(tǒng)安德魯·杰克遜(Andrew Jackson)和參議院選定為美國(guó)銀行的政府董事[1]。他們被視為公職人員并被設(shè)計(jì)成實(shí)現(xiàn)公共目標(biāo)的工具,作為“哨兵”進(jìn)入董事會(huì)是為了觀察公司的行為并監(jiān)督公共利益,隨時(shí)準(zhǔn)備向政府報(bào)告董事會(huì)每一項(xiàng)可能損害人民利益的行為[2]。
政府董事與政府公司相伴而生。政府公司是一個(gè)古老的政治發(fā)明,其是經(jīng)濟(jì)、政治和社會(huì)發(fā)展的產(chǎn)物。在美國(guó),第一家政府公司是美國(guó)第一銀行,它是1791年由國(guó)會(huì)特許設(shè)立的混合公司,政府持有20%股份。1816年美國(guó)第二銀行接替了它的位置,其創(chuàng)新在于授權(quán)總統(tǒng)在獲得參議院同意的情況下任命該行25名董事中的5名政府董事。基于該授權(quán),總統(tǒng)任命了上述政府董事[3]。至于為何設(shè)立政府董事,早在美國(guó)第一銀行設(shè)立時(shí),其創(chuàng)辦人哈密爾頓(Hamilton)就設(shè)想通過(guò)任命公職人員擔(dān)任政府董事“檢查銀行往來(lái)賬目,監(jiān)督和防止銀行管理不善的弊端”。美國(guó)第二銀行創(chuàng)辦人亞歷山大·達(dá)拉斯(Alexander Dallas)則明確指出,國(guó)家銀行不應(yīng)被簡(jiǎn)單地視為商業(yè)銀行,其運(yùn)作不僅僅依靠股東的資金,更多的是依靠國(guó)家的資金。它的建立不只是為了商業(yè)利潤(rùn),更是為了實(shí)現(xiàn)國(guó)家的政策目標(biāo)。在這種情況下,公共利益的保護(hù)應(yīng)當(dāng)加強(qiáng),而委派政府董事是實(shí)現(xiàn)這一目標(biāo)的有效手段[1]。
政府董事自1833年產(chǎn)生以來(lái),在世界各國(guó)從未間斷并得到了廣泛發(fā)展。例如1862年美國(guó)國(guó)會(huì)特許設(shè)立了聯(lián)合太平洋鐵路公司,該公司20名董事會(huì)成員中有5名政府董事;1962年設(shè)立了美國(guó)通信衛(wèi)星公司(Comsat),該公司15名董事會(huì)成員有3名政府董事[4]。即使在私人擁有的政府支持企業(yè)(GSEs),由于其為國(guó)會(huì)特許設(shè)立并承擔(dān)了某種公共使命(如房利美和房地美),美國(guó)總統(tǒng)也保留了任命少數(shù)政府董事的權(quán)力[5]。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jī)后,美國(guó)政府更是收購(gòu)了多家私企的股權(quán),如收購(gòu)?fù)ㄓ闷嚬径鄶?shù)股權(quán)并任命了12名董事會(huì)成員中的10名政府董事[6]。在其他國(guó)家,政府董事也普遍存在,如英國(guó)、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加坡等英美法系國(guó)家;法國(guó)、德國(guó)、意大利、俄羅斯、西班牙、瑞士等大陸法系國(guó)家。可以說(shuō),當(dāng)今世界各國(guó),基于政治、經(jīng)濟(jì)及社會(huì)等原因,其國(guó)企董事會(huì)中均存在國(guó)家代表并呈進(jìn)一步發(fā)展趨勢(shì)[7]。
(二)政府董事的功能
1.對(duì)英美法系國(guó)家政府董事功能的考察。
在美國(guó),政府董事有責(zé)任監(jiān)督企業(yè)的日常運(yùn)行,并在企業(yè)發(fā)生不正當(dāng)行為時(shí)向政府報(bào)告。以美國(guó)通信衛(wèi)星公司的政府董事為例,其有兩個(gè)特殊角色:一是利用他們的存在和投票權(quán)來(lái)影響涉及公共利益的決策;二是作為總統(tǒng)和政府機(jī)構(gòu)的“窗口”,讓他們了解公司的活動(dòng)并傳達(dá)其觀點(diǎn)[4] 。在英國(guó)和新西蘭,其混合公司的政府董事并不是為了制約這些大公司,而是出于一些政策方面的考慮。例如英國(guó)政府自1875年認(rèn)購(gòu)蘇伊士金融公司股份以來(lái),一直參與各種混合企業(yè),在石油、飛機(jī)、農(nóng)業(yè)、證券和國(guó)際金融等領(lǐng)域直接擁有股份。而新西蘭政府則涉足紙張、鋼鐵、煤炭、紡織品和貿(mào)易等行業(yè)。上述這些投資都是為了在特定領(lǐng)域?qū)崿F(xiàn)具體的政策目標(biāo):或是出于戰(zhàn)略性的外交政策原因;或是為了保護(hù)特定產(chǎn)業(yè)不受外國(guó)競(jìng)爭(zhēng)的影響;或是為了對(duì)私人公司的援助請(qǐng)求作出回應(yīng)等[8]。
在澳大利亞,政府公務(wù)員通常會(huì)被政府提名擔(dān)任公司董事,以便讓政府了解公司事務(wù),并在董事會(huì)中代表政府立場(chǎng)。政府董事通常有權(quán)調(diào)查或補(bǔ)充政府政策或其行政管理的某些方面,他們?cè)跊Q策的每一個(gè)環(huán)節(jié)都需考慮政府政策[9]。在菲律賓,政府通常也委派其公職人員到“政府所有或控制的公司”(GOCCs)擔(dān)任董事,該類公司由政府創(chuàng)建,目的是“實(shí)現(xiàn)發(fā)展目標(biāo),特別是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服務(wù),以及基礎(chǔ)設(shè)施發(fā)展。”2011年菲律賓頒布《政府公司法案》,明確規(guī)定政府董事作為政府的受托人對(duì)國(guó)家負(fù)責(zé),并應(yīng)以國(guó)家的最佳利益行事[10]。
2.對(duì)大陸法系國(guó)家政府董事功能的考察。
在法國(guó),根據(jù)其1983年頒布的《公共部門民主化法案》,國(guó)有企業(yè)必須成立一個(gè)三方董事會(huì):1/3為國(guó)家代表(政府董事),1/3為職工代表,1/3 為“合格人員”(獨(dú)立于管理層和政府的人員)。其中國(guó)家代表一般來(lái)源于前財(cái)政部、商業(yè)部、農(nóng)業(yè)部或其他工業(yè)部門的官員,負(fù)責(zé)監(jiān)督執(zhí)行國(guó)家的政策[11]。在意大利,其國(guó)企一直被當(dāng)作追求政治最大化的工具。其作用在于通過(guò)開展公共活動(dòng)來(lái)發(fā)展戰(zhàn)略性產(chǎn)業(yè),彌補(bǔ)私人資本的不足。對(duì)國(guó)企而言,其主要的控股股東是中央政府的經(jīng)濟(jì)財(cái)政部(MEF),委派的政府董事對(duì)政府及公眾負(fù)責(zé)。2008年意大利修改《民法典》,規(guī)定國(guó)家可以在沒(méi)有所有權(quán)的公司任命政府董事,而之所以任命也是為了在特殊的私人公司維護(hù)公共利益[12]。
在俄羅斯,其重要的經(jīng)濟(jì)部門往往由國(guó)企主導(dǎo),而且對(duì)員工超萬(wàn)人和屬于關(guān)鍵產(chǎn)業(yè)的公司,國(guó)家為自己保留了“黃金股”,允許政府在不持有普通股的情況下派遣一名政府董事,并有權(quán)否決董事會(huì)的任何決議[13]。到21世紀(jì)后,國(guó)家間接持股是常見做法,即通過(guò)對(duì)母公司的控制進(jìn)而對(duì)子公司擁有控股權(quán),并推選其公職人員擔(dān)任董事。有證據(jù)表明,俄羅斯國(guó)企董事會(huì)并不是決策的中心,而是作為上級(jí)政府決策的傳遞者。在戰(zhàn)略投資決策等關(guān)鍵問(wèn)題上,政府董事按照上級(jí)政府的指示進(jìn)行投票,即實(shí)際決策者不出現(xiàn)在董事會(huì)中。聯(lián)邦政府認(rèn)為,在國(guó)企管理中,政府董事的任命是保護(hù)其利益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手段[14]。
綜上所述,國(guó)外政府董事均為政府實(shí)現(xiàn)其目標(biāo)的工具,即使在混合所有制甚至私人企業(yè)也不例外。研究文獻(xiàn)還表明,政府董事不僅僅是“沉默的看門狗”,他們還積極參與公司的運(yùn)作。政府董事有義務(wù)讓其各自的部長(zhǎng)了解董事會(huì)面臨的所有問(wèn)題,相關(guān)信息、意見和建議可以在政府和公司之間傳遞,從而更好地實(shí)現(xiàn)政府的目標(biāo)[15]。
(三)政府董事的法律地位及其法律責(zé)任
政府董事具公司董事和政府官員雙重身份,其具公私法上雙重法律地位并承擔(dān)雙重法律責(zé)任,這在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國(guó)家并無(wú)二致。在公司法上,政府董事與普通董事無(wú)異。正如學(xué)者所言:“一旦某人被選為公司董事會(huì)成員,就應(yīng)對(duì)公司所有股東忠心不二,不管其是由誰(shuí)提名或如何被提名。”[16]
例如美國(guó)通信衛(wèi)星公司章程宣布,所有董事包括政府董事在內(nèi)都對(duì)公司負(fù)有相同的信托責(zé)任[4]。在新西蘭,幾乎所有混合所有制公司的政府董事都是政府任命的高級(jí)公務(wù)員,而實(shí)際的任命形式通常支持這樣一種觀點(diǎn):即政府有意讓其被任命者與其他董事以完全相同的方式發(fā)揮職能,除有關(guān)任期外,任何情形下都不可優(yōu)于或不同于其他董事[15]。在澳大利亞,盡管政府董事為公務(wù)員,但仍須承擔(dān)公司法上的董事義務(wù),否則可能承擔(dān)相應(yīng)的民事責(zé)任及刑事責(zé)任[9]。在智利、愛沙尼亞、以色列和斯洛文尼亞,其公務(wù)員擔(dān)任的政府董事受到公司法的約束,而且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有義務(wù)遵守董事會(huì)的保密規(guī)定。同樣,在以色列,政府董事受到公司法的規(guī)制,不受政府的不當(dāng)干預(yù)[17]。
那么,如何看待政府董事的雙重法律地位及其雙重責(zé)任?其是否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這種嚴(yán)格的責(zé)任?有學(xué)者認(rèn)為,政府董事承擔(dān)個(gè)人責(zé)任是可取的,特別是當(dāng)政府公司像一個(gè)以利潤(rùn)為導(dǎo)向的私人公司運(yùn)作時(shí)[18]。還有學(xué)者認(rèn)為,雖然政府董事的雙重身份可能造成沖突,但其在行使商業(yè)判斷時(shí),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quán)來(lái)考慮社會(huì)和政策因素,只要其行為誠(chéng)信,就會(huì)受到商業(yè)判斷規(guī)則的保護(hù)[6]。另有學(xué)者認(rèn)為,政府董事的雙重責(zé)任之所以能夠維持,是因?yàn)槠涫芡胸?zé)任在理論上根本就沒(méi)有明確。換句話說(shuō),董事的受托責(zé)任是消極的,只規(guī)定董事必須“不做”的事而且相當(dāng)寬泛。此外,立法機(jī)關(guān)并沒(méi)有以一種指令性的方式來(lái)界定“董事”,董事缺乏法律上的區(qū)分和類別制度,故適用同質(zhì)原則[16]。當(dāng)然,政府董事的雙重身份有利于其所任職公司獲得政府的支持;反之,也可能犧牲公司的經(jīng)濟(jì)利益而照顧政府的公共利益,而其治理效果則取決于公司與政府利益的趨同或分歧[19]。
綜上,政府董事基于其雙重身份,具有公私法上的雙重法律地位,由此也產(chǎn)生了雙重法律責(zé)任。即對(duì)政府基于其公務(wù)職責(zé)的公法上的責(zé)任以及對(duì)所在公司基于其董事身份的私法責(zé)任。雖然這可能會(huì)導(dǎo)致政府董事角色上的沖突,但各國(guó)立法均承認(rèn)該雙重責(zé)任。這一方面是由于政府設(shè)立的國(guó)企或政府公司本身國(guó)家處于控股地位,政府利益與公司利益大體趨同;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需要借助公司形式實(shí)現(xiàn)其目標(biāo),也便于吸納私人資本的參與,故須滿足公司法上的規(guī)定。此外,政府董事“受托責(zé)任”的寬泛性、董事類別在立法上的同質(zhì)性以及公司法上“商業(yè)判斷規(guī)則”的保護(hù)機(jī)制等,可避免對(duì)政府董事的不當(dāng)干預(yù),這使得其雙重責(zé)任在各國(guó)得以保持至今。
二、國(guó)外政府董事具體制度的考察
(一)政府董事的選任
1.對(duì)英美法系國(guó)家政府董事選任的考察。
在英國(guó),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國(guó)家在一些私人企業(yè)中持有股份,故有從公職人員或退休公務(wù)員中挑選政府董事的做法。任命由首相或部長(zhǎng)決定,不必經(jīng)議會(huì)確認(rèn)或批準(zhǔn)。例如蘇伊士運(yùn)河和英伊石油公司的政府董事由首相任命,而航空事務(wù)部長(zhǎng)任命兩個(gè)航空公司的政府董事,農(nóng)業(yè)部長(zhǎng)則任命英國(guó)糖業(yè)公司的董事長(zhǎng)及另外兩名政府董事。作為政府董事,其不能被所在公司免職[20]。在美國(guó),政府董事不是由股東選舉的,而是由總統(tǒng)和參議院任命的,如前述美國(guó)政府公司中的政府董事。在新西蘭,政府董事的任命通常相對(duì)簡(jiǎn)單。一旦政府決定認(rèn)購(gòu)某一公司的股份,相應(yīng)的部長(zhǎng)將與其秘書通過(guò)非正式的方式討論可能的任命,并通知候任董事。如果各方都同意,部長(zhǎng)則提出正式建議,必要時(shí)提交內(nèi)閣批準(zhǔn)[15]。在加拿大,政府董事通常由內(nèi)閣根據(jù)部長(zhǎng)的推薦任命。在一些公司,董事的任命需征求管理層的意見。精明的經(jīng)理可能會(huì)建議那些在對(duì)待商業(yè)的態(tài)度以及在政治上都可以接受的人,這樣政府實(shí)現(xiàn)了其政治任命,而管理層得到了一個(gè)它認(rèn)為可以接受的董事[21]。
2.對(duì)大陸法系國(guó)家政府董事選任的考察。
在大陸法系國(guó)家,政府董事的提名一般由行使國(guó)企所有權(quán)職能的機(jī)構(gòu)和相關(guān)部委共同承擔(dān)。許多國(guó)家還明確了政府董事提名的最低標(biāo)準(zhǔn),這些標(biāo)準(zhǔn)通常與候選人的教育和專業(yè)背景有關(guān),制定這些標(biāo)準(zhǔn)的目的是改進(jìn)董事會(huì)的組成。在法國(guó),政府所有權(quán)職能部門管理著一個(gè)“董事池”,由各有關(guān)部的部長(zhǎng)選任并以法令形式任命。在以色列,任命董事會(huì)成員須經(jīng)一個(gè)政府委員會(huì)批準(zhǔn),該委員會(huì)確認(rèn)候選人是否符合法律規(guī)定的最低標(biāo)準(zhǔn)。在葡萄牙,公共行政招聘和選拔委員會(huì)根據(jù)具體標(biāo)準(zhǔn)對(duì)董事會(huì)候選人進(jìn)行審查。除了最低標(biāo)準(zhǔn)外,在填補(bǔ)董事會(huì)空缺時(shí),還會(huì)采取一種量身定做的方法來(lái)確定其技能、經(jīng)驗(yàn)和個(gè)人特性的適當(dāng)組合。在意大利,經(jīng)濟(jì)財(cái)政部(MEF)部長(zhǎng)負(fù)責(zé)董事會(huì)成員的選任,政府董事往往是根據(jù)其政治忠誠(chéng)度而不是商業(yè)才能挑選的[12]。在俄羅斯,政府董事一般為高級(jí)官員,有關(guān)提名受個(gè)人偏好和關(guān)系的影響很大,而以專業(yè)素質(zhì)為依據(jù)的提名則極少。據(jù)經(jīng)濟(jì)合作與發(fā)展組織(OECD)報(bào)告稱,采用雙重所有權(quán)模式的國(guó)家往往比采用單部門模式或集中模式的國(guó)家擁有更多的政府董事,這是由于政府機(jī)構(gòu)之間的利益沖突得不到解決,導(dǎo)致爭(zhēng)相向國(guó)企派出盡可能多的董事。而俄羅斯就是采用該模式的國(guó)家,導(dǎo)致其國(guó)家機(jī)構(gòu)之間存在著激烈的爭(zhēng)權(quán)斗爭(zhēng)[14]。
(二)政府董事的考評(píng)
傳統(tǒng)上,國(guó)企董事會(huì)缺少一個(gè)正式的程序考評(píng)其成員,但這已經(jīng)開始轉(zhuǎn)變。埃及、智利、印度、馬來(lái)西亞、新西蘭、南非、泰國(guó)以及許多OECD國(guó)家現(xiàn)在都要求或鼓勵(lì)董事會(huì)進(jìn)行定期考評(píng),目的是了解成員如何為董事會(huì)的任務(wù)作出貢獻(xiàn)并提供反饋[22]。各國(guó)考評(píng)做法不盡相同:在把國(guó)企視為政府部門一樣管理的國(guó)家,趨向于自上而下的考評(píng),即國(guó)有股權(quán)部門根據(jù)公司目標(biāo)對(duì)董事會(huì)進(jìn)行考評(píng);而在更商業(yè)化的國(guó)企,趨勢(shì)則是更多地依靠董事會(huì)自我評(píng)估。通常是把董事會(huì)作為一個(gè)整體進(jìn)行評(píng)估,同時(shí)也在一定程度上考評(píng)董事個(gè)體,一個(gè)正在達(dá)成的共識(shí)是將考評(píng)結(jié)果反饋至提名過(guò)程[23]。
1.對(duì)英美法系國(guó)家政府董事考評(píng)的考察。
在英國(guó),國(guó)有股東事務(wù)管理局不定期評(píng)估董事會(huì)成員的表現(xiàn),另對(duì)董事會(huì)組成和績(jī)效進(jìn)行定期評(píng)估。此外,董事會(huì)主席通過(guò)借助“外腦”或自我評(píng)估,對(duì)董事會(huì)整體績(jī)效進(jìn)行年度內(nèi)部評(píng)估,該結(jié)果將用于其與國(guó)有股東事務(wù)管理局討論董事會(huì)的未來(lái)構(gòu)成[23]。在澳大利亞,國(guó)企董事長(zhǎng)每年須向持股部長(zhǎng)提交一份董事會(huì)業(yè)績(jī)?cè)u(píng)價(jià)報(bào)告,而績(jī)效應(yīng)符合國(guó)企的戰(zhàn)略目標(biāo)[9]。在新西蘭,政府要求國(guó)企董事會(huì)進(jìn)行定期自我評(píng)估,具體方式是董事長(zhǎng)接受董事會(huì)的評(píng)價(jià),而所有董事又要受到董事長(zhǎng)的單獨(dú)評(píng)價(jià)[24]。在菲律賓,2011年通過(guò)了《政府公司法案》,授予監(jiān)管政府公司的政府委員會(huì)廣泛職權(quán),包括建立績(jī)效評(píng)估體系,使用績(jī)效計(jì)分卡對(duì)公司及董事進(jìn)行定期考評(píng),要求公司報(bào)告運(yùn)營(yíng)和管理情況等[10]。
2.對(duì)大陸法系國(guó)家政府董事考評(píng)的考察。
在波蘭,國(guó)庫(kù)部在國(guó)企年度股東大會(huì)上要對(duì)單個(gè)董事會(huì)成員進(jìn)行評(píng)價(jià),而其負(fù)面評(píng)價(jià)會(huì)成為股東大會(huì)改變董事會(huì)組成的動(dòng)力。如果政府董事沒(méi)有得到國(guó)庫(kù)部的認(rèn)可,則不能在之后的三年繼續(xù)代表國(guó)庫(kù)部出任董事[23]。在挪威,其《公司治理實(shí)務(wù)守則》規(guī)定,董事會(huì)應(yīng)當(dāng)每年對(duì)董事業(yè)績(jī)和專業(yè)知識(shí)進(jìn)行評(píng)價(jià),并將結(jié)果反饋給提名委員會(huì),該規(guī)定適用于所有上市國(guó)企。在希臘、斯洛伐克等國(guó)家,董事會(huì)在向所有權(quán)機(jī)構(gòu)、行業(yè)部門或議會(huì)提交報(bào)告時(shí),會(huì)被問(wèn)及是否存在偏離公司目標(biāo)的情況[24]。在智利,所有權(quán)機(jī)構(gòu)(SEP)管理董事會(huì)的年度考評(píng),對(duì)董事會(huì)成員進(jìn)行問(wèn)卷調(diào)查,重點(diǎn)關(guān)注董事會(huì)整體績(jī)效。考評(píng)由外部專家完成,SEP會(huì)對(duì)考評(píng)結(jié)果與往年進(jìn)行比較。SEP對(duì)董事會(huì)成員的出勤率、目標(biāo)完成情況以及國(guó)企的整體表現(xiàn)進(jìn)行評(píng)估。在秘魯,所有權(quán)機(jī)構(gòu)則為國(guó)企董事會(huì)建立了一個(gè)正式的考評(píng)程序。現(xiàn)行制度包括每位董事 (董事長(zhǎng)除外)的自我評(píng)價(jià),每位董事對(duì)董事會(huì)的整體評(píng)價(jià),以及董事長(zhǎng)對(duì)每位董事的評(píng)價(jià)。考評(píng)標(biāo)準(zhǔn)則是評(píng)估整個(gè)董事會(huì)的運(yùn)作和每個(gè)董事會(huì)成員的參與程度[25]。
總而言之,對(duì)政府董事的考評(píng),主要是與其所在國(guó)企董事會(huì)的整體考評(píng)緊密聯(lián)系的。研究表明,考評(píng)如果是正式的、設(shè)計(jì)良好的、公平的、反復(fù)的且與改進(jìn)計(jì)劃聯(lián)系在一起,那么考評(píng)是有用的。考評(píng)還可作為查明國(guó)企董事會(huì)技能差距的一種手段,以幫助尋找新的合適的董事會(huì)成員[26]。
(三)政府董事的激勵(lì)
各國(guó)實(shí)踐表明,如果由公務(wù)員擔(dān)任政府董事,為避免分裂忠誠(chéng)的可能,其應(yīng)從政府領(lǐng)取工資并對(duì)政府負(fù)責(zé)。而從私營(yíng)部門選任的政府董事,則可考慮其薪酬參照市場(chǎng)標(biāo)準(zhǔn),但仍應(yīng)低于市場(chǎng)水平,因?yàn)檎侣毼凰鶐?lái)的聲譽(yù)可對(duì)其今后的職業(yè)生涯產(chǎn)生積極影響[26]。
1.對(duì)英美法系國(guó)家政府董事激勵(lì)的考察。
在英美法系國(guó)家,對(duì)政府董事的激勵(lì)基本遵循公職人員的規(guī)定。為了防止其利用公司職位尋租,多以精神激勵(lì)為主。例如美國(guó)銀行的政府董事,他們聲稱在這個(gè)職位上得不到任何報(bào)酬[2]。又如在新加坡淡馬錫公司,對(duì)于政府董事和非政府董事實(shí)行兩套完全不同的激勵(lì)機(jī)制。為了切斷政府董事與公司的利益關(guān)聯(lián),確保其公平和中立,政府董事不能從淡馬錫公司得到任何實(shí)質(zhì)性的獎(jiǎng)勵(lì),對(duì)其激勵(lì)實(shí)行“經(jīng)營(yíng)優(yōu)而升”的原則。而對(duì)非政府董事一般按市場(chǎng)規(guī)則予以激勵(lì),主要包括年薪、董事會(huì)津貼以及專門委員會(huì)的任職薪酬等[27]。而在菲律賓,為了結(jié)束政府公司之間的不同待遇,所有政府公司均被《薪酬標(biāo)準(zhǔn)化法》所覆蓋。另《政府公司法案》規(guī)定,負(fù)責(zé)監(jiān)管的政府委員會(huì)應(yīng)制定適用于一切政府公司官員和雇員的統(tǒng)一職位薪酬分類體系,即使有相反的法律規(guī)定,也應(yīng)適用該職位薪酬分類體系[10]。近年來(lái),為了吸引專業(yè)人士擔(dān)任政府董事,經(jīng)濟(jì)合作與發(fā)展組織(OECD)建議國(guó)企董事會(huì)的薪酬應(yīng)反映市場(chǎng)狀況。然而在實(shí)踐中,多數(shù)國(guó)家國(guó)企董事會(huì)的薪酬仍低于市場(chǎng)水平[12]。政府傾向于限制國(guó)企董事會(huì)成員的薪酬,往往禁止股票期權(quán)等激勵(lì)措施,政府董事的最終薪酬應(yīng)被視為是公平的[26]。
2.對(duì)大陸法系國(guó)家政府董事激勵(lì)的考察。
在大陸法系國(guó)家,政府同樣傾向于限制國(guó)企董事的薪酬,其薪酬均低于市場(chǎng)水平,各國(guó)都希望避免公共部門薪酬過(guò)高而引發(fā)公眾爭(zhēng)議[25]。在西班牙,政府董事除了參會(huì)津貼,不再接受任何酬勞。在立陶宛,禁止政府董事獲得官員薪俸之外的收入,其獎(jiǎng)懲適用公務(wù)員標(biāo)準(zhǔn)[28]。在波蘭,國(guó)企董事的薪酬與私人企業(yè)的同行相比,后者的薪酬是前者的十倍。在挪威,政府于2006年發(fā)布《國(guó)有企業(yè)薪酬白皮書》,明確國(guó)企不得在管理層使用股票期權(quán)。捷克、芬蘭、拉脫維亞近年來(lái)對(duì)國(guó)企薪酬也進(jìn)行了限制,發(fā)布了相關(guān)薪酬指引。德國(guó)、意大利、瑞士則實(shí)施了旨在加強(qiáng)國(guó)企董事誠(chéng)信的規(guī)則。據(jù)調(diào)查,70%的國(guó)家對(duì)國(guó)企董事會(huì)的薪酬設(shè)定了某種法律或政策限制[12]。
(四)政府董事的監(jiān)督
1.對(duì)英美法系國(guó)家政府董事監(jiān)督的考察。
在英美法系國(guó)家中,新西蘭國(guó)企的股份通常由兩個(gè)部委持有,對(duì)其監(jiān)督由半自治的皇家公司監(jiān)督咨詢機(jī)構(gòu)(CCMAU)執(zhí)行。CCMAU還就國(guó)企戰(zhàn)略、投資機(jī)會(huì)和其他與國(guó)企相關(guān)問(wèn)題為部長(zhǎng)提供咨詢。除了接受審計(jì),國(guó)企及其董事會(huì)還要接受國(guó)會(huì)的監(jiān)督(包括特別委員會(huì)的審查)和監(jiān)察專員的監(jiān)督[29]。在新加坡,政府與國(guó)有控股公司之間的關(guān)系,體現(xiàn)了政府作為所有者和監(jiān)管機(jī)構(gòu)的角色分離,在監(jiān)管時(shí)必須同時(shí)考慮代理成本和政治成本,建立有效的監(jiān)督工具,如績(jī)效評(píng)估、披露要求、基于績(jī)效的合同和獨(dú)立的董事會(huì)成員等[30]。在菲律賓,《政府公司法案》規(guī)定,負(fù)責(zé)監(jiān)管的政府委員會(huì)應(yīng)銘記特定類型信息披露的目的,并應(yīng)建立機(jī)制確保信息能夠?yàn)槠胀ü娝斫狻E兜娘@著性和透明度非常重要,這是平衡公司和監(jiān)管者之間信息不對(duì)稱的重要措施。政府委員會(huì)可以授權(quán)成立一個(gè)由其控制的公司內(nèi)部審計(jì)辦公室協(xié)助其監(jiān)督,對(duì)于公司業(yè)績(jī)和戰(zhàn)略目標(biāo),政府委員會(huì)也可建立對(duì)其審計(jì)的監(jiān)督程序[10]。
2.對(duì)大陸法系國(guó)家政府董事監(jiān)督的考察。
在大陸法系國(guó)家中,通過(guò)信息公開來(lái)強(qiáng)化對(duì)國(guó)企及其董事的監(jiān)督。如瑞典國(guó)企被要求發(fā)布詳細(xì)的季度報(bào)告,一些國(guó)企還組織了“資本市場(chǎng)日”,讓外部財(cái)務(wù)分析師和記者就公司相關(guān)問(wèn)題進(jìn)行提問(wèn)。此外,瑞典于2007年通過(guò)了《國(guó)有企業(yè)對(duì)外報(bào)告指引》,規(guī)定國(guó)企外部報(bào)告應(yīng)與上市公司一樣透明[31]。在德國(guó),2009年頒布的《聯(lián)邦預(yù)算法案》規(guī)定,不僅聯(lián)邦政府控股管理局的官員,而且國(guó)企董事會(huì)成員也可被要求出席特定的議會(huì)委員會(huì)接受質(zhì)詢。在希臘,2005年的立法改革將內(nèi)部審計(jì)引入了國(guó)企,政府至少任命一名內(nèi)部審計(jì)師,由其向國(guó)家所有權(quán)機(jī)構(gòu)報(bào)告。在土耳其,通過(guò)2007年的部長(zhǎng)理事會(huì)法令,財(cái)政部在收集國(guó)企信息和國(guó)企年度匯總報(bào)告等方面的作用得到了加強(qiáng)。在智利、愛沙尼亞、以色列、斯洛文尼亞四個(gè)國(guó)家,其透明度和披露安排包括編制國(guó)企總體年度報(bào)告,建立內(nèi)部審計(jì)職能和程序,實(shí)施年度獨(dú)立外部審計(jì)以及高質(zhì)量的會(huì)計(jì)和審計(jì)標(biāo)準(zhǔn),等等[17]。
三、國(guó)外政府董事制度對(duì)我國(guó)的啟示
通過(guò)對(duì)國(guó)外政府董事制度立法與實(shí)踐的考察,我們發(fā)現(xiàn),政府董事制度自1833年發(fā)端于美國(guó)銀行以來(lái),在世界各國(guó)從未間斷并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其共性在于:一是政府董事均由政府基于股權(quán)或公共利益任命,其功能則在于實(shí)現(xiàn)政府的政策目標(biāo)或其他經(jīng)濟(jì)目標(biāo);二是政府董事均承擔(dān)著公務(wù)職責(zé),其具公私法上雙重法律地位并承擔(dān)雙重責(zé)任;三是基于其承擔(dān)的公務(wù)職責(zé),對(duì)其考評(píng)、激勵(lì)與監(jiān)督等制度均體現(xiàn)了強(qiáng)烈的公法性。政府董事制度的差異則在于,各國(guó)因歷史、經(jīng)濟(jì)、政治及法律傳統(tǒng)等原因,其國(guó)家所有權(quán)的行使模式及國(guó)企治理機(jī)制有所區(qū)別,進(jìn)而導(dǎo)致政府董事的相關(guān)具體制度有所不同。基于以上考察,結(jié)合我國(guó)國(guó)企董事會(huì)實(shí)踐,我們可以獲得以下啟示。
(一)我國(guó)的國(guó)有股權(quán)董事當(dāng)為政府董事
國(guó)有股權(quán)董事是否為政府董事,似乎是一個(gè)頗具爭(zhēng)論的問(wèn)題。依出資人股東與企業(yè)法人分離之法理,企業(yè)的董事為其自身法人機(jī)關(guān)成員,絕非個(gè)別出資人股東(政府)的董事。但實(shí)踐中,我國(guó)的國(guó)有股權(quán)董事實(shí)際又受國(guó)資委等代表政府履行出資人職責(zé)機(jī)構(gòu)的控制,現(xiàn)行理論無(wú)法作出合理解釋。本文通過(guò)對(duì)國(guó)外政府董事制度的梳理發(fā)現(xiàn),我國(guó)的國(guó)有股權(quán)董事實(shí)際與國(guó)外的政府董事無(wú)異,其具潛在的公職身份并承擔(dān)著國(guó)資經(jīng)營(yíng)監(jiān)督之公務(wù)職責(zé),實(shí)質(zhì)為國(guó)資委代表政府委派的公務(wù)代表。故國(guó)資委對(duì)其控制是源自行政權(quán)的控制而不是股權(quán)的控制,股權(quán)僅是其當(dāng)選為政府董事的手段。故從公法的角度看,國(guó)資委的控制是符合法理的。
近年來(lái),我國(guó)學(xué)者相繼提出了我國(guó)政府董事的概念。有學(xué)者認(rèn)為,政府董事即國(guó)家直接投資下的國(guó)有股權(quán)董事,是典型的股東董事而不是政府官員[32];有學(xué)者則認(rèn)為,政府董事當(dāng)為公務(wù)員,但僅存在
于國(guó)有資產(chǎn)經(jīng)營(yíng)公司,而在其轉(zhuǎn)投資的普通國(guó)企不存在[33];還有學(xué)者認(rèn)為,政府董事即國(guó)企董事會(huì)中具有一定級(jí)別、由政府支付薪酬的外部董事,廣義上則指政府選派的所有國(guó)企董事會(huì)成員[34];另有學(xué)者認(rèn)為,政府董事即政府委派的董事且均應(yīng)設(shè)置為外部董事[35]。然而,上述概念雖具政府董事之名但無(wú)其實(shí)質(zhì)內(nèi)涵,因?yàn)檎率钦诠蓹?quán)或公共利益而委任到公司董事會(huì)中履行公務(wù)職責(zé)的國(guó)家代表,不是私法上所謂的“股東董事”或“外部董事”。
從國(guó)外實(shí)踐看,政府董事通常是政府通過(guò)出資預(yù)先取得股東身份,進(jìn)而通過(guò)公司法上的選舉機(jī)制,將其公職人員或遴選的專業(yè)人士推選到公司董事會(huì),同時(shí)賦予其相應(yīng)的公務(wù)職責(zé),以實(shí)現(xiàn)對(duì)公司日常經(jīng)營(yíng)的監(jiān)督并達(dá)成政府的公共目標(biāo)。換言之,政府董事是政府借助私法機(jī)制實(shí)現(xiàn)其公共目標(biāo)的工具。我國(guó)的國(guó)有股權(quán)董事與國(guó)外的政府董事實(shí)質(zhì)相同,只不過(guò)其雖具潛在的行政級(jí)別卻不具公職身份,由此造成其僅為公司董事的錯(cuò)覺而忽視了其本質(zhì)內(nèi)涵。但如此一來(lái),一方面,褪除了其本應(yīng)承擔(dān)的公務(wù)職責(zé);另一方面,又混淆了國(guó)資委行政權(quán)與股東權(quán)的邊界,損害了公司正常運(yùn)行之機(jī)理。因此,我們只有揭開國(guó)有股權(quán)董事私法身份的“面紗”,還原其政府董事的本來(lái)面目,方能實(shí)現(xiàn)其本質(zhì)功能并避免國(guó)資委行政權(quán)的濫用,確保國(guó)家資本與私人資本的有機(jī)融合,防止混合所有制企業(yè)國(guó)資流失并保障政府目標(biāo)的實(shí)現(xiàn)。
(二)我國(guó)的國(guó)有股權(quán)董事當(dāng)具公私法上雙重身份
國(guó)外立法與實(shí)踐表明,當(dāng)政府作為出資人時(shí),往往委派其公職人員或遴選專業(yè)人士出任公司董事,該類董事兼具公私法上雙重身份,并負(fù)責(zé)監(jiān)督董事會(huì)的日常經(jīng)營(yíng)決策。而在我國(guó),國(guó)有股權(quán)董事即使原為黨政機(jī)關(guān)公職人員,一旦其轉(zhuǎn)任國(guó)企,則僅具公司董事的私法身份且多兼經(jīng)理層職務(wù),并非純粹在董事會(huì)中履行監(jiān)督職責(zé)。這一方面使得其混同于非國(guó)有股權(quán)董事,與普通董事無(wú)異,其個(gè)人利益與公司內(nèi)部人員高度重合,喪失了作為政府董事的功能;而另一方面,其仍保留相應(yīng)的行政級(jí)別,變成了名不符實(shí)的“雙面人”。
我國(guó)目前國(guó)有股權(quán)董事的私法“面具”,掩蓋了其潛在的公法身份,方便其規(guī)避公法義務(wù)。在國(guó)外,由公職人員擔(dān)任政府董事是普遍現(xiàn)象,而為何賦予政府董事以公職身份,除了便利其履行公務(wù)職責(zé)外,還有一個(gè)重要原因,即“國(guó)企公司化的背后,往往隱藏著國(guó)企及其官員逃避公法規(guī)制的愿望”[36]。同理,我國(guó)的國(guó)有股權(quán)董事同樣具此動(dòng)機(jī),只有將其公法身份顯露于外并予以公法規(guī)制,方能使其區(qū)別于非國(guó)有股權(quán)董事,發(fā)揮作為政府董事的功能。此外,鑒于政府董事承擔(dān)著對(duì)國(guó)資經(jīng)營(yíng)的監(jiān)督職責(zé),其當(dāng)為“非管理層董事”而不能兼任經(jīng)理層職務(wù),以保障其履行監(jiān)督職責(zé)的純粹性并防止內(nèi)部人控制。該身份定位與當(dāng)前國(guó)資委對(duì)國(guó)有獨(dú)資公司委派的外部董事類似,只不過(guò)政府董事作為國(guó)有股權(quán)董事,凡國(guó)有股權(quán)所在之處均存在政府董事,該定位適應(yīng)了推進(jìn)國(guó)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需要。
我國(guó)將國(guó)有股權(quán)董事定位為政府董事并賦予其公法身份具有現(xiàn)實(shí)可行性。一是我國(guó)含國(guó)有股權(quán)董事在內(nèi)的國(guó)企領(lǐng)導(dǎo)均具潛在的行政級(jí)別,各級(jí)組織部門將其納入“企業(yè)領(lǐng)導(dǎo)干部”管理,事實(shí)上為公職人員,我國(guó)《刑法》也將其界定為“國(guó)家工作人員”。二是我國(guó)《公務(wù)員法》明確規(guī)定了黨政機(jī)關(guān)與國(guó)有企事業(yè)單位領(lǐng)導(dǎo)之間的轉(zhuǎn)任、調(diào)任等交流制度,對(duì)專業(yè)性較強(qiáng)的職位還可實(shí)行聘任制公務(wù)員并采用協(xié)議工資制。該類規(guī)定打通了國(guó)家公職人員與政府董事身份互換的渠道,且有利于國(guó)資委聘請(qǐng)市場(chǎng)專業(yè)人士擔(dān)任政府董事并納入公務(wù)員管理,確保其公務(wù)職責(zé)的履行。三是根據(jù)我國(guó)《公司法》,國(guó)資委作為股東推選國(guó)有股權(quán)董事是其法定權(quán)利,而至于該候選人是否為公務(wù)員在所不問(wèn),只要不違反公司法上董事消極資格的規(guī)定即可。基于我國(guó)國(guó)企客觀現(xiàn)實(shí)及上述法律上的依據(jù),明確我國(guó)國(guó)有股權(quán)董事的公法身份,有利于其作為政府董事功能的實(shí)現(xiàn)。
(三)我國(guó)的國(guó)有股權(quán)董事制度當(dāng)回歸其公法性
基于國(guó)有股權(quán)董事本質(zhì)上為政府董事,在具體制度構(gòu)建中,我們當(dāng)突破現(xiàn)行依其私法身份的制度構(gòu)建路徑,著重其公法身份的回歸。
在選任上:一是明確公法上的選任主體。政府董事應(yīng)由國(guó)資委代表政府統(tǒng)一遴選并委派,但事先應(yīng)在政府內(nèi)部協(xié)調(diào)好相關(guān)行業(yè)主管部門及組織部門之間的關(guān)系。二是完善選任標(biāo)準(zhǔn)。在堅(jiān)持政治性的前提下更加注重技術(shù)性,建立資格準(zhǔn)入制度,開發(fā)“政府董事池”。三是實(shí)行“雙軌運(yùn)行”的選拔機(jī)制。對(duì)原具公職身份擬任政府董事的采用行政性選任,而對(duì)專業(yè)人士擬任政府董事的則采用市場(chǎng)性選拔并實(shí)行聘任公務(wù)員制,以此兼顧其政治性與專業(yè)性。
在考評(píng)上:一是規(guī)范考評(píng)權(quán)主體的權(quán)限。根據(jù)我國(guó)國(guó)情,政府董事的業(yè)績(jī)考評(píng)由國(guó)資委代表政府集中行使,而相關(guān)組織部門則負(fù)責(zé)其管理權(quán)限范圍內(nèi)政府董事的綜合考評(píng)。二是完善考評(píng)標(biāo)準(zhǔn)。應(yīng)著重政府董事履行國(guó)資經(jīng)營(yíng)之監(jiān)督職責(zé)的考評(píng),即“監(jiān)督業(yè)績(jī)”的考評(píng)而非“經(jīng)營(yíng)業(yè)績(jī)”的考評(píng),后者僅作參考,使之區(qū)別于對(duì)經(jīng)理層的考評(píng)。三是創(chuàng)新考評(píng)方式并注重結(jié)果運(yùn)用。對(duì)常任制與聘任制公務(wù)員擔(dān)任的政府董事實(shí)施分類考評(píng),后者還當(dāng)依聘任合同考評(píng)。將董事會(huì)的整體考評(píng)與董事個(gè)體考評(píng)相結(jié)合,完善考評(píng)信息保障機(jī)制,建立考評(píng)結(jié)果反饋機(jī)制并與繼任計(jì)劃掛鉤。
在激勵(lì)上:一是明確政府董事的激勵(lì)主體當(dāng)為國(guó)資委而非其所在公司;二是激勵(lì)依據(jù)當(dāng)為其履行公務(wù)職責(zé)的考評(píng)結(jié)果;三是激勵(lì)方式以政治激勵(lì)為主物質(zhì)激勵(lì)為輔,恢復(fù)公職人員的激勵(lì)方式,取消績(jī)效年薪與任期激勵(lì)等市場(chǎng)化薪酬(聘任制政府董事依合同),同時(shí)建立信息公開制度。
在監(jiān)督上:一是明確公法性監(jiān)督主體及其監(jiān)督內(nèi)容。國(guó)資委主要對(duì)其履行國(guó)資經(jīng)營(yíng)之監(jiān)督職責(zé)實(shí)施監(jiān)督,審計(jì)部門側(cè)重對(duì)其實(shí)施任期及離任審計(jì)監(jiān)督,紀(jì)檢監(jiān)察部門側(cè)重對(duì)其廉潔及作風(fēng)等實(shí)施監(jiān)督。二是協(xié)調(diào)構(gòu)建公法性監(jiān)督規(guī)范體系,完善公法性監(jiān)督方式與程序。三是健全信息公開機(jī)制,發(fā)揮企業(yè)內(nèi)部監(jiān)督與社會(huì)公眾監(jiān)督的作用。
在法律責(zé)任上:政府董事的民事責(zé)任與普通董事無(wú)異,但鑒于其實(shí)際受國(guó)資委的行政控制,為遏制國(guó)資委行政權(quán)的濫用,立法應(yīng)創(chuàng)設(shè)“影子董事”責(zé)任制度并建立國(guó)家民事賠償機(jī)制,以有效區(qū)分國(guó)資委與政府董事的民事責(zé)任;在政府董事的公法責(zé)任方面,應(yīng)突出基于其公職身份的行政責(zé)任,而行政處分當(dāng)為其最主要的責(zé)任形式,在刑事責(zé)任方面則適用國(guó)家公職人員的規(guī)定。
參考文獻(xiàn):
[1] Gilpin H D .Government directors of the United States bank[R].Working Paper, U. S. Congressional Serial Set,1833:1-40.
[2] Benton T H.Thirty years view:A history of the working of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from 1820 to 1850[M]. Whitefish:Kessinger Publishing Co,2010:387-391.
[3] Hon S Chan,David H Rosenbloom. Public enterprise reforms in the U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 drift towards constitutionalization and departmentalization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J].The Journal of Institute of Public Enterprise,2010(1&2):1-29.
[4] Herman Schwartz. Governmentally appointed directors in a private corporation:The communications satellite act of 1962[J].Harvard Law Review,1965(2):350-364.
[5] Guido Ferrarini,Marilena Filippelli.Independent directors and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around the world[R].ECGI Working Paper Series in Law,2014:1-39.
[6] Barbara Black.The U.S.“as reluctant shareholder”:Government,business and the law[J]. Entrepreneurial Business Law Journal,2010(2):561-596.
[7] Curtis J Milhaupt,Mariana Pargendler.Governance challenges of liste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round the world: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a framework for reform[J]. Cornel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2017(3):473-542.
[8] Philip Siller.Taming the modern corporation through government directors[J].University of Toronto Faculty of Law Review,1976(1):30-49.
[9] Meredith Edwards,John Halligan,Bryan Horrigan,et al.Public sector governance in Australia:Board governance in authorities and companies[M].ANU Press,2012:131-150.
[10]Leandro Angelo Y.Aguirre.Shifting paradigms:The need to recognize agency problems in government-owned-and-controlled corporations in the Philippines[J].Philippine Law Journal,2013(4):820-856.
[11]Pascual-Fuster,Bartolome,and Rafel Crespi-Cladera.Politicians inside the boardroom:Is it a convenient burden?[D].Palma:Universitat de les Illes Balears,2016:1-52.
[12]OECD.Ownership and govern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A compendium of national practices[R].OECD,2018:1-85.
[13]Carsten Sprenger.State ownership in the Russian economy:Its magnitude,structure and governance problems[J].The Journal of Institute of Public Enterpris,2010(1&2):63-110.
[14]Frye,Timothy M, Ichiro Iwasaki.Government directors and business-state relations in Russia[J].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11(4):642-658.
[15]Kyle P R. The government director and his conflicting duties[J].Victoria U.Wellington L.Rev,1973(7):75-95.
[16]Martin Gelter,Genevieve Helleringer.Constituency directors and corporate fiduciary dutie[M]//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Fiduciary Law.Andrew Gold & Paul Miller ed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1-24.
[17]OECD.State-owned enterprise governance reform:An inventory of recent change[R].OECD,2011:1-56.
[18]Hobbs D.Personal liability of directors of federal government corporations[J].Case Western Reserve Law Review,1980(4):733-779.
[19]Hongjin ZHU,Toru Yoshikawa.Contingent value of director identification:The role of government directors in monitoring and resource provision in an emerging economy[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6(8):1787-1807.
[20]Davies,Ernest.Government directors of public companies[J].The Political Quarterly,1938(3):421-430.
[21]Robert W Sexty.Autonomy strategies of government owned business corporations in Canada[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80(4):371-384.
[22]World Bank.Corporate govern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A toolkit[R].Washington,DC:World Bank,2014:1-315.
[23]經(jīng)濟(jì)合作與發(fā)展組織.公司治理:國(guó)有企業(yè)董事會(huì)若干國(guó)家做法的概述[M].曾詳展,王婭菲,譯.北京:經(jīng)濟(jì)科學(xué)出版社,2018:7-112.
[24]經(jīng)濟(jì)合作與發(fā)展組織.國(guó)有企業(yè)公司治理:對(duì)OECD成員國(guó)的調(diào)查[M].李兆熙,謝暉,譯.北京:中國(guó)財(cái)政經(jīng)濟(jì)出版社,2008:167-169.
[25]OECD.Board practices and financing for Latin American state-owned enterprises[R].OECD,2015:1-58.
[26]W Richard Frederick.Enhancing the role of the boards of director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R].OECD Corporate Governance Working Papers,2011:1-30.
[27]Christopher Chen.Solving the puzzl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The path of the Temasek model in Singapore and lessons for China[J].Northwest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Business,2016(2):303-370.
[28]胡改蓉.國(guó)有公司董事會(huì)法律制度研究[D].上海:華東政法大學(xué),2009:175.
[29]Peter McKinlay.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crown companies in New Zealand[J].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1998(18):229-242.
[30]Hyungon Kim,Kee Hoon Chung.Can state-owned holding (SOH) companies improve SOE performance in Asia? Evidence from Singapore,Malaysia and China[J].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2018(2):206-225.
[31]Simon C Y. Wong.Improv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SOEs:An integrated approach[J].Corporate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2004(2):5-15.
[32]肖海軍.政府董事:國(guó)有企業(yè)內(nèi)部治理結(jié)構(gòu)重建的切入點(diǎn)[J].政法論壇,2017(1):173-181.
[33]胡改蓉.國(guó)有資產(chǎn)經(jīng)營(yíng)公司董事會(huì)之構(gòu)建——基于分類設(shè)計(jì)的思考[J].法學(xué),2010(4):94-107.
[34]王樹文.完善我國(guó)大型國(guó)有企業(yè)政府董事制度建設(shè)的途徑[J].中國(guó)行政管理,2008(11):74-76.
[35]高明華,等.中國(guó)國(guó)有企業(yè)公司治理分類指引[M].上海:中國(guó)出版集團(tuán)東方出版中心,2016.
[36]Mariana Pargendler,Aldo Musacchio,Sergio G Lazzarini.In strange company:The puzzle of private investment in state-controlled firms[J].Cornell Int'l L.J,2013(46):569-610.
(責(zé)任編輯:王鐵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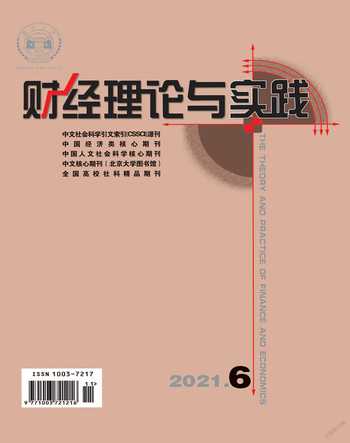 財(cái)經(jīng)理論與實(shí)踐2021年6期
財(cái)經(jīng)理論與實(shí)踐2021年6期
- 財(cái)經(jīng)理論與實(shí)踐的其它文章
- 人口老齡化對(duì)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jí)的影響:促進(jìn)還是抑制?
- 城市網(wǎng)絡(luò)視角下金融中心性與區(qū)域技術(shù)創(chuàng)新
- 新常態(tài)下中國(guó)貨幣政策的宏觀經(jīng)濟(jì)效應(yīng)研究
- 東道國(guó)金融發(fā)展影響中國(guó)與“一帶一路”國(guó)家間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的實(shí)證檢驗(yàn)
- 勞動(dòng)保護(hù)影響了企業(yè)經(jīng)營(yíng)績(jī)效嗎?
- 個(gè)人投資者情緒對(duì)企業(yè)履行社會(huì)責(zé)任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