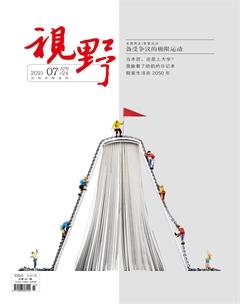古詩里的打工人
2021-04-25 03:47:27蓬山
視野 2021年7期
蓬山
在古詩中,處處充滿了打工人的興、觀、群、怨。
“忽憐長街負重民,筋骸長彀十石弩。半衲遮背是生涯,以力受金飽兒女。”(張耒《勞歌》)現在,頂烈日冒風雨的外賣小哥、快遞騎手,哪一個不是如此呢?
“筋力年年減,風光日日新。退衙歸逼夜,拜表出侵晨。”(白居易《晚歸早出》)這種“996”的工作節奏,加班族,尤其是健康狀況每況愈下的“前浪”們,真是感同身受。這充分說明,好詩歌的確是可以跨越時空的。
“書多筆漸重,睡少枕長新……秋風千里去,誰與我相親。”(姚合《別賈島》)此乃“新聞民工”“文案狗”中大齡“剩男”“剩女”的特寫詩。孤家寡人,青燈一盞,咖啡、香煙、泡面續命,通宵趕稿子、寫報告、改方案,就是這個味兒。
好不容易有了喘息之機,趕緊約兄弟出來“擼串”,約閨密一起做美甲。肉串還沒烤熟,指甲剛做了兩個,臨時加班指令又來了。此乃:“樓頭尚有三通鼓,何須抵死催人去。”(孫洙《菩薩蠻》)。
明初錢宰,官至翰林,但其實也是一個打工人。他私下忍不住“吐槽”:“四鼓咚咚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某日,耳目眾多的洪武皇帝突然對他說:“‘嫌字改‘憂字如何?”嚇得錢宰連呼“死罪”。是啊,上班本就不應該遲到,哪能抱怨呢?這是打工人必備的自我修養。
(秋水長天摘自《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