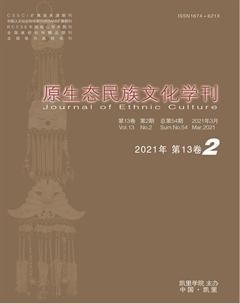內蒙古非遺文化衍生產品開發的設計路徑、方法及應用研究*
李志春 張路得 包長江



摘 要:從非遺文化的生產性保護與創新式傳承角度出發,研究提出內蒙古非遺文化衍生產品開發的設計路徑與系統設計方法,并以“蒙古族刺繡”文化衍生產品設計為例展開應用,實現了“蒙古族刺繡”文化衍生產品的設計。其結果驗證了該“設計路徑”和“文化衍生產品系統設計方法”的可行性,為內蒙古非遺文化衍生產品的開發與設計提供了理論支撐與設計依據。此研究有利于促進內蒙古非遺文化的保護傳承與轉化利用,助力內蒙古文化產業的發展。
關鍵詞:內蒙古非遺文化;文化衍生產品;設計路徑;蒙古族刺繡
中圖分類號:C95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 - 621X(2021)02 - 0084 - 14
世界發達國家以文化創意與文化創新為特征的文化產業發展已進入更高的實質階段,被看作創新經濟時代的國家戰略選擇與政策組成部分。在我國出臺的文化產業發展、文化創新保護與設計服務等相關政策的指引下,推進文化創意、設計服務與文化產業的融合發展,以及實施文化創新、非遺文化生產性保護等措施是實現文化產業發展的有效途徑。非遺文化衍生產品是非遺文化創新、非遺文化生產性保護與設計服務的具體融合對象,可借助其承載的文化屬性與商品屬性,實現非遺文化的文化價值傳承與經濟價值轉化。內蒙古是非遺文化大省,經統計內蒙古僅國家級非遺文化項目計81項[1],其為實施文化衍生產品開發提供了豐富而獨特的文化資源。結合非遺文化生產性保護措施與當今文化產業發展中對文化衍生產品的市場需求與設計需求,研究非遺文化衍生產品開發路徑與設計應用對文化創新與產業發展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鑒于此,該研究主要以探尋非遺文化衍生產品開發的有效設計路徑與系統方法為目標,以內蒙古國家級傳統美術類非遺項目中的“蒙古族刺繡”為例,作為具體非遺文化的設計轉化對象,展開非遺文化衍生產品開發的設計路徑、方法的應用及可行性驗證。
一、設計路徑
內蒙古地處北疆少數民族聚居區,具有富集的非遺文化資源,然而文化產業發展的滯后,制約了非遺文化的創新式傳承及衍生產品的開發。非遺文化衍生產品開發涉及政策扶持、產業環境、文化企業、人才隊伍、文化消費需求、文化挖掘、文化創意設計、加工制造與市場營銷模式等諸多因素與環節,需從有效提升內蒙古文化產業發展中思考非遺文化衍生產品的開發路徑。在創新驅動模式中包含技術驅動創新、市場驅動創新、設計驅動創新、用戶驅動創新等。設計驅動創新模式強調圍繞用戶、市場需求,運用設計思維與手段,整合相關資源、技術與功能,實現滿足用戶需求的新產品,具有研發周期短、見效快、投入低與風險小等優勢[2],是面對內蒙古文化產業發展環境欠佳、文化企業規模小及人才隊伍支撐不足等瓶頸下推進內蒙古文化產業發展的有效創新模式。故此,借助內蒙古富集的非遺文化資源,重點從設計驅動創新角度探尋內蒙古非遺文化衍生產品開發的設計路徑。非遺文化衍生產品是文化與產品的融合,是以非遺文化為基礎、物質產品為載體,運用設計思維、方法與手段實現非遺文化與產品功能的有機結合,形成滿足用戶文化認知與使用功能雙重價值的消費商品。故通過設計的角度分析其路徑:(1)文化是文化衍生產品的靈魂,需展開非遺文化的文化認知,解析并提取與設計相關聯的文化組成成分(設計因子);(2)非遺文化是抽象的而設計是需要具象的視覺語言,需將與設計相關聯的非遺文化組成成分(設計因子)轉化為供設計實施的設計符號;(3)非遺文化的意象是以物質產品為載體呈現的,需在文化體現與功能價值的雙重約束下,以設計思維與手段展開非遺文化衍生產品載體的選取與重塑;(4)非遺文化衍生產品是文化與產品的融合,即非遺文化生成的設計符號、選取與重塑的產品載體等設計要素的融合,需要研究構建相應的要素融合構造法,并結合設計符號與產品載體的特征進行選取;(5)為使非遺文化衍生產品各設計要素與構造法在設計融合上的系統性與直觀性,借助矩陣的表達方式呈現,形成要素組合矩陣,并依照要素組合矩陣展開非遺文化衍生產品的設計開發。經過以上分析,歸納出內蒙古非遺文化衍生產品開發的設計路徑,該設計路徑實現了從文化到文化衍生產品的層層推演,見圖1。
二、系統設計方法
針對內蒙古非遺文化衍生產品開發的設計路徑,選取筆者提出的“文化衍生產品系統設計方法” [3]140作為內蒙古非遺文化衍生產品設計的系統方法。“文化衍生產品系統設計方法”主要針對文化衍生產品設計,引入模塊化設計思想,解構文化產品構成要素,并利用構成要素逐項求解再融合的方法與技術構建了文化衍生產品設計的系統方法模型,見圖2。該方法模型從解構文化衍生產品構成要素出發,其構成要素由三個模塊組成,針對三個模塊逐項展開成形方法的研究,推演出文化衍生產品設計的具體構成要素,形成相應的設計要素庫,并利用要素組合方式建立三要素的組合矩陣,通過組合矩陣選取相應的設計要素展開具體文化衍生產品的設計開發。該系統設計方法的提出對內蒙古非遺文化衍生產品開發給予了設計理論與方法的支撐,并將以此展開內蒙古非遺文化衍生產品開發的具體設計應用。
三、設計路徑與方法的應用—以“蒙古族刺繡”文化衍生產品設計為例
文化衍生產品開發目的是使非遺文化實現生產性保護與創新式傳承,生產性保護強調將非遺文化及其資源轉化為文化產品的保護方式,并主要在傳統技藝、傳統美術和傳統醫藥藥物炮制類非遺文化領域實施[4],生產性保護的提出為非遺文化實現創新式傳承指明了應用對象與實施范疇。“蒙古族刺繡”是2014年確定的第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傳統美術類的擴展項目,由內蒙古自治區蘇尼特左旗申報,屬于非遺文化生產性保護的實施領域,可以文化衍生產品的設計開發,并借助其作為商品的市場傳播性和經濟價值性,促進“蒙古族刺繡”非遺文化的大眾認知及價值轉化,實現“蒙古族刺繡”的生產性保護與創新式傳承。故運用內蒙古非遺文化衍生產品開發的設計路徑與系統設計方法,展開“蒙古族刺繡”文化衍生產品設計的應用研究與可行性驗證。
(一)“蒙古族刺繡”文化及組成成分解析
蒙古族刺繡是蒙古族人民在生產生活中對自然的祈福、圖騰的崇拜、宗教的信仰和裝飾美的追求而產生的一種文化藝術創作表現形式[5],并形成世代相傳的手工技藝,是蒙古族民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6]。其以各色多題材的象征圖案和獨特針法技藝,應用于日常生活用品上,并以其鮮明的地域題材特色和凝重質樸的藝術表現形式,承載了蒙古族的傳統文化與民族精神,成為蒙古族民族識別的標記,具有特定的文化性、裝飾性和民族性。2014年被確定為第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的擴展項目展開保護與傳承。
1.“蒙古族刺繡”的傳承與應用
“蒙古族刺繡”早期的傳承受生產生活方式的影響,主要由蒙古族婦女來完成,由于生產力低下,蒙古族婦女承擔起了為全家人制作四季服飾和繡品的任務,并逐步形成了學習刺繡技藝的傳統習慣、愛好追求和必須掌握的生活技能,產生了“蒙古族刺繡”的“家庭式傳承”模式,即母女相傳、姐妹相促,所以蒙古族婦女人人擅長刺繡,這為刺繡的繁榮與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7]。隨著生產生活方式的改變、市場經濟的驅動和國家對民族文化保護傳承的重視,“蒙古族刺繡”在傳承過程中,人們逐步意識到了民族文化的文化價值和經濟價值,開始對“蒙古族刺繡”從無意識傳承向主動傳承轉變[8],形成了蒙古族婦女積極參與各級各類民族刺繡制作和展覽、各類師徒傳授的“蒙古族刺繡工作室”、學校傳承的“蒙古族刺繡班”、 政府不定期舉辦的蒙古族刺繡活動和展會等多元傳承方式的繁榮景象,極大的給予了“蒙古族刺繡”文化傳承的活力。蒙古族刺繡是蒙古族生產、生活和信仰中的重要裝飾元素及向美的表現形式,其刺繡線材多以牲畜的鬃、毛、筋及各色絲棉線為主,采用繡、貼、堆、剁技法在皮、布、綢等基礎材料上繡出各種粗獷美麗的裝飾紋樣[9]。根據不同的選材,在應用上兼顧了耐用、舒適、文化信仰等的裝飾功能特點,其應用包括考慮耐用的居住裝飾用品(門簾、掛毯、氈包、蒙古包等)和生產輔助裝飾用品(駝鞍、馬鞍等)、考慮舒適的生活輔助裝飾用品(荷包、煙袋、碗袋、繡花氈、坐墊、枕套等)和服飾和配飾用品、考慮文化信仰習俗的裝飾用品(神佛繡像、唐卡、長幡、蓮座等)等。
2.“蒙古族刺繡”的圖案題材
蒙古族刺繡是蒙古族人民寄情、祈福、向美的一種藝術表現形式,其內容主要集中在刺繡圖案的選擇和設計上,并形成圖意相融、向美向善的文化藝術特征[10]。經過對相關文獻的梳理,將“蒙古族刺繡”圖案的題材歸納為7個方面:(1)自然崇拜的祈福圖案。由于蒙古族是以游牧為主展開的生產生活方式,自然環境為其帶來了生產的便利與災難,在與自然相融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萬物皆有靈”的哲學觀念,產生了對天地中自然物神祇崇拜[11]23,并演繹成各種用以祈福的紋飾和圖案,如卍字紋寓意太陽的轉動和四季如意,火紋代表著美好、象征著興旺發達,云紋(哈木爾)有吉祥如意的含義等。(2)原始崇拜的圖騰圖案。在對自然神祇崇拜中,蒙古族認為每個氏族都與自然物或某種動物、植物有著血緣的系屬關系[11]26,逐漸選擇性的將其作為本民族的圖騰。當然對于蒙古族圖騰崇拜學界觀點不同,尚未有準確的定論,整理學界不同專家認為的蒙古族圖騰有:《蒙古秘史》中的狼鹿圖騰;現代學說中的馬圖騰;多圖騰學說中的狼、鹿、鷹、熊、天鵝、犬、白馬、太陽、樹木等圖騰[12]。在此尚不考究圖騰的定論,但其演變出的視覺化圖騰圖案卻一直為蒙古民族使用,并成為一種精神寄托。(3)宗教信仰的神物圖案。蒙古族早期信仰薩滿教,薩滿教與蒙古族圖騰崇拜有著天然的聯系,對自然界心存敬畏,并形成“世間萬物皆有靈,堅持信仰長生天”的世界觀,薩滿教主要體現為自然崇拜、動物(祖先)崇拜。自然崇拜方面最突出的表現是對“天體(騰格里)”“星辰”“太陽”“火”“敖包/土堆”“天樹(樺樹)”“上天的布馬爾(蒙古薩滿翁袞重要的護身符,是青銅器時代使用的一種工具或武器,通常在雷電襲擊過的地方找到)”等的崇拜[13];動物(祖先)崇拜方面最突出的是“鹿”“蛇”“熊”“鳥(鷹、隼、喜鵲等)”等的崇拜[14],并形成了宗教的祭祀活動和符號化的神物圖案。在元代以后,藏傳佛教進入蒙古高原,經過不斷的傳播和融合,發展成蒙古族的普遍宗教信仰,藏傳佛教的興起給蒙古族裝飾圖案增添了豐富的內容,尤其是寓意吉祥的圖案受到青睞,如藏族的吉祥圖案八瑞相,亦稱八吉祥徽、藏八仙和藏八寶,還有佛手、寶相花、摩尼珠等圖案。(4)動物鳥禽的象征圖案。蒙古族游牧、狩獵的生產生活方式與動物鳥禽產生了密切的聯系,除圖騰崇拜和宗教信仰中的動物鳥禽之外,蒙古族對現實生活中的動物鳥禽也同樣寄予象征意義,如象征興旺的五畜(馬、牛、駝、山羊、綿羊)[15]、犬、駱駝,象征英雄的鷹、虎、獅,象征自由的魚,象征多子母親或好事成雙的蝴蝶、象征祝壽吉祥的蝙蝠,象征吉祥喜慶的象、燕子、喜鵲等動物鳥禽,在圖案的表現上除寫實圖案外,還轉換成抽象的象征圖案,如犄紋、牛鼻紋、魚紋、蝴蝶紋、蝙蝠紋等應用于生活中。(5)植物花卉的唯美圖案。蒙古族對植物(草)的依賴和熱情使其形成的圖案成為日常生活的重要裝飾。這些植物花卉圖案主要由兩類構成,第一是源于蒙古族生存的自然環境,大草原是形成植物花卉圖案的重要“源流”,在與自然共生的過程中逐漸賦予植物花卉以美好的象征,并通過唯美的圖案寓意吉祥,如卷草紋、纏枝紋、杏花紋、桃花紋、石榴紋等,以及建立在單純審美層面上寓意吉祥和美好生活向往的植物花卉唯美圖案。第二是受宗教信仰影響的植物花卉圖案,如薩滿教崇拜天樹形成的樹紋,佛教寓意圣潔的蓮花紋,集蓮花、牡丹、菊花等特征于一體的寶相花紋和佛手果實圖案等。(6)幾何連續的裝飾圖案。蒙古族的幾何圖案是在自然紋樣、動植物紋樣的基礎上,運用簡化抽象、幾何模塊等形式轉化而來的,基本型有圓形、方形和三角形,而且蒙古族的幾何圖案受到了伊斯蘭文化藝術“復雜規律的紋樣,繁瑣的植物圖案”[16]的影響,形成“連續不斷、均勻分布”的幾何連續裝飾圖案,蒙古族比較常見的幾何連續式圖案有畸形紋樣、漁網紋(哈那紋)、盤腸紋(圓角盤腸紋、直角盤腸紋)、云紋(雙關法云紋、鏤空云紋、勾聯式牛鼻云紋、勾聯式的云紋)、壽字紋(蘭薩紋、普斯賀紋)、萬字紋(菱形萬字紋、中心萬字紋、T形萬字紋、三向萬字紋)、回紋(S形回紋、T形回紋、萬字回紋)、勾聯紋(線性勾聯紋、帶狀勾聯紋、方勝和圓勝形成的勾聯紋、卉紋勾)[17]等。(7)文化融合的吉祥圖案。蒙古族文化受漢、藏和伊斯蘭等文化的影響,在圖案上出現了文化融合的吉祥圖案,如受漢文化影響的龍鳳紋、纏枝牡丹紋、葫蘆紋、鴛鴦紋、太極八卦圖、福祿壽喜紋等;受藏文化影響的佛教文化圖案;受伊斯蘭文化影響的幾何連續裝飾圖案等。
3.“蒙古族刺繡”的色彩體系
“蒙古族刺繡”的色彩運用源于蒙古民族崇尚的顏色,即黑色、白色、紅色、青色(藍色)、黃色、綠色和金銀色,蒙古族色彩觀的形成主要受其生存的自然環境和民族宗教信仰影響[18]。蒙古族以游牧作為生產生活方式,遷徙于廣袤草原的各個角落,在探索自然、認識自然的過程中,產生了對大自然的敬畏與崇拜,藍天、白云、綠地和金色太陽的色彩景象,融入蒙古人民心中,并賦予其象征意義,形成了獨特的民族色彩觀;蒙古族的原始宗教為薩滿教,其產生源于與自然共生對抗而形成的畏懼與依賴的矛盾心理意識,所以蒙古族敬畏“長生天”“太陽”“火”、崇拜“土地”,并賦予其顏色以象征意義。也因為蒙古族畏懼黑暗,而賦予黑色以神秘、強大的未知力量,進而被視為一種權利和力量的代表,形成尚黑的色彩觀。金銀色是光澤色,象征著富貴,受藏傳佛教的影響,成為重要的裝飾色彩。經過對大量蒙古族刺繡作品的色彩構成提取和相關文獻研究,歸納其色彩構成體系為無彩色系中的黑色、白色,有彩色系中的紅色、綠色、青色(藍色)、橙色、黃色和紫色[19],且在蒙古族刺繡作品中都賦予色彩以文化象征意義。在色彩的選取應用上多為互補對比色,如黑與白、紅與綠、藍與橙、黃與紫,形成“蒙古族刺繡”作品具有色彩艷麗、對比強烈、明快粗獷的色彩藝術風格,“蒙古族刺繡”的色彩體系見表1。
4.“蒙古族刺繡”的工藝技法與針法路徑
“蒙古族刺繡”的工藝技法主要分為“繡花”“貼花”“綜合類”三種[20],其中“繡花”是“蒙古族刺繡”中最為常用和基礎的一種,其工藝技法主要取決于刺繡針法的運用,“蒙古族刺繡”最基礎、最常用的針法分別為:平針、回針、滾針、直針(又稱齊針,蒙古語稱“踢各泰”)、 接針(蒙古語稱“套各其呼”和“沙嘎拉夫”)、 打籽針(又叫結籽,蒙古語稱“敖日亞馬拉”)、釘線針、插針(蒙古語稱“莎瑪拉住奧由”)、 拉鎖子針、鎖繡針、墊繡針、馬鬃纏線針、眉睫針、人字針、鎖扣針、戧針、刻鱗針、撒針、擻和針(又叫長短針)、剁針和松針等[21]18。在刺繡過程中根據刺繡作品的圖案構成和表現效果進行針法的選取,如平針形成的虛線,可用于勾邊、裝飾;回針形成的實線可表現須發、藤草及勾勒紋樣輪廓;滾針用于表現粗獷的線條,如植物輪廓、枝條和葉莖等;直針主要用來表現人物、動植物、器皿等的塊面;打籽針多用來繡花蕊、動物的眼睛等點狀紋樣;插針實現各色線條的長短錯落排列,用于刺繡塊面的色彩過渡,表現立體效果;“貼花”是“蒙古族刺繡”較為普及和實用的一種刺繡形式,主要采用各色布料、皮料剪刻成特定的紋樣和形狀,貼繡于繡底上,用接針、鎖針、打籽針等針法刺繡固定,早期用于替代“繡花”形式中大面積的單色填充,起到省時省力的作用,后期成為一種刺繡的表現形式,亦出現了多色布塊拼合的貼花效果。“貼花”多用于裝飾生活用品,如服飾、床品和蒙古包等,具有較高的實用價值。“綜合類刺繡”是將“繡花”與“貼花”技法混搭使用的一種刺繡表現形式,此種形式避免了“貼花”單純的大塊面積的單一、呆板和“繡花”裝飾的耗時耗力,也形成了刺繡作品的線面塊面對比和大小色塊對比的藝術效果,“綜合類刺繡”是對刺繡藝人藝術表現能力的綜合考量。
“蒙古族刺繡”作品在制作過程中需要考慮針法的路徑,即刺繡過程的順序。“蒙古族刺繡”路徑基本分為整體構圖路徑和個體紋樣路徑[21]44。“整體構圖路徑”即按照刺繡作品紋樣的主次,依“主紋→輔紋→邊紋”的路徑順序進行繡制。“個體紋樣路徑”即整體刺繡作品中個體紋樣的兩種刺繡方式:①上下分層(圖3),主要針對具有顏色深淺順序變化的個體紋樣,選擇從個體紋樣中深色繡起,逐步推到淺色,這種路徑方式對顏色深淺推演較好把握,且可避免長時間刺繡過程中對淺色的污染,保證繡品整潔。②軸對稱(圖4),主要針對具有中心發散特點的個體紋樣,其方法是從個體紋樣中心繡起,逐層向外擴散。
(二)“蒙古族刺繡”文化衍生產品設計構成要素提取與轉化
經上述解析了“蒙古族刺繡”的圖案題材、色彩體系、工藝技法與針法路徑等文化組成成分,運用提出的開發路徑和設計方法,展開“蒙古族刺繡”文化衍生產品中構成要素“文化設計符號”“文化產品載體”的設計推演及構成要素的融合。
1.“蒙古族刺繡”的文化設計因子提取與設計符號轉化
“蒙古族刺繡”的文化設計因子提取。對照“文化衍生產品系統設計方法”可知,文化可提取出11種文化設計因子類別[3]137、[22]207(見圖2),結合“蒙古族刺繡”文化組成成分中象征圖案、對比色彩搭配、工藝技法與針法路徑的獨特性,提取具有“蒙古族刺繡”代表價值的文化設計因子“技藝”“圖案”“色彩”三類作為“文化設計符號”的轉化基礎與文化來源,具體解析見表2。
“蒙古族刺繡”文化設計因子的設計符號轉化。針對所提取的“蒙古族刺繡”文化設計因子“技藝”“圖案”“色彩”展開設計符號的轉化,對照“文化衍生產品系統設計方法”中四種“文化設計因子的設計符號轉化方法” [3]138、[22]207(見圖2),選取其中“材質、工藝、技藝、結構和功能的再現”“圖案和色彩的沿用與提煉”兩種方法展開對應文化設計因子的設計符號轉化。“材質、工藝、技藝、結構和功能的再現”方法主要針對文化設計因子“技藝”展開設計符號轉化,“蒙古族刺繡”文化設計因子“技藝”的再現是將“蒙古族刺繡”中針法技藝、路徑走向通過特定的載體呈現,在工藝技法的表現形式方面可以按照設計需求選擇“繡花”“貼花”和“綜合類”,旨在將“蒙古族刺繡”技藝大眾化、商品化,擴大“蒙古族刺繡”技藝的應用人群,形成創新式的傳承與保護途徑;“圖案和色彩的沿用與提煉”方法主要針對文化設計因子“圖案”和“色彩”展開設計符號轉化,“蒙古族刺繡”文化設計因子“圖案”的沿用可選取“蒙古族刺繡”中具有文化象征的典型紋樣加以直接使用,讓人們直觀的感受蒙古族刺繡紋樣所蘊含的表情、表意和審美特征。“蒙古族刺繡”文化設計因子“圖案”的提煉是依照形式美法則,選取傳統、典型的蒙古族刺繡紋樣,采用圖形的組合、分割、變異、形狀文法等方法手段,在保證蒙古族刺繡紋樣形式風格特征和文化語意的基礎上進行“圖案”在再創造。“蒙古族刺繡”文化設計因子“色彩”的沿用與提煉方面,采用直接選取“蒙古族刺繡”的八種常用搭配色,按照設計需求進行組合搭配,具體轉化見表3。
2.“蒙古族刺繡”文化衍生產品載體的選取與重塑
針對形成的文化設計符號,運用“文化衍生產品系統設計方法”中文化衍生產品載體的構建方法(見圖2),展開“蒙古族刺繡”文化衍生產品載體的選取與重塑,以實現與文化設計符號的融合。“蒙古族刺繡”是手工技藝下的視覺性裝飾藝術,轉化的文化設計符號為“技藝”“圖案”“色彩”,由于其廣泛的裝飾于日常辦公學習用品、居家生活用品與休閑娛樂用品上,所以在產品載體的選取與重塑上重點考慮以上類別的產品。針對文化設計符號“技藝”在選取文化產品載體方面,目的是可以通過文化產品載體實現蒙古族刺繡技藝的傳承,所以采用文化產品載體的重塑方式,以滿足蒙古族刺繡“技藝”的再現;針對文化設計符號“圖案”,可直接選取市場上辦公學習用品、居家生活用品與休閑娛樂用品類產品作為文化產品載體。在載體的重塑方面,結合文化衍生產品的造型、功能、結構等因素,對二維圖案進行三維造型轉化,與產品融合形成立體化載體[22]208;針對文化設計符號“色彩”,文化產品載體的選取與重塑受限較小,只要符合文化產品的特征即可,可根據文化衍生產品設計需要,選擇蒙古族刺繡傳統的八種搭配色進行選色配色。以上相關結果見表4。
3.“蒙古族刺繡”文化衍生產品設計的要素融合構造法選取
文化設計符號依附于文化衍生產品載體形成文化衍生產品,要素融合構造法建立了二者的融合關系。經上述推演“蒙古族刺繡”文化衍生產品的“文化設計符號”為“技藝”“圖案”“色彩”,對照“文化衍生產品系統設計方法(見圖2)”中“要素融合構造法”的類別與適用的文化設計符號,選擇“元素再現法”和“元素移植法”兩種展開“蒙古族刺繡”文化衍生產品設計中“文化設計符號”與“文化產品設計載體”的融合,融合關系見表5。
4.“蒙古族刺繡”文化衍生產品設計的構成要素組合矩陣構建
構成要素組合矩陣是“文化衍生產品系統設計方法”中“要素組合方式”(見圖2)的直觀表現形式,是利用矩陣的形式呈現前期推演和選取的“文化設計符號”“文化產品設計載體”“要素融合構造法”三者的匹配關系。“蒙古族刺繡”文化衍生產品設計的構成要素組合矩陣中選取“技藝”“圖案(MCT - T - 1、MCT - T - 2、MCT - T - 3、MCT - Y - 1)”“色彩”作為文化設計符號;選取“裝飾畫”“筆記本”“明信片”等作為文化產品載體;選取要素融合構造法中的“元素移植法”“元素再現法”建立了文化設計符號與文化產品載體的融合關系,見圖5。構成要素組合矩陣的構建是展開后期“蒙古族刺繡”文化衍生產品具體設計的主要依據。
(三)“蒙古族刺繡”文化衍生產品設計
經過對“蒙古族刺繡”文化衍生產品各構成要素的推演與融合,在建立的“構成要素組合矩陣”中選取三種文化衍生產品展開具體設計實施與方法驗證,其他文化衍生產品的設計之需按照以上方法展開即可。
1.“蒙古族刺繡”文化衍生產品—DIY套裝式蒙古族刺繡裝飾畫設計
根據“蒙古族刺繡”文化衍生產品構成要素組合矩陣,“DIY套裝式蒙古族刺繡裝飾畫”設計中,“蒙古族刺繡”文化設計符號首先以“技藝”為主要文化符號,以技藝的再現實現蒙古族刺繡的大眾化傳承;其次以文化設計符號“圖案”中的沿用圖案“MCT - Y - 1”為“DIY套裝式蒙古族刺繡裝飾畫”設計中的主要視覺圖案,圖案“MCT - Y - 1”采用烏拉特蒙古族刺繡傳承人孟和其其格的刺繡作品《飄馬鐙》上的傳統牡丹圖案,其作品構圖飽滿、色澤艷麗、精致大膽,有著“真愛要用無言去領悟,把名譽藏在花紋的牡丹”的美好寓意,見圖6;文化設計符號“色彩”沿用蒙古刺繡常用的黑、白、紅、黃、綠、藍六色象征著對美好生活的祝愿及對自然與自由的崇拜。
文化產品載體為重塑的生活裝飾類產品—裝飾畫,在文化產品載體的重塑上,為了實現蒙古族刺繡針法技藝、路徑走向的再現和大眾化的傳承與使用,采用DIY的設計思路,將“蒙古族刺繡裝飾畫”以套裝的形式出現,即針、蒙古族刺繡常用八色線、布(皮)、標準化繡底、蒙古族常用圖案和制作技藝說明,見圖7,“標準化繡底”的設計見圖8(亦可為其他形狀)。
在要素融合構造法上選取“元素再現法”,將圖6根據“制作技藝說明”,用針線在“標準化繡底”再現蒙古族刺繡的針法技藝和路徑走向,見圖9。“標準化繡底”的設計可以使刺繡制作者省時省力,亦可按照“標準化繡底”的坐標確定主體圖案和配色的位置。設計完成的“DIY套裝式蒙古族刺繡裝飾畫”見圖10所示,2018年6月該設計作品入選了由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廳、內蒙古自治區教育廳和內蒙古自治區經濟與信息化委員會聯合舉辦的“2018內蒙古創意設計展”。
2.“蒙古族刺繡”文化衍生產品—“蒙韻·宜字宜繡”圖案明信片套裝設計
根據“蒙古族刺繡”文化衍生產品構成要素組合矩陣,“蒙韻·宜字宜繡”圖案明信片套裝設計中,“蒙古族刺繡”文化設計符號以“圖案”為主要文化符號,為表3中提煉的圖案“MCT - T - 1” “MCT - T - 2” “MCT - T - 3”三種,見圖11。此三種圖案是通過對蒙古族刺繡常用圖案進行提煉與重組來實現,其中圖11a(MCT - T - 1),選取的是蒙古族服飾的前襟和袖口圖案,與代表吉祥的云紋相結合形成組合圖案,因為蒙古族服飾的前襟和袖口是最易磨損的,借助該語意與明信片需要珍藏的語意進行對位,該圖案設計有著愛護、保護的寓意;圖11b(MCT - T - 2),在圖案的重組上,底部圖形采用蒙古族的接奶桶進行抽象演化,象征著財富與健康,上部圖形為抽象的蒙古族祿馬風旗,加以火焰圖案,象征著守護、永恒和永不熄滅的火種;圖11c(MCT - T - 3),在圖案的重組上,選取蒙古族刺繡的吉祥紋樣“蝙蝠紋”與“萬字紋”進行組合,將“蝙蝠紋”塑造為整體色塊,以圓形陣列方式進行五副圖形的連續構圖,并與代表著吉祥、永恒的“萬字紋”相結合,寓意五福臨門、萬事萬物吉祥。其次文化設計符號的“色彩”選用蒙古族刺繡常用的黑、白、紅、綠進行配色。
文化產品載體選取辦公學習用品類—明信片套裝,要素融合構造法選取“元素移植法”,將圖11中的三副重塑圖案直接移植到明信片套裝上,使文化設計符號與明信片套裝載體相結合,得到“蒙韻·宜字宜繡”明信片套裝的設計,見圖12。2018年6月該設計作品入選了由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廳、內蒙古自治區教育廳和內蒙古自治區經濟與信息化委員會聯合舉辦的“2018內蒙古創意設計展”。
3.“蒙古族刺繡”文化衍生產品—蒙古族刺繡文化符號“五色本”設計
蒙古族刺繡文化符號“五色本”設計中,文化設計符號“圖案”仍選用表3中提煉的圖案“MCT - T - 1” “MCT - T - 2”和“MCT - T - 3”三種,見圖11。文化設計符號“色彩”選取蒙古族刺繡常用的五種吉祥色(紅、黃、藍、綠、紫)作為文化衍生產品的主題色;文化產品載體選取筆記本,要素融合構造法選取“元素移植法”,將圖11中的三副重塑圖案和選用的色彩直接移植到筆記本上,使文化設計符號與筆記本載體相結合,設計的蒙古族刺繡文化符號“五色本”見圖13。 2018年6月該設計作品入選了由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廳、內蒙古自治區教育廳和內蒙古自治區經濟與信息化委員會聯合舉辦的“2018內蒙古創意設計展”,并被收藏。
四、結論
非遺文化的生產性保護是非遺文化實現創新式傳承的有效措施,可以文化衍生產品為載體實現非遺文化的多元化創新傳承。文化衍生產品兼具文化屬性與經濟屬性的特征,亦是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故此非遺文化衍生產品的開發是實現文化傳承與經濟增長的融合點,而非遺文化與產品相融合的路徑與方法則決定了非遺文化衍生產品開發的有效性。綜上,以內蒙古國家級非遺“蒙古族刺繡”文化衍生產品設計為例,驗證了提出設計路徑與系統設計方法的可行性,亦是尋求非遺文化與產品相融合的有效設計途徑,以實現內蒙古非遺文化的創新應用,助力內蒙古地區文化產業的發展。
參考文獻:
[1]? 劉春玲.內蒙古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結構類型與空間分布研究[J].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 2017(5):192 - 199.
[2]? 李若輝,關惠元.基于設計創新驅動的中小型制造企業生態化發展策略[J].企業經濟,2017(10):9 - 14.
[3]? 李志春,張路得.創新式傳承下文化衍生產品系統設計方法研究[J].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2018(4):134 - 142.
[4]? 文化部非遺司.《文化部關于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的指導意見》文非遺發〔2012〕4號[EB/OL].(2012 - 02 - 02)[2020 - 10 - 12]http://www.ihchina.cn/14/14811.html .
[5]? 李宏復.中國刺繡文化解讀[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5.
[6]? 包巧云. 鄂爾多斯刺繡藝術研究[D].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2017.
[7]? 田建強.蒙古族民間刺繡藝術風格探微[J].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版),2008(3): 197 - 198.
[8]? 鮑可心.翁牛特蒙古族刺繡傳承方式初探[J].開封教育學院學報,2018(7):262 - 264.
[9]? 王正. 獨具特色的蒙古族刺繡[J]. 實踐(黨的教育版),2016(5):33.
[10]付光輝.花卉刺繡在蒙古族傳統服飾中的應用[J].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4):70 - 72.
[11]李效銳. 蒙古族裝飾圖案的審美特征及文化內涵研究[D].徐州:中國礦業大學,2014.
[12]樊永貞,額爾敦其其格.蒙古族圖騰崇拜問題綜述[J].西部蒙古論壇,2014(4):80 - 84.
[13]李明紅.《蒙古薩滿教》(5 - 8章)英漢翻譯實踐報告[D].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2018.
[14]趙娜娜.《蒙古薩滿教》(13 - 15章)英漢翻譯實踐報告[D].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2018.
[15]白鳳. 蒙古族傳統圖案分類和樣素分析[D].呼和浩特:內蒙古農業大學,2010.
[16]武翀智. 蒙古族圖案的文化內涵和藝術表達研究[D].杭州:浙江農林大學,2011.
[17]烏恩琦. 蒙古族圖案花紋考[D].內蒙古師范大學,2006.
[18]查薩娜. 蒙古族色彩在城市色彩景觀設計中的應用研究[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學,2015.
[19]王琨.蒙古族刺繡圖案紋樣中色彩的應用[J].大眾文藝,2017(1):81.
[20]陶海巍. 蒙古族“烏拉特刺繡”研究[D].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2015.
[21]楊艷. 蒙古族傳統刺繡數字化關鍵技術探討[D].呼和浩特:內蒙古農業大學,2017.
[22]李志春,張路得.國家級非遺“包頭剪紙”文化衍生產品設計[J].包裝工程,2018(22):205 - 212.
[責任編輯:吳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