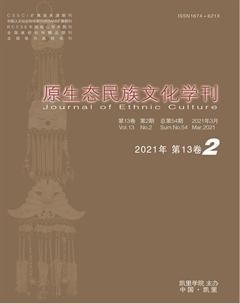文化生態重建與價值更新
摘? ?要:節日是人類在特定時間和空間中舉行的慶典活動和社會實踐,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空間,生產出集體文化認同與公共社會意義。盤王節是祭祀型節日,起源于遠古時期的盤瓠神話以及渡海神話中瑤人與盤王的神圣誓約,承載著瑤族的歷史記憶與民族認同,具有多重社會功能,成為瑤族最寶貴的精神財富和文化盛宴。當前,重建盤王節文化生態,實現其當代價值和功能更新,是瑤族鄉村文化振興及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路徑。
關鍵詞:瑤族;盤王節;生態重建
中圖分類號:C95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 - 621X(2021)02 - 0128 - 8
節日,是人類在特定時間和空間中舉行的慶典活動和社會實踐。具體而言,根據自然生態、歷史淵源、文化功能等之不同,傳統節日可分為農事型、祭祀型、紀念型等多種類型。節日是儀式表演、社會關系呈現、民間藝術展演的綜合場域,也是物質消費最集中的時期,不僅體現了一定人群關于生計、時間節律、農事安排的地方性知識,關于宇宙、歷史的認知和實踐,還以公共的時間、空間以及迥異于日常生活的“閾限”或“狂歡”行為實踐構建了一種獨特的文化空間,生產出集體文化認同與公共社會價值。盤王節是瑤族1民眾于農歷十月十六日紀念始祖盤王的節日,以祭盤王、跳盤王、唱盤王為主要內容,是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一節日起源于瑤族民間拜王還愿的祭祀儀式,是當代學者、地方政府和民間共同建構的節慶展演,衍生出許多不同的內涵、表征與功能。本文將盤王節放置于遺產學脈絡中進行剖析,厘清其淵源、表現方式和功能,以及如何成為當前瑤族鄉村文化振興的核心文化元素,思考其創新傳承發展之可能路徑。
一、盤王崇拜之知識考古
盤王節是祭祀型節日,信仰內核來源于神犬盤瓠神話與盤王崇拜,在瑤族口述傳統及民間文獻中,其形成有較為明晰的脈絡。盤王崇拜結合了祖先崇拜和神靈崇拜的特征,盤王節是其集中體現的場域。
(一)“盤”“瓠”的詞源
盤瓠之源流眾說紛紜,有關“盤”“瓠”詞源及盤瓠的來歷主要有以下幾種說法。
1.“頂蟲化犬”、以盛器為名說。據《搜神記》記載:“高辛氏,有一老婦人居于王宮,得耳疾歷時。醫為挑治,出頂蟲,大如繭。婦人去后,置于瓠蘺,覆之以盤,俄而頂蟲乃化為犬,其文五色,因名盤瓠,遂蓄之。”至今,盤姓為瑤族12姓之大姓。
2.“龍犬”說。此為普遍之說,見于各地瑤族文書《評皇券牒》中:“瑤人根骨,即系龍犬出生。自混沌年間,評皇出世,得龍犬一只,身高三尺,身長一丈,毛色斑黃,有如猛虎之威。”[1]27
3.盤瓠、盤古、伏羲同源說。聞一多在《伏羲考》中從神話母題和音韻學的角度,論證了伏羲、女媧為葫蘆之化身,伏羲與盤瓠音訓相通,出于同源。認為頂蟲盛于瓠中而化身為犬,亦為洪水神話中伏羲女媧葫蘆生人之母題。“槃即剖匏為之,槃瓠猶匏瓠。槃瓠與包羲字異而聲義同。在初本系一人,為二民族共同之祖,同祖故同姓”[2]60。袁珂也將盤瓠等同于盤古,并認同伏羲與盤瓠神話出于同源之說[3]33。受此觀點影響,一些學者認為盤古、伏羲、盤瓠音近義通,同源異流,為同一神祇在不同民族中的分化與異傳[4]。但將盤古與盤瓠等同的觀點近年受到諸多批評。
4.“巴特魯”之借用說。此說反駁盤瓠神話乃南方型神話的觀點,主張其源出北方。認為人犬結合型母題故事是在犬戎族犬圖騰崇拜的基礎上衍生,而苗瑤畬族與犬戎族有血緣關系,“盤瓠”借用了阿爾泰語系之蒙古語族或通古斯語族的“巴特魯”(忠勇之人)一詞[5]。
5.源出蠶馬神話說。認為盤瓠神話的原型是蠶馬神話,有相似的“許諾——悔婚——結合”的情節結構,盤瓠神話中以犬替代了馬,各地流傳的民間盤瓠龍犬的“毛色斑黃”形象依然留有蠶的五彩痕跡[6]。
6.盤瓠的本質為圖騰崇拜。岑家梧將“南蠻”的盤瓠神話歸納為中國各民族最顯著的十一大圖騰祖先神話之一[7]123,他提到相關神話的2種類型:(1)某種動植物化身而為部族之祖先;(2)人與某種動植物交而生其部族。盤瓠神話屬于B類[7]18。因此,盤瓠崇拜兼有圖騰崇拜與祖先崇拜的雙重屬性,由龍犬、盤瓠而盤王的稱謂變化還反映了其由圖騰逐漸升格為祖先神的特性。
(二)盤瓠神話、文書與盤王節之源流
與盤王有關的神話包括盤瓠神話和渡海神話。盤瓠神話除在瑤族民間廣為流傳之外,還見于《風俗通義》《山海經》《搜神記》《玄中記》《后漢書.南蠻傳》《魏略》《桂陽志》等歷史文獻記載中,并主要在瑤族勉語支系中保留了漢文神話文書《過山榜》(又名《評皇券牒》)。《過山榜》以圖文結合的方式,記載了盤瓠的出生、受封及瑤人遷徙過程。盤瓠神話的大致情節是,盤瓠是上古時期高辛帝(高王)飼養的一只龍犬,英明神武,因咬殺敵方首領有功,高辛帝賜予三公主與其婚配,并賦予人形。婚后二人奔赴深山(一說南山)居住,生育6男6女,6男6女自相婚配繁衍后代,此為瑤人12姓的來源。盤瓠在一次打獵中不幸被山羊頂下懸崖,掛于樹上而死,其后人獲封廣闊土地良田,從事耕山廣業,擁有不納賦稅等特權。渡海神話出現的時間比盤瓠神話晚,是以瑤人遷徙災難以及遷徙途中獲盤王搭救圣恩為中心的敘事。大致情節是,大旱三年的自然災害和無盡的朝廷征戰打破了瑤人的寧靜生活,被迫往南遷徙。在“漂洋過海”途中突然遭遇狂風大浪,搭載族人的船只漂泊七天七夜不辨方向、不能靠岸,有老人提議在船頭燒香拜求盤王顯靈搭救,并許下重建家園后立廟祭祀酬謝盤王之愿。如愿求得盤王顯圣,不多時水面風平浪靜,眾人不出三日便到達對岸。瑤人每遷徙到一地不忘建盤王廟祭祀還愿。“盤瓠神話與盤瓠王顯靈搭救十二姓瑤民的渡海神話相結合,成為瑤族祭盤王、還盤王愿儀式的根源,并強化了對盤瓠始祖神的認同感”[8]。在此盤瓠已由神話中的神犬上升為盤王先祖和神靈。操勉語方言的瑤族支系多以家庭或家族為單位做還盤王愿儀式,非周期性的節日活動,一般為逢族中添丁、生病或遇事不順之年舉辦,或視財力多寡,每3、5、10年舉辦1次。
由還愿儀式發展為融合祭祀、慶賀、娛樂的盤王節慶典是較為晚近之事。由于瑤族支系繁多,各地瑤族祭盤王、還盤王愿的時間和方式并不一致。1984年8月,廣西民族事務委員會召開桂湘粵三省瑤族干部座談會,商定以“勉”支系還盤王愿為基礎發展為盤王節,時間統一為農歷十月十六。2006年,瑤族盤王節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9]。基于這一歷程,如今的瑤族盤王節主要有兩種類型,一是公祭型,由政府組織,桂滇湘粵各瑤族自治縣輪流承辦;二是鄉村型,在各地瑤族村落舉辦。兩種類型的舉辦形式差異較大,但祭、唱、跳盤王均為不可缺少之核心內容。祭盤王即還盤王愿,包括許愿和還愿儀式。村落集體還愿與家庭還愿的“愿頭”不同,村落集體還愿主要是還瑤人渡海之大愿;家庭還愿則可有添丁、消災等多種愿頭,春天做簡單的許愿儀式,立冬后做還愿儀式。還盤王愿至少三天三夜,根據許愿之大小和類別需要1 - 3頭豬不等的祭品。儀式過程深受道教影響,一般包括謝圣和謝王兩部分,謝圣指請道教神祇和家先,還元盆愿、祭兵愿;謝王指請盤王,還歌堂愿。唱盤王即唱《盤王大歌》,內容為開天辟地、人類起源、盤瓠神話、渡海神話、瑤人遷徙歷史等,有儀式中穿插唱和坐歌堂兩種形式。跳盤王即《嶺外代答》中之“踏瑤”:“瑤人每歲十月,舉峒祭都貝大王于廟前,男女各群聯袂而舞,謂之踏瑤。”如今表現為吹笙撻鼓,在盤瓠神話中,盤瓠在打獵途中不幸被山羊頂下山崖而死,家人剝下山羊皮制成鼓面,世代跳長鼓舞紀念。將吹笙撻鼓結合的多見于平地瑤支系,有代表性者如廣西恭城瑤族自治縣觀音鄉、三江鄉平地瑤的吹笙撻鼓舞,1廣西富川瑤族自治縣平地瑤的蘆笙長鼓舞。
二、歷史記憶與民族認同:盤瓠神話的敘事策略
“族源性紀念儀式大都有一個神話敘事的根源,‘推原神話特指那些解釋萬物起源和族群來源的神話”[10]。作為“推原神話”和元敘事的盤瓠神話,與作為慶典儀式形態的盤王節一道構成了完整的盤王崇拜體系,成為瑤族最重要的集體記憶和文化盛宴。
(一)民族根骨象征與社會制度合理敘事
盤王崇拜是瑤族民族精神的象征,是維系遷徙歷史長、分布區域廣、支系繁多的瑤族凝聚力和文化認同的核心紐帶。通過追溯盤王始祖,瑤人堅守擁有共同血緣、族源、歷史與文化的信念。在此意義上,盤王崇拜可視為一種根基性的“原生紐帶”以及象征性的社會文化建構,使瑤族共同體“獲得內聚外斥的力量和根據”[11]45。作為客觀世界的折射和集體表象的表達,神話及其傳播體現了族群精神和內聚機制。族群認同理論的神話 - 符號叢論就強調體現深層信仰和感情的神話對于族群認同的重要性,認為族群的核心是神話、記憶、價值和象征符號,神話處于中心位置,族群的生命力和特性在于神話和符號的性質[11]59 - 62。如《過山榜》開篇所言之“瑤人根骨,乃龍犬出生”,強調盤瓠作為先祖的血脈根骨象征的神話思維,“瑤族不僅將虛構的神犬神話當作整個民族族源的根骨和血脈加以儀式化和神圣化,而且還通過瑤文書的制作使之具有憑照式依據”[12]。
同時,盤瓠神話還成為歷史上瑤人不納稅、盤瑤十二姓社會制度的“合法性”敘事。在遠古時期,神話既是神圣崇高的虛構故事,也被視為合理的“真實”歷史,尤其被用來解釋自然現象和社會文化事項。伊利亞德指出,神話“敘述了事物的產生和存在,還論證了人類之所以如此言行的根據”[13]174。瑤人久居深山,從事刀耕火種,不納賦稅,史稱“莫徭”,神話中將其原因解釋為盤瓠護國有功而獲圣賜永免徭役,實為崇高化敘事;渡海神話則不僅重申了盤瓠作為始祖神和救世主的地位,解釋了瑤人由還盤王愿而建立的祭祀共同體之根源,還確立了六男六女十二姓制度為瑤人族性認同的明確標志和界限,瑤族民族認同經由具體的儀式和社會制度得到進一步強化。
(二)選擇性歷史記憶:“逃避統治的藝術”
構建共同的歷史記憶是達成群體認同的重要途徑。盤瓠神話及其衍生出的歌謠、文書、儀式等盤王崇拜體系承載了瑤族獨特的記憶方式。莫里斯.哈布瓦赫指出:“集體記憶不是一個既定的概念,而是一個社會建構的概念。”[14]39歷史記憶并非鐵板一塊,而是情境性和變動性的,主體會根據不同的社會秩序和集體訴求對某些事件作出有選擇性的詮釋。
首先,瑤族通過放大遷徙史的災難敘事來增強民族向心力。克服輾轉流離、艱苦卓絕遷徙之路的困難傳襲至今的堅韌是瑤人獨特的民族精神氣質,對這一苦難歷史的追憶尤為體現在渡海神話和千家峒傳說中。瑤族先民發祥于黃河、長江中下游地區,即口述中的“會稽山”“南京十寶殿”,因戰亂、天災、瘟疫等原因,被迫往南遷徙。渡海神話即可能是對瑤人某次大遷徙的集中反映。日本瑤學者竹村卓二認為旱災可能只是瑤人對歷史上實際民族災難的借喻方式 [15]263,從盤瓠神話到渡海神話的過渡恰恰反映了瑤族社會處境的變化。14世紀以后,當瑤人被編戶,華南地區不斷發生暴動,以保證優惠地位為前提并顯示和漢族有穩定共存關系的盤瓠神話,已經不能再代表民族存在的基礎;而渡海神話作為民族精神的規約,成為統一各部族的新的象征[15]268。可以說,盤瓠神話和渡海神話正是瑤人對不同歷史時期境況的選擇性歷史敘事和記憶,巧妙地用漂洋過海與盤王恩義將遷徙災難和盤王崇拜結合起來,成功建構新的“十二姓”禮儀共同體。
其次,盤瓠神話敘事中“逃避統治的藝術”和瑤族認同的混融性。盤瓠神話折射出古代華夷政治格局、瑤人與中央王朝的政治關系。一方面,歷史上瑤族先民飽受排擠和壓迫,生存空間被限制,“吃盡一山又一山”,生存特權是最緊迫的族群訴求。因此盤瓠神話強調瑤人因盤瓠有功于高辛帝而獲封賜土地、券牒,使其居住地遠離中央王朝控制,不納入編戶、不納稅、不服徭役的做法具有特權之特征和政治合法性;同時,用《評皇券牒》中“遇人不作揖,過渡不用錢,見官不下跪,耕山不納稅”“十二姓皇瑤子孫,出給管山執照,豁免身丁夫役”“皇瑤子孫浮游天下,乃助國之人”等表述區分我族與他族,強調瑤人之族群特性,從而爭取本族權利和平等。另一方面,盤瓠為高王身邊之“龍犬”,通過立功與三公主成婚,其后人獲以上生存特權,并稱為“皇瑤子孫”,又體現出瑤人力圖建立與漢人和中央王朝之緊密聯系的心理。瑤人通過立功、聯姻的敘事方式緩解與統治者、強勢民族的緊張關系,實為爭取資源配置的生存策略和智慧,猶如詹姆斯.斯科特筆下廣大的贊米亞地區人民“逃避統治的藝術”[16]。
三、儀式型慶典:當代盤王節的塑造與衍生
盤王節是“表達某種感情的、精密的傳統形式”[17]33的一種慶典,包括儀式、表演和其他公開性集體行為。由于經濟消費高、師公技藝失傳等原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還盤王愿在很多瑤族地區一度中止,在非遺保護浪潮下,盤王節在新時期得以重構,煥發出新的生命力。各地官方盤王節和鄉村盤王節的舉辦極大地激發了瑤族民眾的文化主體意識和文化自信,在重現認知記憶和習慣記憶的“體化實踐”操演中,瑤人“以現在的舉止重演著過去”[18]90,使盤王節成為集體情感歸屬與家園遺產,彰顯出傳承瑤族文化、保護傳統技藝、延續宗教禮俗和契約精神、促進鄉村經濟繁榮等多重社會文化功能。
盤王節在各地的復興同時也是一個文化衍生和塑造的過程,其組織方式、表現形式、價值功能等均發生巨大變化。總體而言,官方舉辦的盤王節具有弘揚瑤族文化、帶動旅游產業、招商引資等多重目的,可謂是“節慶搭臺,經濟唱戲”。慶典內容則趨于舞臺化、節目化和程式化,祭盤王一般作為開幕式的開場節目呈現,其他歌舞、服飾、技藝、體育競技等展演較多。舉辦時間一般為一天一夜,有的地方還會同時召開瑤族文化研討會。雖然官方舉辦盤王節的歷史不長,但因為南嶺地區幾省聯合的模式,還邀請海外瑤族參加,加強了海內外瑤族之間的交流,影響力非常廣泛。鄉村盤王節的規模較小,但還盤王愿儀式所占比重較大,在組織、籌備和開展的整體過程中,瑤族民眾占主導地位,積極性高。近年來,政府從資金和政策上支持鄉村盤王節的舉辦,使得各地鄉村盤王節出現復興熱潮,大大豐富了瑤民的文化生活。
軍田頭、瓦窯面是隸屬廣西興安縣華江瑤族鄉千祥村的兩個毗鄰自然村寨,村民屬過山瑤,共350人,主要姓氏為趙、盤、李、馮、鄧,幾個姓氏均來源于廣東韶州府樂昌縣,最早的趙姓于康熙年間遷入。因瑤族傳統文化氛圍濃郁,2個村寨于2014年共同被列入“中國少數民族特色村寨”名錄。兩個村落的盤王信仰濃郁,保留有秋后集體還盤王愿和家庭還愿的相關傳統,于2012、2013、2016、2019年聯合舉辦了4屆盤王節。筆者參與觀察了2016年第三屆盤王節,此次盤王節依然由兩村村民組織操辦,興安縣民族局和華江鄉政府撥款2.5萬元為活動經費。節日持續2天,第一天農歷十月十六為祭盤王、跳盤王及其他歌舞、民俗展演,第二天為坐歌堂活動。祭盤王儀式在村里的民族文化廣場舞臺舉行,由4位師公主祭,另有男性助手12名,吹奏嗩吶和牛角的樂師3名,跳長鼓舞青年女性12名。主要祭品為1頭豬。由于盤王廟被毀,祭盤王中斷了很多年,現在做還愿已大大簡化。盤王節上3個小時的祭盤王儀式自然是高度濃縮的,呈現舞臺化特征。但“篾無三道不卷,話無三道不靈”,本著祭祀的神圣性,嚴肅莊重的“三請三送”并沒有改變。舞臺中央的盤王畫像代替了盤王神像,并設祭臺、香爐和供品。儀式過程主要包括:請盤王,師公念誦經文請盤王即位;接盤王,發功曹、請圣;排盤王,師公為請來的道教神靈、盤王及其五旗兵馬、家先、土地龍神等“排位”;歌章娛神,師公依次唱《奉水歌》《招兵歌》《降盤王歌》等歌章,帶領眾人跳長鼓舞,向盤王祭壇行跪拜禮;祭鬼;還愿送圣,殺豬供奉豬頭,焚燒祭壇上的木架及紙花,師公吟唱還壇歌,送神歸位。
祭盤王儀式之后是華江瑤族鄉各村委文藝隊的民族特色文藝匯演,包括軍田頭、瓦窯面文藝隊的《瑤族長鼓舞》《歡聚一堂》,洞上文藝隊的《幸福瑤寨》《多嘎多耶》,千祥文藝隊的《瑤鄉美》《穿新鞋》,銳煒落林口文藝隊的《瑤家姑娘采茶忙》《溜溜的山寨溜溜的醉》,銳煒江頭文藝隊的《竹竿舞》《華江秀》,千祥竹山腳文藝隊的《快樂的瑤家嫂子》等舞蹈。下午是過山瑤民俗文化展示和競技活動,包括當地精美的反面刺繡、打油茶、打糍粑,爬竹竿、背簍裝繡球、捉野豬等傳統競技項目,晚上是瑤族長桌宴。第二天舉行隆重的“坐歌堂”活動,參與者為千祥村各自然村派出的歌師代表。
可以看到,在少數民族特色村寨、非遺保護的雙重契機推動下,軍田頭、瓦窯面村過山瑤的盤王節得以復興和重構。經由儀式向節慶的文化衍生,盤王節被塑造為一個復合型慶典,這一“傳統的發明”涵括了還盤王愿儀式、坐歌堂、跳盤王,飲食、競技、刺繡等多種傳統技藝展示,不僅延續和弘揚了盤王崇拜及其衍生藝術,營造了過山瑤傳統文化傳承氛圍,也成為村落與周邊村鎮進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臺。
筆者調查的另一個桂林市龍勝縣江底鄉盤王節與以上同中有異,2004年得以復興,每3 - 5年由各盤瑤村寨輪流承辦。第一屆在1933年桂北瑤胞起義的發源地梨子根寨舉辦,2004年11月,龍勝縣在此成立“瑤胞起義總部重點文物保護室”,揭牌儀式和第一屆盤王節同時進行。盤王節由龍勝縣民族局、文化局、江底鄉政府、桂林市民委等部門進行指導、組織和協調,建立了一個村寨承辦,其他村寨共同組織祭祀、表演等節目事宜的機制。節日內容主要包括:首先是祭盤王儀式,即起壇掛圣,擺祭品,掛盤王像,師公請圣,唱盤王歌、樂神歌,殺大命紅豬祭祀;其次是歌唱展演12姓盤瑤人接牛角,反映盤瑤人祖居千家峒,因戰亂被迫遷徙,十二姓兄弟將牛角鋸成12截,各執1截,以做今后相認憑證,如今十二姓瑤人得以重逢相聚,重接牛角認祖歸宗;再次是青年男女跳盤王,跳長鼓舞;江底鄉盤瑤《過山榜》文物展示;最后是集體宴席和坐歌堂。每一屆盤王節內容有變化和新增,但以上基本程序不變。盤王節在江底盤瑤地區得以被重新挖掘、展示與再造,成為傳承盤瑤歷史記憶、增強區域性族群認同的重要文化空間。相比過去,盤王節的形式和內容均有變遷與創新:一方面,由主要以自然村為單位組織的祭盤王和還愿演變為以建新村、江底村聯辦的形式,冗雜煩瑣的宗教儀式程序逐步簡化;另一方面,與盤王節相關的追溯瑤人祖先創世、遷徙、耕山、狩獵、生產生活的千家峒傳說、《盤王大歌》,以及藝術表現形式長鼓舞等內容與喜聞樂見的山歌等結合,得到繼承和提升。今天的盤王節還成為全鄉瑤族村寨聯動交流的重要契機,以及展示區域文化品牌的窗口,獲得了全新的生命力,在文化功能更新中得以重新傳承。類似上述村落盤王節復興的案例不勝枚舉,而探究其多元化、可持續發展之路及與鄉村文化振興的互動關系則是當前的重中之重。
四、結論與討論
漢學人類學家葛蘭言指出,節慶的目的在于“以息老物”,在與日常生活的漫長時期相對應的這一短暫時期,節慶以近乎奇跡般的強化作用,激發成員對他們正在共同實行的行為所具有的效力產生一種無可壓制的信賴感。社會契約得到了更新[19]158 - 195。從內涵上看,瑤族盤王節肇始于神圣的盤瓠神話、渡海神話,體現了瑤族遵守契約的寶貴品質和堅韌的生存智慧,是維系瑤族共同體的精神支柱;從外延上看,盤王節涵括了還盤王愿、瑤傳道教、師公技藝、長鼓舞藝術、吹笙撻鼓藝術、鳴響樂藝術、瑤歌演藝、特色飲食服飾等物質民俗、口述傳統、社會關系之傳承與建構。盤王節是瑤族珍貴的精神財富和文化遺產,理應世代傳承,生生遺續。而在當前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如何使盤王節成為瑤族鄉村文化振興的核心元素,在轉型中得到新生,并切實助推村落內生文化動力的涵育,筆者認為有以下幾點值得深入探討:
(一)盤王節文化生態重建。任何傳統文化都不是一個孤島,而是特定文化體系整體中的一元,盤王節在過去的傳承斷裂是因為其賴以生存的瑤族文化生態遭到破壞,其在復興后的可持續發展亦須重啟和營造這一文化生態。包括重視瑤族村落內外部文化環境的互動,保護與還盤王愿儀式和跳盤王、唱盤王相關的信仰、儀式、舞蹈、歌謠、神話等,如盤王廟空間、師公信仰及其知識體系、盤瓠神話及歌謠傳唱、吹笙撻鼓傳習等。即以盤王節之“點”帶動瑤族村落傳統文化之“面”的傳承發展,“通過文化重啟和保護,獲得自由生長的空間和向度,從而重新獲得生命力”[20]。
(二)盤王節功能價值更新。在社會文化轉型期,必須正視傳統文化功能和價值更新的問題,固步自封一味追求“原生態”弊大于利。應引導盤王節的祖先信仰及民族凝聚核心價值植入當代活動空間,并發揮其激活鄉村文化活力、傳播瑤族文化、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助力鄉村振興等新功能,在文化適應中逐步轉型,在新時代獲得新的傳承空間。當然,基于信仰節慶類文化遺產的特殊性,商品化問題應盡力規避。
(三)盤王節傳承方式創新。信仰類文化遺產的傳續往往面臨宗教職能者傳承人斷裂、民眾崇信觀念變化、資金缺乏、社會環境影響等問題,探索其創新傳承方式是長期之要務。竊以為與旅游相結合不是唯一且最好的路徑,應吸引多方社會力量,增強村落內生文化自覺和行動力,可從發展跳長鼓舞、吹笙、唱瑤歌等盤王節衍生藝術入手,活躍村落文化氛圍,并逐步甄選和培養青年一代傳承人,如廣西恭城縣水濱村、富川縣青山腳村等平地瑤村落自發組織的文藝隊就是比較成功的案例。另外,村落聯辦、輪辦、互訪和交流等形式均是促進盤王節創新發展、推廣傳播的途徑。
參考文獻:
[1]? 廣西壯族自治區編輯組.廣西瑤族社會歷史調查:第八冊[M].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85.
[2]? 聞一多.伏羲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 袁珂.中國古代神話[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
[4]? 吳澤順.盤瓠神話的深層結構[J].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2(2):31 - 34.
[5]? 苑利.盤瓠神話源出北方考[J].民族文學研究,1994(1):47 - 54.
[6]? 吳曉東.蠶蛻皮為牛郎織女神話之原型考[J].民族文學研究,2016(2):28 - 38.
[7]? 岑家梧.圖騰藝術史[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7.
[8]? 馮智明.瑤族盤瓠神話及其崇拜流變——基于對廣西紅瑤的考察[J].文化遺產,2014(1):93 - 97.
[9]? 奉恒高.瑤族盤王節[M].北京: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13.
[10]彭兆榮.儀式敘事的原型結構 ——以瑤族“還盤王愿”儀式為例[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2009(5):53 - 58.
[11]納日碧力戈.現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構[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12]彭兆榮.無邊界記憶——廣西恭城平地瑤“盤王婆”祭儀變形[J].廣西民族研究,2005(4):46 - 56.
[13]伊利亞德.宇宙創生神話和“神圣的歷史”[C]// 阿蘭·鄧迪斯.西方神話學讀本.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14]莫里斯·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M].畢然,郭金華,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15]竹村卓二.瑤族的歷史和文化[M].金少萍,朱桂昌,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16]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的無政府主義歷史[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
[17]杰克.古迪.神話、儀式與口述[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
[18]保羅.康納頓.社會如何記憶[M].納日碧力戈,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9]葛蘭言.古代中國的節慶與歌謠[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20]陳華文.文化重啟:傳統村落保護可持續的靈魂[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2018(5):47 - 52.
[責任編輯:龍澤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