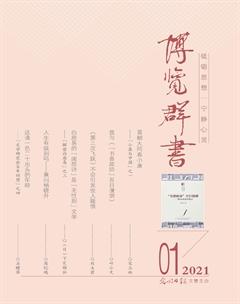《鄭振鐸年譜》本不該是我的第一本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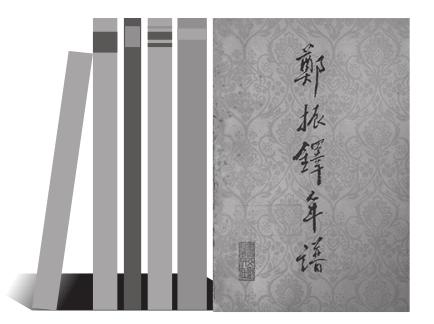
我這輩子出的第一本書,是1988年書目文獻出版社(對這個社名我很留戀,也非常喜歡,可惜這個名后來改過好幾次,先是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后又改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我覺得還是“書目文獻”最雅)出版的《鄭振鐸年譜》。但是,我本來更早應該出版的第一本書并不是這本年譜,而是《鄭振鐸研究資料》。我必須從這本未刊書稿開始說起。這件事對我來說是有點遺憾的。
上世紀80年代初,我作為當時全國最早的研究生在復旦大學就讀。那時我已經開始研究鄭振鐸先生。那年頭,所謂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是很熱門的。但當時很多“現代文學”專家,幾乎都還沒有認識到鄭振鐸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舉個例子吧,當時有很多專家開會研究,要組織撰寫出版一套中國現代文學作家傳記叢書,胃口很大,反復推敲搞了個幾十位作家的名單(包括其實沒什么可寫,而且到最后也寫不出傳記來的作家),約了很多人來寫,最初就根本沒有想到鄭先生其人。(后來這套叢書中有了我寫的一本《鄭振鐸傳》,但那是我寫好以后努力說服出版社收入的,并非專家原計劃里就有。)不過,大概因為鄭先生生前是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的創始所長,所以當時社科院文研所的一個非常宏大的項目,“中國現代文學作家作品研究資料叢書”里面,倒是列入了《鄭振鐸研究資料》一種的。我當時只是個學生,雖已發表了一些有關鄭振鐸研究的文章,但誰也不會想到找我。這本書,是他們交給上海文藝出版社理論讀物編輯室主任余仁凱編的。有一天,我到上海文藝出版社去,余主任叫住我說,我看到你發表了好幾篇研究鄭振鐸的文章,社科院交給我編鄭先生資料的任務,但我對鄭先生沒有研究,而且我工作也太忙,如果你愿意承擔這個任務的話,我就向他們提出來轉給你好嗎?我當然很高興地答應了。
這個國家級社科重大項目國家是投了不少錢的,可是你知道嗎,我承擔這個重大項目下的一個子項目,那到我手里是多少經費呢?現在說出來你肯定不相信,100元。我當時就領了這100元開始工作了。(后來,有關同志覺得不好意思,又要我打報告再申請了200元。所以,我第一次得到學術研究基金是很早的,比很多同齡人早得多了;但最早得到的基金只有100元,一共300元錢。)好在,那時我們國家還比較窮,物價也比較低,人的欲望也不高。
我非常努力地按時按要求完成了《鄭振鐸研究資料》書稿。如果順利的話,完全可以在畢業前就出版。大約有50來萬字,那是他們限制的字數,本來我覺得應該搞得再多一點,因為鄭振鐸的資料非常豐富。那時復印機還遠沒有普及,照相機也是稀罕物,書稿所有的內容都是手抄手寫的,包括我的父親也辛苦地幫我抄寫了不少(現在想起來,我還非常感謝先父,也覺得很對不起他的)。我交稿后,社科院文研所的領導就轉交給了這套叢書的一個編委“審讀”。可是非常納悶的是,她遲遲不作處理,理由是她有其他的工作,太忙。本來,所謂的“審讀”也就是看看符不符合體例和要求,其中大部分內容(如作家生平自述、創作自述、文學主張、研究者對作家的評論等)其實根本就不用多看。但人家就是拖著不看。我除了寫信詢問外,好幾次出差到京,都到她家里去問;后來我又上京當了博士生,更去她家好多次(當然,我也從沒想到應該提一點什么禮物送去)。后來,連她的忠厚的愛人(也在社科院文研所工作)在一旁也覺得不好意思了,曾當著我的面對她說,你就快點幫小陳看看吧。但她就是一直拖著。我向文研所領導也反映了,他們說沒辦法,也不好換人。過了好久好久,她總算“審讀”完了,也沒有提出什么問題來,書稿才交到這個大項目的負責人馬良春那里。老馬倒是非常爽快的,立刻就作了批示通過,并將書稿給了福建某出版社,因為鄭振鐸就是福建人嘛。
不幸的是,由于被長期拖延耽擱,這部書稿錯過了出版的機會。此時的出版界已很不景氣。出版社大概認為,既然是國家重大項目,有很多經費的,可是給他們的出版補貼卻太少了,于是就不愿出。該社的編輯與我也認識,他就坦白地跟我講,書稿是編得好的,但如果你另外搞不到經費的話,出版就“想也不要想了”。又過了多時,我也就絕望了,把書稿也要了回來。此前,我又曾向社科院文研所提出,在那大項目下再編選一本《彭家煌研究資料》(他們原計劃中沒有),得到他們批準立項,并已著手進行,也因為我怕做了白做,沒有繼續做到底。但我想,自己對《鄭振鐸研究資料》下了這么多功夫,包括老父親也為我費了很多力,難道就這樣白干了嗎?因為書稿里面,本來就按要求有我撰寫的《鄭振鐸生平活動大事記》《鄭振鐸著譯年表》等,但因為限于叢書體例與字數的規定,比較簡單,所以我就想不妨利用這些資料,另行撰著(我拒絕用“編”這個字)一本《鄭振鐸年譜》吧。就這樣,本來《鄭振鐸研究資料》應該是我的第一本書,可惜卻石沉大海。
撰著《鄭振鐸年譜》完全是我的“自選科研項目”,沒有“立項”,沒有一分錢的“科研經費”。但我樂此不疲。就在我反復修訂當中,一次到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的書目文獻出版社的《文獻》雜志編輯部去玩。我是他們的作者,當時的主編劉宣先生很看得起我,常對我說他在編雜志的過程中“發現”了一男(指我)一女兩個十分努力的青年人。我向他談起了我的《鄭振鐸研究資料》,和正在撰寫中的《鄭振鐸年譜》。不料他頓時雙目發光,非常熱情地對我說:“為鄭先生寫年譜好啊!鄭先生對我們北圖也是有恩的,相信你這么多年認真研究,質量一定會好。你完成后拿來,我推薦到我們社出版!”就這樣,我這輩子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書,就是書目文獻出版社的《鄭振鐸年譜》了。我永遠感謝已故的劉宣老先生。
我的《鄭振鐸年譜》書稿交到出版社去時,劉老已經退休了。該書的責任編輯是賀敬美。老賀人非常樸實,我在京讀書時常到他辦公室和他家里聊天。他的哥哥就是抗戰時期著名的延安革命詩人賀敬之,時任中宣部和文化部的領導。但是老賀在我面前從不提他哥。我提起了,他還跟我說,我哥是我哥,我是我,我不沾哥哥的光。當時,書目文獻出版社剛創辦不久,編輯的經驗也不足,書的裝幀印刷有時不那么好。例如我的這本書,印好后他們才發現在封面、書脊和扉頁上都沒印我的名字。他們肯定覺得很不好意思,于是就把“陳福康編著”五個鉛字沾了油墨,像蓋圖章一樣,不辭辛勞地一本本手工打印在扉頁上。盡管如此,我仍然非常喜歡這本我請鄭先生老友郭紹虞、李一氓先生題簽題詞的,封面樸素無華,而且沒有印我名字的書,一本厚厚700頁,卻僅售4.60元的書。一本趕在鄭振鐸誕生90周年、犧牲30周年時出版的書。
這就是我的第一本書的故事。還有一些余聞,亦可一說。
此書出版后,很快就賣完了。而我仍繼續不停的研究鄭振鐸,又發現了很多新的史料,也發現了有些地方原先記述不準確,所以我不斷地做著修訂。我曾向出版社試探提出再出修訂本,但當時他們確有困難,沒有積極回應。一過又是十多年,原社領導和編輯也都退休了,這時,我們國家有了很大的發展,出版形勢也好轉了。我的修訂工作有幸列入了我當時的工作單位上海外國語大學的科研項目,這樣,按學校規定我就可以把修訂書稿交給本校出版社出版了。可是沒想到的是,山西古籍出版社總編輯張繼紅兄聽說我在修訂這部年譜,立即主動表示希望在他們社出版。又沒想到的是,在我即將交稿之際,北圖出版社(即原書目文獻出版社)的當時我還不認識的殷夢霞編輯(現已是該社總編輯)來電話談別的事,得知我這一書稿已修訂完成,當場表示還是應在她們那里再版。我對北圖出版社一直感恩在心,但我已與山西古籍出版社談好了,怎么辦呢?殷夢霞說沒關系,她們郭社長與山西古籍出版社張總是老朋友,打個電話就成。我想起聽張總說過,山西古籍社是個小出版社,經濟獨立核算,自負盈虧,而我這本書又賺不到什么錢,因此我對殷夢霞說,只要張總同意,我就沒意見。過了沒幾天,殷夢霞來電話說,他們社長親自給張總打電話了,但張總不愿“割愛”。修訂本于2008年鄭先生誕生110周年、犧牲50周年時出版。書從一冊變成了兩冊。
但我仍是繼續不停地研究鄭振鐸,又發現了很多新的史料,又發現了有些地方原先記述不準確,所以我仍舊不斷地做著修訂。在學界友人的年譜專著修訂工作獲得國家基金立項的啟示和鼓勵下,在上海外國語大學領導和科研處的大力支持下,我便也嘗試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會申請,竟幸運地也得到了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的批準!在我的修訂增補工作正式啟動以后,曾有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等多家著名出版單位的編輯和領導主動向我索要書稿,表示可以安排出版。對此,我真有點“受寵若驚”了。我深深感受到,近幾十年來我們國家對社科研究和出版的投入之不斷增大,使社科研究和出版環境有了明顯的改善;同時,我又深深感受到人們對鄭先生的認識有了很大的提高。這是我感到非常高興和幸福的。我的第二次大規模修訂的《鄭振鐸年譜》,最后還是給了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那是當過我多本書的責任編輯的李振榮兄主動向我要去的。于2017年出版,書又變成了厚厚的三冊,成為第二年紀念鄭先生誕生120周年、犧牲60周年的獻禮。
我的這部書,先后榮幸地獲得過第三屆全國優秀古籍整理圖書二等獎、第十四屆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和第八屆全國高等院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二等獎。
(作者系福州外語外貿學院鄭振鐸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