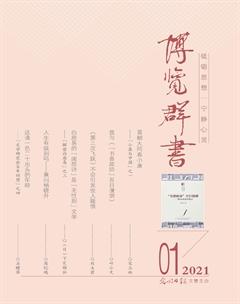看魯迅的“小悲歡”與“全世界”
1921年1月,一批優秀的知識分子成立了文學研究會。他們對當時文壇上黑幕橫行、鴛鴦蝴蝶亂飛深感不滿,起而要求建設一種新的文學觀。“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游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了。我們相信文學也是一種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為了這人生,并且要改良這人生,從此成為了現代作家講述中國故事的主流思想。后來,人們自然意識到游戲的、消遣的文學自有其價值,或許那樣的小說才是小說之正宗。隨著網絡文學興起,故事講述的黑幕化、鴛鴦蝴蝶化急劇泛濫開來,更有一般寫手肆意地敘述著一己之私欲,炫耀其金錢的文藝觀,且有愈演愈烈之勢。百年前文學研究會成立時面對和思考的問題,似乎又擺在了當今人們的面前:文學何為?故事,又該怎樣講述?套用時下流行的話說,便是如何講好中國故事。
殷鑒不遠,來者可追,惟能繼往者方有開盛世之希望。現代文學發生至今,已形成了優良的新的文學傳統,文學研究會便是這新的文學傳統的重要源頭。百年回首,不單是為了紀念過去,更是因為溫故方能知新。一個世紀亦是一輪回,是以總有世紀末焦慮的出現。時間的輪回不必導致循環論,循環的是時間,人的思想若要跳出循環之外,需要時時警惕曾經的不好的思想的重來,繼承發揚優良的文化傳統,尤其是新民主主義以來的新的文化傳統——講好中國故事,當有此格局。
——咸立強(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2019年4月16日,《求是》雜志第8期發表了習近平總書記的文章《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能沒有靈魂》,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文化文藝工作者要跳出“身邊的小小的悲歡”,走進實踐深處,觀照人民生活,表達人民心聲,用心用情用功抒寫人民、描繪人民、歌唱人民。
其中,“身邊的小小的悲歡”用的是魯迅的話,出自《〈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原語是:
一切作品,誠然大抵很致力于優美,要舞得“蹁躚回翔”,唱得“婉轉抑揚”,然而所感覺的范圍都頗為狹窄,不免咀嚼著身邊的小小的悲歡,而且就看這小悲歡為全世界。
魯迅不是文學研究會成員,但是他對文學創作中“咀嚼著身邊的小小的悲歡”所持的態度,卻與文學研究會主導思想相一致。
因教育部官員這一身份的限制,魯迅沒有列名文學研究會,但是很多人都將魯迅視為文學研究會的編外成員。魯迅的許多文字也發表在文學研究會的刊物上,他的文學思想和創作主張與文學研究會也頗為一致。比如魯迅在小說二集導言中所說的上述那段話,文學研究會的主將茅盾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中也有類似的表述。茅盾在導言中指出那時候(第一個“十年”的前半期)創作界的兩個很重大的缺點:“第一是幾乎看不到全般的社會現象而只有個人生活的小小的一角,第二是觀念化。”魯迅和茅盾對當時創作界拘囿于“身邊的小小的悲歡”“個人生活的小小的一角”表示不滿,他們的意見,通過《中國新文學大系》不斷地被經典化為文學研究會的主流思想。
魯迅所說的“小悲歡”顯然不等同于“個人悲歡”,“小”不等于“個人”,惟囿于個人而漠視或隔絕社會的才是“小”,這樣的“小”不能與現在的或未來的“大”共鳴共振,這樣的“小”是真正的“小”,仿佛海中一粟,雖在海中,卻與海水格格不入,是相互隔膜不能相通的靈魂。然而,“小悲歡”與“全世界”并非截然對立的關系,“小悲歡”中可以蘊含著“全世界”,而“全世界”也正是由一個又一個的“小悲歡”組成;沒有“小悲歡”的“全世界”也就不成其為真正的“全世界”,結果只能變成錢谷融在《論文學是人學》中批評的那種空洞的、抽象的“整體現實”。文學研究會的作家冰心寫道:
誰信一個小“心”的嗚咽。
顫動了世界?
然而它是靈魂海中的一滴。
只有本是“海中的一滴”,方能融入大海,與大海渾然一體,故而自己小小的嗚咽才能震動整個的世界。
魯迅和茅盾關于文學創作“小悲歡”與“全世界”的思考需要放到具體的語境中,通過觀照上下文才能夠準確地把握和理解。被魯迅評價為“就看這小悲歡為全世界”的是彌灑社的一群作者,小說方面的代表有胡山源、唐鳴時、趙景深等。他們在魯迅眼里是“為文學的文學的一群”,而與為人生的文學的一群相對立。《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共有十集,其中三本小說集,小說一集主要編選文學研究會的小說,小說三集主要編選創造社的小說,小說二集則由魯迅編選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之外的小說。因此,魯迅在小說二集導言中評價的都是自己所編選的小說,并不旁及創造社的小說。但是,當魯迅批評彌灑社的小說創作時,竊以為也很可以視為是對創造社小說的批評。“不免咀嚼著身邊的小小的悲歡”,這幾乎就是郁達夫身邊小說的恰切寫照。此外,魯迅并沒有就“小悲歡”與“全世界”展開對彌灑社小說的具體分析,這固然與小說集編選的篇目有關,另一方面似乎也是魯迅借此對為藝術的創造社小說創作的順手一擊。
魯迅談到自己為什么要進行小說創作時,說自己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并且要改良這人生。啟蒙就是光明照亮黑暗,而要照亮的不僅是自己,更要照亮他人,乃至于全世界。《狂人日記》里的狂人覺醒之后,首先想到的便是啟蒙自己的大哥。“我詛咒吃人的人,先從他起頭,要勸轉吃人的人,也先從他下手。”《狂人日記》表面上說是以狂人口吻寫出,“語頗錯雜無倫次”,實際卻隱藏著作家對啟蒙深刻而周密的啟蒙思考。啟蒙,固然是要照亮別人,但是如何照亮,從誰開始著手,卻是頗費思量的事情。狂人的啟蒙大業從自己的大哥開始,選擇從身邊最親近的人開始,竊以為這才是啟蒙事業的應有之義。自古至今,多有以啟蒙大業自任之輩,夢想要以自身的光芒照亮全世界,他們心中的全世界卻大多并不包含自己的親人。一個連親人都無法啟蒙的人,卻總想著去啟蒙、改變自己并不熟悉的他人(全世界),竊以為這并非是在掃一屋與掃天下之間進行選擇,而是有點不敢直面真正的問題,是以頗有古代易子而教的意思。何為易子而教?孟子說:“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要點在于“以正不行,繼之以怒”。對親人,繼之以怒容易招致“反夷”。但是,易子而教就沒有“反夷”之弊了嗎?應該也是有的,只是對于以親緣關系為主導的社會來說,只要“反夷”不出現在親人之間就可以了。但是這種教育思想恐怕與老子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太相符,大同社會理想的實現恐怕還是要消除易子而教的“反夷”之弊才好。換言之,便是啟蒙最好還是從身邊親人做起比較好,這樣才能夠更清晰地讓啟蒙者思考啟蒙不能行時是否要繼之以怒,繼之以怒而有“反夷”之弊時又當如何處理?有親親之心,而無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念,實際上將全世界里的他人都視為了抽象的數字,強行以自身之光照亮親人之外的全世界,不能如意時動輒便要繼之以怒,渾然不顧“反夷”之弊,自以為特異于眾,實則與眾隔膜,名為啟蒙,實為禍害,這肯定不是魯迅理想中的啟蒙,也不是魯迅想要的那種顧及全世界的做法。
魯迅對彌灑社“咀嚼著身邊的小小的悲歡”的批評主要來自文本閱讀,以個人的敏銳的文學感知把捉到了文壇創作的某種傾向,而茅盾對“只有個人生活的小小的一角”的批評卻大不相同,乃是“根據了那時候三個月中間已發表的小說120余篇來研究它們的題材,思想,與技術”,而后得出結論,“竟可說描寫男女戀愛的小說占了全數百分之九十八”了。近百年前,茅盾就以嚴格的統計數據報告人們文學創作的大體傾向,指出弊病,引起人們的注意。現在,我們已經進入了大數據分析的時代,但是卻甚少看到像茅盾那樣的統計分析,各種研究論著充斥著的主要還是傳統的文學閱讀,經驗判斷為主,伴隨著少量的局部的數據統計。近些年來,中國小說的出版數量龐大,每年僅長篇小說就有幾千部,大數據分析時代最善于處理的應該就是這類體量大的研究對象。一旦我們能夠借助大數據分析,像茅盾那樣,對每年發表的小說的題材、思想、技術等進行分析統計,一些文學上的問題就會更顯豁地呈現出來,才能有針對性地采取一些相應的措施,否則的話,對問題的分析和認識各不相同,解決的辦法往往不是驢頭不對馬嘴,便是空空洞洞的一句“讓它自由發展”。
如何使創作走出“身邊的小小的悲歡”?其實,這個問題更應該反過來問,為什么有些作家樂于表現“身邊的小小的悲歡”?魯迅談到了作家文藝觀的影響,茅盾則側重從作家生活經驗的局限性進行了分析。樂于表現“身邊的小小的悲歡”,一則是作家的創作個性使然,一則是作家自身的生活經驗使然。江山易改稟性難移,一個作家一旦形成了自身的個性氣質,改變起來很困難,容易改變的往往不是最有成績的作家。想要使作家的創作走出“身邊的小小的悲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較為可行的便是讓已成作家們多多經驗新的生活,或徑直發掘培養新的作家。茅盾年輕時揮斥方遒,批評文壇,指出作家的創作應該顧及“全般的社會現象”而不應該“只有個人生活的小小的一角”的時候,還不是小說家。待到大革命失敗后,茅盾從事《蝕》三部曲的創作,開手便顧及了“全般的社會現象”,以大氣魄大格局征服了文壇。后來,《子夜》更是以空前的大格局譜寫出輝煌的社會史詩。這時候,那些曾被茅盾批評為“只有個人生活的小小的一角”的作家,大部分依然還沒有走出“身邊的小小的悲歡”。
“小悲歡”與“全世界”講的主要是“小”與“大”的問題,就藝術本身而言,“小”與“大”跟作品的好與壞沒有必然關系,以“小悲歡”為描寫對象的小說可以成為經典,以“全世界”為描寫對象的小說也可以是粗制濫造。但是,站在百年前奉行啟蒙主義的文學研究會的立場上來看,文學創作自然需要走出“身邊的小小的悲歡”,正如茅盾所說,“我覺得表現社會生活的文學是真文學,是于人類有關系的文學”,“因為我既是一個‘人,就應該負人群進步的責任”。這自然是啟蒙者的文學觀,也便是文學研究會奉行的文學觀。他們的著眼點本來就是人群與人類,與人群、人類的悲歡不相通的“小悲歡”無益于表現他們心目中的人生,也就無法改變這人生。百年以降,世界已成地球村,人類的與世界的意識應該越來越發達才是,若是現在的人在這方面的表現反不如百年前文學研究會成員,則與魯迅尊奉的“改良這人生”自是冰炭兩途。
在魯迅的筆下,“小悲歡”這個詞語只使用過一次,倒是“全世界”用的次數很多,在15篇文章中先后使用過23次之多。其中有些表述,即便是放在當下,也足以讓站在21世紀前沿的知識分子們警醒,如魯迅在《二心集·序言》中這樣解剖自己:
我時時說些自己的事情,怎樣地在“碰壁”,怎樣地在做蝸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惱,萃于一身,在替大眾受罪似的:也正是中產的知識階級分子的壞脾氣。
這樣的“壞脾氣”,時下也頗為流行,有些以為大眾代言自詡的人所敘說的全世界的苦惱,終究不過是個人的牢騷罷了,但是這些人偏偏將個人的“小悲歡”隱藏在“全世界”的名目下,將水攪渾,目的不過是借著“全世界”的名目謀取個人的私利罷了。魯迅對于大的名目,向來抱有很大的警惕。在《電影的教訓》中,魯迅談到影片《瑤山艷史》:
這部片子,主題是“開化瑤民”,機鍵是“招駙馬”,令人記起《四郎探母》以及《雙陽公主追狄》這些戲本來。中國的精神文明主宰全世界的偉論,近來不大聽到了,要想去開化,自然只好退到苗瑤之類的里面去,而要成這種大事業,卻首先須“結親”,黃帝子孫,也和黑人一樣,不能和歐亞大國的公主結親,所以精神文明就無法傳播。這是大家可以由此明白的。
中華民族傳統的家國天下思想,隱含著“全世界”的美夢,這自然是大事業;但是對以“結親”來達成“主宰全世界的偉論”,魯迅并不認可,類似《瑤山艷史》那樣的影片無論怎樣“竭力宣傳”,也不能真正地引起“全世界”的顫動。這是值得我們至今還應當思考和重視的。
(作者為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