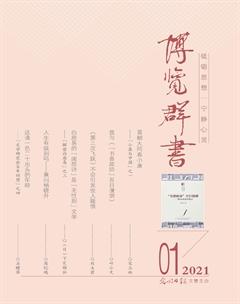《小說月報》為什么如此“譯介”
高志強
五四時期,俄國革命的巨大變化吸引了探索民族道路的中國知識分子的關注。瞿秋白說:“大家要追溯他的原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覺全世界的視線都集于俄國。”研究俄國社會和文化,一時之間成為知識界的風氣。對俄國文學的譯介高潮也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勃然興起,出現了一大批熱心譯介和研究俄國文學的翻譯家、學者,俄國文學作品和理論著作被大量引進,種數之多,迅速超過英法等國,極一時之盛,而這與《小說月報》的大力倡導鼓吹分不開。俄國文學和被損害民族的文學,是《小說月報》在革新的第一年、以專號形式最先聚焦的對象。
從1921年到1931年,《小說月報》的翻譯文學以俄國數量為最多,并遠遠超出次之的法、英、日等國。僅從1921年到1923年這三年來看,除了《被損害文學專號》外,其他各期都有俄國翻譯文學,絕大多數時候(僅有一兩次例外)數量都居當期譯作之首,極為引人注目。1921年9月,革新第一年的《小說月報》推出的第一個號外,就是《俄國文學研究》,分為論文、譯叢、附錄和插圖四個部分,對俄國文學作了全面的介紹。號外發表了20篇論文,如鄭振鐸《俄國文學的啟源時代》、沙洛維甫著、耿濟之譯《19世紀俄國文學的背景》、沈雁冰《近代俄國文學家三十人合傳》、魯迅《阿爾志跋綏甫》、郭紹虞《俄國美論與其文藝》、沈澤民《俄國的敘事詩歌》等,涉及文學史、文藝理論、作家研究、作品分析、文類研究、藝術批評等多方面內容;選譯了29篇作品,上自普希金,下迄高爾基,其中還包括赤色詩歌(《國際歌》)和三篇赤色小說。這樣大規模的翻譯介紹,在讀者中引起的反響是可想而知的。1923年,《小說月報》14卷5至9號連載了鄭振鐸著《俄國文學史略》,共14章,后整理成書,1924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該書體例嚴謹,脈絡清晰,資料翔實,書目完備,是國內最早的一本俄國文學史專著。可以毫無疑問地說,在《小說月報》的翻譯活動中,對俄國文學的譯介占據了最為重要的位置。
《小說月報》為什么如此重視俄國文學的譯介呢?最主要的原因有兩點。
其一,國情相似性所引起的情感共鳴和思想暗示。周作人在《文學上的俄國與中國》一文中談到:
我的本意只是想說明俄國文學的背景有許多與中國相似,所以他的文學發達情形與思想的內容在中國也最可以注意研究。
…… ……
他(俄國文學)的特色是社會的、人生的。俄國的文藝批評家自別林斯奇以至托爾斯泰,多是主張人生的藝術。……中國的特別國情與西歐稍異,與俄國卻多相同的地方,所以我們相信中國將來的新興文學,當然的又自然的也是社會的人生的文學。
俄國也是一個古老的國度,和中國一樣,在其漫長的歷史發展中也經歷了長期的集權專制時期,同樣是晚近時期才受到西方文明影響,開始近代轉型。在西方中心話語中,俄國也是被打上“落后”“不發達”烙印的后發現代化國家,處于被壓迫民族的弱勢地位。而在十月革命以前,俄國社會也是處在苦苦探索出路、各種矛盾尖銳沖突、各種思潮激烈震蕩的時期,就俄羅斯的民族精神而言,也同樣充滿了苦難和沉重的記憶。這些特點都與中國的情形相似,特別是同處于被壓迫地位,容易激起中國知識分子的情感共鳴,而俄國作為后發現代化國家,其在社會變革、民族文學建設等方面取得的經驗,特別是19世紀俄國文學所取得的世界矚目的輝煌成就,也會對中國知識者形成一種思想暗示,使后者獲得鼓舞,看到希望,相信被壓迫民族也一樣能產生偉大的文學和精神,并從而振興民族。魯迅在1932年寫道:
15年前,被西歐的所謂文明國人看作半開化的俄國,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勝利的。這里的所謂“勝利”,是說,以它的內容和技術上的杰出,而得到廣大的讀者,并且給予了讀者許多有益的東西。
…… ……
那時就知道了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因為從那里面,看見了被壓迫者的善良的靈魂,的酸辛,的掙扎……然而從文學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
對《小說月報》同人來說,文學從來就不是獨立于民族國家現實之外的,而俄國文學基于上述種種社會歷史原因,顯然比西歐諸國文學更能為中國的社會變革和文學建設提供可資借鑒的經驗,《小說月報》譯者對俄國文學情有獨鐘,也就很自然了。
第二個重要原因,是俄國文學“為人生”的現實主義特點,與文學研究會和《小說月報》“為人生”的文學觀正相印合。魯迅曾說,俄國的文學,從尼古拉斯二世時候以來,就是“為人生”的,無論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決,或者墮入神秘,淪于頹唐,而其主流還是一個:為人生。具體而言,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為人生”的特點主要表現在兩個層面,一是深廣的社會性。他們始終懷著高度的民族責任感和使命感關注俄國現實,批判社會,批判國民性。在《小說月報》同人看來,西歐現實主義作家筆下盡管也有對社會的批判,但往往著重批判社會的一個方面,對社會作整體性的批判反思的作品并不多,而很多俄國作家則總是力圖把自己的關注對象擴大到整個社會和民族性的廣度和高度,例如果戈理在談到他的《死魂靈》就說:“我想在這部小說里至少從一個側面表現全俄羅斯”,“全俄羅斯都將包括在那里面”。這樣的視野胸懷使得俄國作家的作品常常具有一種洞察社會與人生的深刻力量,在反映社會人生的廣度和深度上也具有一種雄渾的氣勢。沈雁冰在《近代俄國文學雜談》一文中對此曾有明確的評價。“為人生”的另一落實點就是俄羅斯文學深厚的人道主義精神傳統,從普希金的《驛站長》、果戈理的《外套》,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到契訶夫的小說……俄國作家始終關注底層“小人物”的命運,滿懷同情地描寫他們的不幸和掙扎,表現他們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生命運,所以周作人在《文學上的俄國與中國》一文中指出:
俄國的文人都愛那些“被侮辱與損害的人”,因為——如安特來夫所說,我們都是一樣的不幸,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伽爾洵,科羅連珂,戈爾奇,安特來夫都是如此。
沈雁冰比較西歐和俄國現實主義作家時也說:
英國作家狄更思未嘗不會描寫下流社會的苦況,但我們看了,顯然覺得這是上流人代下流人寫的,其故在缺乏真摯濃厚的感情。俄國文學家便不然了。他們描寫到下流社會人的苦況,便令讀者肅然如見此輩可憐蟲,耳聽得他們壓在最下層的悲聲透上來,即如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那樣出身高貴的人,我們看了他們的著作,如同親聽污泥里的人說的話一般,決不信是上流人代說的。
很顯然,《小說月報》同人敏銳地把握了俄國現實主義文學最突出的特點,并自覺地將其與西歐現實主義進行比較,既指出它們都具有關注現實、細致描寫的共性特點,也強調俄國現實主義的獨特之處。與西歐現實主義作品相比,俄國文學這種鮮明的“為人生”特點顯然更能使那些關注現實人生、懷有強烈使命感的中國作家產生“心有戚戚焉”的感受,因此,毫不奇怪,作為成熟的“為人生”的文學范本,俄國文學成為《小說月報》最重要的譯介對象。魯迅后來回憶道:
為人生,這一種思想,在大約20年前即與中國一部分的文藝紹介者合流,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契訶夫、托爾斯泰之名,漸漸出現于文字上,并且陸續翻譯了他們的一些作品,那時組織的介紹“被壓迫民族文學”的是上海的文學研究會,也將他們算作被壓迫者而呼號的作家的。
至此,我們已經不難了解,正是國情相似性引起的情感共鳴和思想暗示,以及“為人生”的現實主義文學特點所激發的觀念應和,構成了《小說月報》譯介者高度青睞俄國文學的時代背景。
此外,《小說月報》對于被損害民族文學的譯介也是其翻譯文學的重要內容和特色之一。1921年,在推出“俄國文學專號”的同一年,《小說月報》12卷10號推出《被損害民族的文學號》,包括引言一篇,介紹波蘭、捷克、塞爾維亞、芬蘭、新猶太、小俄羅斯等國文學的論文七篇,波蘭、希臘、芬蘭、保加利亞、捷克、塞爾維亞、烏克蘭等國的小說十篇和詩作十篇,等等。
對于被壓迫民族文學的關注,在中國近現代翻譯史上是從周氏兄弟《域外小說集》開始的,當時收錄了短篇小說16篇,童話寓言若干,重點介紹了北歐和東歐弱小民族國家的作品。魯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中回憶:
注重的倒是在紹介,在翻譯,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別是被壓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為所求的作品叫喊和反抗,勢必至于傾向于東歐。
很顯然,譯者意圖在于引起同樣遭受侵略壓迫的國人的心理共鳴,激起他們的反抗和斗爭。但是由于當時中國譯界的整體風氣是,從作品選擇而言傾向西歐強國,從翻譯策略而言采用意譯,而周氏兄弟選擇弱小民族文學作品,提倡直譯,雖有開風氣之功,但在當時的讀者中卻反響不大。這也說明,在翻譯文學的產生和傳播過程中,接受環境同樣是相當重要的一環。五四時期弱小民族文學能夠產生影響,和時代與社會的整體氛圍、讀者素質的普遍提高、譯界風氣的根本轉變等因素是分不開的。
對于為什么要研究和譯介被損害民族的文學,《小說月報》編者是這樣說的:
一民族的文學是他民族性的表現,……要了解一民族之真正的內在的精神,從他的文學作品里就看得出。
…… ……
凡被損害的民族的求正義求公道的呼聲是真的正義真的公道。……他們中被損害而向下的靈魂感動我們,因為我們自己亦悲傷我們同是不合理的傳統思想與制度的犧牲者;他們中被損害而仍舊向上的靈魂更感動我們,因為由此我們更確信人性的沙礫里有精金,更確信前途的黑暗背后就是光明!
這段話清楚地表明了編者推出這樣一個專號,和當年的周氏兄弟有著同樣的思路:通過被損害民族與中國同處于被壓迫地位的國情相似性,激起人們的心理共鳴,或是因其不幸而同情,或是因其奮發而振作。不久之后,沈雁冰在《一年來的感想與明年的計劃》更進一步明確地闡發了自己的意圖:
我鑒于世界上許多被損害的民族,如猶太如波蘭如捷克,雖曾失卻政治上的獨立,然而一個個都有不朽的人的藝術,使我敢確信中華民族哪怕將來到了財政破產強國共管的厄境,也一定要有,而且必有不朽的人的藝術!而且是這“藝術之花”滋養我再生我中華民族的精神,使他從衰老回到少壯,從頹喪回到奮發,從灰色轉到鮮明,從枯朽力爆出新芽來!在國際——如果將來還有什么“國際”——抬出頭來!
結合這兩段話,《小說月報》大力譯介被損害民族文學的動機和目的就非常清晰了。編者希望,或者說相信,首先,相似的國情可以激發人們對于被損害民族文學的接受興趣;其次,其他被損害民族文學的成就,可以帶給中國讀者強烈的心理暗示,激勵國人建設新文學;再次,文學可以振作民族精神,最終實現強國理想。可以看出,《小說月報》同人的基本理路是:弱小民族的現實—其民族性—其文學—中國文學—中國民族性—中國現實,而其最基本的前提仍然是文學與社會現實的密切關系。在這樣的接受前提下,《小說月報》對于弱小民族的譯介,顯然不是從藝術性標準出發,因此技巧的選擇在其次,而現實的因素則是重要的標準了。同時也應指出,有關“被壓迫民族”的話語就其本質而言,實際上是對東北歐弱小民族的一種想象性認同,它反映著像中國這樣的非西方國家在現實危機中的某種自我認定。歸根到底,是出于迫切的現實需求而產生的文學和翻譯策略。
(作者為中央民族大學文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