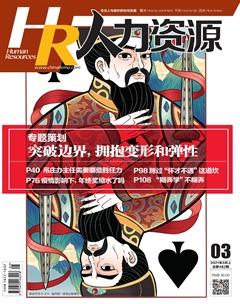工傷賠償“私了”當謹慎
胡笑笑

實踐中,部分用人單位依法為勞動者繳納工傷保險,在勞動者發生工傷后,為了節約成本和避免漫長的訴訟過程,往往通過簽訂“私了協議”的方式處理。同時,部分勞動者由于希望盡快拿到賠償,自愿選擇“私了協議”的方式解決。這種“私了協議”的法律效力到底應該如何確認?
【案情簡介】
駱某為某服裝行的操作工,服裝行為其繳納了社會保險。2017年12月16日,駱某下班途中因交通事故受傷。當地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于翌年4月11日作出工傷認定,認定駱某所受傷為工傷。當地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于同年12月26日對駱某的工傷勞動能力作出鑒定,鑒定為六級傷殘。駱某與服裝行經協商,同意于2019年4月23日終止勞動關系。
2019年5月4日,駱某向仲裁委申請仲裁,稱服裝行方故意選在其無法聯系代理人的周末與其協商協議內容,致其在緊迫或缺乏經驗的情況下簽訂顯失公平的協議。請求服裝行賠償醫療費、住院伙食補助費、護理費、一次性傷殘補助金、一次性工傷醫療補助金、一次性傷殘就業補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資、解除勞動合同經濟補償等,合計291522.2元。
2019年5月13日,駱某與服裝行簽訂《協議書》,約定:“乙方(服裝行)一次性補償甲方(駱某)與第三人梁某機動車交通事故所產生的工傷醫療費及工傷保險待遇共計156000元人民幣,支付時間為2019年5月17日之前;上述補償金額內容包括但不限于工傷醫療費用、護理費、工傷保險待遇、停工留薪期間工資、伙食補助等費用;甲方承諾并保證,不再對本次工傷問題再次向乙方要求任何賠償,或再次申請勞動仲裁或起訴要求任何賠償,甲方應于乙方匯款后立即向仲裁委申請撤回對該案件的勞動仲裁;任一方違反本協議,應承擔違約責任……”
2019年5月16日,服裝行依照約定向駱某支付了156000元。
2019年5月19日,駱某向仲裁委申請變更仲裁請求:(1)撤銷駱某與服裝行簽訂的《協議書》;(2)服裝行向其支付醫療費、住院伙食補助費、護理費、一次性傷殘就業補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資、后續醫療費;(3)服裝行協助其向社保基金申領一次性傷殘醫療補助金;(4)服裝行支付未簽訂勞動合同雙倍工資;(5)服裝行支付解除勞動合同補償金。以上費用合計262293.2元。
在仲裁審理過程中,駱某又向當地人民法院起訴請求撤銷駱某與服裝行簽訂的《協議書》;服裝行協助駱某向社保基金申領一次性傷殘醫療補助金21624元。
仲裁委認為,駱某的第一項、第三項請求不屬于《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規定的受理范圍,故對這兩項請求不予受理;雙方當事人已就簽訂的《協議書》向法院起訴,法院的判決結果對仲裁的裁決有直接影響,決定中止審理該仲裁案件。
【一審判決】:《協議書》不存在重大誤解、顯失公平等情況
一審法院認為,本案屬合同糾紛,其焦點在于涉案《協議書》是否存在重大誤解、顯失公平等情況。
駱某主張:《協議書》中約定的賠償額156000元,達不到其損失的70%,顯失公平;因服裝行的律師誤導,其誤以為后續治療費用可以向工傷保險基金報銷,不知道簽訂了《協議書》就要放棄工傷保險基金支付的一次性工傷醫療補助、一次性傷殘補助金,構成重大誤解。
而服裝行主張:《協議書》的簽訂是駱某在理性評估后同意的,是駱某經過考慮后作出的權利處分結果,不存在欺詐、脅迫和乘人之危、重大誤解、顯失公平等情形。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
●駱某對所受損害及應得賠償有一定程度的認識,因此與服裝行達成協議,屬于對自身權利的處分
駱某自發生工傷至簽訂《協議書》期間,曾有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并擬訂了仲裁申請書,表明駱某對自身所受損害及應當得到的賠償有所認識。根據駱某的第一份仲裁申請書,駱某在得知自身工傷賠償總額大約是二十多萬的情況下,與服裝行協商,最后達成協議,由服裝行賠償156000元,這是駱某對自身權利的處分。
●駱某無法證明主張,應承擔舉證不能的后果
駱某稱,服裝行的賠償額低于損失的70%,顯失公平,但不能提供證據證明,且雙方在《協議書》中明確約定:服裝行一次性補償駱某因交通事故所產生的工傷醫療費及工傷保險待遇共計156000元,補償金額內容包括工傷醫療費用、護理費、工傷保險待遇、停工留薪期間工資、伙食補助等費用等。駱某應當清楚其要求的一次性工傷醫療補助、一次性傷殘補助金,已經在協議中得到了賠償。
對于后續治療費,駱某稱受服裝行律師的誤導,以為可以向工傷保險基金報銷,但駱某不能提供證據證明,因此應當承擔舉證不能的后果。因此,一審法院對駱某要求撤銷該《協議書》的請求不予支持。
此外,《協議書》中明確約定服裝行支付給駱某的賠償中包括了工傷保險待遇,故駱某要求服裝行協助其向社保基金申領一次性傷殘醫療補助金的請求,無事實和法律依據,法院不予支持。
【二審判決】:涉案《協議書》具法律效力,不予撤銷
二審法院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是涉案《協議書》應否撤銷的問題、服裝行是否應協助駱某向社保基金申領一次性傷殘醫療補助金的問題。
關于涉案《協議書》應否予以撤銷的問題:
●駱某對于“重大誤解”“顯失公平”事由負舉證責任
《合同法》第五十四條規定,“下列合同,當事人一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一)因重大誤解訂立的;(二)在訂立合同時顯失公平的……”,即因重大誤解訂立的合同確屬法律規定的可撤銷合同范圍。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71條規定,“行為人因對行為的性質、對方當事人、標的物的品種、質量、規格和數量等的錯誤認識,使行為的后果與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較大損失的,可以認定為重大誤解”。第72條規定,“一方當事人利用優勢或者利用對方沒有經驗,致使雙方的權利義務明顯違反公平、等價有償原則的,可以認定為顯失公平”。
由此可見,重大誤解、顯失公平的認定亦需符合前述司法解釋規定,結合民事案件舉證規則,重大誤解事由的存在須由駱某負責舉證證明。

●《協議書》不存在重大誤解的情形
本案中,駱某首先進行工傷認定和工傷勞動能力鑒定、申請法律援助,進而擬定仲裁申請書、申請仲裁,隨后簽訂《協議書》,在協議款項到賬后又變更仲裁請求。
通過上述一系列事實不難得知,駱某系在工傷事故發生一段時間之后,通過多種渠道對請求標的、請求內容、請求對象等涉及法律行為效果的重要事項已有明確、直觀的了解。
從駱某提交的仲裁申請書來看,其請求內容包括醫療費、住院伙食補助費、護理費、一次性傷殘補助金、一次性工傷醫療補助金、一次性傷殘就業補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資、經濟補償等項目,其請求給付前述款項的對象則為服裝行。但服裝行已經為其辦理社會保險手續,駱某可依法向工傷保險基金申領工傷保險待遇。在此情況下,駱某仍然選擇要求服裝行給付由工傷保險基金支付的費用部分。故可推知,雙方在調解協商時,已包含由工傷保險基金支付的一次性費用部分。
因此,雙方約定由服裝行向駱某支付的156000元款項,亦已包含一次性傷殘補助金和一次性工傷醫療補助金部分。
法院據此認定,雙方訂立涉案《協議書》不存在法律意義上的錯誤認識,雙方訂約所產生的法律效果也不符合與真實意思相悖的法定情形,且服裝行已如約付款,駱某亦未因此而造成較大損失。
此外,駱某在一審過程中雖然提出其在后續治療費方面因受對方律師誤導而作出錯誤意思表示,但其并未為此進行充分舉證。綜上,駱某以重大誤解為由主張撤銷涉案《協議書》,理由不能成立,應不予支持。
●《協議書》不存在顯失公平的情形
涉案《協議書》簽訂之前,駱某已在專業人士的幫助下獲得對其可依法享受的工傷保險待遇項目及其數額的明確、直觀了解,《協議書》訂立之時,駱某并不存在緊迫或者缺乏經驗的情形,其對協議法律效果的相關重要事項應不存在認識上的顯著缺陷。
另外,將駱某前后仲裁請求數額與涉案《協議書》約定由服裝行支付款項的數額相對比,未見存在權利義務嚴重不對等的情形。雖然駱某的仲裁請求數額高于涉案《協議書》的約定數額,但相應差額可視為雙方以協議方式解決糾紛的情況下,駱某對其民事權利的自愿、合法處分。
此外,駱某所提仲裁請求數額尚未經由法定程序審查確認,駱某以此為據徑行主張《協議書》的約定數額屬于明顯不合理低價,理據不充分。
綜上,駱某以顯失公平為由主張撤銷涉案《協議書》,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
●關于請求服裝行協助申領一次性傷殘醫療補助金問題
《協議書》約定由服裝行向駱某支付的款項當中,已包含由工傷保險基金支付的一次性傷殘補助金、一次性工傷醫療補助金,相應約定對雙方均有法律約束力。在服裝行已履約付款的情況下,駱某又提請服裝行協助其向社會保險基金申領一次性傷殘醫療補助金,理據不足且不符合本案事實。
【實務指引】
對于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簽訂的“私了協議”,到底該如何確認其法律效力?
根據目前的司法實踐,“工傷私了協議”是否有效,應當根據不同的情形來具體認定。當用人單位違反國家的強制性規定,為規避法律法規的制裁,損害勞動者利益,欺詐或威脅勞動者簽訂的工傷協議,應當認定為無效;當事人按照雙方意思自治原則達成協議,用人單位給付勞動者的待遇不低于《工傷保險條例》規定標準的,該協議應當認定為有效。
那么,哪些情況屬于前述“規避法律法規的制裁,損害勞動者利益,欺詐或威脅勞動者”的情形呢?
《合同法》第五十四條規定,“下列合同,當事人一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一)因重大誤解訂立的;(二)在訂立合同時顯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受損害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三)》(法釋[2010]12號)第十條規定,勞動者與用人單位達成的協議存在重大誤解或顯失公平情形,當事人請求撤銷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68-72條的規定,上述情形是指:
“重大誤解”:行為人因對行為的性質、對方當事人,標的物的品種、質量、規格和數量等的錯誤認識,使行為的后果與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較大損失。
“顯失公平”:一方當事人利用優勢或者利用對方沒有經驗,致使雙方的權利與義務明顯違反公平、等價有償原則。
“欺詐”:一方當事人故意告知對方虛假情況,或者故意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當事人作出錯誤意思表示。
“脅迫”:以給公民及其親友的生命健康、榮譽、名譽、財產等造成損害,或者以給法人的榮譽、名譽、財產等造成損害為要挾,迫使對方作出違背真實的意思表示。
“乘人之危”:一方當事人乘對方處于危難之機,為牟取不正當利益,迫使對方作出不真實的意思表示,嚴重損害對方利益。
由此可見,如相關協議約定符合上述情形之一,當事人可以向仲裁委或法院請求撤銷。
對于“私了協議”的法律效力問題,各省市的司法實踐并不統一,主要在于對于上述協議可撤銷情形的具體認定標準各不相同。
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的《民事審判若干問題的解答》第五條規定,工傷事故發生后,勞資雙方就賠償數額達成協議并履行,事后勞動者反悔并申請仲裁、提起訴訟,經審查,不存在欺詐、顯失公平等情形的,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認可雙方簽訂的賠償協議的效力。
上述案例中,法院基本采納的也是廣州市的裁判觀點。但同樣的問題在江蘇省卻需要區分兩種情形對待。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勞動爭議案件審理指南(2010年)》第四章第二節第四項第3點規定,勞動者受到工傷,用人單位與勞動者達成賠償協議后,勞動者又提起仲裁和訴訟,要求用人單位按照工傷保險待遇賠付的,對該協議的效力應當區分情況處理。
如果賠償協議是在勞動者已認定工傷和評定傷殘等級的前提下簽訂,且不存在欺詐、脅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應認定有效;如果勞動者能舉證證明該協議存在重大誤解或顯失公平等情形,符合可變更或可撤銷情形的,可視情況作出處理。
如果賠償協議是在勞動者未經勞動行政部門認定工傷和評定傷殘等級的情形下簽訂,且勞動者實際所獲補償明顯低于法定工傷保險待遇標準的,可以變更或撤銷補償協議,裁決用人單位補充雙方協議低于工傷保險待遇的差額部分。
而同一問題在北京地區則有相對嚴格的認定規則。《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北京市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關于勞動爭議案件法律適用問題研討會會議紀要(一)》第30條第2款規定,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就工傷保險待遇達成的協議在履行終了后,勞動者以雙方商定的給付標準低于法定標準為由,在仲裁時效內請求用人單位按法定標準補足差額部分的,應予支持。
由此可見,工傷賠償“私了協議”的效力認定,在各省市都有不同的司法裁判觀點。用人單位如果希望與勞動者協商解決工傷賠償糾紛,建議在傷殘等級鑒定完成且各項賠償待遇明確后,雙方再自愿協商達成協議,最好通過各級調解機構形成調解書,以免在支付了賠償款項后再發生爭議和糾紛。
總之,對于工傷賠償“私了協議”,不應一概認定為無效,而應當根據不同情形來具體認定。
作者單位 廣東勝倫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