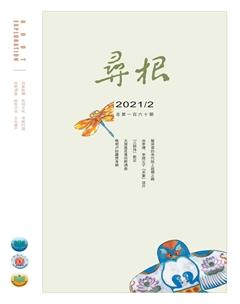“狗屁不通”出于前人作文評語
魏伯河
“狗屁不通”本是一句詈語,商務版《成語大詞典》的釋義是:“形容說話或寫文章在邏輯或語法上極不通順,也泛指對某些知識根本不懂,一竅不通。”詞典的解釋已延續多年,本無異議。但近年有人提出新解認為:“狗屁不通”其實是“狗皮不通”。其理由是:狗的皮膚沒有汗腺,酷夏時只能伸出舌頭來散發燥熱。由于“皮”與“屁”諧音,而屁又為污濁之物,于是對文理不通的詩文或不明事理的人,以屁貶之。后來人們將錯就錯,約定俗成地將“狗皮不通”說成了“狗屁不通”。此說本十分牽強,不足為訓。但個別媒體卻傳播了這種說法,又經過網絡的大量轉發,此說頗有眾口一詞之勢。
筆者以為,這一所謂“新解”并不能成立。
首先,如果說“狗屁不通”是“狗皮不通”之訛,那就應該先有按其本義使用“狗皮不通”的先例。但這樣的用例在上述新解之前卻不見于任何書籍和文字,新解提出者也未能舉出一例作為證明,可見此說實屬無中生有。
其次,“狗屁不通”的用例已見于清代石玉昆的《三俠五義》。如果“狗屁不通”是“狗皮不通”之訛,則“狗皮不通”的說法無論見不見于書典,都應產生于“狗屁不通”之前。但那時候,近代生物學和西方醫學都還沒有正式傳入中國,人們盡管知道狗皮可以保暖御寒,但是否知道狗皮沒有汗腺(事實上,狗皮并非沒有汗腺,只不過不太發達,又有長毛覆蓋,才在燥熱時借助舌頭散熱),大可懷疑。眾所周知,在比喻中,喻體必須是人們生活中的常見之物或易曉之理,否則便起不到比喻的作用。如果人們并不普遍具備狗皮沒有汗腺這樣的常識,“狗皮不通”就不可能成為俗語為人熟知,也就不會訛為“狗屁不通”。
最后,“狗皮不通”僅有“不通”一義,只是陳述了一種物理現象;“狗屁不通”則具有濃重的感情色彩,表現出強烈的反感、厭惡之情。二者均為貶義詞,但貶抑程度上差別很大,前者相對于后者,表現力大為遜色。
多年來,筆者對這一俗語的構成產生過不止一次的思考,因為“狗屁不通”作為一個整體本身就是矛盾的:如果“不通”,“狗屁”就不成其為狗屁;但既能約定俗成,又必定有其來源。后來,我逐漸體悟到:這一詈語的原始出處或許是過去先生對學生作文的批語,而且“狗屁”與“不通”最初應該是分別使用的,后來才連在一起。
先說“不通”。“不通”是日常用語,本義為阻塞、不通達,用來借指文理悖謬不順。學生初學作文,出現不合文理、邏輯混亂的句子是難免的。先生看到這樣的句子,往往用紅色直線標出,旁加批語曰“不通”,意為文理不通,以引起學生注意。有時這樣的句子接連出現,便會連寫幾個“不通”。還有那富有幽默感的先生,把批語用歇后語形式寫成“高山擂鼓——不通不通(“撲通”的諧音)”。客觀地說,這樣的批語雖然嚴厲,但還不屬于詈語。
再看“狗屁”。“狗屁”或“放狗屁”作為罵人胡說八道的詈語,日常生活中很常見,而且應該出現很早了。見于書籍的較早用例,如《儒林外史》第六回《鄉紳發病鬧船家,寡婦含冤控大伯》里大老爹罵仆人四斗子的話:“放狗屁!快替我去!來遲了,連你一頓嘴巴!”先生批改學生作文,見到其中的無知妄說,氣惱之下,把這樣的詈語拿來作為批語,斥之為“狗屁”或“放狗屁”,也是常有的。清人程世爵《笑林廣記》里說:“人之氣血,下行為順,上行為逆。屁者,谷氣下泄也。打胡說者,謂之屁;作謬文者,亦謂之屁:腐氣上行也。”還有的先生則更進一步,把“狗屁文章”區分為三等,謔而且虐,雖不足為訓,但卻可作為此類批語流行的旁證。如《笑林廣記》中的《學究批文》:
一學究與人看文,遇紕繆者,最喜批“放狗屁”三字。或勸之曰:“先生批文,何必用此批,太覺不雅。”先生曰:“此乃一等批。還有二等三等者。”或究其詳,先生說:“第一等是放狗屁,放狗屁者,人放狗屁也,尚有人言,不盡是狗屁;第二等是狗放屁,狗放屁時甚少,偶一放之,屁尚不多;第三等放屁狗,狗以屁名,簡直的全是狗屁也。”問者釋然。
“不通”與“狗屁”既然常被用作批語,有的先生把“狗屁”和“不通”連用,對認為十分悖謬——內容上既屬無知妄說、詞句上又格難通的文章徑直批為“狗屁不通”,也就不足為奇了。《三俠五義》里說“馮生聯句狗屁不通”,便是就馮生作詩對句過于拙劣而言,不過批評者不是先生,而是書的作者。
“狗屁不通”作為作文批語,事實上應該出現很早,使用頻率也不低,不過由于此語不雅,不會進入高雅詩文;曾被批為“狗屁不通”的作文,更不會傳播開來,因而在傳世文獻中難得一見。直到通俗小說流行之后,“狗屁不通”才進入書面文字,留下若干蛛絲馬跡。
如果此說可以成立,其中的內在矛盾也便迎刃而解了。“狗屁不通”的前后兩部分,即“狗屁”與“不通”二者之間,只是并列關系,并非主謂關系,更非因果關系,并不存在自相矛盾,也不存在以訛傳訛或將錯就錯的問題。某些愛鉆牛角尖的人,或許由于對這一俗語的前后關系不得確解,才挖空心思、別出心裁,把“狗屁”聯想到“狗皮”上面去。
作者單位:山東外事職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