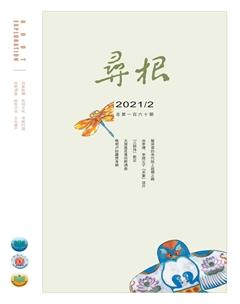宋槧本《清波雜志》刊刻年代及后世流傳考
趙健



國圖藏宋槧本《清波雜志》付梓于
嘉泰前后(1201-1207)
國家圖書館藏宋槧本《清波雜志》中并未注明成書年代,但根據文本中遺留的蛛絲馬跡,可推定大致刊刻于宋寧宗嘉泰前后。
該書后有天臺徐似道于“慶元戊午(慶元四年,1198年)立秋前一日”所書跋文:“余來中都,聞有所謂周處士昭禮《清波志》,急祈借傳錄,洪益處最多。”可見彼時尚無刻本流傳。倘或有之,則徐氏直接到書肆購買即可,無勞神費力地“祈借傳錄”之必要。
該書卷一“祖宗家法”條記述呂大防向哲宗開陳北宋的“祖宗家法”,其中有意空出29字,此29字為“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事,此待外戚之法也”。
為什么防范外戚弄權的話變得敏感甚至成為禁忌,不得不在槧本上“開天窗”呢?揆諸南宋史事,當與韓胄專政、發動“慶元黨禁”有關。
韓胄,字節夫,韓琦曾孫,以蔭入仕。娶高宗憲圣吳皇后侄女。歷門祗候、宣贊舍人、帶御器械。淳熙末,以汝州防御使知門事。憑借身份的特殊性,他在紹熙內禪中承擔了高層間串聯的工作,立下功勛。但內禪甫一完成,他即因對利益分配不滿,與趙汝愚分裂乃至對立。慶元元年(1195年),韓胄與京鏜等人合謀,成功排擠宰相趙汝愚,韓氏晉官保寧軍節度使。其又斥理學為偽學,起“慶元黨禁”,擊敗政敵,一手總攬朝政,累拜太師,封平原郡王,授平章軍國事。韓氏后見金朝勢弱,遂籌劃北伐。起用主戰派官員,追封岳飛,追貶秦檜。開禧二年(1206年),兵分三路,大舉伐金。因軍事準備不充分,北伐不久即遭挫敗。次年,韓胄被禮部侍郎史彌遠與楊皇后等人合謀誅殺。
當韓胄用事時,“群小阿附,勢焰熏灼。胄凡所欲為,宰執惕息不敢為異”。在這種情勢下,再提防范外戚弄權的“祖宗家法”,既顯得不合時宜,恐怕又有現實的政治風險。韓胄被害之后,宋廷不僅應金人的要求斫棺取出韓氏的首級奉上,還“詔史官改紹熙以來韓胄事跡”,官方宣傳為之一變。此后至南宋滅亡,外戚弄權之事不再。防范外戚專權的話頭又屢屢被提及,如刊刻于嘉定十一年(1218年)的《致堂讀史管見》卷十七中就唐太宗任命長孫無忌為宰相事發議論說“以外戚則不當與朝權”,并無前時的避忌。
此外,還可從避諱的角度推測槧本《清波雜志》的刊刻時間。今傳紹定三年(1230年)重刊本《禮部韻略》中所附“淳熙重修文書式”,列舉了截至宋理宗以前的兩宋諸帝應避舊諱及嫌名。槧本《清波雜志》避諱的情況如下表。兩相對照,槧本《清波雜志》并未嚴格按照紹定三年的規定避諱。這既有無須避而避的情況,如為避宣祖諱而將“殷”字缺筆,為避仁宗諱而將“懲”字缺筆,為避孝宗舊諱將“瑗”字作“爰”,也有按規定當避而未避的現象,如“屬”字犯英宗諱,“慎”字犯孝宗諱,“郭”字犯寧宗諱。導致此現象的最可能原因,當是該書刊刻的時間在紹定三年之前,彼時關于避諱的規定,并不完善或與后來不同。
當然,制度的規定是一回事,實際的執行可能又是另外一回事,在古代的人治社會,兩者完全有可能脫節。不過好在我們還可以通過對南宋出版業中避諱實際執行情況的對比,發現實踐中發揮作用的“實質”規則的變遷。
慶元六年(1200年)紹興府刻宋元遞修本《春秋左傳正義》卷二十四中,對于孝宗舊諱“瑗”,是通過缺筆來避諱的,但不避“郭”字;而嘉定十一年(1218年)衡陽郡齋刻本的《致堂讀史管見》中,不避“瑗”字,而“郭”字已經通過缺筆來避諱了。所以,從槧本《清波雜志》將“瑗”字改作“爰”,且不避“郭”字的情形來看,其問世于慶元六年至嘉定十一年間的可能性最大。
綜上,國圖藏宋槧本《清波雜志》的刊刻時間,當在韓胄專權的嘉泰前后(1201-1207)。
國圖藏宋槧本《清波雜志》在后世的流傳情況
根據國圖藏宋槧本《清波雜志》上的藏書印,可大致梳理出其自明代起有序流傳的情況。
該書自南宋問世以后,經元迄明代中期一直隱而不現。首先發現該書的人,很可能是生活于明中期的童佩。在該書卷一首頁版心右側上半葉中部兩欄下方空白處、卷七首兩欄右下方、卷十二尾頁版心左側下半葉左四五欄中部稍下處、跋語末兩欄下部,均鈐有“童氏藏書”朱印。
童佩,字子鳴,龍游縣人。其父童彥清是往來吳越之間的書商,童佩自幼就隨父親販書于蘇州、杭州、常州、無錫等地,后來又繼承父業販書為生。雖然家業僅有“薄田數十畝”,但得益于販書生涯的近水樓臺,他積累了數量眾多的善本書,“藏書數萬卷,皆手自讎校”。胡應麟見過他的藏書目錄后,稱贊說:“得足下藏書目閱之,所臚列經史子集皆犁然會心,令人手舞足蹈。”
童氏藏書目錄現已不存,后人所輯童氏遺著《童子鳴集》亦無藏書狀況的記載,目前尚難以坐實該藏書章主人即為童佩。但鑒于童佩經歷的特殊性與該朱印尺寸頗大、刻工簡率,“童氏藏書”為童佩藏書印的可能性極大。
明末的焦,是有確鑿證據的該書的最早收藏者。
焦,字弱侯,江寧人。萬歷十七年(1589年)會試,得中狀元,先后授翰林院修撰、皇長子侍讀等職。焦知天命時方步入仕途,按理應該老成,但由于個性鮮明,此后的遭際卻并不順利。《明史》說:“既負重名,性復疏直,時事有不可,輒形之言論,政府亦惡之。二十五年主順天鄉試,舉子曹蕃等九人文多險誕語,被劾,謫福寧州同知。歲余大計,復鐫秩,遂不出。”
雖然仕途不盡如人意,但焦的學問大是舉世皆知的,《明史》評價他:“博極群書,自經史至稗官、雜說,無不淹貫。”他愛讀書,也愛藏書,多年的積累,使他成為晚明著名的私人藏書家。
焦藏書,以抄本和宋明刊本居多。焦曾編有兩卷本的《焦氏藏書目》,惜今已不傳。其藏書樓有“澹園”“竹浪齋”“欣賞齋”等。國圖藏宋槧本《清波雜志》卷首張貴謨序頁首兩欄下方、卷七首兩欄中部靠下處,均鈐有“欣賞齋書畫記”朱印。此外,在《焦氏筆乘》卷八中,焦還曾抄錄《清波雜志》中的四條記載。
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焦去世后,該書為徐乾學所得,在張貴謨序頁焦“欣賞齋書畫記”朱印之下,有“昆山徐氏家藏”朱印。在目錄首頁首兩欄下方,有“乾學之印”“健”兩方白印。
徐乾學,字原一,號健庵,昆山人,清初大儒顧炎武外甥,與弟徐元文、徐秉義并稱“昆山三徐”。徐乾學于康熙九年(1670年)中探花,授編修,先后擔任日講起居注官、《明史》總裁官、侍講學士、內閣學士、左都御史、刑部尚書等職。曾主持編修《明史》《大清一統志》《讀禮通考》等。其私人藏書的“傳是樓”,為清代著名的藏書樓。徐乾學著有《傳是樓書目》,其中記載“清波雜志十二卷,又別志三卷,周輝,四本抄本,又一部,一本抄本”。可能當時徐氏編此書目時,尚未得到《清波雜志》的宋槧本,故而失于記載。
今國圖藏宋槧本《清波雜志》接下來的收藏者,是活躍于嘉慶、道光年間的汪士鐘。汪士鐘,字春霆,號閬源。該書周輝自序頁首欄上部、跋文末頁末欄下方,分別鈐有“平陽汪氏藏書印”朱印。目錄、卷四、卷七、卷十首頁首欄分別鈐有“汪士鐘印”白印、“閬源真賞”朱印。
汪士鐘之父汪文琛,因經營“益美布號”,富甲一方,且熱衷藏書。汪士鐘繼述父志,不惜重金,廣搜博取。當時江南四大著名藏書家黃丕烈、周錫瓚、顧之逵、袁廷,藏書均以精博稱,所藏之書后均歸于汪氏門下。汪士鐘建起藏書樓“藝蕓書舍”,藏書為當時海內之首。汪氏曾編《藝蕓書舍宋元本書目》,內載“清波雜志? 十二卷”。
藝蕓書舍雖煊赫一時,但在汪士鐘歿后,隨即衰敗。同治《蘇州府志》記載:“觀察(汪士鐘)多子,身后兄弟瓜分,家亦落,其書始散。經庚申之亂,掃地盡矣。其為罟里村瞿氏所得者,十之一二也。”
槧本《清波雜志》自序頁首欄最下方,卷四、卷七第一頁版心左側下半葉首欄,卷十首頁右第七欄下方空白處,有汪士鐘族人汪憲奎藏印二方,分別為陰文“憲奎”、陽文“秋浦”。卷第十二末兩欄下部鈐有“平江汪憲奎秋浦印記”白印。汪憲奎生平失考,或為汪士鐘之子。
藝蕓書舍所藏,日后為瞿氏所得者,即包括宋槧本《清波雜志》。該書此后便轉入大名鼎鼎的瞿氏鐵琴銅劍樓。在卷首張貴謨序頁首欄天頭處鈐有“鐵琴銅劍樓”,首欄下部及左側下半葉末欄下部鈐有“瞿氏秘笈”朱印。在周輝自序頁首欄,鈐有“鐵琴銅劍樓”“紹基秘笈”“瞿潤印”“瞿秉淵印”四方白印,右第五欄下方有“良士眼福”白印。卷四首頁首欄、卷七首頁邊框右下方、卷十首頁首欄、跋語尾頁下半葉左第二欄下方,均鈐有“瞿氏秘笈”朱印。跋語尾頁下半葉末欄上部鈐有“鐵琴銅劍樓”白印。
清末民初,該書又轉入王綬珊手中。王綬珊,名體仁,字綬珊,紹興人,清末秀才。遷居杭州,辛亥以后居上海。王氏以經營鹽業起家,嗜典籍,筑九峰舊廬于杭州。
在宋槧本《清波雜志》自序頁,卷四、卷七、卷十首頁,首兩欄天頭處均鈐有“杭州王氏九峰舊廬藏書之章”朱印,首欄均鈐有“綬珊經眼”白印。
該書最后經手的私人藏書家,為周暹。周暹,字叔,著名藏書家,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天津市副市長等職。在宋槧本《清波雜志》的目錄頁首欄、自序頁首欄、卷四首欄、卷十首欄、卷十二末欄,均鈐有“周暹”白文篆字小方印。
這方小小的印章,承載著藏書人濃濃的愛書之情。李堅《周叔先生捐贈給國圖的善本》一文記載:“出于對書的珍愛,周先生用印十分慎重。他早年用過一長方陽文的‘曾在周叔處的圖章,后來在善本書上就只用一枚方形‘周暹兩字白文小印,而且都蓋在書的空白處。此印是童大年刻的,選用這方印并不是因為它特別好,而是因為它小,如果后來的藏書人不喜歡,可以挖掉,不致損書過甚。他用印泥也十分審慎,唯恐把印鈐在書上滲油或變色而損害書籍。幾十年來,他在善本書上鈐印用的是他二十幾歲時在西泠印社買的印泥,經過半個多世紀試驗,它不滲油也不變色。后來又買過多種高價印泥,因未經試驗,始終不敢用在好書上。”
1952年,周叔先生這本宋槧本《清波雜志》和另外715種珍善古籍一并捐給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實現了“珠還合浦,化私為公”的愿望。
作者單位:九三學社深圳市委員會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