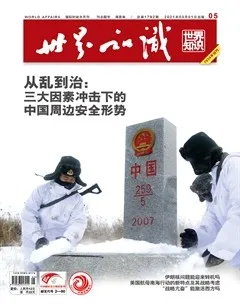地區主要大國關系:“兩冷一熱一平穩”
長期以來,區域內的四組主要大國關系不僅直接影響雙邊關系,而且塑造著區域、次區域的安全局勢。2020年,四組大國關系表現為“兩冷一熱一平穩”。
中美關系進入全面戰略競爭
2020年,美國全方位加大施壓中國力度。在地區層面,美國持續推進“印太戰略”,試圖重構地區新秩序,遏制中國,維護自身的地區主導地位。在意識形態方面,美國把疫情政治化、病毒標簽化,攻擊中國的政治體制和中國共產黨,稱中國政府和世界衛生組織未及時公布相關信息,導致疫情全球大流行;利用疫情追責索賠等問題在國際上煽動對華敵意,加大地區國家對中國的質疑和指責。同時,美國還利用臺灣、香港、新疆和西藏等問題干涉中國內政。在安全領域,美國以臺海、南海等熱點問題為抓手,重點依托“美日印澳四邊對話”,通過信息共享與演習來構建基于盟友與伙伴關系的“網絡化”的地區安全架構。2020年9月,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赴日參加“四邊對話”第二次部長級會議之際,提出打造印太版小北約的建議,塑造地區“新冷戰”格局的意圖昭然若揭。雖然這一提議未能得到日印澳三國的公開響應,但是四國間的雙邊、小三邊安全關系卻在不斷強化。在經濟領域,美國繼2019年提出“藍點網絡計劃”后,又在2020年推出“經濟繁榮網絡”,將對華競爭從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擴大到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試圖形成一個由美國主導的、“去中國化”的地區經濟新秩序。
為推動上述戰略的落實,2020年,蓬佩奧不僅利用東盟地區論壇等一系列地區對話平臺,就南海爭端、非傳統安全等議題隔空挑釁中國,而且還在下半年密集、臨時性出訪東北亞、東南亞和南亞國家,試圖糾集反華同盟。2021年初,美國新任國務卿布林肯先后與韓國、澳大利亞、菲律賓等盟友進行電話外交,確認將繼續實施“印太戰略”,并強調盟友關系對于美國維護地區秩序的重要作用。
就實際成效而言,美國“印太戰略”的落實具有明顯的不平衡性。一方面,無論是美軍在西太平洋上的耀武揚威,還是依托于盟友的安全網絡構建,都表明美國仍在地區安全事務中占有顯著優勢。而另一方面,美國的經濟政策雖然不乏推陳出新,但基本仍是“雷聲大雨點小”,進展有限。這在相當程度上是特朗普政府過度強調“美國優先”并四面出擊實施“貿易戰”所致。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不僅實現了自身經濟增速的正增長,而且基本保持了與周邊國家良好的經貿與投資關系,為地區乃至全球經濟復蘇注入了強大動能,提供了巨大市場。
中俄關系保持高位運行
受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油價下跌、結構失衡、西方制裁等因素的影響,俄羅斯經濟在2020年遭受嚴重打擊,前蘇聯空間出現白俄羅斯總統選舉風波、納卡地區武裝沖突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美俄關系在短期內難有起色,從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國始終將俄羅斯作為競爭對手,保持著對俄嚴厲制裁措施;在歐洲方向,俄羅斯的戰略利益空間也受到持續擠壓。鑒于此,俄羅斯繼續強化其東方外交,特別是加強與中國的戰略協同。
2020年,中俄關系仍然保持高位運行。首腦外交互動頻繁,習近平主席與普京總統年內通話五次,雙方表示愿意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更深層次加強合作,推動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高水平發展。由首腦外交引領,中俄雙方在經濟、安全和科技領域的合作穩步發展,雙邊貿易額在2020年疫情肆虐的情況下仍然保持在1000億美元以上。9月,中國參加了“高加索-2020”戰略演習,這是俄軍年度計劃內的最大規模演習。在國際事務方面中俄雙方戰略協調合作持續深化,正如2021年初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所說,中俄戰略合作沒有止境、沒有禁區、沒有上限。一些學者也指出,面對美國咄咄逼人的遏制,中俄“背靠背”的選擇是必要的。

2021年1月20日拜登偕夫人走向白宮就任美國總統。拜登新政府確認將繼續實施“印太戰略”,并強調盟友關系對于美國維護地區秩序的重要作用。
但近年來俄羅斯的對華意圖以及中俄關系的諸多戰略不平衡性也值得中國審慎對待。俄羅斯具有謀求中方深度參與美俄對抗的意圖。同時,中俄雙方在國力發展、外交謀略、經貿合作等領域的不平衡性仍然呈不斷擴大趨勢,俄羅斯在世界經濟、全球治理領域的地位全面下降,其外交成就主要依靠的是外交手段、政治經驗和軍事力量。從歷史經驗來看,中俄關系應在堅持“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的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靈活應對雙邊和國際事務。
中日關系維持平穩狀態
日本雖然受到新冠疫情的重創并經歷了政府更迭,但日本外交政策的調整更多受到中美戰略博弈的影響。中日關系雖然高開低走,但基本延續了自2019年以來的向好狀態。不過,日本的對華政策具有顯著的“二元態勢”。一方面,中日構建“契合新時代中日關系”的政治共識得到維持,日本首相菅義偉上臺后公開表示,在繼承安倍外交路線的前提下,繼續致力于與中國等鄰國建立穩定關系。在經濟與疫情防控領域,中日雙方依托“10+3”(東盟+中日韓)機制與東南亞國家開展抗疫合作,并在2020年底促成RCEP的簽署,使其成為區域合作的主要推動力。另一方面,中日在意識形態領域與安全領域的對抗態勢沒有根本性改觀。雙方在釣魚島問題、南海問題上時有摩擦,日本國內的對華民意持續走低,這反映出中日關系中存在著長期的結構性矛盾。日本試圖保持安全上依賴美國、經濟上加強對華合作的平衡政策,但總體上,追隨美國仍優先于對華協調合作。需要強調的是,盡管美國對日脅迫力度加大,但日本還是試圖避免直接挑釁中國,突出表現為對蓬佩奧拋出的將“四邊對話”機制打造成“印太版北約”的提議并未作出公開回應。同時,日本還積極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的合作,加強與印度和澳大利亞的雙邊外交與防務合作,試圖借此提升自身影響力,成為中美戰略競爭中的第三種關鍵性力量。其目的正如日本戰略學界所指出的,在美國戰略收縮乃至放棄國際責任的情況下,日本應大力聯合其他民主國家,替代美國的領導作用,將“印太戰略”打造為“新的多極化構想基礎”。
中印關系顯著惡化
2020年是中印建交70周年,但是受加勒萬河谷嚴重肢體沖突、邊境對峙多點爆發等因素的影響,中印關系降至1962年以來的最低點,印度開始全面推行對華強硬政策。
中印邊境沖突發生后,印度國內反華情緒高漲,涉華輿論全面負面化,甚至發起持續的“抵制中國貨”運動。莫迪政府在經貿投資領域試圖與中國脫鉤,通過修改外商投資政策限制中國投資。從2020年6月開始,莫迪政府先后四次以所謂“國家安全”為借口對中國手機應用程序發布禁用令,試圖打擊中國“數字絲綢之路”的建設;同時推出“自力更生的印度”運動,呼應美國的“脫鉤論”,從而減少對華依賴。
在地區層面,印度積極“擁抱”“美日印澳四邊對話”,其中最具標志性的是,印度接受了澳大利亞時隔13年重返聯合軍演的申請,美日印澳四國于2020年11月聯合舉行了新一輪“馬拉巴爾”海上軍事演習,這被認為標志著“四邊對話”的軍事合作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盡管其可持續性仍有待觀察。在“四邊對話”框架下,印度還顯著提升與美日澳三國的雙邊關系,包括建立印美“全面全球戰略伙伴關系”、印澳“全面戰略伙伴關系”以及印日“特殊戰略和全球伙伴關系”,各方均以安全領域為合作重點。其中,隨著印美雙方在2020年10月簽署《基本交換與合作協議》(BECA),印美已經基本達到盟友關系。有分析指出《基本交換與合作協議》加上印美已經達成的《一般軍事信息安全協議》《后勤交流協定備忘錄》《通訊兼容和安全協議》(COMCASA)的內容,正是美國與北約盟國之間安全關系的重要支撐。
四組大國關系對中國周邊安全形勢的影響是有差別的,中美關系所占權重最大,且仍然在上升之中。中美雙方圍繞地區秩序主導權展開的博弈具有長期性和全方位的影響,很大程度上將決定周邊地區秩序未來的發展方向。俄羅斯是中國最大的鄰國,當前俄羅斯對中國周邊的影響力主要集中在東北亞和中亞地區,對于東南亞地區事務的參與則相對有限。日本是“中美夾縫中的第三方力量”,中日關系無論是在雙邊層面還是地區層面都非常復雜,對抗與合作并存,中國需要重視日本的戰略主動性,積極尋找合作機遇。在中印之間,邊境沖突改變了印度對中國的戰略認知,而印度的“轉向”對于美國的“印太戰略”可謂是“及時雨”,因為美國一直極力拉攏印度,試圖通過抬高印度在印太地區事務中的地位,在中國周邊形成更為閉合的“包圍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