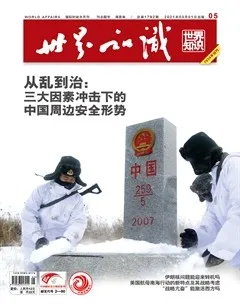新加坡在中美之間的平衡外交進入更艱難階段
許利平
2021年1月29日,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議程”對話會上發表視頻演講時,對中美關系表達了擔憂,強調“中國不是蘇聯”,用冷戰思維對付中國行不通;如果中美兩國不合作且允許彼此關系繼續惡化成全面對抗關系,將無法解決大流行病、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整個世界都將步入“冷戰熱斗”,中美及其他多國也會長期陷在“艱難時刻”里。李顯龍并表示,新加坡將主辦世界經濟論壇特別年會(原定今年5月舉行,后推遲至8月),希望能為中美高官會晤提供場所。
李顯龍關于中美關系的最新評論再次體現了新加坡面對中美緊張關系的焦慮心態。一向在中美之間長袖善舞的新加坡,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加速調整的中美關系,實施平衡術顯得越來越困難。
小國外交的“大國平衡”傳統
1965年,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艱難建國。在一個國土面積僅數百平方公里的彈丸之地,缺乏基本的自然資源,缺少經濟發展的腹地,種族矛盾如影隨形,新加坡的自立之路并不好走。然而新加坡走出了一條不平凡的路。1960年新人均GDP僅為400美元,2020年突破6萬美元,創造了東亞的一個奇跡。新加坡的成功靠的是自身的危機意識、開放意識、創新意識,也離不開外交上的“大國平衡”戰略。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照片攝于2020年12月1日新加坡最高法院門前。
“大國平衡”是新加坡現實主義外交理念的重要體現,也是這個國家一個重要的“生存原則”。李光耀作為新加坡的開國總理,認為新要生存下去,必須努力同各大國均衡發展關系。在李光耀看來,大國在東南亞的存在對新加坡十分有利:政治上,促使大國持續關注東南亞,增加對新加坡的了解,并向新提供支持;經濟上,可使新獲得更多資金、技術和貿易支持;安全上,如果新能夠與所有大國保持密切的對話與合作,沒有哪個大國敢冒然侵犯新。
冷戰以后,新加坡通過嫻熟的“大國平衡”戰略,在中美之間扮演著重要的橋梁角色,同時獲得中美兩國的認可。總體來看,新加坡在擁抱經濟全球化的同時,安全上得到美國的保護,經濟上收獲中國大市場的準入權,享受著中美關系持續發展的紅利,從此一路高歌猛進,完美演繹著小國的獨特生存之道。
重陷中美夾縫的新加坡
進入21世紀,隨著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群體性崛起,“東升西降”成為重要的時代趨勢,地區格局乃至全球秩序發生歷史性變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新興經濟體群體性崛起、特別是中國的崛起越來越不適應,日益感到焦慮。它們仍以固定思維看待東方,甚至用冷戰思維定位東西方關系。
在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政府視中國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在貿易、科技、教育、人權等領域進行全方位打壓和遏制,中美關系滑向對立乃至沖突的邊緣,這對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無疑是一場噩夢。2019年8月18日,李顯龍在新加坡國慶群眾大會演講時說,倘若中美無法建立互信,世界將繼續分化,新加坡經濟增長將受累,前景會變得更加暗淡。當時,由于特朗普政府推行所謂“脫鉤論”,中美貿易摩擦極為尖銳,加劇全球貿易和商業活動萎縮,并對新加坡的產業鏈和供應鏈產生影響,這個外向型經濟體遭遇“寒冬”。2019年,新加坡全年經濟增長率僅為0.7%,創下十年最低水平。
動蕩的中美關系對新加坡來說絕非好消息。2020年7月28日,李顯龍參加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線上視頻座談會時強調,希望美國下任總統能建立穩定的對外關系,特別要穩定與中國的關系。李顯龍還呼吁美重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美退出后在日本協調下升級為《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即CPTPP)。李顯龍進一步指出,亞洲地區的長期穩定和繁榮建立在穩定的中美關系基礎之上。
中美作為全球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對新加坡經濟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2020年,盡管全球需求受新冠疫情影響深重,美國和中國仍然成為新加坡非石油產品出口的前兩大市場。根據2021年2月新加坡企業發展局發布的報告,2020年新加坡出口到美國的非石油產品強勁增長38.3%,總額達299億新元,美成為新最大的非石油產品出口市場(主因是新加坡生物醫藥產品對美出口顯著增長),而同期新加坡出口到中國的非石油產品總額為264億新元。隨著經濟復蘇的推進,中國將超越美國重新成為新加坡非石油產品出口的最大市場。
根據新加坡貿易和工業部今年2月15日發布的報告,新加坡2020年經濟下滑5.4%,是獨立以來表現最差的一年。為了應對疫情,新加坡推出了總額675億美元的刺激計劃,并且動用了部分外匯儲備。2021年新加坡將罕見地出現預算赤字,估計額度將占新GDP的2.1%~4%。預計2021年新加坡經濟將增長4%~6%。為完成這些目標,新加坡同時與中美兩國加強經濟合作十分必要。中國作為2020年全球唯一經濟保持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對2021年全球經濟復蘇起著重要的牽引作用,對新加坡也不例外。李顯龍多次強調穩定中美關系的重要性,首要考慮是給新加坡經濟發展一個明確預期。
兼具內政考慮
同時也應看到,李顯龍不斷就中美關系發表談話,也有國內政治的考量。一定程度上講,是為了在選民面前塑造人民行動黨的權威、專業形象,以及面對紛繁復雜國際變局的洞察力和領導力。在2020年7月10日的新加坡大選中,執政的人民行動黨獲得61.24%的支持率,低于2015年大選時的69.9%支持率。幾乎在所有選區,人民行動黨的支持率都在下降,甚至在蔡厝港集選區支持率暴跌17%,成為新加坡建國以來執政黨取得的第二差成績。而最大的反對黨工人黨同時獲得了兩個集選區和一個單選區的勝利,斬獲十個國會議席,比2015年大選增加六個,取得歷史最好成績。為此,新國會首次設立反對黨領袖職位。
2020年大選折射出新加坡內政的一些矛盾,比如對政府的監督和制衡問題突出,貧富差距和階層固化日益嚴重,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社會福利水平停滯不前,外來人口對新本土勞動力市場沖擊越來越大,等等。對于國土狹小的新加坡來說,要想解決這些問題,可利用的工具不多,需要從外部尋找突破口,而作為世界前兩大經濟體的美國和中國就是這樣的突破口。
李顯龍多次承諾,將把權力交給“第五代領導人”,但何時移交還不得而知。面臨國際新格局,對于不斷在中美之間艱難搞平衡的新加坡領導人來說,其實穿梭空間并不大。根據2月10日新加坡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東盟研究中心發布的“東南亞態勢”報告,“受訪者普遍認為,中國是疫情中給予本區域最多援助的國家,但東南亞對中國的不信任度連續三年增加,對美國的信任度則隨著拜登的上任而恢復增長”。
面對中美兩國在東南亞地區乃至全球影響力的此長彼消,新加坡可能很難再像以前那樣游刃有余地搞平衡了。因為,中美兩國的實力對比本身就在趨向“平衡”,新的地區均勢也在形成。新加坡既不能選邊站隊,又難兩面下注。需要對外交政策做出什么樣的調整,不僅考驗著當下新加坡領導人的智慧和決斷力,更是擺在未來新加坡領導人面前的重大課題。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