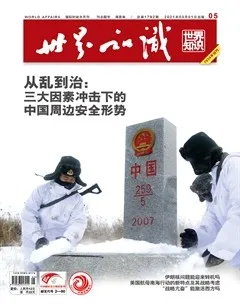美俄延長《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的考量及影響
李喆??羅曦
2021年1月26日,剛就任美國總統僅一周的拜登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通了電話,確認美俄就延長《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New START)達成一致。隨即,兩國以互換外交照會的方式確認將該條約延長五年,有效期至2026年2月5日。
《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作為目前美俄之間僅存的雙邊核軍控條約,其續簽直接影響全球戰略穩定與核軍控機制的前景,短期看完成了核軍備競賽邊緣的一次“懸崖勒馬”,給國際核不擴散機制“打了一針強心劑”。但長遠看,續約更像是兩國從維護自身利益出發進行的“戰略妥協”,未能從根本上改善核軍控機制。
續約背后的精打細算
雙方此次續約用時短、效率高,俄方還專門加快進程,其議會上下兩院通過快速程序對延長條約予以批準。不過,兩國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外交策略調整最大限度地滿足國家利益現實需求。
續約是基于對本國經濟總體狀況的擔憂。2020年,美國受國內政治撕裂、疫情快速蔓延等因素影響,經濟嚴重下滑;俄同樣不樂觀,受疫情及西方經濟制裁影響,經濟下滑態勢愈發明顯。過去一年,美俄國內生產總值(GDP)均出現負增長,也因此無力和無意展開新一輪軍備競賽。
續簽是基于維持全球戰略穩定的需要。繼小布什政府2002年退出《反導條約》、特朗普政府2019年退出《中導條約》之后,美俄之間的戰略武器研發比拼愈演愈烈,自覺不自覺地陷入“安全困境”,一方在戰略武器研發、部署方面的進展會刺激另一方追求以相同或不同方式予以回應。續約將美俄重新拉回戰略穩定框架,為接下來約束對方戰略武器發展提供了前提條件。
續約也是出于扭轉外交局面的考慮。拜登入主白宮后,急欲與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拉開距離,希望通過更加積極的外交姿態和“重回朋友圈”行動贏回國際社會對美國的“信任”與“尊敬”,作為核大國“戰略穩定器”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無疑是其打開外交局面的有力抓手。反觀俄羅斯,“北溪2號”天然氣管線建設在美重重打壓之下受阻后,普京政府更清醒地認識到,無論是在政治還是經濟層面,俄都需在美新一任政府上臺后盡快緩和對美關系。另一方面,俄的“大國情結”促使其需要通過與美對等談判的方式凸顯傳統大國地位,核軍控談判提供了天然的契機。
新約談判道阻且長
《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重點在于對戰略核武器及其運載工具進行數量限制,其所囊括的武器選項相對局限。相較于美俄各自手中的“底牌”而言,條約內容已不能滿足維持戰略穩定的需要。要想進一步有效推動核軍控、核裁軍,簽訂新條約、擴充削減內容是唯一選項。未來,美俄或將就新版條約展開談判。
新型戰略武器研發進展將是新約談判啟動的重要背景。俄近年在新型戰略武器領域突飛猛進,先后研發出“薩爾馬特”洲際彈道導彈、“先鋒”“匕首”高超聲速導彈、“波塞冬”核動力魚雷、“海燕”核動力巡航導彈等。這些進展為俄突破美導彈防御系統提供了更多手段,核常一體的設計更為其拓寬“威懾頻譜”提供了空間。目前,俄方已主動表示愿將“先鋒”高超聲速導彈和“薩爾瑪特”洲際彈道導彈納入新約談判。鑒于此,美俄啟動新約談判有可能以新型戰略武器談判為突破口逐步展開。不過,由于美在相關領域已落后于俄,且俄不愿將“波塞冬”核動力魚雷、“海燕”核動力巡航導彈等納入新約,未來美俄必將圍繞新型戰略武器限制展開激烈且持久的拉鋸。
反導系統限制將是新約談判焦點之一。反導系統雖不屬于進攻型戰略武器,但鑒于其對核武器運載工具構成的強大防御能力,無疑是影響美俄戰略穩定的關鍵因素之一。對俄而言,“以己之矛克彼之盾”的戰略思維要想落地,最急切的需要是對美在全球部署反導系統的行為進行限制。鑒于俄近些年在進攻型戰略武器方面取得了快速突破,其已具備與美就反導系統限制問題展開談判的籌碼,未來核軍控領域“矛與盾”的博弈或將有所突破。

1972年5月26日,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同美國總統尼克松在莫斯科簽署《限制反彈道導彈系統條約》。

2010年4月8日,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杰夫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簽署《新削減戰略核武器條約》。
新約談判也會關注戰術核武器問題。出于對俄戰術核武器的擔憂,特朗普政府曾積極推動核武器小型化、低檔量化改造,并聲稱此舉意在充裕美自身威懾選項并提升“核門檻”。2019年底,美確認已在“三叉戟ⅡD5”潛射彈道導彈上部署W76-2型戰術核彈頭。國際社會圍繞戰術核武器展開的爭論再次甚囂塵上,戰術核武器“能不能用”以及“怎么用”等問題重回視野。目前看,美俄對對方的戰術核武器都有所忌憚,美擔心俄數量眾多的戰術核武器威脅其歐洲盟友,俄則對美風生水起的核武器小型化、戰術化改造深感憂慮。面對戰術核武器使用門檻降低的現實,雙方在相互苛責的同時,也都認為對方在未來一場危機或沖突中使用戰術核武器的可能性漸增。為了更好地明晰核武器研發及使用邊界,戰術核武器問題極可能進入下輪談判進程。
美俄核軍控走向
《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的延長暫時緩和了美俄螺旋上升的核對峙態勢,為雙方下步核軍控談判提供了五年的“時間窗口”。除上述在新約談判過程中可能突出的爭議點,未來幾年美俄核軍控進程本身還將呈現以下三方面趨勢。
第一,美或重提“無核世界”。作為時任總統奧巴馬的副手,拜登的核政策理念與奧巴馬一脈相承。綜合考慮其在擔任副總統及國會參議員時關于核軍控、核裁軍的言論,可以初步判斷,拜登有可能重新倡導全球普遍削核,不排除重啟中斷多年的核安全峰會,通過建制派手段規制有核國家。
第二,美俄嘗試構建“多邊核軍控機制”。隨著中國在軍事領域不斷取得突破和進展,美為從國際機制層面規制中國,已多次通過外交手段嘗試將中國強行拉入美俄核軍控談判進程,構建美俄中“三邊核軍控機制”。同時,俄對英、法近年在核武領域取得的進展疑慮漸增,其也會嘗試拉這兩個國家入局。
第三,維持核武器現代化與核軍控“同頻共振”。美俄正如火如荼地對其核武器及運載工具系統進行迭代升級,以期在保持核威懾的同時,完成核力量“由多向精”的轉型。此類工程耗時長、困難多、花費大,是未來幾十年美俄核武發展的重點。美俄在未來核軍控談判中或有意避開“雷區”,使談判無論從軍備發展層面還是國內政治層面均可服務于其核武器現代化進程。
目前看,太空武器、網絡技術、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尚不會成為美俄軍控談判的主要關注點,未來談判除了需考慮擴充戰略武器限制選項、滿足核武現代化需求、配合國內政治外,還會更多考慮時間因素。這是因為,無論是拜登還是普京,在2024年都將面臨離任或政府換屆的可能,屆時如雙方仍未就簽署新約達成有效共識,談判進程的不確定性將顯著增加。因而,美俄有必要擬定時間表,在看似寬裕、實則緊迫的“窗口期”內盡可能多地展開磋商。
(作者分別為軍事科學院戰爭研究所研究實習員、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