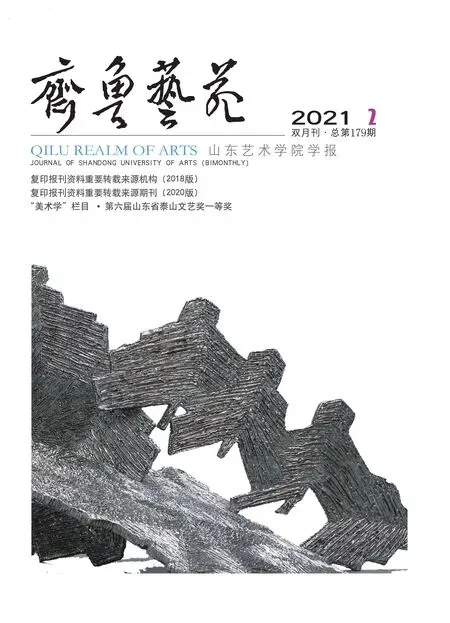俄羅斯圣像畫藝術的歷史發展和影響
王 鵬
(山東大學藝術學院,山東 濟南 250100)
圣像畫、教堂壁畫、馬賽克鑲嵌畫是早期基督教教堂繪畫藝術的主要表現形式,具有裝飾教堂、看圖識史、教化世俗、引領精神參與等多種功能。教堂藝術是可視的、是精神信仰的物化表現。本文所涉及的圣像畫主要指從羅斯(1)關于“羅斯”一詞:現代學者并沒有對如何出現“羅斯”一詞做出統一答案。但公認的是“羅斯”是現代俄羅斯民族的宗族。大多數研究人員指出,最初的羅斯是對一個民族或者部落的稱呼,根據相似程度與楚德人(古羅斯時期對西部芬蘭部落的總稱), весь和Kors部落有關。12世紀的文獻記載著862年發生的事件:“他們繞過大海前往瓦蘭吉人(古羅斯對來自北歐諾爾曼人的稱呼)那里,再到羅斯人的地方。這些瓦蘭吉人自稱羅斯,并且另一部分瓦蘭吉人稱為瑞典人。對于這一相關問題在882年的文獻中記載:“奧列格大公在位,在基輔,奧列格說:是的,就讓基輔成為羅斯城市之母。”當時同時在一起的有瓦蘭吉人,斯拉夫人和其他叫做羅斯的人。德米特里·利哈切夫院士強調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僅僅是“其他人”被稱作羅斯人還是所有人一起。還有一種說法是最初“羅斯”一詞是河流的名稱,與“河道”有關,該詞匯可能意味著河流從中流過。因為自東部斯拉夫人沿河定居以來,他們稱自己為“河流”民族,就像貝都英人稱自己為“沙漠居民”,而沿海楚科奇人稱自己為“海上居民”一樣。接受東羅馬帝國拜占庭東正教藝術至今的、繪制于木板上的圣像畫(икона),除此之外還包括羅斯東正教堂中的圣像壁畫。
一、俄羅斯圣像畫的傳入及其特性
在東羅馬拜占庭的宗教和藝術傳入羅斯之前,拜占庭圣像畫藝術在經歷了兩次圣像破壞運動(公元730—787年和公元802—843年)之后,不僅僅沒有衰落反而更加完善,并形成了獨有的藝術系統。經過與拜占庭長期的政治、商貿交流之后,羅斯當時的國君基輔羅斯大公弗拉基米爾(Владимир 980—1045)最終接受了東正教的洗禮,并開始大規模興建東正教教堂。圣像畫這種繪畫藝術也隨教堂的建設,完整地從拜占庭移植到羅斯,從而對羅斯教會“寫生畫”的形成起到了關鍵作用。
公元988年,羅斯基輔大公弗拉基米爾將東方正教(東正教)定為羅斯的國教,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強制羅斯人接受基督教的洗禮。此后,基輔羅斯在各方面都深受拜占庭的影響。在理解和消化東羅馬帝國遺產的同時,由于地緣、生活方式、民族性格等諸多因素的影響,羅斯人自然并巧妙地逐步將拜占庭藝術與其自身民族傳統文化結合,形成了獨具一格的羅斯藝術。當時羅斯正教藝術是在與政治緊密結合的條件下形成并發展的,因此其繪畫題材、內容和宗教密不可分,并受到教會的嚴格控制。同時,這些繪畫內容也反映了中世紀人們的訴求和愿望。教會中的繪畫創作,尤其是圣像畫的創作,在人物的構圖布局與結構、圖畫的樣式等方面都受到嚴格限制,畫家在繪制時必須嚴格遵守這些法則并沿襲傳承。圣像畫創作完成后需要接受教會嚴格的審查,批準后方可面世。
10世紀末,羅斯在從拜占庭獲得其國教的同時,還獲得了穩定、成熟的教會形象、教會學說及教會“寫生畫”的繪畫技巧,這種繪畫技術很快被羅斯藝術家熟悉并運用與創作中。研究發現,之前異教信仰時期的羅斯已經擁有相當發達的藝術,包括繪畫。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羅斯藝術家接受教會“寫生畫”,并使他們在與拜占庭畫家合作時能夠協調一致。
羅斯教堂繪畫技巧的第一批傳授者為來自遠方拜占庭、希臘的畫家,他們招募了很多羅斯畫家做助手,并傳授給他們技法,使他們成為圣像畫家。遠方和本土的藝術家們共同制作完成了很多教堂的壁畫及圣像,例如,現存著名教堂之一的基輔索菲亞大教堂(Софийский собор ,建于1017或1037年)的壁畫就是拜占庭畫家和羅斯藝術家共同創作完成的。這些遠方傳授者帶來了全新的技術手段及繪畫法則,在那一時期,圣像畫的制作、描繪主要在椴木板上,用有機或礦物粉質在加工過的椴木板上做底子,并融合調制的雞蛋黃制作繪畫,即“蛋彩畫”或曰“坦培拉”。壁畫是用與水調和的色彩在未干的石灰墻壁涂層上創作,即“濕壁畫”。濕壁畫的繪制部分采用坦培拉技術,并且整體技術性要求很高,因為“濕壁畫”繪制過程中幾乎無法修改。這種古典繪畫技術在歐洲宗教繪畫藝術中一直延續,并且對現代歐洲油畫技法的誕生產生影響。
在東正教傳入羅斯最初的一個多世紀里,在普通信徒家庭中擺放的圣像畫并未廣泛普及,主要原因是圣像畫家很少。甚至到12世紀時,鑄造的十字架多數還要從拜占庭輸入,更何況是具有典范意義的圣像。圣像畫尤其是宗教壁畫在教堂裝飾中具有顯著的象征意義。在宗教體系中,教堂是連接精神世界與世俗世界的中間介體,教堂中具有象征意義的繪畫藝術能夠將圣經故事里的賢哲形象、圣人學說和神跡故事形象化地展現在他們眼前,進而使他們領悟圣經的教義。
適用于羅斯圓頂東正教堂嚴整的繪畫范式中,東正教圓形穹頂的中心位置一般描繪的是耶穌基督或圣母的形象,在窗戶的間隔處描繪的是大天使、先知者和圣徒,在鼓起的部分一般繪制福音書里的成員,或在教堂中心后部半圓頂隆起處繪制圣母,稍往下是眾生賢者的像。在吸收和創造豐富的拜占庭遺產的同時,羅斯時期藝術已經融為中世紀歐洲宗教藝術的一部分。與此同時,羅斯藝術家排除了拜占庭藝術中不符合羅斯人深層審美心理的部分,也就是說,正教傳入之初的羅斯藝術,在深層次中傳承了民族自身的審美意志和情趣。不過,在當時的圣像藝術中,這種民族性的體現并不明顯。
10至15世紀期間,羅斯的藝術中心主要在基輔、弗拉基米爾、諾夫哥羅德、普斯科夫、特維爾及莫斯科等地。在這一時期,藝術家創作了數量繁多、多種形式的藝術作品,其中圣像畫占據絕大部分。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圣像畫形成了各種風格,但是它的神性內涵和哲學基礎沒變。其后,伴隨著莫斯科政權的擴張,東正教信仰和藝術也得以廣泛傳播。隨著東正教在俄羅斯的鞏固和發展,圣像畫中反映的精神內涵和哲學思想奠定了16至17世紀俄羅斯民族藝術的基礎,這些良好傳統又保留到18、19世紀。
二、俄羅斯圣像畫藝術的發展
羅斯最早從拜占庭接受基督教的時期正好為拜占庭國內宗教復興的鼎盛時期,而在這一時期,歐洲沒有一個國家在教會藝術發展水平方面能夠跟拜占庭相比,因此,羅斯作為“新皈依者”從拜占庭得到了不少教會藝術珍品,其中包括很多圣像畫。在12世紀從拜占庭流傳到羅斯的圣像畫中,《圣母子像》是最著名的也是現存最早的圣像畫之一。該圣像幾經周折,最后被命名為《弗拉基米爾圣母像》,隨后成為從羅斯時期到俄羅斯時代圣像畫中“圣母子”類繪畫的基本范式。
圣像畫一詞,在羅斯時期意味著在木板上繪制的宗教題材的畫,而不是繪制在粗麻布上的畫。這也并不足為奇,因為當時在羅斯,木材是最主要、應用最廣泛的藝術創作材料,而且在早期石頭的和木質的教堂建筑中,木質結構的教堂占多數,因此馬賽克和濕壁畫在早期沒能成為羅斯教堂內部裝飾的主要組成部分。由于圣像畫極具觀賞性并且輕便、結實、易于攜帶,同時具有顏料鮮艷、耐退色的特點,所以極為適合在木質結構的教堂做裝飾,同時也便于在教堂中擺列。需要強調的是,如同埃及的淺浮雕、愛爾蘭的石雕塑、拜占庭的馬賽克裝飾一樣,羅斯圣像畫以這樣的經典造型藝術的形式出現,是與其帶有一定神秘性的社會地緣及自身原因密不可分的。當然最易保存的,部分早期的石頭教堂及其圣像畫、壁畫還是留存了下來,這顯得非常珍貴。這些留存于世的精美作品使得圣像畫逐漸成為羅斯時期美術的代名詞。羅斯在接受拜占庭宗教文化遺產的同時,對拜占庭教堂藝術的完整接受和領會同樣是當時世界其他地區所無法比擬的。
羅斯圣像畫及教堂藝術在長期的發展中逐漸形成了很多流派,同時出現了許多著名的圣像畫藝術大師,他們為后人留下了至今仍可以看到的圣像像、教堂內的精美壁畫等藝術珍品。第一個公認的圣像畫藝術流派形成于11世紀,由建造、裝飾當初的“十畝”教堂(現存基礎部分)而產生,希臘畫家和羅斯畫家的合作對這一流派的形成起到了直接的作用。其細致特征今天已很難考察。第二個羅斯圣像繪畫流派是由建造基輔著名的圣索菲亞大教堂而產生,繁瑣的建筑結構、巨大的壁畫和數量眾多的圣像畫使之形成一個完整的藝術系統和統一的風格體系。羅斯時期起初的圣像畫、圣像壁還完全遵守了來自拜占庭式的嚴肅、刻板等特點,圣容的刻畫還顯得不太放松。在基輔圣索菲亞教堂畫派之后,隨著羅斯疆域的擴大,圣像畫又分出很多支派,他們在繪畫風格上都有自己獨特和值得研究的地方。
根據《第一位羅斯的圣像畫家阿里皮談》一書記載,最早的一位羅斯著名圣像畫家是阿里皮·別恰爾(Алипий或Алимпий Печерский ?—1114)。阿里皮·別恰爾起初為初級修道士,后來升為主祭職務,他繪制、修復、重畫了很多圣像畫,并且很多圣像畫是為宗教活動而制。在《教父古語集》上曾記載了在基輔教堂的一幅圣像畫被認為是出自阿里皮·別恰爾之手。這幅《圣母》圣像畫后來被弗拉基米爾· 瑪諾馬赫(Владимир Мономах)贈送給了拉斯托夫的烏斯賓斯基大教堂。阿里皮·別恰爾參與繪制了著名的基輔別恰爾修道院的圣像壁畫和基輔別恰爾烏斯賓斯基大教堂的馬賽克裝飾制作,但這些珍貴的遺跡實物毀于1941年德國軍隊的入侵。
費阿芳·格列克 (Феофан Грек 約1340—1410)是羅斯和拜占庭偉大的圣像畫家,小型題材和大型圣像壁畫家。費阿芳·格列克出生于拜占庭時期的希臘,到羅斯之前,他曾在伊斯坦布爾、哈爾克頓(伊斯坦布爾鄰近的城市)及卡費(今天的克里木的菲奧道斯)等地工作,遺憾的是他這幾處圣像繪畫沒有保存下來。費氏當時同東正教教主柯樸利阿一同來到羅斯,后來在羅斯各地教堂繪畫。1378年,他在坐落于諾夫哥羅衣里昂街上的德普列奧普拉救世大教堂從事繪制工作,教堂至今留存。1395年,費氏同西梅翁·且奧爾內在圣母降生大教堂做繪制工作。1399年,他繪制了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內天使長大教堂的壁畫。1405年,又與安德烈·魯布廖夫和來自戈羅潔慈城的普羅霍爾一起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的圣母受胎告知教堂繪制了聞名于世的圣像畫《頓河圣母像》《安息圣像畫》《主易圣榮圣像畫》。受胎告知教堂里的圣像畫《圣列》(Деисусного чина)也被認為出自費氏之手。
費阿芳·格列克的繪畫風格有著驚人和豐富的表現能力,在技術方面,他所描繪的圣像壁畫具有明顯的寫意性和幾近單色的施色特點,舍棄了過多細節和瑣碎的描寫,具有一種強烈的整體氣勢。費阿芳·格列柯的創作一方面反映拜占庭文化中的對上帝創造大自然界的歌頌,突顯了一種神性的光輝,另一方面表現的是一種深層的精神上的嚴謹修行。
與費阿芳·格列克同時期的圣像畫大師是安德烈·魯布廖夫(Андрей Рублёв 約1360/1371—1430),他也是15世紀最杰出的莫斯科流派圣像、書冊和巨幅繪畫代表畫家之一。14世紀下半葉到15世紀初,魯布廖夫對人的道德及心靈層面的認識產生強烈興趣,在中世紀圣像畫的教條框架下,注重提升內心福祉和人類的道德力量的表現,反映在他的《救世主》《天使長米哈伊爾》《圣人巴維爾》等經典圣像畫作品中。
除1405年與費阿芳·格列克及普羅霍爾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受胎告知教堂繪制圣像和壁畫(沒有保存下來)外,1408年,魯布廖夫還與達尼爾·切爾內以及其他畫家在弗拉基米爾烏斯賓斯教堂繪制圣像和壁畫(至今局部保存下來)。這些圣像畫同時也是為他創作三層巨制壁畫而作,是俄羅斯圣像畫繪制的一個重要階段。烏斯賓斯教堂的魯布廖夫的壁畫《審判》,其規模、構圖相當可觀,在這幅畫中,傳統中嚴厲的場面變成了一種開放、莊嚴、公正甚至是輕松的場景,更加強調了人的精神價值。在弗拉基米爾,魯布廖夫達到他藝術的成熟和輝煌時期,也創立了弗拉基米爾圣像畫流派。1420年(一說是1412年),安德烈·魯布廖夫創作了他的舉世名作圣像畫《三圣圖》(現藏莫斯科特列基雅科夫國家美術館)。該畫取自圣經傳統題材,表現出深刻的神學內涵。畫面擺脫了傳統的圣像畫構圖形式,畫面中央是一只大尊,在大尊周圍是三位大天使,大天使的動態形式平穩,但動作又各異。穩重的構圖極符合傳統圣像畫整體氣質上的超脫境界,但三位大天使各異的動作和微低側耳的神情似在私語,這超越了刻板的描繪,已經流露出人間世俗的情態,達到神性和人性結合的繪畫境界。在后來的時間里,魯布廖夫又在不同地方創作了一系列的作品,這些作品成為俄羅斯及世界文化遺產中的重要部分。總的看來,其圣像畫作品反映出其內心的一種靜修和嚴謹的心理訴求。
季奧尼斯(Дионисий 約1440—1502)被譽為是15世紀莫斯科圣像畫的領軍畫家,也被看做是安德烈·魯布廖夫的繼承者。此外,還有很多在當時并不知名但被后來的研究者發現的偉大圣像畫家,像基輔別恰爾修道院的修士圣像畫家格里高利(Григорий 約10至13世紀期間)等。羅斯歷史上的圣像畫家為后人留下了寶貴而豐富的精神財富,尤其是那些藝術珍品,像安德烈·魯布廖夫的《三圣圖》已成為今天人們研究東正教藝術和內容的頂級重要的實證資料,同時,這些藝術作品也為后人研究其作者和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提供了無限的想象空間。
隨著15世紀東羅馬拜占庭的滅亡及小亞細亞基督教國家的穆斯林化,羅斯的藝術也曾一度失去自己的重要性。15世紀中后期,在東正教巨大凝聚力的作用下,俄羅斯(2)現代使用的“俄羅斯”一詞由“羅斯”一詞演進而來。10世紀的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波菲羅涅圖斯的著作《典禮》中首先出現“Rosia”一詞,意為羅斯人的國家。這個詞很快進入了日常書籍,并在14世紀末-15世紀初從希臘教會的書籍中進入到俄語中。在15世紀俄語中,“ Rus”和“ Russia”(帶有一個“ s”)的意思相同,但帶有兩個“S”的詞,實際上就是現代使用的“俄羅斯”一詞,在17世紀的文獻中,第二個單詞開始比“ Rus”更頻繁地出現,并且已經用兩個“ s”,類似于“ Russian”。在1547年獲得沙皇頭銜的伊凡雷帝的統治下,莫斯科大公國成為了俄羅斯王國(或者以拜占庭式的方式成為了俄羅斯王國)。 1721年,彼得一世將俄羅斯王國重命名為俄羅斯帝國。人經過長期征戰擺脫了蒙古-韃靼人的入侵和統治,成為了不可多得的東正教文化中心。
但在俄羅斯文化歷史長河中,圣像畫等繪畫藝術還是經歷了一段時期的沒落,尤其是在彼得一世(Пётр I 1682—1725)改革時期。這一時期,不僅俄羅斯遭受到外國掠奪者們的侵略,而且彼得大帝強制性全面西方歐洲化改革。其后伊麗莎白一世·彼得羅芙娜(Елизавéта I Петрóвна 1709—1761)女皇執政,由于伊麗莎白女皇喜歡風雅藝術,對當時西方的歐洲藝術文學非常熱衷,就藝術方面,她曾邀請了百名之多的歐洲著名的畫家、雕塑家、建筑家等來俄羅斯教授新的油畫和雕塑等技法,很多圣像畫家開始改行學習新畫法和新技術,因而,包括教會“寫生畫”在內的俄羅斯傳統文化藝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歐文化的影響和沖擊,甚至被視為落后與粗野的象征,地位逐漸衰落。然而有意思的是,俄羅斯圣像畫及教會繪畫體系卻以極為簡易且非常純粹的方式完整地保留在了農村,其中最有名的圣像畫繪畫村包括帕列赫(Палех)、瑪斯契拉(Мстера)及厚陸依 (Холуй)等地。
另人欣慰的是,100年以后,在彼得大帝的強制性改革過程中形成的新一代知識分子開始重新尋找這些被遺忘的、但屬于俄羅斯民族自己的文化和藝術。
三、俄羅斯圣像畫的審美功能和繪畫特征
概括而論,基督教圣像畫造型藝術的樣式形成于4至6世紀的羅馬和早期拜占庭時期,發展成為經典的樣式是在9至11世紀的拜占庭時期,此后更加完善。在羅斯時期,宗教繪畫的成熟與繁榮時期出現在14至15世紀。這些圣像畫不僅具有最初的看圖識史和簡單的說教作用,而且后來具有獨立的審美價值。通過可視形象直接感染觀者的心靈、提升他們的精神世界,使他們進入到宗教信仰里的更高領域。圣像畫傳到羅斯保存了畫面視覺上的莊嚴感和基礎構圖嚴謹的對稱特征,肅穆對稱的構圖形式和莊嚴的形象,對觀賞個體也起到感化召示作用,造成人們內心深處對神秘宗教世界的敬慕憧憬,使得觀賞個體從世俗世界的狀態中得以解脫,從現實的苦惱中得到一種自由的精神慰藉。
羅斯圣像畫和教堂藝術創造了穩定的繪畫色彩、造型和線條的完整系統,并且在圣像藝術莊嚴的可視世界里同樣充滿著喜怒哀樂的微妙表達,這一方面,尤其表現在對善與惡的判斷或在面對生與死的思考時。但這種判斷、思考,或宏大辯論的畫面,完全謹守在獨立而穩定的藝術風格里面,并從畫面整體而莊嚴的形式感中傳達出來的。它感召著各個時代的信徒個體,使他們從繁瑣的塵世行為和日常思維的雜念中脫離,進入無形精神的“清凈”世界。這種處世態度返歸到社會現實中,即是如何對待現世的人生態度,教化了民族的處世態度,并形成了社會無形的道德行為的約束性。這種提升和對世俗世界的認識是觀賞者在不停地內心修煉和感悟的量變質變過程,也是國家在政教一體和發展中來統一思想的神學體系,是神秘精神世界和人和藝術的統化的有機結合整體。這種結合培養延續了社會信仰。因此作為宗教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圣像繪畫,它的“原型”和“典范性”特征,即是保持了不受時間影響和本體藝術語言上的不變統一性和傳承性。
圣像畫藝術是世俗心靈與神性思想之間連接的重要介體,表現基督正教思想的造型圖示完全取代了早先羅斯多神教偶像崇拜時期的各種造型的功能。實際上,圣像藝術是把一種重要的、作為新的特殊造型藝術手段的繪畫放進一種嚴格的教規當中。圣像畫藝術始終維持嚴格的傳統“原型”,自身沒有改變并極其恭敬地來體現圣像中的“人物”形象,用看似“冷漠”的基督世界的形式表達無可取代的宗教意義。圣像畫是通過內容和形式來反映神圣精神世界的無限能量,并始終處在敬慕的宗教“解釋”當中的,用一般的眼光來觀看圣像時,它和世俗的繪畫活動有著很大的差距。現代藝術中,新物質材料的出現和繪畫藝術的發展,使得藝術世界實現了無限豐富的表現形式和色彩感覺,讓世俗的精神解說和抽象的不斷變化著的諸多藝術形式交織排列在一起,它們可在同一時間、同一場景內一并展示給觀者,使觀賞個體在思想起伏的審美過程中尋找合適的、階段性的、暫時的精神解放和自由。然而圣像畫藝術是在釋道,沒有暫時性,只有存在性。圣像藝術誕生之后,傳播到四方,隨著地域的變化和時間的推演,雖然有符合自身發展的變化因素,但圣像繪畫長期恪守描繪法則,拉開與世俗繪畫的差距,保持“單純”性和穩重的畫面形式,這種“差距”正反映了圣像畫通過在形色和“規矩”框架下所顯現的神性理念。東正教圣像繪畫(包括教堂壁畫等)釋義對應著圣經的章節典釋,圣像藝術或圣像壁畫情節中那些局部的類似世俗繪畫的“通俗”表情和微妙神態變化體現的是神學的思想和藝術的高度結合。它們不是像世俗繪畫那樣給人們以大喜大悲的強烈感受,而是對世俗情感做出心理上的理性判斷和宗教靜修帶來的克制。人們通過禮拜圣像,去感知現象背后的神圣領域,進而達到和諧統一的心靈境界,使思想匯入神圣的境地,引導靈魂進入神的世界之中。所以圣像本身被視為參與禮拜、神修、祈禱的組成部分,這是圣像繪畫與世俗繪畫的另一個不同之處。
木板上或在墻壁上的圣像畫,在表現眾多人物的情節時,具備兩個明顯特征。首先,在表現圣潔正面的主體人物時,總是描繪得比較大且色彩鮮明,而在描繪魔鬼或邪靈時表現得相對很小,從比例上和色彩上的差別產生主次,彰顯正義和光明,并且天使的出現往往起到點綴和活躍畫面的作用。圣像畫面中無論表現主體或客體,還是動態的天使,總是把這種神的世界里的純潔、高尚、完美的描繪,或是邪惡、罪孽的描繪都一并蘊含在一種肅靜、莊嚴的圣像畫面的精神世界里。其次,尤其是在諸如“審判”這類題材中,因為描繪的人物眾多,并且畫面常常是并列站立的幾排人物,運用類似中國傳統繪畫中“散點”透視的技法。實際上,有人類繪畫歷史以來,這種“散點”的繪畫形式符合最初繪畫的自然法則和繪畫心理“游走”的特征。具有隨意性的自然繪畫法則,即是根據繪畫內容需要什么就畫什么,這種隨意性未被限制到一種像后來現代“科學”意義中的繪畫透視法規上來。再次,這種根據需要繪畫的原始的自然法則,因為在基督可視世界里的實用性而被尊為傳統,并未受到教會外的影響,反而形成獨立完整的形式被傳承下來,成為圣像繪畫體系中的重要特征。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現代繪畫中的某些根據主觀需要而隨意性的構圖和發揮以及“具象表現性”繪畫的很多思想,在古代圣像繪畫中早已存在。
羅斯15世紀前,圣像畫繪畫風格基本保持拜占庭時期的特點,到了14、15世紀,羅斯圣像藝術的本土特點和性格逐漸顯露出來。同時期歐洲重要的圣像藝術的另一代表區域是意大利。意大利的圣像、祭壇畫發展到文藝復興前期時呈現的特點是色彩艷麗細膩、形式活潑。相對而言,羅斯的圣像畫無論從構圖還是色彩方面則趨于簡潔、整體。這也正體現了羅斯民族圣像畫藝術有別于異域的整體特性。由于俄羅斯圣像藝術的成熟和自身的完整性,它在歐洲繪畫藝術中形成獨特的面貌并占據重要的地位。
四、圣像藝術對俄羅斯現代繪畫的影響
東正教的教理及其藝術始終深刻地影響著俄羅斯人的社會生活和民族藝術,遍布俄羅斯大地上的東正教堂歷經時間和政治的變革,至今依然存在。俄羅斯藝術發展到19世紀下半期是批判現實主義的輝煌階段,對社會現實矛盾的深刻認識和批判,是俄羅斯藝術家群體創作的思想基礎,藝術創作的背后不能脫離民族性格中與東正教教理的密切聯系。社會的現實和精神矛盾的反作用力,激活了長期存在于民族藝術家心理深層中對人性美丑善惡的價值判斷和自覺表達的沖動。涌現在文學藝術當中的倫理觀念和對國家、社會、人生的價值觀的剖析,如同福音書中表述的是對真理、公平的追求、對人的憐憫和同情,繼而形成了批判揭露社會現實、描寫世俗生活當中的人間百態和歌頌俄羅斯民族及大自然的藝術作品。這符合傳統信仰中對人間道義所擔負起的責任和義務,也是人類良知的集中流露和自覺表達。在藝術技法上可以看出,雖然深受從前彼得一世時期社會深刻變革以來受到的新表現形式和技術手法的影響,但在繪畫創作上卻依然蘊含著俄羅斯宗教藝術傳統的審美傾向和觀點。這些都反映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藝術創作中,就是整體面貌背后的那種不變的莊嚴性、沉穩的感情色彩和深度的民族理性思維。
20世紀至今,在經歷過復雜的政治動蕩、不同政派意識形態的階段性博弈、人民生活跌宕起伏的過程后,不穩定的大的社會環境因素促使藝術家對現實生活、意識形態和人的精神歸宿重新思考,尤其是那些注重揭示民族心理、強調表現人物題材的俄羅斯屬性的敏感的藝術家們,他們認為只有從本土的傳統藝術中才能發展出具有真正精神內涵的創作,將貼近現實生活、親近人民的傳統基礎和對歷史文化傳統精神的深度體驗相結合,剔除使人迷惑的幻想世界的藝術,直面真正的現實生活,置身于社會,深刻貼近民族的精神根源。現代俄羅斯繪畫大家維克多·伊萬諾維奇· 伊萬諾夫(Иванов 1924—)在他的《人民的真理觀念》一文中曾說:“我所珍視的并不是俄羅斯傳統藝術中個別的代表人物,而主要是它發展的總的趨向。它對描繪對象的強力同情和憐恤深深地吸引著我,完美的道德感、民主精神和對于生活的參與即源于這種同情和憐恤。”伊萬諾夫的繪畫從早年就表現出紀念碑式的概括和對色彩音樂裝飾性的愛好,深受俄羅斯宗教藝術的影響,尤其是圣像畫和壁畫的影響。從畫家的許多人物速寫和獨立的肖像畫中可以看出,他創作的人物既保持著個性特征與描繪對象的特點,又帶有理想典型類型化的、永恒的特征。同樣,畫家在他的許多創作中通過對現實生活的觀察提出了自古至今人類共同關注的根本問題,即人類對生與死的兩極的追問,對完美道德感和民主精神的解釋。如他的《人的誕生》《以撒達葬禮》以及《燭光》等作品,無論從繪畫性層面還是內涵性層面,都體現出整體性與具體性、塵世性與升華性的分寸。平靜而莊嚴的繪畫風格中,流露出一種宗教的神秘感和藝術形式背后的辯證思考,這也體現出當今俄羅斯民族畫派的主要精神根基和來源。
結語
從世界范圍來看,俄羅斯保留著最完整的東正教的傳統體系。尤其是俄羅斯的東正教繪畫藝術,其特有的色彩感、構圖形式、沉穩而整體的氣質、富有哲理的宗教內涵等因素,始終在其深層的精神領域凝聚著民族的思想和向心力。長久以來,受此信仰約束的民族向心力和心靈深處的靜修因素,潛在地影響著俄羅斯現當代繪畫藝術的風格和表現形式。俄羅斯繪畫中多反映出追問人生和生命意義的美學思想,許多藝術創作帶有人間悲情的文學味道,這與東正教傳統教養和民眾對傳統的尊崇關系緊密。諸多現當代俄羅斯畫家的藝術思想源自于對本民族宗教藝術的探索和思考,所以人們看到的俄羅斯的繪畫藝術總是以其特有的俄羅斯式的風格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