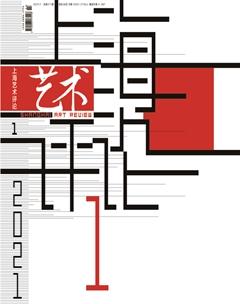現實題材戲劇如何獲得超越性
張之薇
作為戲曲現代戲創作重要省份的河南,在進入21世紀以來,無論是優秀劇作家還是優秀導演均以群體形式出場。2000年河南的《香魂女》在戲曲界一炮而紅,隨后2004年的《常香玉》,2014年的《焦裕祿》,2015年的《風雨故園》,2016年的《秦豫情》,1隨著這些打著河南創作人標簽的戲曲現代戲作品一一亮相,也讓編劇姚金成、陳涌泉、楊林,以及導演李利宏、張平、張俊杰等創作者漸入全國視野。筆者以為,河南戲曲現代戲的崛起得益于話劇人向戲曲創作的滲透,同時也離不開創作者們對現代戲現代精神的把握,以及現代戲樣態的重新思考。
在這些創作者中,劇作家楊林是筆者始終關注的一位。細數楊林的作品,從京劇《霸王別姬》(2004)到豫劇《常香玉》(2005),從話劇《紅旗渠》(2011)到呂劇《百姓書記》(2013),從豫劇《河南擔》2(2016)到滬劇《敦煌女兒》(2018)、淮劇《浦東人家》(2018),如果再加上一些未上演,或即將上演的劇目,3將近二十年的光景,他的作品僅有十部左右,這在當今眾多劇作家中實在算不上高產。但是,令人驚嘆的是,就是在這些屈指可數的劇作中,京劇現代戲《霸王別姬》和話劇《紅旗渠》2006年與2012年兩度榮獲曹禺戲劇文學獎,豫劇《常香玉》在2007年第八屆中國藝術節上獲文華劇作獎,而話劇《紅旗渠》和呂劇《百姓書記》在2013年第十屆中國藝術節上又同時斬獲文華大獎。
如果打破話劇和戲曲的壁壘,可以發現楊林將近二十年的戲劇創作重心都聚焦在一個題材類型上,那就是“現實題材”。而今“現實題材”越來越成為國家對藝術創作的政策導向,對于戲劇界來說研究楊林的作品無疑更具有現實意義。如何將“現實題材”戲劇作品初始的宣傳初衷轉換成藝術作品應有的審美價值,筆者認為楊林是有自己思考的。
讓“現實”融入史詩
首先,突破“現實題材”中對“現實”一詞的窄化認知,是楊林在創作“現實題材”作品時的重要思考。那么,怎么樣才能突破“現實題材”中“現實”窄化的問題呢?楊林的方法是無論書寫時代新人,還是書寫時代精神,都將其放置在一個歷史的大格局中。當筆下的真人真事有了時間的肌理和厚度時,時事劇頓時會被賦予了史詩劇的光澤。
因此,在他筆端無論是常香玉、樊錦詩這些具有璀璨光環的人;還是如楊貴、王百祥(原型王伯祥)這些時代的弄潮兒;抑或是謝廷信(原型劉廷信)這樣被生活壓彎了腰的普通人,楊林都是把他們放在時間的長河之中去回看,努力去探尋他們被社會的光環或生活的瑣碎所遮蔽的“人”的定位。他劇作里的常香玉似乎與以往社會讓我們看到的那個強者常香玉不盡相同,這是一個更為私人化的心靈舞臺。在這個舞臺上,是一名彌留之際的老人去回望她的一生,作者以史劇的格局為那個現實舞臺上光芒萬丈的常香玉一點點“祛魅”,讓她變成一個真實的人。她既是萬人追捧、嶄露頭角的豫劇名伶,也是以一己之力捐出飛機的愛國藝人,更是在舞臺上成就自己、活出自己的角兒,但她還是那個自幼因為學戲被鄉族拋棄的張妙齡,是與地方惡霸周旋的底層戲子,也是那個“文革”中被學生侮辱抬不起頭的“牛鬼蛇神”。
史劇,是楊林書寫“現實題材”的切入口,而詩格則是他想讓史劇抵達的更高境界。無論是書寫紅旗渠、新疆建設兵團這樣的宏大事件,還是書寫樊錦詩、楊貴、王百祥這樣的時代新人,楊林都在盡力探尋人物的歷史滄桑感,而且他并不回避20世紀下半葉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動蕩和各種“運動”的紛擾,只為能夠渲染出大歷史下苦行者的渺小。于是,創造“意象”常常是楊林書寫“現實題材”時營造詩格的一種方法,而“意象”最終的指向則是情感。在楊林的劇作中,《紅旗渠》中的胭脂盒,成為那片干涸土地上最動人的亮色,它既是吱吱這一人物的靈魂寫照,也是所有林縣人對水的渴望的情感投射、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霸王別姬》中那個沉默的水神爺,永遠守護著他懷中的那壺水,他無疑寓意著戲曲人心底對那個小小舞臺圖騰般的守護。《敦煌女兒》中那個多次出現的“九層樓”更是象征著敦煌人的敬畏之心,楊林通過“九層樓”上的“鐵馬”和佛燈的意象寄托了樊錦詩對敦煌無限的深情。這種將情感投射到物象之上的意象化處理,無疑為史劇化的“現實題材”平添了一份濃濃的詩意。
尋找角色和自我情感的連接點
生活永遠是楊林心中的第一角色,將自己的生活體驗滲透于創作中,是楊林創作“現實題材”的另一種自覺。“現實題材”常常以我們身邊的人、我們身邊的事為創作對象,但是從生活到舞臺其實遠非想象得那么簡單,因為戲劇并不是生活本身。如何把平凡、瑣碎的生活本身升華為真正具有審美力量的戲劇藝術作品,這就需要創作者從技術到觀念意識的加持。
英國現代著名哲學家羅賓·喬治·科林伍德說:“最偉大的藝術力量要得以恰如其分地顯示,就需要有藝術力量相當的第一流的技巧。”4
楊林,是一位會寫戲的劇作者,這首先來自于他對編劇技巧嫻熟地運用。他從不滿足于把聽來的“生活”簡單而平鋪直敘地復制到舞臺上,而是擅于制造戲劇性將人物推向情感頂點。豫劇現代戲《秦豫情》中小勤和張大的初遇就是很好的例子。二人相遇的戲劇行動因一車撞碎的瓷器而起,二人一個跑、一個追;一個藏,一個闖,在推進過程中,算命先生馬虎和下層妓女呂嫂相繼登場掩護小勤,在與張大的周旋中,原本并不可愛的馬虎和呂嫂卻顯露出了各自善良的本色。楊林在這場戲中通過矛盾沖突、人物關系、戲劇情境各種因素的變化,對戲劇場面進行了精彩開掘,整場戲讓小勤和張大從兩廂敵對滑向暗生情愫,可謂把戲充分做足,也為下一場的轉換做好準備。可見,楊林深諳講故事是需要技巧的。
實際上,如何運用技巧也是劇作者講述生活、進而思考生活的方式,而將外在于作者的客觀生活充分內在化,不僅需要作者的生活沉淀,更需要作者強大的主體意識,也就是說,任何好的作品都暗藏作者自己。對于楊林來說,每一次創作他都在努力尋找這個題材和題材中的人與自己個體生命情感的連接點,從自己的情感記憶出發去觸摸筆下的人物。他的處女作京劇現代戲《霸王別姬》之所以獲得“曹禺劇本文學獎”,大概即得益于此。《霸王別姬》講述的是當代某城市,當凋敝的戲曲劇團迎來一個千載難逢排戲機會后梨園人的眾生相,這里面既有圈內的堅守者虞姬,也有出圈的戲曲人霸王;既有被舞臺拋棄的梨園守護人水神爺,也有捍衛梨園精神的師父;更有年輕一代的佼佼者青衣。劇中,每一個人物的名字,既是戲曲舞臺上角色的名字,又是對人物性格的隱喻。楊林用自己從13歲起就在劇團中摸爬滾打的人生經歷,將轉型時代下戲曲人內心的沖突和碰撞展示出來,讓我們看到一個“萬花筒”般的世界,也是戲曲人最隱秘的世界:他們對戲的執著是那么令人動容,但是他們對舞臺的占有欲又是那么強烈,當然最終戲與舞臺的魅力讓人與人之間的愛與渴望、守護與信仰跨越了一切,這才是這些戲曲人的主流精神。楊林通過劇團這個小世界放大的是人的本性、私欲與人的崇高理想之間的矛盾。楊林曾經說過:“《霸王別姬》里有我對生活的感悟,有我對人生的看法。在很多人物身上,有我的影子;許多人物的語言,就是我想說的話。”“這是我完全、主動、最純粹的一次創作經歷。創作動機,是我生活安定之后,想對自己的十年人生做一個總結。”5
其實,這種將自己的生活感悟內化之后的藝術創造體現在他所有創作中。《常香玉》中,小張妙齡被迫離家前父親的“三問”就是楊林從小學戲放棄學業,父親與他“三問”的人生寫照;6《紅旗渠》的創作中更是熔鑄了自己父輩人的深厚情感。7他曾經說過:“生活歷練了我,戲劇造就了我”,8生活和戲劇實際上是成就楊林不可或缺的兩面,而戲劇更像是他對自我的找尋和救贖。
讓英雄成為真正的人
對人性的深刻思考,是楊林讓他的作品抵達觀眾內心的密鑰,這主要體現在“現實題材”中,他如何處理正面人物或英雄人物。文藝理論家劉再復先生說:“對于作家來說,真正的英雄式的觀念,是不屈服自己心靈之外的各種壓力,敢于面對人,面對人的真實的復雜的世界,把人按照人的特點表現出來,把人之所以成為人的那些價值表現出來。”9
在楊林的作品中,英雄或時代的弄潮兒,這些國家話語體系下被歌頌的人常常是他的主角,但楊貴、常香玉、樊錦詩、王百祥等這些被謳歌者卻絕不止步于干癟的符號,這首先得益于楊林所持的“英雄也是人”的觀念。比如:在話劇《紅旗渠》中,以當代歷史上河南林縣修建紅旗渠的事跡為背景,楊林寫出了在20世紀60年代修建這一“人工天河”工程的核心人物楊貴的復雜性和多面性。楊林顯然沒有沿襲之前同一題材創作者的固有思路,而是深刻思考那個戰山斗地,人定勝天的特殊年代,同時也是冒進盲從的特殊年代中英雄楊貴的所作所為。劈開太行山,引彰入林,這是一個在當時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楊貴義無反顧,毫不退卻,他既是林縣老百姓的父母官,也是那個年代的狂想者,還是引領眾生走向光明的大無畏的巨人。但是另一方面,在金錢、技術、設備均不充足的情況下,他所有的無畏似乎都與無知、盲目糾纏在一起。他拒絕聽從反對意見,他拒絕承認自己的錯誤,他甚至為了讓紅旗渠順利完成,“發配”反對者黃繼昌至山西平順。顯然,楊林并不滿足于簡單地書寫一位我們慣常看到的完美無瑕的英雄形象,而是想通過挖掘楊貴高光背后的陰影,來讓這個人物接近更真實的人。
必須明確的是,在以真人真事為題材的創作中并不意味著要排斥藝術虛構,相反通過合理的藝術想象進行創造是尤其必要的,在《紅旗渠》中楊林虛構了黃繼昌這一人物,雖然僅僅四場戲,但卻舉足輕重。他是作為楊貴的對立面出場的,在修建紅旗渠這一行動上,黃繼昌表現出的科學、務實、嚴謹與楊貴的豪情、沖動、冒險必然導致矛盾沖突,但這是性格的沖突,而不是立場的沖突。因此,在二人一次次的沖撞中,行動推進著他們內心漸漸靠近。實際上,楊貴和黃繼昌都在為同一個目標努力,只是方式不同,當兩個男人以男人的方式大打出手,其實預示著他們的和解。狄德羅曾言:“說人是一種力量與軟弱、光明與盲目、渺小與偉大的復合物,這不是責難人,而是為人下定義。”10《紅旗渠》中的楊貴和黃繼昌無疑是真正的人的樣子,他們其實都是那個年代的英雄,但英雄也是多層次的,如果說楊貴是“光明與盲目”的集合物,那么黃繼昌就是“偉大與渺小”的復合體,正是楊林對劇中角色的人性開掘才使得《紅旗渠》在一眾同題材作品中顯得卓爾不群。
人性的深度開掘還表現在對人情感多面性的開掘上。在楊林的劇作作品中,人物的私我情感從來不曾缺席。《紅旗渠》中楊貴對死去的少女吱吱和自己年邁父母的情感透露出這個強者的柔情;《敦煌女兒》中的一心撲在事業上的樊錦詩,楊林也寫出了她作為孩子的母親,作為丈夫的妻子,與自己敦煌事業相沖突時的情感矛盾;而《百姓書記》中,楊林既寫出了時代潮頭的改革者王百祥,也寫出了他與老父母的舐犢情深;還有《秦豫情》中的下層妓女呂嫂、算命先生馬虎、甚至張大的母親,每一個人物都不是扁平的,而是讓人物多層次的情感成為其靈魂撕扯的張力。可見,讓人之所以成為人,關鍵是讓人物不同層面的情感緊緊絞纏在一起,形成內心的碰撞。
用發現的眼光深入生活
對于“現實題材”創作者來說,無論是對人性的挖掘,還是對歷史“真實性”的挖掘都應該是一種使命,而如何去“偽”,如何求“真”,以及如何尋求舊題材的新視角同樣是楊林的創作自覺。他從不滿足于在既定題材、既定框架下去沿襲既定的故事套路,相反,他懂得唯有突破“既定”才是一條重生之路。除了“紅旗渠”這類被人們一寫再寫的題材,還有《百姓書記》《秦豫情》《浦東人家》等,均是楊林在前人寫就的基礎上重新動筆,從別人的終點重新出發,然后又打開一個新局面。
新疆建設兵團是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軍人在戈壁灘上建造的奇跡,之前無論是話劇還是戲曲都有作品。盡管如此,楊林的話劇《兵團》11從其對兵團題材新視角挖掘上看還是令人驚艷。在他的筆下,曾經那片廣袤荒涼的土地上那些原本姓名不存、頂天立地的“兵馬俑”們,成為了一個個活生生的、有著七情六欲的人,這是一次屬于楊林的藝術發現。他找到了這片土地上的兄弟情—二年、大年這一對人物。孩子兵二年由于對上戰場內心懼怕,于是,為了兌現母親的承諾,大年代弟從軍,卻不曾想歸來時發現二年還是離去了。于是,大年與二年的棗騮馬在戈壁灘相伴終老,只為等待著魂歸的二年一起回家。這對兄弟情代表了時代號令下無數佝僂的個體,但卻又用信念支撐起自己的那些生命強者。楊林還找到了這片土地上的夫妻情—黃三水和岳玲玲這一對人物。尋著理想而來,自愿報名赴疆的岳玲玲,當真正來到的時候遭遇的卻是倉促無感的婚姻,是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然而現實迫使她接受眼前的一切,當歲月老去時,有夢的女人與粗糲的老紅軍已經無法分割。燕窩兒與王趙成這一對則是楊林找到的戀人情。兩個無助的年輕人在孤島般的戈壁灘上,彼此信任、彼此取暖,讓無處安放的靈魂找到了棲息地。其實,時間才是《兵團》這個作品隱藏的主角,生命的滄桑感才是這個作品真正的主旨。沒有任何口號和概念,也沒有主題先行的宏大敘事,戈壁灘的豪情是時代賦予的,個體的人則逃不開青春被歲月消磨,愛被現實操控,理想被生活擊打,以及唯有迎接與承受的生活本質。楊林力圖尋找那個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以及這些不同的人在那個時代下多棱的情感,使得這一題材進入到一個新的審美空間。
新的發現往往是對現實更深處的探入,隨著近來“懸浮劇”一詞越來越成為人們對“現實題材”作品的揶揄,劇作者是否深入生活的問題愈發引人重視。楊林是從真正的生活中走出來的劇作者,他也意識到作品中每一位個體的靈魂都是浸泡在時代中,并從時代中生長出來的,所以,在他的劇作中首先撲面而來的是濃濃的生活氣息和時代氣息。在淮劇《浦東人家》中,楊林大量選取具有時代特征的環境、電視劇、人物語言、人物典型行動來凸顯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時代印記;京劇《霸王別姬》中,楊林通過下海、歌舞廳獻唱等形形色色的典型動作來展現市場經濟大潮下劇團和社會的“浮世繪”;《敦煌女兒》12中楊林用不同時代的典型氛圍來塑造敦煌人對敦煌的眷戀,他尤其沒有回避特殊時代的錯亂與癲狂,也沒有回避經濟大潮對敦煌人的沖擊,正是因為他對不同時代的白描,反而為人物的“真”添加了養分,讓樊錦詩、常書鴻、段文杰等這些敦煌人的精神與動蕩起伏的年代緊緊聯系在一起的。
以“現代性”品格尋求超越
2021年,“現實題材”戲劇作品即將迎來創作的高潮期,如何運用藝術的法則、從而突破速朽性無疑是很重要的,楊林的“現實題材”作品或許有一定借鑒和示范的意義。
可以說,無論是20世紀初的戲曲改良運動下產生的現代戲,還是1949年之后的現代戲,抑或是如今的“現實題材”皆以正面表現時代和時代中的人為主要目的,而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邁過“時代性”“即時性”抵達“現代性”,始終對于劇作者來說是一個艱難的挑戰。也正是因為此種艱難,現代戲經過歷史的大浪淘沙后所剩無幾,正如著名戲劇理論家劉厚生先生所言:“世紀之初許多戲曲現代戲的出現,就同當時的政治密切聯系,這是對國家和民族命運關心的表現。但是,單憑政治熱情不能保證藝術創造的成功,大量現代戲都由于藝術上的幼稚而失敗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沒有深入總結歷史經驗,反而要求更高。人民的現實生活、時代精神通過現代戲可以更有力地體現,但真理往前一步便成謬誤。過分要求現代戲(其實不止現代戲)直接為政治服務,必然會形成以政治代替藝術,政治家代替藝術家的局面。”13其實,現代戲的問題與當下的“現實題材”的問題是異曲同工的。
進入21世紀以來,戲曲理論界對戲曲現代戲的思考進入另一個層面,即對其是否具有“現代性”表現出極大關注,這不僅是由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在古裝歷史劇方面出現了如《曹操與楊修》《董生與李氏》《金龍與蜉蝣》等極具“現代性”品格的佳作,也與20世紀最后十年中國知識界對“現代性”層出不窮的討論脫不開干系。其實,相較于知識界對“現代性”的多義性探討,以及對“現代性”不同程度的反思,14戲曲理論界對“現代性”的訴求則越來越達成一致,那就是“現代性”品格對現代戲曲的必要性。而筆者也認為,“現代性”正是“現實題材”作品、戲曲現代戲獲得超越的唯一路徑。
那么何謂“現代性”品格?筆者以為,恰如美學理論家周憲先生關于“現代性”的核心概括:“反思乃是現代性概念的核心所在”。15但是同時,“現代性”一定是與轉型這一契機聯系在一起的,無論是社會領域的轉型,還是文化領域的轉型,對“現代性”問題的爭論和探討都會促使人們對過去和未來進行思考。而關乎戲劇中的“現代性”品格,即表現在審美的“現代性”這一問題上,反思性當然也是一把不可丟開的標尺。恰如《曹操與楊修》反思了文人與威權的關系;而《董生與李氏》則是反思了女人與男人的關系,《金龍與蜉蝣》則反思了人在前行的過程中失去與獲得的關系,話劇《狗兒爺涅槃》則反思了1949年之后土地與農民的關系。這些作品之所以成為經典,被公認為是具有“現代性”品格的作品,皆離不開它們的反思性。
楊林的劇作或許稱之為經典還為時尚早,但從他作品中表現出的對現實、對人性、對英雄的思考,以及對“現實題材”創作視角的新把握,則是讓他的作品可以走得更遠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