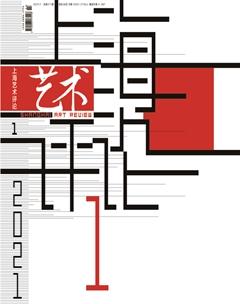西方經典歌劇的中國化呈現
李晶
自歌劇誕生之日起,所有神奇的東西都會在舞臺上運用,觀眾們不僅追求“聽”歌劇的享受,也追求“看”歌劇的樂趣。作為電影產生之前最具跨文化傳播力的舞臺戲劇,歌劇以舞臺制作與呈現區別于其他的藝術形式。舞臺制作是歌劇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它不僅提供場景的更換,提供劇中人物生活的環境,更是在推動劇情發展和營造戲劇氛圍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正是基于這一特點,歷史上留存至今的西方經典歌劇頻繁被制作為不同的版本上演,因而有了很大的傳播空間。
西方經典歌劇的“現代制作”
20世紀中葉,經典歌劇的舞臺演繹成為演出市場中最活躍的因素,導演的制作技術、手法日漸復雜,在舞臺呈現中的作用日趨重要。不少制作突破傳統的模式,運用象征性和抽象性的元素,重構歌劇的敘事,帶來新的創意和詮釋。例如導演彼得·塞拉斯(Peter Sellars)執導的《朱利奧·凱撒》《唐璜》《費加羅的婚禮》《魔笛》等歌劇。進入21世紀,現代歌劇院的旋轉舞臺、側臺、電視監控、數字照明系統以及瞬間換景和3D布景等設備運用與技術革新使得舞臺制作手法更為多元。如何運用現代媒體和元素,突破傳統制作模式,探索戲劇表達和音樂敘事更多的可能性,追求個性化理解與詮釋的“現代制作”成為西方歌劇發展的趨勢。1
“現代制作”中多元素共置所產生的舞臺表現,挖掘作品本身所蘊含的寓意,構建新的敘事方式,以多元化的視角為經典歌劇注入新的活力。這樣的案例在西方歌劇界不勝枚舉。以威爾第的《茶花女》為例,歷史上出現了多個令人難忘的新版制作。例如,2005年奧地利薩爾茨堡國際藝術節上演的由維也納愛樂樂團和國家歌劇院合作完成的《茶花女》。舞臺不再是19世紀巴黎上流社會的奢華生活,取而代之的是現代家庭生活。月牙狀的白色弧形舞臺中間擺放幾組沙發,每一幕沙發布變換色調以完成場景轉換。舞臺右側置放一個巨大的鐘表,具有強烈的象征意味,暗示茶花女最終的結局。同樣是大鐘,在導演彼得·穆斯巴赫(Peter Mussbach)執導的獨幕歌劇《浮士德,最后一夜》(Faustus,The Last Night,作曲家帕斯卡爾·杜薩潘)中別有一番意味。舞臺采用極簡設計,只有一個11個時間刻度的大鐘,浮士德和魔鬼梅菲斯特分別坐在分針和時針上對話。鐘表象征著時間與存在、生存與死亡、短暫與永恒,指向浮士德形而上的追問,奠定了歌劇基調。而鐘表邊緣的攪拌機則屬于偏移性設計,它意在提醒人們,不管絕對知識的誘惑有多大,生存往往還是依賴于衣食住行,這與整部歌劇的基調形成了背離,具有諷刺的意味。
西方當代的制作案例已向我們傳達了—個明確的信息:作為歌劇核心價值的戲劇和音樂固然重要,但制作手法和舞臺呈現同樣不容忽視,已成為歌劇藝術發展不可逆轉的潮流。那么,在這一潮流中,中國制作有哪些創新和突破,如何圍繞音樂本身和戲劇“立意”進行視覺呈現和意蘊挖掘,體現中國化呈現的獨特性,為世界貢獻中國智慧,成為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西方經典歌劇的中國化呈現
現階段,經典歌劇在中國擁有相對穩定的觀眾群,各大劇院既有與國外歌劇院的聯合制作,也有獨立制作,形成了以國家大劇院和上海大劇院領頭的,廣州大劇院、天津大劇院等緊跟其后的制作生產局面。以國家大劇院為例,自2007年大劇院建成以來,選擇歌劇藝術作為其制作的突破口,引進并制作了幾十部經典歌劇,在國內首屈一指。談及歌劇制作,陶辛教授在“歌劇理論評論人才培養項目”講座2中指出了歌劇現代制作的兩大理念:一是“裝修”,即在歌劇的原始劇本和音樂基礎上增光添彩,比如故事換一個地點,增加了新鮮感;二是“搭建”,原始文本和音樂是一個材料,加上各種舞臺的設計,多種元素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全新的敘事。當代中國的經典歌劇制作理念也不外乎于這兩類,但在具體的制作方案和手法上又呈現出不同的特點。結合中國制作的經典歌劇案例,大致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寫實主義制作呈現獨特創意
此類制作和呈現較為傳統,遵循原作的敘事和情節設計,又具有一定的創意,在國內經典歌劇制作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因其受眾面較廣,頗受歡迎。以2010年6月海寧·布洛克豪斯執導的國家大劇院版《茶花女》(La Traviata)為例。這版舞臺制作力求還原19世紀巴黎繁華奢靡的社交生活,采用獨特的、264平米巨幅的“鏡面”創意,將繪制在地板上布景圖、各種擺設裝飾直面呈現給觀眾,營造光影交織的效果,使原本簡潔的設計變得飽滿,與第一幕華麗的音樂、薇奧列塔的詠嘆調相得益彰。第三幕,薇奧列塔離世前的告別場景成為制作中最為精彩的一筆。當第三幕前奏曲響起,鏡子轉向了觀眾席,所有的觀眾都納入到舞臺的鏡子中去,觀眾不再是被動的接受者,而是歌劇表演中的參與者,這一點尤為震撼。在這一幕中威爾第通過音樂來揭示女主角告別人世前復雜的心理變化,而“鏡面”將女主人公的愛情與死亡無限擴大,并將觀眾納入到舞臺之中,更能引發觀眾對薇奧列塔悲劇結局的共鳴和反思。作為制作中最具標志性的元素,“鏡面”既展示了上流社會的繁華,又折射出薇奧列塔的卑微與弱小,象征著現實生活與理想世界的巨大反差。這版制作的立意在于,雖是發生在19世紀的故事,但依然具有現實意義,它像一面鏡子折射出人的內心世界,讓觀眾不斷品味其中的意蘊。
2017年12月,國家大劇院與維也納國家歌劇院首次聯合制作的歌劇《法爾斯塔夫》(Falstaff)在京首演。導演大衛·麥克維卡領銜的團隊力圖將劇中場景、人物造型與故事發生的時代達到高度的契合。《法爾斯塔夫》共三幕六場,制作團隊為觀眾呈現了六個不同場景,以精細的舞美制作還原了亨利四世時期英國小鎮溫莎的古樸景象。在旅館房間、貴族客廳、花園等場景中置放大量具有時代感的道具,比如騎士鎧甲、巨幅油畫、城堡地圖等物品。演員服裝中的細節,如百褶領圈、精美的刺繡禮服、華麗的晚禮服也一應反映出時代特點,細膩的設計展現了英國中世紀貴族的生活景象。第三幕第二場溫莎公園的舞臺設計頗有創意,一輪明月高掛天空,奇幻的燈光效果營造出神秘、奇異之感,為歌劇終場十重唱“凡事都是玩笑”的高潮鋪墊了氣氛。3
由上述案例可見,此類制作基本以原作背景和情節內容出發設計舞臺效果,與故事發生的時代契合,圍繞音樂的發展進行視覺呈現,整體效果豐滿而華美,創意上可圈可點,符合絕大多數中國觀眾的審美期待與理解,不失為普及和呈現經典歌劇的穩妥方式。
2.運用象征元素開掘歌劇內涵
西方經典歌劇的主題和情節本身往往具有進一步深入挖掘的潛力,有關涉當下的價值,因此不少制作中借用象征元素開掘作品的意義。以2014年9月國家大劇院上演的貝利尼《諾爾瑪》(Norma)版本為例。這部歌劇講述了高盧女祭司諾爾瑪與羅馬總督波利尼的愛情故事,全劇以“獻祭贖罪”為主線,諾爾瑪選擇犧牲自己走上火刑臺,塑造了諾爾瑪英雄、悲壯的女性形象。從整體設計來看,圓形作為主導元素貫穿三幕始終,根據音樂的發展和場景的變化進行不同的轉換,類似于音樂中的“主導動機”的手法,風格簡潔而統一,從而突出了作品的深刻寓意。
從場景設置來看,第一幕開場的圣林與最后一幕的神廟遙相呼應,兩處都是舉行祭祀儀式的地方。圓形的盾牌、神秘的圖騰、巨大的樹枝、高聳的廊柱等背景表現德魯伊教徒的信仰,營造神圣莊嚴的氣氛。巧妙之處在于,第一幕諾爾瑪率領族人祭祀月亮女神時,圓形的月亮隨著詠嘆調“圣潔女神”情緒的高漲,逐漸呈現為火紅色,與最后一幕祭壇上的紅色火焰相吻合,暗示著諾爾瑪的獻祭行為,以此凈化了仇恨與背叛,實現了“救贖”。
第二幕諾爾瑪的房間居于歌劇的中間位置,屬于私密空間,主要人物在這里卸下了外在的光環和面具,敞開心扉表達情感。這一幕的矛盾沖突是從諾爾瑪與波利尼的兩個孩子開始的。諾爾瑪懷疑波利尼移情別戀,意欲殺死兩個孩子,卻下不了手。在與阿達爾吉薩互相傾訴中,諾爾瑪得知波利尼的背叛,矛盾和沖突開始升級,在三重唱中達到了高潮。可以說,整部歌劇的主要矛盾和戲劇沖突都是在這一幕的場景展現的。同時,它也是劇情變化的轉折點,諾爾瑪從對波利尼愛情的回憶和期待轉變為對他背叛行為的憤恨,是導致最終悲劇結局的關鍵之處。所以,第二幕的舞美設計最為關鍵,導演運用象征手法將房間設計為凹室,垂下的白色的床單象征著連接母親和孩子的臍帶,不僅突出了諾爾瑪母親的形象,暗示矛盾的原點,也與第一幕諾爾瑪的公眾形象形成鮮明的對比。陰暗的光線、圓形飾板上的花紋增加了場景的神秘感,預示著不祥的發生。
同樣是圓形,在另一部歌劇中則具有別樣的寓意。2016年莎士比亞逝世400周年之際,國家大劇院隆重推出威爾第的第一部莎士比亞歌劇—《麥克白》(Macbeth)。貫穿全劇的象征元素是舞臺中間的圓,它是由不同的形狀組合在一起的,根據音樂和劇情的發展,在不同場景中組合、破裂,延伸出深層的涵義,揭示人類對權力充滿欲望的本性,從而引發對現實的拷問。第一幕,撕裂的圓形與女巫息息相關,陰暗燈光配合尖銳詭異的管弦樂,象征著超自然的黑暗力量;第四幕,舞臺中間懸掛代表審判的圓形,意味著麥克白夫人要為犯下的罪惡付出代價;劇中所有人物都在這個大圓之內,象征著命運的循環和輪回。
整部歌劇的燈光偏暗,冷色調,影射出麥克白、麥克白夫人內心深處的恐懼。尤其是第四幕麥克白夫人“夢游發瘋”場景,是歌劇音樂心理描述最精彩的地方,舞臺上一束追光照在麥克白夫人身上,配合著她喃喃自語的吟唱“消失吧,被詛咒的血跡”,生動地展現了她內心的痛苦和折磨。此劇的服裝設計可圈可點,不僅具有現代感,與人物性格和形象變化密切相關。尤其是劇中的女性—女巫和麥克白夫人的形象塑造上。第一幕第一場女巫們登場,身著白色蒙面長裙,怪異的表演動作配合荒誕的音樂表現出邪惡的力量。麥克白夫人的服飾變化較多,由第一幕的簡約過渡至第二幕、三幕的奢華,最后第四幕瘋癲至死時的服飾大致與女巫相同,暗示著兩者之間的關聯。
可見,歌劇制作中的象征元素是依據作品主旨、劇情提煉而來的,是為了能夠更好地營造音樂場景的氛圍,進一步揭示和挖掘作品精神層面的內涵。當然,歌劇本身應具有進一步深入挖掘的潛力,有關涉當下的意義和價值,這樣融合音樂、舞臺表演以及象征元素的呈現才能整體呈現出更好的藝術效果。
3.多媒體技術打造視聽奇幻效果
近年來,多媒體技術在歌劇中廣泛應用,主創團隊利用聲、光、電、多媒體電腦特技探索歌劇舞臺制作的可能性。前面討論的幾部歌劇或多或少都運用了多媒體技術。
2016年5月,國家大劇院制作的首部捷克民族樂派歌劇德沃夏克的《水仙女》(Rusalka)在京首演。導演烏戈·德·安納采用多媒體3D技術將藝術和技術結合,呈現給觀眾一個美輪美奐的海底夢境。戴著3D眼鏡“看”歌劇,無疑激起了觀眾的好奇心。燈光漸暗,音樂響起,海底世界浮現在眼前。4第一幕和第三幕展現的是水底世界,舞臺上移動的礁石隨著劇情和音樂的發展而變化;第二幕是王子的宮殿,擺放數個內置巨獸的玻璃罩,具有現代風格,意在強調真實世界與童話世界的對比,折射出人類內心的冷漠。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上演的一些中國新歌劇作品對多媒體的運用有一定的創新。以2018年10月在上海東方藝術中心上演的歌劇《畫皮》(編劇王爰飛、作曲郝維亞、導演易立明)為例。《畫皮》的舞臺制作材料很少,道具僅用一桌、一椅。多媒體技術的運用、演員的“摩登”服飾以及燈光色調的處理令《畫皮》呈現出視覺的“新”意。舞臺的不同部位設置了若干攝像機,捕捉演員與場景在某個瞬間的微妙變化,實時傳達上來,并將其投放到大銀幕上。一些象征意味的畫面配合著劇情和音樂的發展,比如“雨天”、姹紫嫣紅的花朵、朦朧的、長發女性的面龐等,展現了王生、媯嫣以及王夫人之間的羈絆與糾纏,直面人性,拷問現實,具有很強的思辨性和反思精神。這種“簡約”而不簡單處理方式,是這部歌劇制作的特色之處。這一點與筆者2015年觀看過的小劇場京劇《饅頭山》5有著類似之處。舞臺布置簡約,力求用最凝練的舞臺語言呈現復雜的劇情,足見戲曲傳統中有很多值得我們繼續深入挖掘的東西。
當然,不論現代媒體技術多么發達, 在多元素融合而成的歌劇中,它始終都應該為表現音樂、塑造人物、推進劇情、宣泄情感、營造氛圍而服務,這樣才能對歌劇的整體呈現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4.現代制作對戲劇意蘊的開掘
近年來,國內在經典歌劇制作上敢于突破傳統模式,引進和參與現代制作,從舞臺設計到文本詮釋呈現的是當代國際歌劇舞臺主流路線。現代制作更多地集中在瓦格納的歌劇。因為他的歌劇包含深刻的哲學理念和抽象的意義符號,有著豐富的詮釋性。2017年國家大劇院與美國大都會歌劇院、波蘭華沙國家歌劇院、巴登節日劇院聯合制作的新版《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Tristan und Isolde)具有先鋒性。歌劇背景從中世紀的海船轉變為現代戰艦,三層甲板與六個艙室將舞臺分隔成不同的表演區來實現場景的轉換。前奏曲演奏時,舞臺上出現一個圓形的雷達掃描圖,隨后與劇情有著密切關聯的重要意象依次展示,暗示著男女主人公的命運與結局。可以說,從前奏曲開始,舞臺上所有的安排和設計細節都與歌劇音樂有直接的關聯,這點不僅高明而且值得借鑒。
難能可貴的是,一些經典歌劇的現代制作從多角度挖掘戲劇意蘊,進行本土化處理,呈現出中國化的視覺效果和獨到的審美特色。
2016年3月,上海歌劇院首演了由易立明執導的威爾第的《茶花女》,將故事從19世紀巴黎的社交場,移植到20世紀20年代的國際郵輪上。郵輪場景的設計突破了《茶花女》傳統的場景模式,減少了制景成本和換景時間。此前,易立明執導的天津衛版《茶花女》第一次嘗試模仿昆曲唱腔的文體翻譯歌劇唱詞,使用民國時期外國人名字的中文譯法,將人物形象本土化、北方化。6上海郵輪版所體現的文化傳統和氣息與天津衛版大相徑庭,郵輪成為上流社會的縮影,充斥著各色人等,為舞臺呈現提供了更大的空間。薇奧列塔搖身變為“白色茶花號”的當紅歌手,阿爾弗雷德則是來上海闖蕩的法國富商的兒子,其他人物形象處理為郵輪上的職員,使故事情節具有了當下性。此版制作在原作的立意和結構基礎上尋求突破,大海暗示著一種無常的宿命,而海上的長途航行則象征著女主角漂泊動蕩的人生境遇,可見制作中的中國元素、“海派”風味具有合理性。如何將西方經典歌劇“移植”到中國文化土壤中,進行“本土化”制作,上海郵輪版《茶花女》無疑做出了有益的嘗試。7
從上述案例可見,經典歌劇的“現代制作”并非簡單的將故事移植到當下,更不只是通過布景、道具、服裝的時尚化拉近與當代中國觀眾的距離,而是要超越于對劇情字面的理解,著力于戲劇意涵上的開掘。在保留音樂文本的基礎上,如何通過現代元素的設計、本土化的處理以及表演方式的改變,對戲劇本身所隱含的寓意進行了外化和拓展,強化歌劇人物的社會屬性和形象寓意,賦予作品有個性的解讀和詮釋。
5.多樣化制作方式與手法探索
不同的制作方式將會使歌劇呈現出不同的藝術效果。除上述案例之外,當下的經典歌劇制作在不斷借鑒話劇、舞臺劇、電影等藝術門類的經驗,探索出新的方式和手法,如近年來引入的浸沒式制作、電影包裝手法、簡約式手法等等。2016年10月,北京國際音樂節引進倫敦寂靜歌劇團(Silent Opera)新版制作莫扎特的《唐璜》(Don Giovanni),2017年又帶來了雅納切克的歌劇《小狐貍》(Little Vixen),都采用浸沒式環境制作手法,打破了傳統的觀演關系,所有人都是演員,整個空間都是舞臺。同時,利用聲音技術的處理、電子合成技術以及無線耳機裝置將所有人包融在同一個聲場之中,讓觀眾與角色一起體會音樂當中所敘述的故事。
經典歌劇的音樂會版制作近年頗受業界推崇,不僅減少了裝景時間和道具服裝,制作成本得以降低,而且票價比較低廉,利于歌劇藝術的推廣。以廣州大劇院2013年5月制作的音樂會版本歌劇《茶花女》為例,劇中薇奧列塔三幕穿著不同的服裝,舞臺沙發的顏色隨著劇情發展而變化,根據音樂的表現采用了“追光”“射燈”“黑燈”等特別設計,在追求舞美視覺效果的同時增強了戲劇性,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總的來看,經典歌劇的中國制作在不斷進步的過程中呈現出兩大趨向:一是,堅持大眾路線。此類制作以原本的音樂戲劇文本為主,在舞美設計和布景裝置上不斷開拓新的詮釋方式,利用現代技術制造氣氛、渲染效果,在細節處彰顯獨具匠心的創意,從而達到延伸歌劇意蘊的目的。這一類歌劇制作重在培育觀眾、普及歌劇藝術,舞臺具有一定的形式,又兼具飽滿的質感,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當前國內觀眾的審美期待,因而在市場中占較大的比重和分量;二是,接軌國際路線。一些顛覆傳統、前衛的現代制作陸續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上演。現代制作以文本為依托,從原始音樂戲劇文本中提煉出一些元素加以放大,運用高度象征手法刻畫和塑造劇中人物,對于戲劇內容有了新的詮釋,制造了新的話題,引發了新的思考。這一類制作強調導演的中心地位,重在個性化語言的表達以及制作手法的實驗性和開拓性,具有很強的思辨性。現階段這類制作在國內市場的比重雖不大,但體現了與國際潮流的接軌,在一定程度上為中國歌劇的傳播與發展,包括中國原創歌劇、新歌劇的實踐提供了可借鑒的經驗。
從國內歌劇市場來看,西方經典歌劇受歡迎和接受程度與日俱增,其中有哪些制作經驗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對中國原創歌劇的創作和舞臺呈現又有著怎樣的啟發呢?筆者看來,歌劇的制作和呈現不論是“新瓶裝舊酒”還是在主題意義上的開鑿,都是建立在原作精湛的音樂寫作和富有邏輯建構的戲劇基礎之上的。進一步而言,一度創作至關重要,所謂“打鐵還需自身硬”,只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創作上,才能寫出具有深刻的戲劇思想命題、清晰的歌劇結構組織和鮮明的音樂性格的歌劇作品8,才有值得費力制作和深度挖掘的價值。其次,歌劇的舞臺呈現應緊緊圍繞戲劇的“立意”開掘,不能一味地追求宏大的舞美制作,也不能過多地依賴現代媒體技術,而是要從劇本和音樂出發,在思想上、“立意上”進行多角度的開掘,在當下意義和價值上做文章。再次,歌劇創作和制作應著眼于培育不同層次的觀眾,既不媚俗,又要向更高的層次引領觀眾,使其獲得深層次的精神體驗。
總之,經典歌劇在中國的呈現應保持傳統、穩步前進的同時,大膽探索新鮮的、多元的、本土化的現代制作,不斷推進獨立制作的能力和水平,生產出藝術精良、具有國際水準的版本。同時,通過對西方經典歌劇的引進、制作與學習,為中國歌劇創作積累經驗,為世界舞臺提供中國藝術家獨特的審美,貢獻中國的方案與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