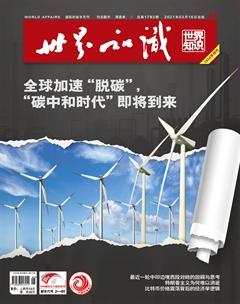最近一輪中印邊境西段對峙的回顧與思考
林民旺
2月25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同印度外長蘇杰生通電話,對去年以來兩國邊境對峙的既往教訓進行了總結,同時也表達了希望兩國關系重回正軌的愿望,從而為進一步改善兩國關系、推進務實合作積累條件。此前不久,中印邊境西段的緊張局勢也開始逐步降溫。2月10日,中印兩軍位于班公湖南、北岸的一線部隊開始同步組織脫離接觸。在實現班公湖地區一線部隊脫離接觸后,2月20日,中印兩軍舉行了第十輪軍長級會談,繼續就解決西段邊境其他地區的問題進行談判。一定意義上說,這次對峙事件正在朝逐步解決的方向發展,當然還可能存在一定的曲折和變數。
本輪中印邊境對峙已成為冷戰結束以來持續時間最長的兩軍對峙事件。如果從2020年5月6日加勒萬河谷地區發生兩國邊防人員肢體沖突算起,此次對峙已經持續了11個月之久。更嚴重的是,這次對峙事件導致兩國都發生人員傷亡,邊境管控機制受到嚴重破壞。特別是印軍蓄意攻擊中方交涉人員,首先在邊境地區開槍,打破了邊境地區的和平安寧。
印方在邊境對峙中的做法和思維
2020年爆發的邊境對峙實際上可分為兩個階段,前期焦點在中印邊境加勒萬河谷地區。2020年6月15日發生加勒萬河谷沖突事件后,雖然局勢緊張,但是現地按照軍長級會晤達成的協議實現了脫離接觸。對峙后期焦點在班公湖地區,主要是印軍在2020年8月底搶占班公湖南岸高地,制造了新的爭議點,擴大了邊境局勢的沖突面,一直延續到2021年2月10日才開始緩解。在這一過程中,印度對華政策的思維方式得到了充分展現。
一是印度行為邏輯的霸道和做法上的進攻性、冒險性。2017年洞朗對峙爆發的原因是印度宣稱出于所謂“安全關切”,印方人員越過邊界線進入中國領土。2020年對峙則是印方首先在加勒萬河谷地區抵邊越線修路架橋,單方面改變當地現狀,并且置中方多次嚴正交涉于不顧,蓄意挑起肢體沖突。印度在邊境地區的行為邏輯完全是霸道的,其自己的所謂“安全關切”必須得到照顧,卻絲毫不考慮挑釁侵略給對方造成的安全損失。
印度行為上的冒險性,充分展現在2020年8月底搶占班公湖南岸制高點的行動上。印軍通過一段時間的細致策劃,竟然采取所謂“先發制人”舉動,并且為阻止中方部隊維權而率先開槍,這極易引發誤判而導致嚴重后果。印度陸軍北部軍區司令喬希在2021年2月的采訪中就坦承,當時的現地局勢一度瀕臨戰爭邊緣。
二是印度試圖通過擴大爭議的方式來達成其圖謀。在中國對印度破壞現地狀況采取有力的反制措施后,印度非常清楚在邊境的基礎設施建設和行動能力方面自己追趕不上中國,于是提出雙方要將邊境狀況恢復到其挑釁之前(4月初)。在發現這一目標難以實現后,印方開始搞事來擴大爭議,以獲得對其有利的“談判籌碼”。以往邊境對峙發生后,印度一旦認為自己吃虧,往往會尋求在其有優勢的地方制造新爭議,“開辟新戰場”,并試圖將兩個爭議點相“掛鉤”。印軍對班公湖南岸的強占,顯然遵從的是相似的邏輯。
此外,印度高層還不斷放話稱,邊境問題是發展印中關系的前提。只有按照印方訴求解決了邊境對峙問題,才能發展印中關系。與之配套的具體做法是,在安全、經貿投資、人文交流等領域,印度不斷采取反華舉措作為“反制”。而且,印方還通過各個渠道放話,如果中方不在邊境問題上滿足其訴求,印度就要在中國敏感并關切的議題上改變過去的做法。
三是印度高層領導與印軍一線官兵在邊境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致的。過去常常將印軍越線和挑釁的舉動歸結于一線印軍軍官更大的決策權和“邀功”心態。在2018年兩國領導人的武漢非正式會晤中,兩國都共同表示要管控好一線官兵。在2020年6月17日的外長通話中,中方要求印方對6月15日加勒萬河谷事件進行徹底調查,嚴懲肇事責任人,嚴格管控好一線部隊。然而,實際的情形正如印度陸軍北部軍區司令喬希所說,一線印軍的開槍和各種舉動都得到了印度高層的授權和認可。
印度不僅不管束一線部隊,實際上還采取措施來刺激一線部隊的挑釁。印度不僅沒有公開調查和追責加勒萬河谷事件的肇事者,反而給死去的官兵搞國葬,還在印度“共和國日”聲勢浩大地嘉獎那些參與挑釁行動的印軍,如制造加勒萬流血沖突的上校巴布。簡言之,印方似乎并不希望在邊境地區“息事寧人”。
中國對邊境對峙的理性應對及經驗啟示
2020年發生的這場中印邊境對峙事件,與中美關系的急劇惡化相呼應,對中國外交與戰略構成了較大挑戰。中國以一貫的理性和克制的態度,堅決維護了國家領土主權,同時這場對峙也考驗了中印關系的“成色”。
與洞朗對峙相比,中國在這次對峙中表現得更加成熟。特別是,這次中國的整體表現可謂行勝于言。在整個對峙期間,中國很注重現地局勢的實際應對和控制,在實際對峙中現地不吃虧,而且始終站在國際道義的制高點上。特別是自始至終明確表示:整個事件的是非曲直是清晰的,責任完全在印度一方。隨著后續越來越多的情況披露,更是驗證了中方的有理有據。

2021年2月21日,市民自發來到河南省新鄉市延津縣烈士陵園,向在與越線挑釁外軍斗爭中壯烈犧牲的衛國戍邊英雄、一等功臣肖思遠的墳墓獻花,緬懷烈士。
在媒體輿論上,中國僅保持必要的官方回應和報道宣傳,客觀上有利于維護兩國關系整體大局。對外部的輿論炒作,中國并沒有一一回應,只是向國際社會提供了權威和連續一貫的事實介紹。更值得稱道的是,在幾次輿論引導上,中國還實現了主動。
中國在對峙中展現了堅決斗爭的一面,特別是大量官兵“陪”印軍在邊境過冬,顯示了捍衛領土主權的決心和意志。最終達成的兩軍脫離接觸,雖然沒有實質性地解決邊境問題,但是將邊境爭端暫時性地“凍結”了起來,減少了爆發沖突的可能。另一方面,中國也展示了善意和追求和平的態度,不斷通過外長會晤和通話、兩軍間的軍長級會晤,以及中印邊境事務磋商和協調工作機制等,與印方保持著各個層級的溝通。
在中印關系大局中,中國一向是維穩的一方,而印度則錯誤地抱有“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偏執態度。邊境對峙發生后,中國以大局為重,多次明確表明“中國對印度的政策沒有變化”;相反,印度高層卻高調宣稱,印度的對華政策回不到從前了。中國的高姿態,是否會在一定程度上助長印度的對華反制,還需要結合印度的文化背景,以及通過對中印關系歷史的研究來做出準確判斷。同樣,由于中印的文化差異,印方常常難以準確理解中方發出的信號。在兩國關系史上,經常出現印方似乎不懂互惠,也不識大局的例子。在是非曲直非常清楚的情況下,中方采取一些照顧印方情緒和顏面的做法,客觀上卻讓中國替印度政府“背黑鍋”。
(作者為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