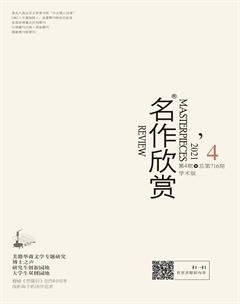歐陽修散文的魏晉情結
摘 要:魏晉風度是魏晉時期形成的特定文化產物,體現了魏晉時期的精神與文化內涵。魏晉風度表現為豁達、率真、灑脫,魏晉名士們熱衷飲酒,聚集清談,寄情山水自然。雖然名士們表面狂傲不羈,但內心卻十分苦悶。宋代的歐陽修受到魏晉風度的影響,表現出率真正直、熱愛飲酒、寄情山水等特征。
關鍵詞:歐陽修 魏晉風度 醉翁
“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痛苦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濃于熱情的一個時代。”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社會動蕩不安,殘酷的社會現實讓士人們產生逃避心理,寄情山水、崇尚飲酒、集會清談等,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如嵇康、阮籍、陶淵明等都對后世的文人們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歐陽修雖生活在宋代,但從他的散文中可以看出他熱愛自然山水、率真正直的人格精神。另外,他自稱為“醉翁”,可見他對酒的癡迷程度。
一、縱情山水,抒懷寄情
崇尚自然山水是魏晉風流的主要內容之一,魏晉時期的名士們對自然山水有著濃烈的熱愛。阮籍登山涉水,終日流連忘返;嵇康在山野中采藥,領略山水之美;而歐陽修也喜愛跋山涉水,感受山水自然風光。
《醉翁亭記》描寫了歐陽修的第一大樂,即山水之中的自然樂趣。“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可以看出歐陽修對山水之樂的表達是從美麗的自然景色中生發出來的。《豐樂亭記》描寫了挺拔高大的豐山之景,可見是僻靜清幽之處深得歐陽修的喜愛。歐陽修每日與滁州人士一同仰望高山,低頭俯視泉水,并采摘幽香的花草,在茂密的喬木下乘涼。文章又描寫了四時的風光,如刮風落霜、結冰飛雪、轉瞬即逝的晶瑩露珠,都是歐陽修寄情之景物。《有美堂記》贊揚了錢塘風光具備天下所有風景之美,而這有美堂又盡得錢塘風景之美,難怪歐陽修會如此喜愛這里。
二、率真正直,不拘禮節
歐陽修在性格和人際關系上,繼承了父親的正直和母親的堅強。他從小生活在逆境中,艱難坎坷的生活歷程造就了他剛正果斷的品格和堅強不屈的個性。壯年時,他敢于議論政事,有事沖在前面。只要他認為是正義的,他就會奮不顧身,勇往直前。如《朋黨論》言辭激烈直接,指出了君子的朋黨與小人的朋黨本質的區別:小人在意個人利益,而君子則在意國家利益。他指出,國君應支持君子朋黨,消除小人朋黨。歐陽修言辭直接犀利,足見他的性格。“英宗初年,未親政事,慈圣光獻太后垂簾。修與二三大臣佐佑兩宮,鎮撫四海。執政聚議,事有未可,修未嘗不力爭。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往往面折其短。英宗嘗面稱修曰:‘性直不避眾怨。”
《與高司諫書》這篇散文采用了按層次說理的方法,首先從縱向時間發展的角度敘述事情,虛寫了高司諫正直的品性,又用實寫來澄清其虛偽的本性,這樣前后頓挫,給人一種曲折的差距感;接下來又對比了范文正和高司諫的人格,在兩者的比較中存在著濃烈的批判精神;最后層層推進,依情闡述道理,對高司諫丑陋、卑鄙的行為進行批判,從而讓說理呈現出睿智鋒利的特色,真正做到了有的放矢、針針見血的論說效果。從語言風格上講,其體現了歐陽修愛憎分明、直言不諱的性格特點。他毫無遮攔地表達自己的喜怒愛憎,感情色彩突出,體現了一代文豪廣闊坦蕩的胸懷和直言不諱的個性。
歐陽修早在景祐年間(1034—1038),就以正直敢言而著名于朝廷。慶歷三年(1043),仁宗決定實行新政,封歐陽修為諫官。歐陽修為新政沖鋒陷陣,上至帝王,下至百官,他不怕別人記恨,直諫不諱,勇敢表現自我觀點,不拘禮節,可謂灑脫率真,與竹林七賢有一定的相同之處。
三、縱酒放達,傲視權貴
中國文人的命運與酒有著密切的聯系,究其原因,是文人自身在仕途命運起伏中借酒消愁,在美好的愿望與現實的反差中尋找慰藉。另外,文人在吟詩作賦、集體暢聊時也要飲酒助興。魏晉風度的代表人物阮籍,“幾乎是泡在酒壇子里度過一生的”。飲酒是魏晉名士的基本標志之一,阮籍愛酒如命,劉伶也是如此。魏晉名士愛酒如命,形成一股飲酒之風,對后世影響深遠。雖然歐陽修沒有愛酒如命,但他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響。
歐陽修在北宋是家喻戶曉的文學大家,屬于北宋具有標志性的人物,同時又是一代士風的開啟者。歐陽修被貶為滁州太守后,自號“醉翁”,顧名思義,就是喝醉酒的老翁。歐陽修經常被貶官,雖然有才但是不受朝廷重視,而且經常得罪人。按他自己的說法就是太清醒了,所以才有之后的寄情山水,才有之后的《醉翁亭記》。他自號為“醉翁”,主要是為了寄托不得志的情懷,借山水寄托惆悵。另外,歐陽修的散文也經常使用“酒”的意象,“《歐陽修詩詞全集》收錄了230首詩詞,其中沾酒字酒意的262處,平均每首詩詞1.14處,是真正意義上的酒氣沖天”。如《醉翁亭記》:“觥籌交錯,起坐而喧嘩者,眾賓歡也。蒼顏白發,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這一段描寫了宴會飲酒的場面:宴飲的樂趣,不是在于絲竹音樂,而是因為投壺的中了,下棋的贏了。觥籌交錯之間,大家歡聲笑語,那是客人們在歡鬧的場景。而歐陽修面容蒼老,頭發斑白,喝醉后昏昏沉沉地坐在人們中間。歐陽修喝醉后也樂在其中,可見飲酒給他帶來的歡樂。
四、歸隱田園,明哲保身
隱逸指隱居山林,逃避塵世。但隱逸并不是一種純粹的逃避和放棄,事實上,隱逸是一種有選擇、有目的、有價值判斷和精神追求的行為。隱逸行為既可以理解為對現實社會的一種間接的批評和質疑,也可以理解為一種對高潔、自由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李春青、桂琳的《雙重生存空間中的歐陽修——兼論歐陽修新型人格結構的生成》一文認為:“歐陽修開始的這種不同空間共存的生存方式則使士人階層嘗試建立一種融進與退,仕與隱,實現社會價值和保留個人意旨為一體的新型的人格結構。”
歐陽修在治平四年(1067)二月時被污蔑與長媳吳氏關系曖昧。雖后來得以證明清白,宋神宗也多次降手詔安慰歐陽修,但是歐陽修受此大辱,再無心參政。他決意求退,懇求外任,以保全晚年名譽,但沒有得到允準。他還寫了《歸田錄》,可見“歸田”已成為他一心追求的生活目標。熙寧四年(1071),歐陽修終于在得到神宗的恩準后,辭別官場,到潁水之濱頤養天年。他將名號改為六一居士,在《六一居士傳》中寫道: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于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
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
可見,歐陽修有一顆隱士的歸隱之心,雖幾次被貶是為了明哲保身,但是晚年時卻是真心歸隱。
五、結語
魏晉之時盛行隱逸之風,儒家、道家思想占據主導地位,儒家倡導進退有度,道家崇尚逍遙自在,兩者有相通之處。儒道交流融合的局面影響了隱士們的歸隱思想。歐陽修雖為宋代文人,卻在很多方面表現出魏晉風度。他縱情山水、抒懷寄情,率真正直、不拘禮節,縱酒放達、傲視權貴,最終歸隱田園、明哲保身。
參考文獻:
[1] 宗白華.美學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08.
[2] 陳新選注.歐陽修選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357-422.
[3] 劉德清.歐陽修論稿[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64.
[4] 孫萍.兩宋酒文化與文人命運的交融[J].文化創新比較研究,2019(6):46.
[5] 易中天.魏晉風度[M].杭州:浙江文學出版社,2015:81.
[6] 李春青,桂琳.雙重生存空間中的歐陽修——兼論歐陽修新型人格結構的生成[J].江西社會科學,2006 (4) :92-98.
基金項目: 本文系牡丹江師范學院科技創新項目《南北朝送別詩在藝術上的新變研究》(項目編號:kjcx2020-36mdjnu);黑龍江省教育廳基本科研業務費一般項目《唐宋文化轉型視域下的韓愈研究》(項目編號:1354MSYYB023)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 者: 譚常雪,文學碩士,牡丹江師范學院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
編 輯:趙斌 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