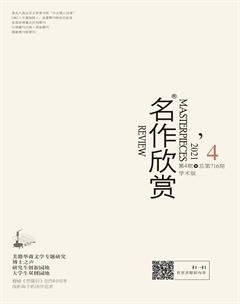反烏托邦文學中外構筑視角與方法差異分析
摘 要:長期以來,反烏托邦文學作為主流文學中的異數存在,是兼有自身特殊的美學氣質和揭示人類生存處境作用的文學體裁和流派。在20世紀文壇,喬治·奧威爾以其被譽為“反烏托邦文學三部曲”之一的著作《1984》享譽世界。而我國反烏托邦文學起步相較英美國家稍晚,王小波是國內該類型文學發展至高峰的代表作家,著有長篇小說《白銀時代》。他曾在作品里屢次提到其小說寫作深受喬治·奧威爾的影響,故造成部分讀者和評論家長久以來的一個共同誤區——即基于這兩位頂尖作家在寫作上的師承關系,中外反烏托邦文學萌芽和發展狀況等因素的綜合分析,認為中國的反烏托邦文學寫作模式是全面繼承西方的。本文旨在對“中國反烏托邦文學是西化和借鑒的產物”這一觀點進行質疑和反思,試圖分析中外反烏托邦文學構筑視角與方法的差異化,最終總結出中國反烏托邦文學中的民族性和創新性,從而帶領部分讀者走出誤區。
關鍵詞:反烏托邦小說 《白銀時代》 《1984》 構筑視角與方法 差異分析
反烏托邦文學的寫作重點和寫作特色集中體現在“如何構筑反烏托邦社會”。對于反烏托邦社會的環境構建、模式構建、人文構建等皆是展現作品獨特性的關鍵,這可被歸納為“文學的建筑性”。英國作家托馬斯·哈代對此提出:“一部小說應該像一個活的有機體那么完整,小說里的所有部分——情節、對話、人物和景色——應該渾然一體給人以一個完整和諧的建筑物印象。”文學作為二維的藝術,和作為立體藝術的建筑同屬文化作品,有著許多基礎的對應、影響和借鑒關系。因此筆者在行文中挪移建筑概念,以類比的方式進行小說的差異闡釋,以此更形象、深入地分析中外反烏托邦作家作品中對于“反烏托邦社會”構筑的差異。
一、價值理念差異——小說和歷史現實的關系
反烏托邦文學非常特殊,它突破了平面靜止的文字表現形式,成為一個時間性互動極強的動態文學種類。小說故事的發生普遍采取未來時態,情節發展普遍凝滯在科幻想象里,但是其文學意義所面對的卻是作者所處的當下時代,背景依據甚至可能是過去久遠的時代。這就形成了三種時態在同一部作品里的隔空互動,無疑復雜化了小說的時間線,豐富了小說的層次,增強了對小說現實意義探索的價值。因此在作家為其作品中所構筑的“反烏托邦社會”進行個人價值理念輸入時,往往逃避不開被問及其小說中的核心理念和所處時代的現實意義關系。
面對諸如此類跨時代性的文學意義追問,部分反烏托邦文學作家在作品表達中選擇巧妙避開,部分作家卻選擇迎而上,這就造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反烏托邦社會”宏觀構筑模式和兩種完全相反的價值理念。
在《白銀時代》中,作家王小波構筑的反烏托邦社會在社會要素的設定上有許多的“異化”之處。其基本模式、運行秩序、生存規律等都凌駕于現實社會之上。他用廣泛的隱喻手法巧妙地將現實意義和歷史暗示幾乎完全隱匿起來,而這種隱喻早已脫離了語言修飾和審美層面,上升到了對社會概念和社會要素的強有力價值總括。他僅用開篇首句的“未來的世界是銀子的。我寫著的小說和眼前發生的這一切,全靠這道謎語聯系著”來維系著小說中建立的反烏托邦社會與自己所處時代的神秘聯系。在描摹社會特質時,王小波用“銀子的物理性質”這一理性化的科學定律代替了可以傳遞作家自我價值理念和主觀態度的諸多感性化形容詞,以此將白銀時代所在的社會本質和深層主題隱藏起來,交予讀者自我分析。事實上,他所構筑的反烏托邦社會正是一個冷漠的、混沌的、金屬感十足的狠辣社會,這符合銀子作為稀有貴金屬的外部特征,對“導熱性”的合理解讀則落腳在白銀時代作為一個急功近利的、物質至上的社會,可以平均分配等量熱度的愚昧,致使該社會中的民眾擁有同樣熱度的盲目舉措和失智行為,從而在現代文明里逐步“退化”了;在描摹社會交流方式時,他將反烏托邦社會中的人際交流方式異化為“猜謎”。社會生活本質由此變成了一道隱喻的謎語,生活方式自然而然變成了更為異質性的猜謎行為。“猜謎”本身是一種游戲化思維的娛樂方式,也有猜測事物真相或語言真意的概念,但在白銀時代里,它卻成為一種主流社會的核心生活方式。這自然引發了讀者對于反烏托邦社會運行模式合理化的質疑,也順水推舟地契合了王小波對于該種社會的真實態度。
這樣從價值理念到語言細節的層層極致隱喻手法,并不是作者的炫技。王小波對于在作品中刻意模糊自己的價值觀念、隱藏現實意義曾正面表態:“有一些小說家喜歡讓故事發生在過去或者未來,但這些故事既非對未來的展望,也非對歷史的回顧,比之展望和回顧,他們更加關注故事本身。我在寫作時,討厭受真實邏輯的控制,認為起碼現實生活中的大多數場景是不配被寫進小說里的,所以,有時候,想象比摹寫生活更可取。”表面上,他是在逃避作品的現實意義,但實質上,他的真實價值理念是:比起對現實意義的表態,更注重小說文學性的保留和高級感的營造。因此,構筑一個凌駕于現實意義之上的社會,將現實與小說保持一定的距離,其目的是為了留出文學和現實影射之間的合理空間,并將這個想象空間交付讀者進行二次創作。
相比而言,喬治·奧威爾所構筑的反烏托邦社會從外部空間組合到內部運行規律都充分滿足了記憶歷史的功能,與作者所處的歷史環境幾乎融合在一起,現實意義十分諧調且清晰。換言之,他所構筑的1984年的反烏托邦社會幾乎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微縮版社會模型,細微差異在于,作家仍保持了文學的夸張性和虛構性,將“二戰”時代升級為一個寡頭政治意味更加濃郁的時代。作為小說真實背景的親歷者,喬治·奧威爾蓄意拉近了作品和現實的距離,刻意模糊了作品的未來時態,甚至小說的細節讓人質疑他所構筑的反烏托邦社會的“未來性”僅存在于主人公身上,而在他的構筑價值理念里早已被悄悄抹掉。喬治·奧威爾構筑了歷史特色極其鮮明的反烏托邦社會,旨在刻意讓讀者平行比較兩個社會。在《1984》里,奧威爾完全沒有隱藏構筑社會的價值理念,也沒有逃避現實意義的追問,他甚至利用主人公角色主動外泄自己被現實壓制的理念,從而進行作家私人化的社會性發言。在這部作品里,文學性是次要的,奧威爾更想記錄模擬現實感的社會,以此諷刺當世,呼吁被統治階級的人類覺醒。
二、角色設置技術差異——主人公的“社會學意義”VS“生物學意義”
在小說作品里,主人公通常是作者內心價值傾向的被賦予者。在反烏托邦社會中,主人公更是該種社會模式的核心實踐者和反饋者。《1984》里,喬治·奧威爾極其注重對主人公溫斯頓的形象塑造,這點從書名的前后變更可以看出。原書名為 《歐洲的最后一個人》,即指溫斯頓是黨統治下仍有希冀反抗的最后一個人格健全的人,以題目的命名來定性主人公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價值,足見其對主人公塑造的重視,后應出版商的營銷需求更名為《1984》。奧威爾極其注重主人公身上所涵蓋的社會價值,注重以個人力量攪動社會的過程和結果,因此將溫斯頓設定為一個社會學意義上的人,以此加強小說人物和社會的層層聯系。可以說,溫斯頓是奧威爾本人社會性發言的傳聲筒,作家借助第三人稱的人物口吻,從根本上傳遞出自己對于反烏托邦社會的真實評價和反抗過程。在《1984》中,溫斯頓是一個反抗行為積極的小角色,先后進行了對反烏托邦環境三個遞進層級的激烈反抗:文字反抗、思想反抗、情感反抗。這三大反抗的門類也被細化到了多個需要反抗的事物種類和具體方面,貫穿了日常生活中的幾乎所有可知的領域。
設定這樣“社會學”意義極強的主人公,對于讀者而言,閱讀體驗較為沉重。雖然借主人公之口,但作家價值理念的強勢傳遞依然從紙面透出,使讀者頗有“應接不暇”的感受。《1984》式的寫作,更多是以達到作家內心要求為初衷,傳遞價值理念是其第一性的要求。
而在《白銀時代》里,王小波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主人公定性方式,他將第一人稱的主人公“我”描摹為一個內斂含蓄,對反烏托邦環境消極冷漠,逆來順受的人。但這并不代表“我”贊同和融入了作者所構筑的反烏托邦社會,相反,作家再次使用了“異化”的巧妙手法,將主人公設定為一個生物學意義上的“怪人”,并將主人公對抗反烏托邦環境的方式從通常意義上的主觀意識行為轉換為罕見的“被動行為”,通過“我”身體部位的異化,以及身體機能的無意識反叛,造就了一種對白銀時代更為幽默、徹底,甚至更具力量的逆自然反抗方式。讓讀者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作為白銀時代社會里的一個普通成員,在身體外形上卻成長為“超大號”的人,僅僅是為了可以變得對社會“大而無用”,最終順其自然地被社會淘汰,變相逃離反烏托邦社會。這樣的主人公設定符合現代主義所推崇的基本精神——“誠實的意識”,即作家寫作不愿避開時代和社會的弊病,因此在作品中將人物傾心表現為荒謬、反叛等反面特點,是對類似于反烏托邦社會這樣災難化的社會模式的真實體驗感的反映。
這種對反烏托邦社會特殊的生理反抗方式,平靜、幽默、不激烈,甚至在社會表面上都留存不下一絲反抗過的痕跡。王小波用這種方式緩慢地、有界限地傳播自己的價值理念,因此帶給讀者的閱讀體驗是更易接受的,更值得深思的。
三、內容結構差異——“復調型”VS“獨白型”
根據文學的“建筑性”類比,作品的結構如同文學建筑的骨骼,作為支撐系統要承擔故事發展的多元因素,因此結構樣式各有不同。縱觀兩位作家對各自反烏托邦社會的構筑結構,形成了極致的區別。《白銀時代》所構筑的是一個擁有繁復的多層結構,故事輻射性極強的“文學建筑”,小說中事實上構筑了三個時期不同、人物設定和角色關系不同的小型反烏托邦社會:第一個時期講述的是主人公從中學時代過渡至職業生涯的生活故事,屬于現在進行時態,即構筑了一個“當代反烏托邦社會”;第二個時期存在于主人公編輯職業的一部作品《師生戀》中,是一個對第一時期生活內容的純粹幻想和文學性虛構,即構筑了一個“未來反烏托邦社會”。第三個時期是最為離奇的埃及封建社會時期,作家將其解釋為《師生戀》小說的另一種故事版本,同樣也是虛構手法,即構成了一個“古代反烏托邦社會”。因此,王小波在《白銀時代》里使用了復調小說手法,平行構筑了三個對立統一的反烏托邦社會,將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反烏托邦大環境和諧兼容起來,讓三個社會以其各自特有的屬性和時代風格作為獨立存在,同時彼此交融影響。它們僅作為反烏托邦模式的不同表現形式,并無小說地位的偏重之分。作家的主要意圖是讓“過去、現在、未來”“三個聲部”平等“發聲”,以此歸納從古至今的反烏托邦社會模式的共性。
《1984》則拋棄了結構的煩冗,仍舊堅持主人公溫斯頓足夠的小說篇幅分量和價值比重賦予,以“獨白型”建立內容結構。因此,奧威爾所構筑的反烏托邦社會僅有一個最主要的“時代發聲聲部”——即溫斯頓。小說通過溫斯頓的視角,傳遞對反烏托邦環境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所舉,運用大量對其的心理描寫,來完成對反烏托邦社會的構筑和重現。相比之下,其他人物的作用也僅是“助聲器”,幫助作家補充實現對反烏托邦社會的全方位、各角度的詳細剖解,如“茱莉亞”的存在,僅是為了助聲反烏托邦社會在人性本能層面的毀滅性,“奧勃良”的存在,則是為了助聲反烏托邦社會對民眾思想層面的根本性改造,夢境中的“母親和妹妹”的存在,則是為了正面助聲主人公對珍貴生動的、絕不妥協的感情的求之不得。
參考文獻:
[1] 段宗秀.論西方文學與建筑的關系[J].世界文學研究,2018,6(1):1-7.
[2] 王小波.白銀時代[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6:1 .
[3] 王小波.未來世界[M].上海: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2008:60-61.
[4] 楊春時.中國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非典型性[J].文藝爭鳴,2008(9):13-18.
基金項目: 2019年上海理工大學創新創業項目“精研·借鑒·創作——優秀作家作品語言特色研究及借鑒”,項目編號:“XJ2019244”
作 者: 歐陽晨煜,上海理工大學在讀本科生,研究方向:英語科技翻譯。
編 輯: 曹曉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