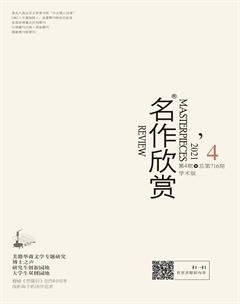凄涼與感傷,自憐與自戀
摘 要:丁寧是民國時期揚州著名女詞人,著有《還軒詞》四卷。其中,婉約詞“于藻采中見骨力,芬馨中出神駿,孤標傲雪,獨具風神”,內容上融自己的凄涼身世與感傷心境為一體,以《浣溪沙·丁卯二月》尤為典型。丁寧在詞作中還表現出了對于自己遭遇的自憐與才華的“自戀”傾向,具有鮮明的藝術特色。
關鍵詞:丁寧 《還軒詞》 婉約詞 藝術特色
丁寧(1902—1980),原名遂文、瑞文,喪母后易名懷楓。丁寧1902年3月5日生于江蘇鎮江東鄉老宅中,12天后生母病逝,次年因父親調任揚州兼八縣裕寧官銀錢局經理隨大母遷居揚州,先住古運河邊大十三灣,后搬至甘泉路雙桂巷12號宅子。1914年父親因兄弟鬩墻氣憤而亡,從此母女二人備受族人欺凌。丁寧受封建禮教的束縛,與黃姓男子結婚,在其凌辱之中生下女兒文兒。1924年2月13日女兒文兒因病去世,丁寧無法再忍受這樣令人痛苦的家庭,憤而提出解除婚姻,在亡父靈前發下毒誓永不再嫁,從此煢煢孑立,形影相吊,孤單一人。丁寧是民國著名女詞人,其《還軒詞》在民國詞壇占有重要的地位。劉夢芙在其《“五四”以來詞壇點將錄》中贊之“賦情之芳馨悱惻,有過于諸大家也”,并以“地彗星一丈青扈三娘”作比。這首《浣溪沙》作于1927年,是《還軒詞》開篇第一首詞作。
凄沁梨云夢不溫,冰鸞曇影渺無痕。清愁如水又黃昏。 芳草有情縈舊恨,游絲何計綰離魂。自甘腸斷向誰論。(《浣溪沙·丁卯二月》)
這首小令清晰地反映了詞人早期的情感基調與詞作特點,是一篇以個人的孤獨、環境的凄清為特點的自我感傷之作。首句,“凄沁梨云夢不溫”即奠定了全詞的悲涼基調。初春那微微的卻能絲絲入骨的涼風悄然溜進詞人的房間,甚至透入她溫暖的夢中。“梨云夢”巧用王建之典,卻盡顯哀怨之意。通常“梨云夢”依然是指代美好、可愛、令人纏綿且不舍的夢境,如明代許自昌《水滸傳·冥感》:“穆虹霓盟心,蹉跎杏雨梨云,致蜂蝶戀昏。”“杏雨梨云”的成語就出自這里。用“梨花云”之典,用意往往在于通過反襯,營造一種凄涼之意境、悲婉之心情。元人薩都剌《小闌·去年人在鳳凰池》云:“去年人在鳳凰池,銀燭夜彈絲。沉水香消,梨云夢暖,深院繡簾垂。”此處的“梨云夢”尚且還是溫暖、雅致的,但其只是薩都剌去年回憶中的美夢。元至順三年(1333),皇帝聽信奸臣讒言,將時任翰林國史院應奉的薩都剌貶為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掾史,離京南下任職,薩都剌對此深感不滿和悲涼,并融入今昔對比的蒼涼之感。由此可見,后人常將“梨云夢”作為一個反襯的“語碼”,隱約含蓄地表達凄涼悲愴的心境。再如清代鄧廷楨《水龍吟·雪中登大觀亭》:“關河凍合梨云,沖寒猶試連錢騎。思量舊夢,黃梅聽雨,危欄倦倚。”同樣運用了“梨云”之典。鄧廷楨是晚清的民族英雄,也是一位杰出的文人。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鄧廷楨因曾隨林則徐參與虎門銷煙,被誣削職,次年遠戍伊犁。本詞創作于他被革職之后,流放伊犁之前。“關河”是冷的,“梨云”是暖的,冷暖交加,盡顯悲涼,同樣也是反襯。而丁懷楓的這首《浣溪沙》在此處的反襯甚至比前人的更妙,除了一如既往的悲涼之外,她還巧將“梨云夢”的溫暖與初春之寒相搭配,身心俱有強烈的反差之感。“不溫”一詞也極妙,“不溫”不是“寒”,不是“冷”,只不過是在溫暖的環境下偶有凄風侵入房間、侵入心間所感到的不適,與前面內容相對應。
“鸞”即鸞鏡,《異苑》載“鸞睹鏡中影則悲”。在詩中多以鸞鏡表示臨鏡而生悲,如南唐馮延巳《南鄉子》:“鸞鏡鴛衾兩斷腸。”為何臨鏡而悲?悲的是什么?文人似乎很愛將臨鏡與“美人遲暮”“容顏不再”“時光易逝”“壯志難酬”等一系列負面情感聯系在一起。北宋詞人錢惟演有詞《木蘭花·城上風光鶯語亂》云:“情懷漸覺成衰晚,鸞鏡朱顏驚暗換。昔年多病厭芳尊,今日芳尊惟恐淺。”此詞是作者晚年謫遷漢東(今湖北隨州)時所作。公元1033年(宋仁宗明道二年)三月,垂簾聽政的劉太后崩,仁宗開始親政,即著力在朝廷廓清劉氏黨羽。與劉氏結為姻親的錢惟演自然在劫難逃。這首詞正是作于此時,離錢惟演去世尚不到一年。詞人臨鏡頓覺“朱顏改”,是因為他自然而然感受到了政治的動向,有“美人遲暮”之感是其心緒敏感的體現,抒發悲哀之情也是自然而然的。男性文人用女人的意象自然是詞體女性化內質的一脈相承,也是臣子對于君王、妻妾對于夫君的同等反映。在這里,“鸞”自身本就陰冷,而在前加一修飾之字“冰”,仿佛置身于漢代陳皇后冷宮中臨鏡自嘆一般,此處也頗有“奈煞西施”(影戀)的傾向。
“清愁如水又黃昏”則點明了時間,“黃昏”是即將進入夜晚的標識,人的生理與心理在此時都會進入低沉的狀態。在生理上,身體狀態相對較差,糖分消耗殆盡,血糖偏低;在心理上,光線的昏暗、氣溫的驟降也會帶動人思緒的擾動,在醫學上被稱為“黃昏憂郁癥”。在初春黃昏這個本就凄冷的時候發愁,這種愁苦的程度自然就攝人心魄。“清愁如水”則巧用了李煜《虞美人》的詞句“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足具藝術魅力。
下闋的景物意象使得詞人的情感表達漸入佳境,“芳草”“游絲”在詞人移情后更顯柔婉。春愁如同絲線一般縈繞著生意盎然的芳草,打破了一片完好美麗的景象,令讀者不得不悲嘆。“游絲”即空中飄飛著的細微的蛛絲,“離魂”是脫離軀體的靈魂,以似有似無之物牽絆住虛無的靈魂,這表明詞人的肉體本就是非常痛苦的,那么就只能將自己的精神寄托于塵世之外,逃離世間無窮無盡的“舊恨”。“游絲”與“離魂”兩個意象本就多由愛情生發,“萬丈游絲是妾心,惹蝶縈花亂相續。”(皎然:《效古詩》)“別后書辭,別時針線,離魂暗逐郎行遠。”(姜夔:《踏莎行》)黑格爾論及女性在愛情上的表現時指出:“愛情在女子身上特別顯得最美,因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現實生活都集中在愛情,她只有在愛情里才找到生命的支持力;如果她在愛情方面遭遇不幸,她就會像一道光焰被狂風吹熄掉。”由此來看,詞人在家庭夢想的幻滅后似乎是失去了生命的支持力,發出“自甘腸斷向誰論”的悲鳴。
女性詞作為一朵詞中“奇葩”,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與美感體驗,女性詞發展的過程是女性發現自我、定位自我的過程。從詞的表面來看,丁寧是一個痛失愛女與家庭的痛苦母親,詞作中表現出了凄涼與感傷;但是從深層面來看,丁寧也是一個心高氣傲的女性,詞作的字里行間也充斥了自憐與反抗的自我意識,顯現出了“影戀”的心理傾向。首先,詞中連用兩個否定式表達,即“不溫”“無痕”,一方面是對于一種安逸現狀的打破,是對于美的破壞,另一方面,表現了對于身邊生存環境的反抗,細微到甚至連溫度都能察覺到變化。如加繆所說:“何謂反抗者,一個說‘不的人。”她反抗一切使她陷入不幸的因素,對于外界的事物保持了一種高度的敏感與抗拒。其次,丁寧是一個極具天賦的才女,這種天性使得她具有高度的自戀心理傾向。《還軒詞》中喜用“鏡子”意象,預示著詞人自己正值青春,而這種臨鏡自我欣賞的行為頗符合“瘦影自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馮小青:《怨》)的“影戀”行為模式。潘光旦先生則說:“唯其體氣虛弱,精神郁結,故其應付環境中之刺激時,有特殊之選擇;若者宜容受,若者宜避免,其有機狀態每預為之地。刺激有屬空間者,有屬時間者,有屬氣候者,有屬天然景物者,有屬事物之動靜狀態者:要唯消極者是受。”生活環境的冷清未必是真正的冷清,實質是生理上的體氣虛弱與心理上的郁悶愁苦在外界的刺激下發生的反應,有的是承受甚至反抗,有的則是避免即逃避。而女性在這種身心的折磨下性心理就會出現“變態”傾向,即“影戀”。由于不存在自己情感的宣泄出口,這種臨鏡自戀就是一個合理的意象從而存在于詞作中。
夏承燾在《天風閣學詞日記》中多次夸贊丁寧:“讀丁寧女士詞,與玉岑可稱二難,誠令人俯首也。”丁寧一生經歷五陰熾盛之苦,背負著封建社會的壓迫、經受著傳統道德的束縛,屢遭困厄,孤獨一生,這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還軒詞》的總體基調是凄婉沉郁、幽咽悲涼的,如“三秋之衰柳”,如“五夜之驚鳥”,悲啼之音貫穿了這首《浣溪沙》,在抒情風格與美感上突出了“纖婉”的風格。在語言風格上,丁寧偏愛以冷色調、朦朧之物入詞,鋪敘描寫,融情入景,委婉細膩,且尤喜用視覺、聽覺、觸覺乃至感覺多個方面對讀者的身心造成身臨其境的效果,眼睛看到的地方毫無色彩、極盡荒蕪,耳朵聽到的皆乃午夜哀鵑泣血之聲,這是詞人選擇意象,也是意象人格化之后迎合了詞人抒情的需要。意象在組合之后成為意境,達到了悱惻動人的境界。
參考文獻:
[1] 劉夢芙.二十世紀名家詞述評 [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06.
[2] 丁寧.還軒詞 [M].劉夢芙編校.合肥:黃山書社,2012.
[3] 黑格爾.美學 [M].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
[4] 加繆.反抗者 [M].呂永真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
[5] 潘光旦.馮小青性心理變態揭秘[M].柏石,禎祥詮注.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
[6] 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記 [A].夏承燾.夏承燾集(第六冊)[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作 者: 王毅,揚州大學文學院古代文學專業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國詞學。
編 輯:曹曉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