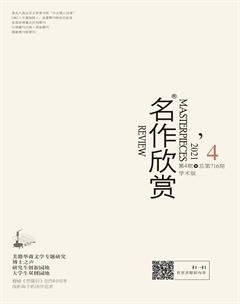淺析海子的詩學追求
摘 要:海子,一個被冠以多種頭銜的詩人,一個早逝卻“多產”的詩人。在從事詩歌創作的短短幾年內,他不僅創作出了兩百余首優秀的抒情短詩和長詩,也寫下了為數不多卻意義深遠的詩學文論。這些作品不僅顯示出海子獨到的詩藝,也從文本方面記錄了海子獨特的詩學追求。海子的詩學追求是動態、多向而具有開創性的,他醉心于純粹的自然描寫,也傾心于“實體”的自我表達,又“迫不得已”地追尋“大詩”的召喚。海子的詩學追求雖“受難”卻“幸福”,他孜孜不倦地探求,也成就了他的詩歌,把讀者帶入一個詩性蕩漾的理想世界。
關鍵詞:海子 詩學 純詩 實體 大詩
海子,“一個年輕、單純、天才、激烈、偏執”(西渡語)的詩人,在宏大的詩學空間中孜孜不倦地探索著自己的詩學道路。他不僅自覺地從語言和內容方面出發去創作純粹的“純詩”,而且潛心于對實體和史詩的探索。在海子看來,“詩,說到底,就是尋找對實體的接觸。這種對實體的意識和感覺,是史詩的最基本特質”a。海子特立獨行的詩學追求與他獨特的詩學理想交相輝映,造就了他最具獨創性的詩學品格,也為他贏得了極高的評價。伍恒山認為,“他是中國20世紀最偉大的浪漫主義的詩人,為中國的詩歌史開辟了一塊前無古人的天地”b。羅振亞認為,“海子詩歌中對神性品質的堅守,麥地詩思的原創性,主題語向的私有化以及個人密碼化的言說方式等諸多取向,都開啟了90年代個人化寫作的先河。因此說,海子詩歌是跨越80年代和90年代的不可逾越的藝術界碑”c。
當代詩壇,人們評述海子及其詩歌時,多以“意象”為切入點來對海子及其詩歌進行研究,海子詩歌中大量出現的“麥子”“大地”“太陽”等意象又往往容易使研究者滿足并止步于對海子“麥地詩人”“鄉土詩人”的評價,卻忽略了對海子詩歌理論層面的進一步挖掘。本文嘗試從詩學理論層面出發,著重對海子詩歌及其詩學追求進行詳細的考察,以期給海子一個準確的定位,對其詩歌進行深層次的解讀。
一、海子的“純詩”觀
“純詩”這一概念,作為一個獨立的詩學命題,一般被認為是由美國詩人愛倫·坡針對當時美國文學出現的嚴重的道德說教現象而首先提出的。愛倫·坡提出一個回歸文學本體的藝術構思,認為應當單純地為詩而寫詩,即“這一首詩就是一首詩,此外再沒有別的了——這一首詩完全是為詩而寫的”d。法國象征主義學派代表詩人瓦雷里發展并完善了“純詩”的內涵:“純詩的問題是這樣:……我們所稱為‘詩的,實際上是由純詩的片段嵌在一篇講話中而構成的。”e瓦雷里所認為的純詩實際上是從觀察推斷出來的一種虛構的東西,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清除詩中所包含的思想和觀念性成分,強調詩歌的自我表現功能;二是竭力避免詩形式上的“散文化”,追求詩歌的音樂性。
“純詩”觀念伴隨著法國的象征主義被引入中國,便迅速被“中國化”了,成為眾多詩人確立自身理論目標的藝術參照。“從梁宗岱走中國‘純詩之路拓寬了中國新詩的境界,到20世紀40年代,‘中國新詩派詩人群在詩歌創作中進行的與‘存在同在的哲學思考,中國新詩在尋找‘詩的藝術之旅上,越來越靠近自己的目標。其實,就一種純藝術追求而言,20世紀80年代中期‘第三代詩人欲從表象和修辭退出,直奔生命烈火,不惜把自己作為一個詩學元素投入其中的藝術欲求,以及20世紀90年代詩人整體的‘個人化純藝術趣味,都表明‘純詩理想一直潛滋暗長在20世紀中國詩學的理論構想和實踐沃土里。”“即使在今天,在中國詩人和批評家對詩歌本質、對詩與現實的關系的探討和反思中,馬拉美和瓦雷里的‘純詩觀念也時時像個幽靈一樣糾纏著人們。”f但對于“純詩”內涵的理解,在詩人那里卻并不能達成統一的認識。詩人們各自堅持著自己的見解,或單獨或合伙進行著實踐。
海子在《動作(〈太陽·斷頭篇〉代后記)》中曾對詩進行了簡單的分類:“詩有兩種:純詩(小詩)和唯一的真詩(大詩),還有一些詩意狀態。”從海子對詩歌的分類我們不難看出,海子應該是以“純詩”為目標而創作短詩的,也可以說,海子對于短詩和純詩這兩種詩歌形式含義的界定是重合的。在這里,我們著重從海子短詩的內容和語言這兩方面入手來探討海子的“純詩”觀。海子的短詩創作成就很高,他寫下了《亞洲銅》《面朝大海,春暖花開》《麥地》《四姐妹》等多首著名的詩篇。用心品讀海子的這些短詩,我們會發現海子的短詩里包含更多的是詩歌主體的自我傳達。如《跳躍者》:“老鼻子橡樹∕夾住了我的藍鞋子∕我卻是跳躍的∕跳過榆錢兒∕跳過鵝和麥子∕一年跳過∕十二間空屋子和一些花穗∕從一口空氣∕跳進另一口空氣∕我是深刻的生命∕我走過許多條路∕我的襪子里裝滿了錯誤∕日記本是紅色的∕是紅色的流浪漢∕脖子上寫滿了遺忘的姓名∕跳吧∕跳多了我就站住∕站在山頂上沉默∕沉默是山洞∕沉默是山洞里一大桶黃金∕沉默是因為愛情。”老鼻子橡樹觸發了詩人的滿腔情思,“從一口空氣∕跳進另一口空氣”。海子直言不諱地傳達著自己的愛情,借著這些常見于自然界里的平凡物象的“自我表達”,海子也把自己對愛情的思考描繪得淋漓盡致。在其短詩中,海子迷戀于描繪“原始粗糙的感性生命和表情”,著重強調“詩不是詩人的陳述。更多時候詩是實體在傾訴。你也許會在自己的詩里聽到另外一種聲音,這就是‘他的聲音。這是一種突然的、處于高度亢奮之中的狀態,是一種使人目瞪口呆的自發性”。他把創作對象集中在大地、麥子、水、橡樹、榆錢、鵝、花穗等自然事物上,“直接關注生命存在本身”,海子儼然開始實踐著自己的“純詩”夢想。
在海子看來,“中國當前的詩,大都處于實驗階段,基本上還沒有進入語言……當前中國現代詩歌對意象的關注,損害甚至危及了她的語言要求”。海子對于詩歌語言的“純詩化”追求較之他人顯示出極大的不同。海子認為“詩人必須有力量把自己從大眾中救出來,從散文中救出來,因為寫詩并不是簡單的喝水,望月亮,談情說愛,尋死覓活”。顯然,海子在詩歌的創作中,已經充分認識到了詩歌的語言方式,“人們應當關注和審視語言自身”,“新的美學和新語言新詩的誕生不僅取決于感性的再造,還取決于意象與詠唱的合一”。海子對于意象與語言的探索,也正是其把握“純詩化”的切入點。在海子的許多詩歌中,海子十分注意自己的語言實驗。他不僅嘗試中國民間歌謠的語言表達形式,如《謠曲·之二》中“白鴿白鴿你別說∕美麗的腦袋小太陽∕到了黑夜變月亮∕白鴿白鴿你別說”;也借鑒日本民間詩歌的語言敘述方式,如《主人》中“你在漁市上∕尋找下弦月∕我在月光下∕經過小河流∕你在婚禮上∕使用紅筷子∕我在向陽坡∕栽下兩行竹∕你的夜晚∕主人美麗∕我的夜晚∕客人笨拙”。海子對語言規范的要求近乎苛刻,他把一系列幻想的、實際的、真實的、虛無的、詩意的、平淡的且互相之間似乎毫無關聯的意象融入語言。這些相互摻雜、互相碰撞的意象所產生的特殊韻味,與海子明澈的、區別于散文的語言融會貫通,從而成就了海子的抒情短詩,即“純詩”。
二、海子的“實體”觀
“尋找對實體的接觸”是海子的另一重要詩學追求。在其詩論中,海子反復引入實體這個概念:“詩,說到底,就是尋找對實體的接觸。”“詩不是詩人的陳述。更多時候詩是實體在傾訴。”海子的詩歌以實體的視角來審視一切,海子把土地、河流、月亮等視為“巨大的物質實體……希望能找到對土地和河流——這些巨大物質實體的觸摸方式……用自己的敏感力和生命之光把這黑乎乎的實體照亮”。可以說,海子對于“實體”的傾慕已經到了“走火入魔”的境地。那么,實體是什么呢?海子為什么那么執著于追求實體呢?
實體,是一個哲學概念。亞里士多德曾對實體下過這樣的定義:“實體,在最嚴格、最原始、最根本的意義上說,是既不訴說一個主體,也不存在一個主體中。”“近代哲學正是用這種實體概念來規定世界的,世界就是由實體構成的,或者說,就是一個巨大的實體。”g實體的內涵經過笛卡爾、斯賓諾莎、萊布尼茲、康德、黑格爾等人的不同詮釋,被賦予了不同的含義。從海子的詩歌及其文論來看,海子對于“實體”的認識和理解正是來源于哲學領域的。“從后來的詩歌及其文論來看,在對整個人類文化浩海長川風景的領略中,海子又是深得德國古典哲學文化精髓的人……而與歌德同一時代,18世紀末葉德國圖賓根神學院的兩位同窗好友——荷爾德林與黑格爾則更是海子直接的精神導師和他視作知己的人。”h海子的實體觀基本上繼承了從黑格爾那里發展下來的對于實體的認知,認為實體是客觀存在的認識對象。“海子站在超越的立場上,把‘彼岸世界也當作理想中的實體來追求。他把理想中詩意棲居的家園建筑在‘彼岸世界和‘自在之物等的綜合上,這就是海子獨有的實體觀。”i顯然,海子已經將對實體的理解融入了自己的詩歌觀,一個哲學概念和一個詩學元素的融合也顯然發生了奇妙的作用,使海子的詩學追求通向“民族的心靈深處”,進而“歌唱自身”。
海子寫詩,就是要回歸實體,就是要在回歸物象本體的基礎之上重新進行藝術創造。在海子看來,所有的物象本體都是活生生的,是具有生命和靈性的。在感性層面,所有的物象都是平等的,它們都有著自己的特性,有著屬于他們自己的“情感”,是和感性層面意義上的“人”這個個體一樣平等地存在于這顆星球上的。詩人所要做的應該是獨立發掘這種特性,發掘這些原始粗糙的感性生命和表情。《河流》是一首涵蓋廣闊并帶有詩人心靈自傳特色的長詩:“你誕生∕風雪替你鑿開窗戶∕重復的一排∕走出善良的母羊∕走出月亮∕走出流水美麗的眼睛∕遠遠望去∕早晨是依稀可辨的幾個人影∕越來越直接的逼視你∕情人的頭發尚未挽起∕你細小的水流尚未挽起∕沒有網和風同時撒開∕沒有潔白的魚群在水面上∕使我想起生殖∕想起在滴血的晚風中分娩∕黃金一樣的日子∕我造飯,洗浴,趕著水波犁開森林∕你把微笑擱在秋分之后∕擱在瀑布睡醒之前∕我取出∕取出……”在《河流》里,河流作為實體已經被海子賦予了靈性,已經成為活生生的具有生命特色的元素。海子不斷地尋找對實體的接觸,不斷地回歸實體。在這個持續的回歸過程中,海子一直嘗試著實體的自我表達,不停地深入實體,探求實體。“你應該體會到河流是元素,像火一樣,他在流逝,他有生死,有他的誕生和死亡。必須從景色中進入元素,在景色中熱愛元素的呼吸和言語,要尊重元素和他的秘密。你不僅要熱愛河流兩岸,還要熱愛正在流逝的河流自身,熱愛河水的生和死。有時熱愛他的養育,有時還要帶著愛意忍受洪水的破壞,忍受他的秘密,忍受你的痛苦。”從海子的這段文論中,我們不難看出,海子對于實體的追求是如何的狂熱,如何的“不能自拔”。
三、海子的“大詩”追求
海子在《詩學:一份提綱》中曾聲稱:“我寫長詩總是迫不得已,出于某種巨大的元素對我的召喚,也是因為我有太多的話要說,這些元素和偉大的材料的東西總會漲破我的詩歌外殼。為了詩歌本身——和現代世界藝術對精神的壟斷和優勢——我得舍棄我大部分的精神材料,直到它們成為詩歌。”海子執著地追求大詩,強烈地表達自己對于大詩的期望,希望“融合中國的行動成就一種民族和人類的結合,詩和真理合一的大詩”,并激情澎湃地投入其中,嘗試大詩的創作。
海子認為,“偉大的詩歌,不是感性的詩歌,也不是抒情的詩歌,不是原始材料的片段流動,而是主體人類在某一瞬間突入自身的宏偉——是主體人類在原始力量的一次性詩歌行動”。顯然,海子是從整個詩學的角度來探求大詩意義的。海子認為“在偉大的詩歌方面,只有但丁和歌德是成功的,還有莎士比亞”。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海子理想中的“大詩”是十分深邃并且難以輕易寫就的。盡管成就“偉大的詩歌”十分艱難,但是海子對此卻始終報以樂觀的態度并預言:“這一世紀和下一世紀的交替,在中國,必有一次偉大的詩歌行動和一首偉大的詩篇。”
從已問世的海子的詩歌著作來看,海子的史詩即大詩主要有《太陽·斷頭篇》《太陽·土地》《太陽·大扎撒》《太陽·你是父親的好女兒》《太陽·弒》《太陽·詩劇》《太陽·彌賽亞》七部。在海子這些引以為豪的“大詩”中,其史詩的內容和語言最能體現他的“大詩”追求。海子的“大詩”輪廓宏大,包羅萬象;故事情節曲折,幻想奇特。海子的“大詩”元素浩繁:不僅包含山川、大地、月亮、太陽、朝霞、沙漠等自然元素,還容納了豹子、公牛、馬、羔羊、鷹等生命元素。這些原始的自然生命元素在海子的“大詩”中匯合,生命輪回與四季循環相互交織,以一種前所未有的組合形式得到交流、反應甚至“變異”,便立刻呈現出一種咄咄逼人的態勢和一種全新的絕無僅有的面貌。在他的筆下,“太陽”和“水”不再是死的沒有靈性的自然物,而幻化為靈魂的奧秘載體和哲學意蘊的載體:詩中的“水”已經外化為一汪生機盎然、靈性四溢的生命水,“水”的內蘊已經從原本的原始物象上升為人水之間貌似神合的生物體,已經成為包容萬物的精神象征,具備了哲理合一的特性,切入了東方文化精神的中心;詩中的“太陽”也已經成為生長和燃燒著的生命元素,成為詩人借以表達詩歌理想的得力“助手”,成為一個集歷史榮辱、精神命運為一體的哲理集合體。
海子的“大詩”充滿了原始的、生動的靈性,海子迥異于他人的“大詩”追求已經完全使他本人進入了一個瘋狂的境地。與他充滿幻想、結構宏大的“大詩”內容相比,他的“大詩”語言也毫不遜色。在海子看來,“中國當前的詩,大都處于實驗階段,基本上還沒有進入語言……當前中國現代詩歌對意象的關注,損害甚至危及了她的語言要求”。海子對于詩歌語言的要求是極高的,他并不滿足于平淡的詩歌語言,他曾在他的日記中這樣寫道:“舊語言舊詩歌中的平滑起伏的節拍和歌唱性差不多已經死去了。死尸是不能出土的,問題在于墳墓上的花枝和青草。新的美學和新語言新詩的誕生不僅取決于感性的再造,還取決于意象與詠唱的合一。意象平民必須高攀上詠唱貴族。”海子所追求的語言是動態的,是具有獨特的音韻意味的。如在《太陽·土地》中,他寫道:“壯麗的豹子/靈感之龍/閃現之龍 設想和形象之龍 全身全身燃燒/芳香的巨大老虎 照亮整個海灘/這灰燼中合上雙睛的閃閃發亮的馬與火種/獅子的腳 羔羊的角/在莽荒而饑餓的山上/一萬匹的象死在森林。”詩中豐富的原始意象、新穎的另類修飾、動態的音韻語言互相交雜產生的特殊韻味使其長詩體現了一種獨具個人特色的形態。
四、海子詩學觀念的演變
對于海子詩學追求的演變歷程,海子的生前好友西川曾這樣描述:“海子期望從抒情出發,經過敘事,到達史詩,他殷切渴望建立起一個龐大的詩歌帝國:東起尼羅河,西達太平洋,北至蒙古高原,南抵印度次大陸。”j海子追求詩歌的“純詩化”,持之以恒地“尋找對實體的接觸”,并以此為契機而走上了他所認定的“大詩”創作之路。
綜觀海子的詩歌創作,細加分析其詩歌意象,可以發現,從“純詩”到“大詩”有著一條很清晰的演變脈絡。海子的早期詩歌以短詩即純詩為主,在海子的許多帶有鄉土氣息的純詩中,經常映入讀者眼中的是高粱、蘆花、流水、小船、井、木頭、麥子、小花等一些質樸簡單的意象,這些質樸簡單的意象不僅是他對自然界里原始物象的摘取,也是他自己的情愛和自然界里平凡生命活動的有機交融。這些散布在海子詩歌各個角落的質樸簡單的意象,使他迷戀純粹自然的情結得以一覽無余,也鮮明地反映了海子“純詩化”的詩學追求。后期詩歌中,海子的注意力已完全轉向“大詩”,此時海子大詩中的多數意象已變得十分沉重,詩中反復出現的多是太陽、海洋、土地等龐大的意象載體。在其大詩中,海子一遍又一遍地拷問靈魂,探索生死。在海子看來,那些活生生的原始物象帶給他的已不是幸福和歡笑的“牧歌”,而是死亡和淚水的“交響樂”。面對那些具有生命和靈性的實體,海子感受到的也已不是平靜,而像是野獸在咆哮。海子在他的大詩里曾不止一次地渲染沖突、戰斗、燃燒、混沌、盲目、殘忍甚至黑暗,在他的詩里,一切都被毀滅和重造:大部分物象都被他用“黑夜籠罩”,都被他用“太陽的光輝加以灼燒”。從早期意象的“質樸”到后期的“沉重”,海子從“純詩”到“大詩”的詩學觀的轉變更加鮮明。
而在“純詩”到“大詩”演變過程中起至關重要作用的卻是海子對“實體”的不懈追求。實體這一概念是海子詩論中的主要元素,“尋找對實體的接觸”貫穿于海子的整個詩學追求歷程。不論是早期對“純詩”的追求,還是后期對“大詩”的探求,“尋找對實體的接觸”都一直貫穿其中。“尋求對實體的接觸”是海子詩歌的出發點,他幾乎所有的詩歌都在努力探尋原始的巨大的物質實體,渴望通過對實體的把握來達到描繪純粹自然的目的,希望通過這種對實體有意識的接觸來完善自身的史詩特質,進而通向“民族的心靈深處”,實現自己“偉大的詩歌”的理想。
海子是一個執著的浪漫主義精神追求者,他渴望純粹地描繪自然,強調“實體”的自我傾訴,夢想成就集體的民族大詩。海子不斷完善自己對詩學的追求,不管是“純詩”“尋找對實體的接觸”,還是“大詩”,海子始終如一地嘗試著自己的詩歌理想,希望創作出“更高一級的創造性詩歌”,以達到“人類形象中迄今為止的最高成就”。
a 海子:《海子詩全集》,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7頁。(本文有關該書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b 伍恒山:《海子傳》,江蘇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2頁。
c 羅振亞:《海子詩歌的思想與藝術殊相》,《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7年第1期。
d 〔美〕愛倫·坡:《詩的原理》,見楊烈:《準則與尺度——外國著名詩人文論》,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頁。
e 〔法〕瓦雷里:《純詩——一次演講的札記》,見豐華詹:《現代西方文論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頁。
f 王家新:《為鳳凰找尋棲所》,見《為鳳凰找尋棲所·現代詩歌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70頁。
g 李文閣:《回歸現實生活世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頁。
h 燎原:《撲向太陽之豹·海子評傳》,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65頁。
i 萬孝獻:《實體之死——論海子詩學觀的轉變歷程》,《湖南科技學報》2006年第9期。
j 西川:《懷念》,見伍恒山:《海子傳》,江蘇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220頁。
作 者: 王繼國,文學碩士,聊城大學東昌學院中文系教師,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
編 輯:趙斌 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