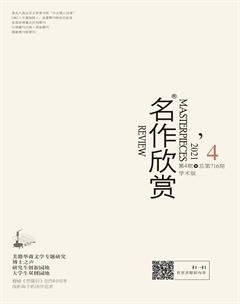主流話語視域下21世紀詩歌一瞥
摘 要:21世紀詩歌呈現出多元分化格局,主流與支流并行,秩序與雜蕪并立,機遇與挑戰并存,在喧囂的表面下隱現著種種困境。循著左翼詩歌一脈發展的“主流詩歌”曾在很長一段時間占據當代詩壇的主導地位,20世紀80年代以來則因其過于濃重的意識形態色彩導致的審美價值削弱而招致批評。進入21世紀的“主流詩歌”,上承左翼文學精神傳統,下繼個人化寫作浪潮,嘗試在公共性與個人性之間取得平衡。這種探索不僅有利于其自身詩歌樣式的完善,也為21世紀詩歌發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關鍵詞:左翼文學傳統 個人化寫作 主流話語 21世紀詩歌
一、相關概念的界定
“21世紀詩歌”是“21世紀文學”這個概念的自然生發,但其不只是單純地從時間維度展開,更多是一種具有審美特征的文學史概念。“21世紀詩歌”概念是在新詩發展過程中緩慢孕育的,很難準確界定其起點,但一般而言,1999年的“盤峰詩會”及與之相關的“盤峰論爭”是“21世紀詩歌”這個概念“一個最好的,也是最有價值的‘歷史關節點”a。“話語”概念最早由福柯提出,區別于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提出的“語言”和“言語”,是指與社會權力關系相互纏繞的具體言語方式。b文學即是一種話語,而且是一種以“審美意識形態”方式運行的社會實踐。c“主流話語”是一種體現了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體系,在一個社會中占主導地位,并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對其他話語進行規約。“主流”的釋義,一般指“占據主導或中心地位的(方面),與支流、傍流相對”。本文中的“主流詩歌”概念,則是從當代主流話語視角出發,指一種主要受主流意識形態影響,傳遞主流話語的詩歌樣式。“主流詩歌”在新詩發展的各個階段有不同形態,在當代也被稱作“主旋律詩歌”“體制內詩歌”等。“民間詩歌”是相對于“主流詩歌”而言的概念,在當代也被稱作“體制外詩歌”“亞體制詩歌”等,是一種民間立場的詩歌樣式。本文所用的“民間詩歌”概念主要參照陳思和先生對文學中民間立場的闡釋:“在實際的文學創作中,‘民間不是專指傳統農村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宗法社會, 其意義也不在于具體的創作題材和創作方法。它是指一種非權力形態也非知識分子精英文化形態的文化視界和空間, 滲透在作家的寫作立場、價值取向、審美風格等方面。”d
二、個人化寫作與21世紀詩歌的多元分化格局
改革開放以來,較為寬松的文化政策和由經濟開放帶來的觀念開放,為文學提供了一個有利的發展環境。雖然“新時期文學”的命名與政治關系密切(“關于新時期文學的歷史起點,有四種代表性的學術觀點,即分別以‘四五運動、20世紀六七十年代、十一屆三中全會、第四次文代會為新時期文學的開端”e),但作為其發端的“朦朧詩”,卻是“產生于對主流思想文化的懷疑與潛在反抗”f。由于過去政治對文學的干預,新時期詩歌對主流話語的介入懷有一定警惕。但“朦朧詩”的這種“反抗”本質而言仍是置于主流話語語境之中,與當時“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主流話語相呼應。對新時期文學的敘述,正是通過“思想解放”來完成的:“這場思想解放的春風,催發了新時期文學園地的芳菲桃李。而新時期文學本身,對思想解放運動又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g新時期詩歌此時仍自覺地擔負起時代的使命,與主流話語在表面的疏離中又聯系緊密。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在反朦朧詩的旗號下,詩歌向個人化寫作轉向。這一時期的詩歌,“由于排斥和厭倦以往那種意識形態的強加,竭力躲避被動的詩對于政治的圖解,于是鮮明地強調詩的藝術屬性”h。在新詩創作實驗的名義下,詩歌的思想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拋棄,而淪為完全個人的產物,某種意義上又滑向了另一個極端。“詩一旦表現重大的主題,或是被希求為一定的主題發言,此舉就會無例外地招來質疑并受到鄙薄,以為‘政治又回來了。事情正好來了個倒換,這就是新的歷史時期的‘政治恐懼癥。”i這當然是令人遺憾的,正如謝冕先生所說:“今天,我們理所當然地為文學重獲自由而感到欣悅。但這種無所承受的失重的文學,又使我們感到了某種匱乏。”! 0
隨著市場化轉型的深入,20世紀90年代文壇興起了個人化寫作浪潮。“個人化寫作”是一個很難被定義的概念,最初提出者也很難追溯,但確實是90年代最具影響的文學現象。不同學者圍繞“個人化寫作”有著不同界定,這種差異主要是由不同的參照系所致,例如同“宏大敘事”相對的“個人小敘事”;同“集體經驗”相對的“個人經驗”;同“共名”相對的“無名”等。! 1但“個人化寫作”產生的語境還是比較明晰的,源自“一種創傷性的記憶,一種對于公共生活的不自主的回避”! 2。這一時期的個人化寫作,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對公共性的疏離。
21世紀詩歌延續了90年代的個人化寫作! 3,而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繁榮、大眾傳媒的蓬勃發展,以及網絡普及等外部因素,詩歌的個人化寫作實際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遠超90年代。進入21世紀,不同話語體系同時存在,文學的多元分化格局仍未被打破,并且由于詩歌寫作門檻的進一步降低,21世紀詩歌的多元分化格局更加鞏固。詩歌曾在21世紀最初的十年陷入一場“狂歡”,對于一些初入詩壇的詩歌寫作者而言,詩歌原有的價值體系被剝離,自身就可以是衡量詩歌好壞的標尺。“21世紀詩歌呈現出離心、彌散的態勢,其體量增加,邊界得到了相當程度的擴展,內部充滿了差異性與復雜性,價值觀念、審美取向、藝術技法等方面的探索在不同的向度上得到了展開。”! 421世紀詩壇的多元分化格局給詩歌發展同時帶來了機遇與挑戰,但總體而言,機遇大于挑戰。
三、21世紀詩歌兩種話語的合作與融合
盡管詩歌“邊緣化”概念已基本成為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詩狀況描述的共識,并通常被視作負面判論,但進入21世紀,詩歌“一方面喪失了傳統的崇高地位和多元功用,另一方面它又無法和大眾傳媒競爭,吸引現代消費群眾”! 5,這種“雙重邊緣化”反而使詩歌得以回歸本身,而不必承載過多本不屬于它的東西。詩歌的“常態化”使得主流話語和民間話語爭奪詩歌主導權的角力有所緩和,減弱了二者的對立程度,由此為兩種話語的合作創設了一定場域。一方面,主流話語不再強加于詩歌,“政治環境、文藝政策對文學的作用,表現出間接性、潛在性、混合性的特征,政治對文學的治理在反思硬性管控方式的基礎上,采取更加軟性的方式”! 6;另一方面,由于相較于小說等文體,詩歌商業化程度不高,因此詩歌寫作受商業文化的影響也并不那么直接。與此同時也應注意,“盡管‘個人寫作‘解構宏大敘事等口號和實踐改寫了中國文學的路向,但這種‘去政治本身就是一種政治”! 7。文學不可能將政治完全剝離而轉向個人化的詩歌寫作,由于詩人本身處于大眾消費時代,因此也不可能完全不受其影響。21世紀詩歌就這樣保持著和兩種話語若即若離的關系。體制內詩歌受官方刊物及各類官方文學獎項支持,“以獎勵的方式引導和鼓勵文學的健康發展”! 8;而體制外詩歌也有對應的民間刊物、詩歌節、詩歌獎、讀者市場等形式的導向。在對詩歌的影響上,主流話語和民間話語保持著微妙平衡。這是新的文學現象。從新詩發展的歷史來看,兩種詩歌體制的關系往往并不融洽,有時甚至呈現出對抗姿態。但21世紀以來“官方性的詩歌體制和亞體制在各自運作的同時,經常會走向合作與融合”! 9。
21世紀詩歌兩種話語的合作和融合,為左翼文學傳統與個人化寫作產生交匯提供了可能性。從早期無產階級詩歌、左翼詩歌、政治抒情詩到當代“主流詩歌”,左翼文學傳統在不同時期都發生了不同方面、不同程度的流變,但“人民性”始終是其核心。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和我國當代文學建設的基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就提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并從“人民需要文藝”“文藝需要人民”“文藝要熱愛人民”三方面具體闡釋。@ 0左翼文學傳統和個人化寫作在描寫對象和表現情感上存在難以消弭的差異:前者傾向于描寫作為群體的“人”,后者則更傾向于作為個體的“人”;前者表現的是人民的集體情感,而后者更多是表現個體情感。但是,在創作主體和接受對象上,左翼文學傳統又與個人化寫作存在契合之處。“文藝大眾化”是左翼文學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文藝的創作者和受眾角度回應了作為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重要價值取向的“人民性”。“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中的人民性,與經典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中的人民性一樣,對人民大眾的文學創作始終持鼓勵態度。”@ 1個人化寫作盡管給21世紀詩歌造成了創作上的良莠不齊,但客觀上確實擴大了詩歌的寫作人群和受眾。那么“主流詩歌”在21世紀這個特定的文學語境下,就不能不正視個人化寫作存在的合理性,否則就會陷入一種尷尬的境地:詩歌創作面向的對象在讀這些所謂為他們而作的詩時只覺索然無味,毫無感觸,甚至他們因興趣原因根本就不讀這些詩。茅盾很早就認識到了作品與讀者相割裂的危險性,他在《從牯嶺到東京》一文中寫道:“一種新形式新精神的文藝若沒有相應的讀者界,那么這種文藝要么枯萎,要么就是歷史奇跡,卻無論如何不能推動時代精神的發展。”@ 2茅盾寫下這段話的背景是批評當時盛行的革命文學實際上并未深入群眾。這對我們現在的文學創作也有很大啟發,文學的影響主要是通過讀者的閱讀接受完成,只有在確保一定讀者群的前提下,文學才有產生影響的可能。“主流詩歌”承載著為時代發聲的責任,但如果處于時代中的大多數人都對這種發聲產生不了共鳴,那么其對時代精神發展的推動也便無從談起。
在21世紀詩壇,“主流詩歌”在堅持左翼文學傳統的同時,開始有意識地從個人化寫作中汲取養分,在公共性和個人性之間尋求平衡,希望借此彌補自身的天然短板(話語介入對文學審美性的削弱),以期達到審美性和意識形態性的統一。“主流詩歌”堅持了主題宏大的基本特征,但在具體寫作策略上,為個體經驗的介入提供了可能性,這點與此前該類詩歌樣式(如“十七年文學”時期的政治抒情詩)“傾向于排斥、抵制個體情感、經驗的加入”@ 3有很大不同。可以說,這種嘗試,無論是對于“主流詩歌”還是整個21世紀詩歌的發展而言都非常有益,左翼文學傳統與個人化寫作的交匯對二者的影響是雙向的。目前,詩歌的個人化寫作也有從“世俗化”滑向“流俗化”的危險傾向@ 4,而“主流詩歌”的天然優勢(對宏大主題的準確把握,對公共題材的及時反映,對群體和群體情感的藝術表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糾偏”和“規約”作用。
四、21世紀“主流詩歌”的具體寫作策略
21世紀“主流詩歌”的具體寫作策略主要有以下三種傾向:視角個人化、觀念形象化、日常生活審美化。這是三種不同向度的探索,具體表現了左翼文學傳統與個人化寫作的交匯:“視角個人化”是“主流詩歌”對個人化寫作的借鑒和融合;“觀念形象化”是“主流詩歌”對傳統寫作策略的堅守和進一步探索;而“日常生活審美化”則更多體現了“主流詩歌”對個人化寫作的警惕和反思。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很多優秀的“主流詩歌”往往同時融入以上三種寫作策略,在詩歌創作中的具體運用和表現也是復雜的。囿于篇章限制,為了論述方便,下面將就三種具體寫作策略列舉典型詩人詩作,以供參考。
(一)視角個人化
個人視角在詩歌的個人化寫作中很普遍,但這種寫作策略在很長一段時間都不為“主流詩歌”這類詩歌樣式輕易選用,原因就在于個人視角和宏大主題二者之間存在著天然矛盾:“主流詩歌”所要傳遞的話語,以及所要表現的“大我”,很容易被“小我”的視角所限制。在這方面,20世紀50年代“政治抒情詩”的代表詩人郭小川曾進行過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創作出一些好的作品,“個人—群體、個體—歷史、感性個體—歷史本質的關系,是郭小川50年代一系列重要作品的主題”@ 5。郭小川對詩藝的開掘現在已得到學界認可,但在當時,由于政治環境的原因,批評界對他的這種探索大多持消極態度,甚至僅僅因為在詩中采用了“我”的敘述人稱和“我號召”的話語就招致批評。@ 6隨著政治環境的寬松和個人化寫作的興起,經過長期沉寂,一些詩人接續中斷了的探索,重新思考個人視角介入宏大題材的可能性與價值,這其中,雷抒雁在21世紀的詩歌創作就較有代表性。
雷抒雁被譽為“人民詩人”,他的詩關注社會現實,反映時代進程,有學者認為他在“一些人力圖斬斷審美與社會的關系,相信詩的目的在詩本身,拒絕對歷史社會等公共空間的書寫”的思潮背景下,“是一個孤獨者,也是現實主義詩歌觀的堅守者”@ 7。雷抒雁曾說自己的詩歌更多是寫“個人心靈在時代的際遇中的興會、感發和情感”@ 8,他的詩歌將宏大主題和個體經驗很好地結合在了一起,從個人視角發掘出了時代的詩意。
面對2008年中國南方雪災,詩人寫下了長詩《冰雪之劫:戰歌與頌歌》。@ 9雷抒雁的這首詩表現的是黨和人民抗擊雪災的決心和力量,但他并沒有先寫雪災的巨大破壞力,而是從自己的個體情感體驗出發,用雪花“飄落在我的嘴唇”這樣一個很有詩意的畫面,抒發了對雪的美好期待。這是真實的,也可能是當時大多數人的感受。這種從個人視角切入宏大主題的寫作策略,一方面拉近了詩與讀者的距離,增進了詩的現實感;另一方面,也是在積蓄情緒,使詩歌在激情噴薄時更具力量。讀者在讀到“冰雪和嚴寒/凍結了溫熱的土地/南半個中國在同聲喊冷”“曾經讓我們以為溫柔的雪花/怎么一夜間板起殺手的面孔”這樣的詩句時,就能對當時人們所感到的現實與美好期待的巨大落差感同身受。同樣的,當讀者讀到“黨啊,又一次動員/把八方的力量/聚集起來,凝成鐵拳/又一次,調動/把潛在的能源/組織起來,燃起烈焰”,就能感到黨的堅定領導;在讀到“大雪紛飛,大雪紛飛/紛飛的大雪里,我看見/在南國挺立著一座座昆侖天山”時,就能感受到人民的力量。通過個人視角的切入,雷抒雁在詩中實現了時代情感的自然流露,詩歌在宏大主題和個體經驗、主流話語的呈現和藝術審美的表現中達到了平衡。
(二)觀念形象化
抽象的觀念由于其復雜性,受眾在接受時有一定難度,人們對形象的感知則相對更為容易。形象性是詩歌的基本特征之一,詩歌跳躍的結構一定程度上剝離了原有的邏輯體系,通過形象化的語言傳遞給讀者一種感受,而感受相對于嚴密的邏輯能被更直觀地體會。因此無論是革命時期、建國初期還是當代,詩歌這一文體與主流話語宣傳一直關系密切。詩歌的本質特征是抒情,如何通過形象化的語言將觀念轉化成情感,是“主流詩歌”一直以來的艱難探索,在整個“主流詩歌”的發展脈絡中,不乏淪為觀念羅列的“政治標語式”詩歌,因為觀念形象化的過程并不容易。
吉狄馬加是當代著名詩人,其民族詩人、中國詩人、世界詩人的多重身份,對21世紀詩歌產生了無可替代的影響力。作為體制內詩人,吉狄馬加的很多詩歌都著眼于宏大的社會主體,及時反映時代風氣。在他的詩中,對時代的反映通常是通過將時代形象化的寫作策略實現,因而在兼顧主流話語呈現的同時也富有審美價值。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胡風曾寫下《時間開始了》,向新中國致敬;為了致敬十九大的召開,吉狄馬加寫下了《時間的入口》,向新時代致敬。《時間的入口》廣受歡迎,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在很多活動中都能聽見朗誦者朗讀這首詩的富有力量的聲音。“時間”是抽象的,但是詩人形象地寫出時間帶給我們的緊迫感:“時間的鐵錘,無論在宇宙深邃隱秘的穹頂,還是在一粒微塵的心臟,它的手臂,都在不停地擺動,它永不疲倦,那精準的節奏,敲擊著未來巨大的鼓面。”“時代精神”也是抽象的,但是詩人用“像一只真正醒來吼叫的雄獅,以風的姿態抖動紅色的鬃毛”這富有詩意而又生動的句子,形象地表現了銳意進取的新時代精神。結尾處,詩人寫道:“我們將再次出發,吹號者就站在這個隊伍的最前列,吹號者眺望著未來,自信的目光越過了群山、森林、河流和大地,他激越的吹奏將感動每一個心靈。他用堅定的意志、勇氣和思想,向一個穿越了五千年文明的民族,吹響了前進的號角,吹響了──前進的號角!”讓讀者感受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帶來的振奮。將時代形象化,一定程度可以減弱話語介入對詩歌審美性的削弱,使詩歌在觀念呈現和情感表現之間取得平衡,通過將主流話語轉化成形象可感的喻象,就不會過于空洞,讀者在體會喻象包裹下的觀念時就更易把握,也更易接受。并且由于感受相較邏輯更易進入深層意識,這種影響是深遠而可持續的,在潛移默化中完成主流話語的規約作用。
(三)日常生活審美化
生活意象、日常口語入詩是詩歌個人化寫作中的一個常見現象,這一方面拉近了詩與生活的距離,另一方面卻有從一個極端滑向另一個極端的危險傾向:一些詩歌由于對個人性極度推崇而呈現出“私語化”的情緒,陷入詩人“自說自話”的怪圈。“日常生活審美化”和“日常生活化”雖只兩字之差,本質卻截然相反,這兩個概念“一個是通過日常生活的審美活動凸顯人生價值和提升精神人格,從而進入詩意的境界;一個力圖將‘藝術轉換成生活,使藝術揚棄詩意的審美性格從而回歸日常現場”# 0。21世紀詩壇充斥著大量只是“日常生活化”而非“日常生活審美化”的詩歌創作。
21世紀“主流詩歌”也有意象設置生活化、語言運用口語化的傾向,但都是在對生活意象、日常口語進行藝術改造的前提下完成的。個體意象在構建作為整體的意象體系時,通常有著更深層的象征意義(如“我”—人民、土地—民族、花朵—生命等);作為整體的語言系統具有指征性,能指漂浮而所指多向,這樣就鞏固了詩歌的審美價值。
在21世紀詩歌中,底層詩歌較為鮮明地表現了這種日常生活審美化的傾向。“底層文學”是21世紀獨特的文學景觀,其與左翼文學傳統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有學者將之稱為“新左翼文學”,甚至認為其“已經構成了21世紀中國的文學主潮”# 1。 現實精神和底層關懷是左翼文學的基本特征,左翼文學興起之初想象中的對象是底層勞苦大眾(由于文學樣式的不成熟,實際可能并非如此),主觀意圖是通過文學為無產階級發聲。進入21世紀,底層詩歌一定意義就是承繼了這一條發展流脈,只是由于時代變遷,階級矛盾不再是社會主要矛盾,左翼文學中的革命主題趨隱,而底層關懷則被置于主要地位。為了寫作更好地貼近底層民眾,為了更好地表現他們的生活,生活意象和日常口語在詩中的使用是自然而然的。
例如谷禾的《宋紅麗》(《人民文學》2007年第3期),這首詩在主題、結構、意象、語言、修辭等各方面都將日常生活納入了審美化范疇。在結構形式上,詩人以報紙的形式寫詩。相對于詩,報紙更為普遍,是生活中常見的事物。詩共48行,其中長達35行是對宋紅麗一生冰冷的簡短介紹,從始至終,詩歌的語言始終是日常口語,沒有用晦澀的詞語,也沒有用華麗的文字,在冰冷的敘述中,詩人一直在克制自己的感情。詩歌的意象大多源自生活,如“假煙”“工地”“二手板車”“潞河醫院”等,但這些意象都通過各種手法,傳遞出更深層的象征意義。在宋紅麗的一生結束時,“2005年1月16日上午9時23分/宋紅麗懷抱小小,身背編織袋/橫穿京哈鐵路時不幸被一輛飛馳而來的/貨運列車攔腰撞飛(像一只鳥)/并當場斷氣”。在生活的重壓(“編織袋”)之下,宋紅麗們仍小心呵護著對美好的想象(“小小”),但社會的進步(“京哈鐵路”“貨運列車”)有時不僅沒有為她們帶來新的希望,反而加深了生活的困頓。宋紅麗被撞飛得“像一只鳥”,卻沒有鳥的自由,生活給她戴上了沉重的枷鎖,沉重得使她“當場斷氣”。詩人情感的節制在這里噴薄而出,帶給讀者心靈上的沖擊。
但詩人的意圖顯然不止于此,詩人又繼續“客觀”地寫道:“希望大家一定吸取血的教訓/過馬路要格外謹慎/尤其不要帶僥幸心理。”對于宋紅麗的離世,記者只是平淡地提醒大家“過馬路要格外謹慎”,而沒有關注到宋紅麗急著過馬路的真實原因,沒有關注到社會進步與底層掙扎的鮮明對比。寥寥幾句“結語”,與詩人之前的鋪張形成鮮明對比。谷禾通過冷靜的敘述、平實的語言,抒寫了貼近生活而非高高在上的底層關懷。
21世紀“主流詩歌”將生活意象納入豐富的象征體系,通過將日常生活審美化拉近了詩與現實的距離,并使詩進入了一個更闊大的境地。這就避免了個人化寫作中部分詩歌存在的對生活意象和日常口語的處理上為了呈現而呈現的誤區,以及由此導致的情感和意義的雙重缺失。
我國古代詩歌理論上就有“化俗為雅”的類似說法,可見“俗”的呈現不是目的本身。將生活引入詩歌,但詩歌又不只是對生活的呈現,是21世紀“主流詩歌”日常生活審美化的重要特征,對詩歌的個人化寫作中過于泛化了的“日常生活化”,或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五、余論:21世紀詩歌發展的可能性
21世紀以來,“主流詩歌”對個人化寫作的整體趨勢持包容態度,體制內詩歌和體制外詩歌走向合作和融合。在橫向上,21世紀“主流詩歌”被納入21世紀詩歌發展的整體脈絡之中,不可避免地受其影響,“主流詩歌”在寫作策略上的有益探索,如視角個人化、觀念形象化和日常生活審美化,都較鮮明地體現出一些個人化寫作的特點。在縱向上,21世紀“主流詩歌”承繼的是左翼詩歌一脈,對現實精神的堅守、對詩歌公共性的自覺、對時代和人民性的重視等,都是其重要特征。
21世紀“主流詩歌”的藝術探索不只是有利于其自身詩歌樣式的完善,就整個21世紀詩歌而言也有推動作用。對左翼詩歌的批評多是由于其過多注重政治話語的傳遞而導致的審美價值削弱。然而,進入21世紀以來的詩歌發展,由于個人化寫作存在走向極端的危險傾向,在詩歌中重新呼吁公共性和思想性,對左翼文學優秀傳統進行承繼和革新,似乎正可為21世紀詩歌注入新的活力。
兩種話語的融合、左翼文學傳統與個人化寫作的交匯,為21世紀詩歌發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a 崔勇:《21世紀,新詩歌——世紀初中國新詩走向研討會綜述》,《文藝爭鳴》2006年第1期,第86—88頁。
b 童慶炳主編:《文學理論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76頁。
c 童慶炳:《審美意識形態論作為文藝學的第一原理》,《學術研究》2000年第1期,第104—111頁。
d 陳思和、何清:《理想主義與民間立場》,《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5期,第1—9頁。
e 黃發有:《第四次文代會與文學復蘇》,《文藝爭鳴》2013年第10期,第39—52頁。
f 陳曉明:《中國當代文學主潮》,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65頁。
g 顧驤:《思想解放與新時期的文學潮流》,顧驤:《顧驤文學評論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5頁。
h 謝冕:《世紀反思——21世紀詩歌隨想》,《河南社會科學》2004年第3期,第65—67頁.
i 謝冕:《世紀反思——21世紀詩歌隨想》,《河南社會科學》2004年第3期,第65—67頁。
j 謝冕:《輝煌而悲壯的歷程》,謝冕:《1898:百年憂患》,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5—10頁。
k 南帆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批評99個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28—30頁。
l 王曉明:《在創傷性記憶的環抱中》,《文學評論》1999年第5期,第48—50頁。
m 羅振亞:《面向21世紀的“突圍”:詩歌形象的重構》,《東岳論叢》2011年第32期,第5—9頁。
n 王士強:《21世紀詩歌:活力大于危機》,《南方文壇, 2018年第4期,第121—124、134頁。
o 奚密:《從邊緣出發——現代漢詩的另類傳統》,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頁。
p 黃發有主編:《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大系 2001-2010 史料卷》,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3頁。
q 孟繁華:《21世紀文學:文學政治的重建——文學政治的內部視角與外部想象》,《文藝爭鳴》2010年第21期,第104—108頁。
r 黃發有主編:《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大系 2001—2010史料卷》,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頁。
s 何言宏主編:《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大系 2001—2010詩歌卷》,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5頁。
t 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4年10月15日),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4/ c_1116825558.htm,2015年10月14日。
u 季水河、季念:《論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人民性》,《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9年第48期,第74—87頁。
v 茅盾:《從牯嶺到東京》,原載于《小說月報》第19卷,1928年10月。
wy z 洪子誠、劉登翰:《中國當代新詩史(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97頁,第99頁,第103頁。
x 張汗勤:《論21世紀詩歌的世俗化潮流》,華中師范大學2009年論文。
@ 7 李國平:《變革時代的抒情詩人》,《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43期,第55—57頁。
@ 8 雷抒雁、牛宏寶:《叩問變革年代的詩境——雷抒雁訪談》,《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39期,第78—83頁。
@ 9 雷抒雁:《花雨 唱給共和國的抒情詩》,寧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5—84頁。
# 0 王巨川:《論21世紀詩歌日常生活審美化傾向》,《藝術評論》2012年第6期,第17—21頁。
# 1 何言宏:《當代中國的“新左翼文學”》,《南方文壇》2008年第1期,第5—11頁。
基金項目: 本文系國家級大學生創新訓練項目(項目編號:201910347012)
作 者:魏振國,湖州師范學院文學院在讀本科生。
編 輯:曹曉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