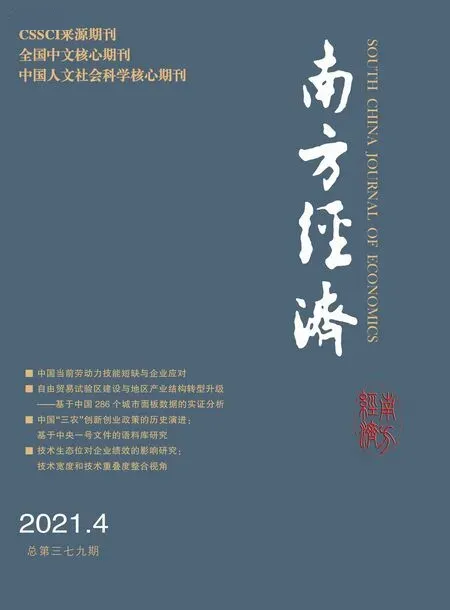技術(shù)生態(tài)位對企業(yè)績效的影響研究:技術(shù)寬度和技術(shù)重疊度整合視角
朱正浩 戚聿東 趙志棟
一、引言
技術(shù)能力指企業(yè)通過內(nèi)部努力創(chuàng)造可用于開發(fā)和改進產(chǎn)品和工藝的科學和技術(shù)知識儲備(Quintana-García et al.,2008)。技術(shù)能力被認為是導致企業(yè)績效差異的重要原因,資源基礎(chǔ)理論認為技術(shù)能力是企業(yè)保持持續(xù)競爭優(yōu)勢最重要來源之一(Dierickx et al.,1989;Nelson,1991),新熊彼特主義經(jīng)濟學家指出技術(shù)能力是企業(yè)實現(xiàn)績效趕超的關(guān)鍵因素(Mazzoleni and Nelson,2013),這些理論從技術(shù)能力角度理解企業(yè)績效,但對技術(shù)能力發(fā)展機制分析不夠(Foss,1997;路風,2018),重要原因在于測量企業(yè)技術(shù)能力的困難。傳統(tǒng)視角下,Schoenecker et al.(2002)和Coombs et al.(2006)對企業(yè)技術(shù)能力測量方法做了系統(tǒng)性梳理后指出,研發(fā)支出、研發(fā)強度等技術(shù)投入指標、專利數(shù)量、專利質(zhì)量、科學發(fā)表等技術(shù)產(chǎn)出指標是學者們常用的測量工具。技術(shù)生態(tài)觀視角下對技術(shù)能力的測量聚焦組織技術(shù)生態(tài)比較,技術(shù)重疊度(Sears et al.,2014)、技術(shù)距離(金曉雨等,2020)、技術(shù)勢差(江志鵬等,2018)和技術(shù)生態(tài)位(Stuart and Podolny,1996;許蕭迪,2007;何巨峰,2008;姚艷虹等,2017;雷雨嫣等,2019)等構(gòu)念被用來比較企業(yè)間技術(shù)能力相對位置。
從測量效果看,Sears(2014)發(fā)現(xiàn)傳統(tǒng)測量方法導致了差異化結(jié)果,原因是上述指標不能很好測量企業(yè)技術(shù)能力,Coombs et al.(2006)利用201家美國制造業(yè)上市公司的數(shù)據(jù)實證發(fā)現(xiàn)研發(fā)支出和企業(yè)專利數(shù)量不是測量企業(yè)技術(shù)能力的有效指標。另一方面,技術(shù)生態(tài)觀下對技術(shù)能力的測量方法多從企業(yè)技術(shù)能力某一維度入手,難以刻畫企業(yè)技術(shù)能力全貌,如技術(shù)重疊度被用來衡量企業(yè)間技術(shù)的相似性,多出現(xiàn)在企業(yè)間技術(shù)并購和技術(shù)合作的討論中(如Yan et al.,2020;Sears et al.,2014)。還有研究獨立檢驗技術(shù)寬度和重疊度與創(chuàng)新績效的關(guān)系(姚艷虹等,2017;雷雨嫣等,2019),上述研究為探索企業(yè)技術(shù)能力對企業(yè)績效的作用提供了新見解,但是,由于將技術(shù)寬度和重疊度作為獨立解釋變量,未能揭示技術(shù)寬度與技術(shù)重疊度之間內(nèi)在邏輯與聯(lián)系,難以全面反映企業(yè)技術(shù)能力全貌。
為更好揭示企業(yè)技術(shù)能力發(fā)展過程及對績效的影響機制,提供一個能全面反映企業(yè)技術(shù)能力的構(gòu)念十分必要。本研究借鑒技術(shù)生態(tài)觀相關(guān)思想,整合了企業(yè)技術(shù)寬度和重疊度,發(fā)展出“技術(shù)追隨型”、“技術(shù)多樣型”、“技術(shù)專長型”和“技術(shù)平衡型”四類技術(shù)生態(tài)位。通過搜集2011-2018年滬深醫(yī)藥上市公司面板數(shù)據(jù),實證比較不同技術(shù)生態(tài)位企業(yè)對企業(yè)的短期績效和長期績效影響。結(jié)果顯示,相對于“技術(shù)追隨型”,“技術(shù)多樣型”、“技術(shù)專長型”和“技術(shù)平衡型”企業(yè)有更高短期績效,且“技術(shù)多樣型”、“技術(shù)專長型”企業(yè)有更高長期績效;相對“技術(shù)多樣型”,“技術(shù)平衡型”企業(yè)有更高短期績效,而二者在長期績效上差別不顯著。技術(shù)生態(tài)位分類有助于更全面準確地測量企業(yè)技術(shù)能力,更清晰地解釋技術(shù)能力對企業(yè)績效的作用機制,也為理解企業(yè)技術(shù)能力演化過程提供了新視角。
二、整合技術(shù)寬度和技術(shù)重疊度的企業(yè)技術(shù)生態(tài)位分類
(一)企業(yè)技術(shù)生態(tài)位概念界定及辨析
本研究定義企業(yè)技術(shù)生態(tài)位為企業(yè)技術(shù)能力相對位置和發(fā)展?jié)摿Γl(fā)展了何宇寧(2008)對技術(shù)創(chuàng)新生態(tài)位的理解,何宇寧引入了組織生態(tài)學中的“態(tài)勢”理論,認為技術(shù)生態(tài)位的“態(tài)”是創(chuàng)新主體過去技術(shù)創(chuàng)新活動的積累,是與創(chuàng)新環(huán)境作用結(jié)果,技術(shù)生態(tài)位的“勢”體現(xiàn)了創(chuàng)新主體對創(chuàng)新環(huán)境的支配能力。本研究聚焦企業(yè)競爭而非廣義的企業(yè)與環(huán)境互動所形成的“態(tài)”和“勢”,為了更好理解這一問題,借鑒Carlsson et al.(2002)技術(shù)系統(tǒng)框架分析范式構(gòu)建企業(yè)技術(shù)生態(tài)位概念示意圖如下:
假設共有三家企業(yè)Firm1、Firm2、Firm3生產(chǎn)P1至P5五種有類似功能的產(chǎn)品,大方框內(nèi)T1至T9構(gòu)成了產(chǎn)品技術(shù)基礎(chǔ),C1至C6代表用戶群體,如圖1,F(xiàn)irm1擁有T1、T2、T3、T4四種技術(shù),F(xiàn)irm2擁有T1、T3、T5、T6、T7、T8 六種技術(shù),F(xiàn)irm3擁有T7、T9兩種技術(shù)。企業(yè)技術(shù)能力相對位置可以通過企業(yè)技術(shù)能力異質(zhì)性體現(xiàn),F(xiàn)irm1有T2、T4兩種獨有技術(shù),F(xiàn)irm2有T5、T6、T8三種獨有技術(shù),F(xiàn)irm3有T9一種獨有技術(shù),更多獨有技術(shù)意味著更高技術(shù)能力現(xiàn)狀和企業(yè)技術(shù)生態(tài)位的“態(tài)”,這是因為企業(yè)發(fā)展過程中累積的競爭對手難以模仿的異質(zhì)性技術(shù)是企業(yè)保持競爭優(yōu)勢的基礎(chǔ)(Barney,1991)。另一方面,企業(yè)技術(shù)能力發(fā)展?jié)摿梢酝ㄟ^技術(shù)資源豐富程度體現(xiàn),F(xiàn)irm1擁有T1、T2、T3、T4四種技術(shù),F(xiàn)irm2擁有T1、T3、T5、T6、T7、T8六種技術(shù),F(xiàn)irm3擁有T7、T9兩種技術(shù),擁有越多技術(shù)資源的企業(yè)對環(huán)境變化適應能力越強,從而擁有更高技術(shù)生態(tài)位的“勢”,這是因為企業(yè)技術(shù)發(fā)展是關(guān)聯(lián)的,技術(shù)創(chuàng)新提高了發(fā)現(xiàn)其他創(chuàng)新機會(Nelson and Winter,1982),擁有多技術(shù)資源的企業(yè)更能抓住技術(shù)機會。此外,隨著環(huán)境變化,企業(yè)原有“核心能力”可能不適應變化而轉(zhuǎn)變?yōu)椤昂诵膭傂浴?Leonard-Barton,1992),掌握多技術(shù)領(lǐng)域知識的企業(yè)更易發(fā)現(xiàn)新技術(shù)機會,實現(xiàn)產(chǎn)品和企業(yè)轉(zhuǎn)型。

圖1 企業(yè)技術(shù)生態(tài)位概念示意圖
企業(yè)技術(shù)生態(tài)位定義有別于戰(zhàn)略生態(tài)位管理理論中的技術(shù)生態(tài)位構(gòu)念,該構(gòu)念以技術(shù)為研究對象,指為激進式創(chuàng)新建立的一個避免和主流技術(shù)競爭的“保護空間”(Schot and Rip,1997),根據(jù)圖1,一項新技術(shù)如T9,如何在一個相對“隔離”于主導技術(shù)(T1)的“受保護空間”內(nèi)發(fā)展,“受保護的空間”可以理解為TP=f(Firm3,P5,C6)。
(二)技術(shù)生態(tài)位測量維度與分類
技術(shù)重疊度可以理解為企業(yè)技術(shù)資源相似程度,Stuart and Podolny(1996)假設技術(shù)相似企業(yè)具有相似的技術(shù)能力,通過企業(yè)間專利引用數(shù)據(jù)構(gòu)建了技術(shù)重疊度指標,高技術(shù)重疊度意味著企業(yè)間高技術(shù)相似,低技術(shù)重疊度則體現(xiàn)企業(yè)技術(shù)能力異質(zhì)性,該指標運用多出現(xiàn)在企業(yè)間技術(shù)并購和合作討論中(如Yan et al.,2020;Han et al.,2018)。從競爭視角看,企業(yè)間技術(shù)資源相似程度描述了企業(yè)間技術(shù)競爭強度,高技術(shù)重疊度表示與該企業(yè)擁有相同技術(shù)資源企業(yè)多,企業(yè)面臨技術(shù)競爭強度高,企業(yè)技術(shù)能力相對位置不利。反之,低技術(shù)重疊度表示與該企業(yè)擁有相同技術(shù)資源的企業(yè)少,企業(yè)面臨技術(shù)競爭強度低,企業(yè)技術(shù)能力相對位置有利。另一方面,技術(shù)寬度測量企業(yè)技術(shù)資源豐富程度,高技術(shù)寬度代表企業(yè)有大的知識基礎(chǔ),Prencipe(2000)使用了組織擁有的技術(shù)領(lǐng)域數(shù)量測量技術(shù)寬度,這一思想被后來學者們吸收利用(如Pan et al.,2018;Kim et al.,2016)。由于知識基礎(chǔ)是企業(yè)吸收能力和創(chuàng)新能力的重要影響因素(Cohen and Levinthal,1990),因此知識基礎(chǔ)反映出企業(yè)技術(shù)能力發(fā)展?jié)摿Γ夹g(shù)寬度越高,企業(yè)技術(shù)能力發(fā)展?jié)摿υ酱螅髽I(yè)技術(shù)生態(tài)位的“勢”越高。
與姚艷虹等(2017)、雷雨嫣等(2019)將技術(shù)寬度和技術(shù)重疊度作為獨立解釋變量檢驗技術(shù)生態(tài)位與創(chuàng)新績效間關(guān)系的思路不同,本研究認為單一指標難以刻畫企業(yè)技術(shù)能力全貌,這是由于技術(shù)寬度只能體現(xiàn)企業(yè)技術(shù)能力發(fā)展?jié)摿Γ雌髽I(yè)技術(shù)生態(tài)位的“勢”,并不能說明企業(yè)在技術(shù)競爭中的相對位置,而技術(shù)重疊度雖然反映了企業(yè)技術(shù)能力競爭現(xiàn)狀,即技術(shù)生態(tài)位的“態(tài)”,但是難以刻畫企業(yè)技術(shù)能力發(fā)展?jié)摿Γ挥邪褍烧哒掀饋恚拍芡瑫r體現(xiàn)企業(yè)技術(shù)能力的現(xiàn)狀和發(fā)展?jié)摿Γ纤悸穫鞒辛薆urns and Stalker(1961)、Thompson(1967)等學者對不同外部環(huán)境特征下組織追求效率(efficiency)和柔性(flexibility)兩難問題的討論,技術(shù)生態(tài)位的“態(tài)”,即技術(shù)重疊度,體現(xiàn)了組織對效率的戰(zhàn)略追求,技術(shù)生態(tài)位的“勢”,即技術(shù)寬度,體現(xiàn)了企業(yè)對柔性的戰(zhàn)略追求,兩者整合反映了企業(yè)效率與柔性、現(xiàn)有技術(shù)能力和未來技術(shù)能力間戰(zhàn)略平衡。由此,本研究根據(jù)技術(shù)重疊度和技術(shù)寬度的“高”和“低”,將企業(yè)技術(shù)生態(tài)位區(qū)分為四個類型(如圖2所示)。

圖2 基于技術(shù)寬度與重疊度的企業(yè)技術(shù)生態(tài)位分類
第一,“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技術(shù)能力特征為:(1)技術(shù)寬度低,企業(yè)掌握有限技術(shù)領(lǐng)域知識,或者對各技術(shù)領(lǐng)域知識利用能力不平衡。(2)技術(shù)重疊度高,企業(yè)技術(shù)資源面臨強外部競爭。“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往往處于產(chǎn)業(yè)鏈低端,知識基礎(chǔ)小,缺乏辨識外界技術(shù)機會能力(Cohen and Levinthal,1990),企業(yè)通過購買和使用機器設備、從事產(chǎn)品部件生產(chǎn)等途徑掌握了特定產(chǎn)品組件知識,此類企業(yè)往往“使用知識”而不是“變革知識”(Amin and Cohendet,2004),缺乏更新組件技術(shù)能力和系統(tǒng)集成知識,技術(shù)上追隨集成企業(yè)和上游企業(yè)要求,使用一般性技術(shù),面臨激烈外部競爭。
第二,“技術(shù)多樣型”企業(yè),技術(shù)能力特征為:(1)技術(shù)寬度高,企業(yè)掌握多技術(shù)領(lǐng)域知識且對各技術(shù)領(lǐng)域利用能力相對平衡。(2)技術(shù)重疊度高,企業(yè)面臨強外部技術(shù)競爭。該類型企業(yè)雖然面臨強技術(shù)競爭,但是由于擁有大的知識基礎(chǔ),仍有潛力利用機會窗口來提升在競爭中的位置。典型的情況包括產(chǎn)品技術(shù)升級迭代過程中發(fā)展出的技術(shù)能力多樣性,以及企業(yè)在跨產(chǎn)業(yè)升級過程中的技術(shù)多樣化等(Gereffi,1999)。
第三,“技術(shù)專長型”企業(yè),技術(shù)能力特征為:(1)技術(shù)寬度低,企業(yè)掌握有限技術(shù)領(lǐng)域知識,或者對各技術(shù)領(lǐng)域利用能力不平衡。(2)技術(shù)重疊度低,企業(yè)面臨弱外部技術(shù)競爭。“技術(shù)專長型”企業(yè)往往是產(chǎn)業(yè)主導技術(shù)明確以后產(chǎn)業(yè)內(nèi)分工演化和長期知識積累的結(jié)果。在產(chǎn)業(yè)內(nèi)企業(yè)間合作管理、決策規(guī)則、程序、激勵安排等問題處于穩(wěn)定狀態(tài)之后(Dosi et al.,2003),對已有技術(shù)領(lǐng)域持續(xù)的知識積累成為提升企業(yè)效率、降低生產(chǎn)成本,發(fā)揮規(guī)模經(jīng)濟優(yōu)勢的重要途徑。“技術(shù)專長型”企業(yè)的挑戰(zhàn)來自于產(chǎn)業(yè)內(nèi)分工調(diào)整和顛覆性技術(shù)出現(xiàn),因此對外部技術(shù)變化保持足夠知覺是該類企業(yè)生存的必要條件。
第四,“技術(shù)平衡型”企業(yè),技術(shù)能力特征為:(1)技術(shù)寬度高,企業(yè)掌握多技術(shù)領(lǐng)域知識且對各技術(shù)領(lǐng)域利用能力相對平衡。(2)技術(shù)重疊度低,企業(yè)面臨弱外部技術(shù)競爭,該類企業(yè)知識基礎(chǔ)規(guī)模大,掌握主導技術(shù),擁有不斷完善主導技術(shù)和將該技術(shù)應用到多個產(chǎn)品領(lǐng)域的創(chuàng)新能力。此外,此類企業(yè)也儲備了其他領(lǐng)域的知識,當外部條件變化時,企業(yè)有辨識技術(shù)機會的能力。
三、研究假設:技術(shù)生態(tài)位對企業(yè)績效的影響
四類技術(shù)生態(tài)位分類反映了不同技術(shù)能力潛力和相對位置的組合,有助于更準確地刻畫企業(yè)技術(shù)能力,根據(jù)Schwab(1980)等學者思路,新構(gòu)念是否有效需要檢驗預測有效性的問題,即新構(gòu)念能否被用來預測理論上相關(guān)的某個應變量。根據(jù)這一思路,由于技術(shù)能力是企業(yè)間績效差異的重要原因,企業(yè)技術(shù)生態(tài)位分類是否有意義,可以通過不同技術(shù)生態(tài)位企業(yè)的績效差異來檢驗。理論上,不同技術(shù)生態(tài)位在長期和短期內(nèi)都影響了企業(yè)績效。技術(shù)生態(tài)位的“勢”,即技術(shù)寬度,反映了企業(yè)在不同技術(shù)方向的能力分布,從而支撐了企業(yè)在多個產(chǎn)品方向布局,成為獲得范圍經(jīng)濟的技術(shù)基礎(chǔ),與企業(yè)短期績效相關(guān)。更為關(guān)鍵的是,企業(yè)不同技術(shù)方向的能力分布也為進一步搜尋鄰近技術(shù)信息,判別技術(shù)機會提供了基礎(chǔ),為企業(yè)持續(xù)競爭力提供了技術(shù)基礎(chǔ),從而與企業(yè)長期績效密切相關(guān)。
技術(shù)生態(tài)位的“態(tài)”,即技術(shù)重疊度,反映了行業(yè)內(nèi)企業(yè)間技術(shù)能力的相對位置。從演化經(jīng)濟學角度看,技術(shù)重疊度高或低是企業(yè)技術(shù)行為路徑累積結(jié)果,企業(yè)靠近以前技術(shù)商業(yè)化成功路徑,搜索和識別信息,協(xié)調(diào)包括研發(fā)、財務、市場、生產(chǎn)流程等組織內(nèi)部關(guān)系,開發(fā)新產(chǎn)品新工藝形成了專門技術(shù)行為路徑。技術(shù)行為路徑嵌入在企業(yè)總體“慣例”中,具有高度連貫性和內(nèi)部粘滯性,低技術(shù)重疊度與規(guī)模經(jīng)濟、研發(fā)效率、生產(chǎn)成本、互補資產(chǎn)等因素緊密相關(guān)并影響了企業(yè)短期績效,體現(xiàn)了企業(yè)“從創(chuàng)新中獲利的互補資產(chǎn)和組織能力”(Teece,1986)。
(一)處于“技術(shù)追隨型”和“技術(shù)多樣型”生態(tài)位的企業(yè)績效比較
“技術(shù)多樣型”比“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更高短期績效來自于更高研發(fā)績效和范圍經(jīng)濟帶來的增長。隨著工業(yè)社會向知識經(jīng)濟轉(zhuǎn)型,越來越多的知識問題需要多個技術(shù)領(lǐng)域知識,與“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相比,“技術(shù)多樣型”企業(yè)掌握多技術(shù)領(lǐng)域知識,更有能力應對復雜的知識問題,有更高研發(fā)績效,大量研究證實了企業(yè)技術(shù)多元化和創(chuàng)新產(chǎn)出之間的顯著正相關(guān)(Nesta et al.,2005;Garcia-Vega,2006)或者倒U型關(guān)系(Leten et al.,2007)。另一方面,“技術(shù)多樣型”企業(yè)擁有更多樣化產(chǎn)品,Suzuki et al.(2004)通過對Takeda和Canon公司研究表明,技術(shù)多樣化與產(chǎn)品多樣化和銷售增長相關(guān),持續(xù)的技術(shù)多樣化是企業(yè)保持“范圍經(jīng)濟”優(yōu)勢的技術(shù)資源基礎(chǔ)。
相比“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技術(shù)多樣型”企業(yè)更高長期績效來自在變動環(huán)境中抓住技術(shù)機會的能力,這是因為,第一,擁有多個技術(shù)領(lǐng)域知識的企業(yè)有更大可能性產(chǎn)生更多的“強制性技術(shù)”(Rosenberg,1969)。第二,技術(shù)領(lǐng)域間潛在互補性增強了產(chǎn)生技術(shù)機會可能,擁有通用技術(shù)的企業(yè)能夠發(fā)展出更多衍生技術(shù)。第三,“技術(shù)多樣型”企業(yè)過去經(jīng)歷強化了識別技術(shù)機會能力,更能正確決策企業(yè)研發(fā)活動的方向和投入水平,如Teece(1997)指出的:“企業(yè)歷史上所從事的那些技術(shù)機會的深度和廣度也會影響到企業(yè)對于其研發(fā)活動應有的數(shù)量和水平標準的確定。”第四,隨著環(huán)境變化,企業(yè)原有“核心能力”不能適應環(huán)境而轉(zhuǎn)變?yōu)椤昂诵膭傂浴保莆斩鄠€技術(shù)領(lǐng)域知識的企業(yè)更容易發(fā)現(xiàn)新技術(shù)機會,實現(xiàn)產(chǎn)品和企業(yè)轉(zhuǎn)型。已有研究結(jié)果支持了上述結(jié)論,實證研究表明技術(shù)多樣化與企業(yè)短期績效(如Pan et al.,2018)或是長期績效(Lin and Wu,2010)顯著正相關(guān),綜上所述,
假設1:“技術(shù)多樣型”比“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有更高短期績效。
假設2:“技術(shù)多樣型”比“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有更高長期績效。
(二)處于“技術(shù)追隨型”和“技術(shù)專長型”生態(tài)位的企業(yè)績效比較
“技術(shù)專長型”比“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更高短期績效來自產(chǎn)品領(lǐng)域規(guī)模經(jīng)濟優(yōu)勢和技術(shù)領(lǐng)域累積優(yōu)勢。第一,低協(xié)同成本。隨著“技術(shù)專長型”企業(yè)在某一技術(shù)領(lǐng)域知識不斷積累,與研發(fā)部門開展創(chuàng)新協(xié)作的生產(chǎn)、銷售等部門獲取的背景知識和特定技術(shù)知識越來越豐富(Vincenti,1990),通過將知識嵌入組織內(nèi)部“慣例”中,產(chǎn)品和技術(shù)生產(chǎn)所需要協(xié)同成本不斷下降。第二,高互補資產(chǎn)。“技術(shù)專長型”比“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擁有技術(shù)能力商業(yè)化所需更高的“互補資產(chǎn)”,如生產(chǎn)設備、營銷渠道等,能夠以更小成本和更快速度抓住技術(shù)機會,從創(chuàng)新中獲利。第三,高專用資產(chǎn),“技術(shù)專長型”企業(yè)在特定領(lǐng)域形成強大研發(fā)能力,擁有大量專用資產(chǎn),如專用研發(fā)設備和專用試驗生產(chǎn)線等,為潛在進入者設置了代價高昂的進入壁壘。第四,“技術(shù)專長型”企業(yè)擁有更多難以模仿和獲取的專利技術(shù)和在生產(chǎn)中形成的隱性知識,使得企業(yè)能夠持續(xù)收取創(chuàng)新租金。
相比“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技術(shù)專長型”企業(yè)更高的長期績效來自于創(chuàng)新能力。第一, “技術(shù)專長型”企業(yè)在某一類產(chǎn)品技術(shù)領(lǐng)域擁有豐富知識,建立了穩(wěn)定有效的外部信息獲取網(wǎng)絡,能以較低成本及時獲取該類產(chǎn)品或技術(shù)的新信息。第二,“技術(shù)專長型”企業(yè)在某一技術(shù)領(lǐng)域擁有豐富知識增強了企業(yè)應對復雜產(chǎn)品研發(fā)的能力。綜上所述,
假設3:“技術(shù)專長型”比“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有更高短期績效。
假設4:“技術(shù)專長型”比“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有更高長期績效。
(三)處于“技術(shù)追隨型”和“技術(shù)平衡型”生態(tài)位的企業(yè)績效比較
相比“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技術(shù)平衡型”企業(yè)兼具“技術(shù)平衡型”和“技術(shù)專長型”企業(yè)優(yōu)勢。“技術(shù)平衡型”企業(yè)高短期績效由多樣化技術(shù)帶來,表現(xiàn)為更高研發(fā)績效和范圍經(jīng)濟帶來的績效增長,此外,“技術(shù)平衡型”企業(yè)高短期績效也可能來自產(chǎn)品領(lǐng)域規(guī)模經(jīng)濟優(yōu)勢和技術(shù)領(lǐng)域的累積優(yōu)勢,具體包括前述的低協(xié)同成本、高互補資產(chǎn)、高專用資產(chǎn)和豐富的隱性知識等方面。長期看,相比“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技術(shù)平衡型”企業(yè)掌握多技術(shù)領(lǐng)域知識,更容易感知環(huán)境變化,發(fā)展出更多技術(shù)機會,實現(xiàn)產(chǎn)品和企業(yè)的轉(zhuǎn)型,此外,“技術(shù)平衡型”企業(yè)能夠以更低成本搜索外部信息和實施組織內(nèi)部的協(xié)同創(chuàng)新,擁有更低的技術(shù)生產(chǎn)協(xié)同成本和更高的應對復雜研發(fā)問題的能力。綜上所述。
假設5:“技術(shù)平衡型”比“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有更高短期績效。
假設6:“技術(shù)平衡型”比“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有更高長期績效。
(四)處于“技術(shù)多樣型”和“技術(shù)平衡型”生態(tài)位的企業(yè)績效比較
相比“技術(shù)多樣型”企業(yè),“技術(shù)平衡型”企業(yè)技術(shù)資源面臨弱外部競爭。“技術(shù)平衡型”企業(yè)更高短期績效來自成功的技術(shù)行為路徑,包括低協(xié)同成本、高互補資產(chǎn)和專用資產(chǎn),以及專利和技術(shù)訣竅等帶來的成本優(yōu)勢、市場優(yōu)勢和創(chuàng)新優(yōu)勢。長期看,兩類技術(shù)類型企業(yè)各有優(yōu)劣勢。“技術(shù)平衡型”企業(yè)技術(shù)多樣化的背景在長期內(nèi)可能為企業(yè)帶來更多技術(shù)機會,然而,在面臨研發(fā)投資決策時,在某一領(lǐng)域技術(shù)和生產(chǎn)優(yōu)勢可能會“阻止甚至延緩企業(yè)經(jīng)理放棄某一種特定的技術(shù)”(Burgelman,1994),企業(yè)面臨“核心僵化”風險。相比之下,“技術(shù)多樣型”企業(yè)不存在這種“成功是失敗之母”的風險,然而,“技術(shù)多樣型”企業(yè)短期績效低,即便識別出潛在技術(shù)機會,也可能因為受財務條件約束而不得不放棄。綜上所述,
假設7:“技術(shù)平衡型”比“技術(shù)多樣型”企業(yè)有更高短期績效。
除上述比較外,進一步比較“技術(shù)多樣型”和“技術(shù)專長型”企業(yè)績效。短期看,“技術(shù)多樣型”企業(yè)不具備某一技術(shù)領(lǐng)域競爭優(yōu)勢,但是享有更高研發(fā)績效和范圍經(jīng)濟帶來的績效增長。“技術(shù)專長型”企業(yè)擁有某一技術(shù)領(lǐng)域競爭優(yōu)勢,過去成功技術(shù)行為路徑,使得企業(yè)技術(shù)能力能夠通過高規(guī)模經(jīng)濟、高研發(fā)效率、低生產(chǎn)成本、高互補資產(chǎn)和高專用資產(chǎn)等因素影響企業(yè)短期績效。兩種類型企業(yè)短期績效比較取決于上述優(yōu)勢比較。長期看,“技術(shù)多樣型”企業(yè)擁有更多技術(shù)機會,但是財務約束可能成為企業(yè)利用潛在技術(shù)機會的制約條件,“技術(shù)專長型”企業(yè)如果不能夠?qū)ν獠凯h(huán)境變化保持知覺,也可能阻礙其利用新的技術(shù)機會。最后討論“技術(shù)專長型”和“技術(shù)平衡型”企業(yè)績效比較。短期看,兩種類型企業(yè)都有技術(shù)競爭優(yōu)勢,“技術(shù)平衡型”企業(yè)還擁有技術(shù)多樣化帶來的研發(fā)優(yōu)勢和范圍經(jīng)濟優(yōu)勢,哪類企業(yè)有更高短期績效取決于上述優(yōu)勢之間比較結(jié)果。長期看,雖然“技術(shù)平衡性”企業(yè)享有技術(shù)多元化為企業(yè)帶來的更多技術(shù)機會和范圍經(jīng)濟優(yōu)勢,但是,在主導技術(shù)不變情況下,“技術(shù)專長型”企業(yè)在某一領(lǐng)域累積的技術(shù)和生產(chǎn)優(yōu)勢可能更為突出。在主導技術(shù)不明情境下,“技術(shù)平衡性”企業(yè)可能依賴更強技術(shù)靈活性和對環(huán)境適應能力取得更高長期績效。
四、數(shù)據(jù)搜集與研究方法
(一)數(shù)據(jù)采集
研究樣本為2011-2018年間中國滬深股市207家醫(yī)藥制造業(yè)企業(yè)。專利原始數(shù)據(jù)來源于國家知識產(chǎn)權(quán)局專利檢索及分析數(shù)據(jù)庫(pss-system.cnipa.gov.cn/),企業(yè)財務數(shù)據(jù)來自于國泰安CSMAR數(shù)據(jù)庫。選擇醫(yī)藥制造業(yè)企業(yè)為研究樣本有三方面考慮:一是近年來中國醫(yī)藥行業(yè)市場規(guī)模快速增長,主營業(yè)務收入從2012年的9680億元上升到2019年的18945億元,為分析企業(yè)技術(shù)生態(tài)位提供了良好宏觀環(huán)境。二是醫(yī)藥制造業(yè)是公認的以技術(shù)創(chuàng)新為主要驅(qū)動力行業(yè),近年來中國制藥企業(yè)研發(fā)銷售比不斷上升,醫(yī)藥行業(yè)創(chuàng)新性特征進一步明顯,如2015-2017年間,制藥行業(yè)總研發(fā)支出從2015年151億元增至2017年232億元,增長了50%以上。第三,運用專利數(shù)據(jù)信息分析制藥企業(yè)技術(shù)能力具有較高可靠性,醫(yī)藥制造企業(yè)研發(fā)投入大、風險高,相比其他行業(yè),專利保護對于醫(yī)藥制造行業(yè)意義更為重大,制藥企業(yè)更傾向于將研發(fā)成果申請專利,此外,專利易于觀察和得到,也更可靠。
為計算企業(yè)技術(shù)寬度和技術(shù)重疊度,需要搜集目標企業(yè)在某一年份累計申請專利的技術(shù)領(lǐng)域和頻數(shù)。我國采用國際專利分類(IPC)體系,IPC分類號信息構(gòu)成了識別專利技術(shù)領(lǐng)域的首要參考。因此,對目標企業(yè)技術(shù)領(lǐng)域和頻數(shù)搜集就轉(zhuǎn)化為申請專利的IPC分類號(IPC分類號前四位)和頻數(shù)的搜集。首先甄別出滬深上市醫(yī)藥公司中不適合作為本研究樣本企業(yè),如S.T公司、主營業(yè)務轉(zhuǎn)型為非醫(yī)藥制造業(yè)公司等。其次,厘清上市公司股權(quán)關(guān)系,形成一份醫(yī)藥上市公司及子公司名錄。最后,根據(jù)名錄采集專利技術(shù)領(lǐng)域數(shù)據(jù),數(shù)據(jù)獲取后均經(jīng)過人工逐條清洗并反復核實以確保樣本數(shù)據(jù)真實性和準確性,整理形成包含股票代碼、年份、IPC分類號和頻數(shù)在內(nèi)的有效觀測值13301條。
運用Levins寬度指數(shù)公式中的Shannon-Wiener指數(shù)來計算企業(yè)間技術(shù)生態(tài)位寬度:
(1)

借鑒Diestrei et al.(2012)做法,用Pianka公式衡量技術(shù)重疊度:
(2)
NOik代表企業(yè)i和企業(yè)k之間技術(shù)生態(tài)位重疊度,r代表兩企業(yè)技術(shù)資源等級數(shù)(技術(shù)類別總數(shù)),Pij代表企業(yè)i對技術(shù)資源j的利用占其對全部技術(shù)資源利用頻度,Pkj代表企業(yè)k對技術(shù)資源j的利用占其對全部技術(shù)資源利用頻度。NOik具有值域[0,1]。把有效觀測值13301條按照年份分成8組,利用Stata16.0軟件,對2011-2018年滬深醫(yī)藥上市公司技術(shù)寬度和技術(shù)重疊度值標準化處理,設定聚類數(shù)為4(K=4),進行中位數(shù)聚類分析,報告“技術(shù)追隨型”473個,“技術(shù)多樣型”393個,“技術(shù)專長型”154個,“技術(shù)平衡型”194個。把上述結(jié)果放入以技術(shù)寬度為橫軸,技術(shù)重疊度為縱軸象限如圖3所示。

圖3 2011-2018年滬深醫(yī)藥上市公司技術(shù)生態(tài)位均值與標準差注:括號內(nèi)左邊數(shù)據(jù)為技術(shù)寬度,右邊數(shù)據(jù)為技術(shù)重疊度。
技術(shù)寬度和技術(shù)重疊度全樣本均值分別為2.01和0.81,“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技術(shù)寬度和技術(shù)重疊度均值為1.48和0.96,表明企業(yè)技術(shù)領(lǐng)域知識有限且面臨激烈外部競爭。“技術(shù)多樣型”企業(yè)技術(shù)寬度和技術(shù)重疊度均值分別為2.37和0.91,企業(yè)掌握多技術(shù)領(lǐng)域知識但是面臨激烈外部競爭。“技術(shù)專長型”企業(yè)的技術(shù)寬度和技術(shù)重疊度均值分別為1.67和0.48,企業(yè)技術(shù)領(lǐng)域知識有限,但是有技術(shù)競爭優(yōu)勢。“技術(shù)平衡型”企業(yè)的技術(shù)寬度和技術(shù)重疊度均值分別為2.59和0.52,企業(yè)有多個技術(shù)領(lǐng)域知識,且擁有技術(shù)競爭優(yōu)勢。
(二)變量定義與測量
1.被解釋變量
根據(jù)已有文獻思路(Odusanya et al.,2018),使用資產(chǎn)凈利潤率(ROA)測量企業(yè)短期績效,使用ROE作為替代ROA的穩(wěn)健性檢驗指標,使用托賓Q指標來測量企業(yè)價值或者長期績效,并使用剔除無形資產(chǎn)和商譽后的托賓Q指標作為穩(wěn)健性檢驗指標。
2.解釋變量
企業(yè)技術(shù)生態(tài)位變量分四類,用虛擬變量來表示,即“技術(shù)追隨型”(低技術(shù)寬度和高技術(shù)重疊度)、“技術(shù)多樣型”(高技術(shù)寬度和高技術(shù)重疊度)、“技術(shù)專長型”(低技術(shù)寬度和低技術(shù)重疊度)和“技術(shù)平衡型”(高技術(shù)寬度和低技術(shù)重疊度)。
3.控制變量
控制變量共有6個,包括企業(yè)規(guī)模、企業(yè)年齡、賬市比、總資產(chǎn)負債率、股權(quán)性質(zhì)和股權(quán)集中度。企業(yè)規(guī)模以總資產(chǎn)對數(shù)來測量。企業(yè)年齡根據(jù)企業(yè)成立年份計算。參考Lam et al.(2002)研究結(jié)論,使用賬面市值比指標用來控制短期績效。資產(chǎn)負債率指標體現(xiàn)企業(yè)財務杠桿。股權(quán)性質(zhì)指上市公司是國有控股企業(yè)或非國有控股企業(yè),采用虛擬變量表示。遵循趙建武(2018)的思路,以前10大股東持股比例之和作為股權(quán)集中度的測量指標。

表1 主要變量的定義測量及數(shù)據(jù)來源
(三)基本模型構(gòu)建
基于上述分析,設定基本模型如公式(3)所示:
FPit=α+βTTYPEit+γControlit+εit
(3)
其中,i代表企業(yè),t代表時間,F(xiàn)Pit代表企業(yè)績效;解釋變量TTYPEit指企業(yè)技術(shù)生態(tài)位,Controlit代表控制變量,共6個,包括企業(yè)規(guī)模、企業(yè)年齡、賬市比、資產(chǎn)負債比、股權(quán)性質(zhì)和股權(quán)集中度。εit為擾動項,t∈[1,8]。
五、實證模型與結(jié)果分析
(一)變量描述性統(tǒng)計與多重共線性討論
所有變量觀測數(shù)、均值、標準差、最小值和最大值如表2所示。計算變量相關(guān)系數(shù)及方差膨脹因子檢驗變量間是否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結(jié)果顯示變量間相關(guān)系數(shù)均在0.6以下,表明并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考察變量膨脹因子(VIF)發(fā)現(xiàn),平均膨脹因子為1.285,單個變量最高膨脹因子為1.535,遠小于10,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1)限于篇幅,變量相關(guān)系數(shù)和膨脹因子分析結(jié)果可向通訊作者索取。。

表2 變量的描述性統(tǒng)計
(二)實證模型選擇
根據(jù)基本模型(3),需要在混合回歸、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中選擇合適模型展開實證。首先,F(xiàn)檢驗的P值為0.0000,LSDV法下,絕大部分個體虛擬變量都很顯著(P值為0.000),所以強烈拒絕原假設,認為固定效應模型優(yōu)于混合回歸。其次,LM檢驗的P值為0.0000,強烈拒絕不存在個體隨機效應的原假設,認為隨機效應模型優(yōu)于混合回歸。最后,豪斯曼檢驗的P值為0.0000,強烈拒絕原假設,認為固定效應模型優(yōu)于隨機效應模型,最后采用固定效應模型,設計短期績效模型如公式(4)和長期績效模型如公式(5):
ROAit=?0+?1TTYPEit+?2LNTAit+?3AGEit+?4BMRit+?5LEVit
+?6ENIDit+?7SCONit+ui+εit
(4)
TobinQit=?0+?1TTYPEit+?2LNTAit+?3AGEit+?4LEVit+?5ENIDit
+?6SCONit+ui+εit
(5)
(三)內(nèi)生性問題與工具變量的使用
模型(4)和(5)中,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之間可能存在遺漏變量、反向因果等,從而引發(fā)內(nèi)生性問題,為了避免出現(xiàn)“假”的回歸結(jié)果,借鑒Wooldridge(2002)和郭立新等(2019)做法,建立固定效應模型(模型6),討論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內(nèi)生性問題。
FPit= α+β1TTYPEit+β2Controlit+β3TTYPEi,t+1+β4Controli,t+1+ui+γt+εit
(6)
其中,F(xiàn)Pit代表當期企業(yè)績效,ui代表個體異質(zhì)性,γt代表時間固定效應,εit代表擾動項,TTYPEit代表當期解釋變量,Controlit代表當期控制變量,TTYPEi,t+1代表后期解釋變量,Controli,t+1代表后期控制變量。原假設為所有變量為外生變量,如果后期變量系數(shù)顯著,則拒絕原假設,表示該變量在統(tǒng)計意義上為內(nèi)生變量。分別以ROA、ROE和TobinQ為被解釋變量進行聚類穩(wěn)健回歸,設定5%顯著水平,當被解釋變量為ROA和ROE時,報告企業(yè)規(guī)模(p<0.01)、資產(chǎn)負債率(p<0.05)和股權(quán)性質(zhì)(p<0.05)為內(nèi)生變量。當被解釋變量為TobinQ時,報告企業(yè)規(guī)模(p<0.01)為內(nèi)生變量。進一步在經(jīng)濟意義上考察內(nèi)生變量,發(fā)現(xiàn)企業(yè)規(guī)模、資產(chǎn)負債率、股權(quán)性質(zhì)等變量受到國家宏觀政策、金融市場波動等外來因素影響。宏觀政策對企業(yè)規(guī)模擴張有顯著影響,例如徐保昌等(2020)研究發(fā)現(xiàn)環(huán)境規(guī)制與企業(yè)規(guī)模擴張呈現(xiàn)U型關(guān)系。宏觀政策環(huán)境影響了企業(yè)資產(chǎn)負債率,例如王宇偉等(2018)實證發(fā)現(xiàn),2008年以來較為寬松的宏觀政策環(huán)境下,金融資源被過多配置到資產(chǎn)周轉(zhuǎn)率和增加值率較低企業(yè),是企業(yè)杠桿率猛增的主要原因。
綜上,當被解釋變量為短期績效時,接受企業(yè)規(guī)模、資產(chǎn)負債率和股權(quán)性質(zhì)三個變量為內(nèi)生變量。當被解釋變量為長期績效時,由于經(jīng)濟意義上不能否認資產(chǎn)負債率和股權(quán)性質(zhì)受到國家宏觀政策、金融市場波動等外來因素影響,把企業(yè)規(guī)模、資產(chǎn)負債率和股權(quán)性質(zhì)列為內(nèi)生變量。分別對內(nèi)生性變量采用1-2期滯后作為工具變量,采用帶有工具變量的固定效應模型(FE-IV),分別以ROA、ROE和TobinQ為被解釋變量進行回歸。Davidson-Mackinnon檢驗結(jié)果分別在5%和10%的水平上顯著,拒絕了原假設,表明對可能的內(nèi)生性變量采用工具變量是必要的。
(四)實證結(jié)果分析
1.技術(shù)生態(tài)位對短期績效的影響:以“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為參照組
以ROA或ROE為被解釋變量,以“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TTYPE1)為參照組,分別使用個體固定效應模型和帶有工具變量的固定效應模型回歸,使用穩(wěn)健標準誤,結(jié)果如表3。
以ROA為被解釋變量,使用個體固定效應模型的實證結(jié)果表明,“技術(shù)多樣型”(TTYPE2)比“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TTYPE1)的ROA高出1.2%且在10%水平顯著,“技術(shù)專長型”(TTYPE3)比“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的ROA高出1.6%且在5%水平顯著,“技術(shù)平衡型”(TTYPE4)比“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的ROA高出1.9%且在1%水平顯著。使用工具變量回歸后,主解釋變量的系數(shù)和顯著性提高,“技術(shù)多樣型”比“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的ROA高出2.3%且在1%水平顯著,“技術(shù)專長型”比“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的ROA高出2.5%且在5%水平顯著,“技術(shù)平衡型”比“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的ROA高出3.9%且在1%水平顯著。考察FE-IV模型中工具變量合理性指標,Kleibergen-Paap rk LM統(tǒng)計量為33.005,對應P值為0.0000,強烈拒絕工具變量不可識別的原假設,Hansen J統(tǒng)計量為0.042,對應P值為0.8370,說明不存在識別過度問題,因此模型選取的工具變量是合適的。控制變量回歸結(jié)果表明,更長企業(yè)年齡、更高股權(quán)集中度、更低賬市比和更大企業(yè)規(guī)模能顯著增加醫(yī)藥上市企業(yè)短期績效。使用FE-IV模型的實證結(jié)果更加顯著,系數(shù)水平更高,控制變量的回歸結(jié)果與已有文獻結(jié)論基本一致。FE和FE-IV模型下,以凈資產(chǎn)收益率(ROE)為被解釋變量的實證結(jié)果驗證了上述結(jié)果。

表3 技術(shù)生態(tài)位對企業(yè)短期績效影響的回歸結(jié)果:以“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為參照組
實證結(jié)果驗證了假設1:“技術(shù)多樣型”比“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有更高短期績效,假設3:“技術(shù)專長型”比“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有更高短期績效,假設5:“技術(shù)平衡型”比“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有更高短期績效。
2.技術(shù)生態(tài)位對長期績效的影響:以“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為參照組
以TobinQ為被解釋變量,以“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為參照組,分別使用個體固定效應模型(FE)和帶有工具變量的固定效應模型(FE-IV)回歸,使用穩(wěn)健標準誤,結(jié)果如表4。

表4 技術(shù)生態(tài)位對企業(yè)長期績效影響的回歸結(jié)果:以“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為參照組
FE模型和FE-IV模型實證結(jié)果表明,“技術(shù)多樣型”比“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TobinQ系數(shù)分別低0.55和0.592且在1%水平顯著,“技術(shù)專長型”比“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TobinQ系數(shù)分別低0.709和0.976且在1%水平顯著,“技術(shù)平衡型”企業(yè)比“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TobinQ系數(shù)分別低0.577和0.647且在5%水平顯著。考察工具變量的合理性,顯示模型選取工具變量是合適的,控制變量回歸結(jié)果與已有文獻結(jié)論基本一致。初步回歸結(jié)果顯著拒絕了假設2、假設4和假設6,相比“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技術(shù)多樣型”、“技術(shù)專長型”和“技術(shù)平衡型”企業(yè)有更低長期企業(yè)績效,實證數(shù)據(jù)結(jié)果與經(jīng)濟學直覺和常識不符合。
進一步考察TobinQ指數(shù)構(gòu)成,取決于企業(yè)市值與總資產(chǎn)比值,技術(shù)生態(tài)位通過計算專利申請技術(shù)領(lǐng)域和頻數(shù)獲得,醫(yī)藥企業(yè)從申請專利到最后藥品上市,還要經(jīng)歷生產(chǎn)工藝改進、臨床試驗和申請注冊審批等多個環(huán)節(jié),投資者不太可能馬上對企業(yè)申請專利的行為做出反應。同時,相比“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其他類型企業(yè)申請專利后更可能將研發(fā)費用作資本化調(diào)整,推動了企業(yè)無形資產(chǎn)和總資產(chǎn)上升。上述原因?qū)е铝丝此啤胺闯!钡幕貧w結(jié)果。
為檢驗可能存在的投資者反應滯后效應,加入技術(shù)生態(tài)位指標滯后1-2期再回歸(TobinQ2),在技術(shù)生態(tài)位滯后2期情況下,在FE和FE-IV模型下,“技術(shù)多樣型”比“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的TobinQ系數(shù)分別高了0.555和0.544,且在1%水平顯著;“技術(shù)專長型”比“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的TobinQ系數(shù)高了0.507和0.588,且在10%水平顯著。“技術(shù)平衡型”比“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的TobinQ系數(shù)分別高了0.375和0.4,但是不顯著。將主解釋變量的滯后期加入到3期以上,發(fā)現(xiàn)相比“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其他類型企業(yè)的回歸系數(shù)都不顯著。這是因為受到宏觀環(huán)境風險增大、市場勢力變更、主導技術(shù)變更等多種因素影響,長期內(nèi)處于較高技術(shù)生態(tài)位企業(yè)獲取競爭優(yōu)勢的不確定性進一步放大。
綜上,采用滯后兩期的技術(shù)生態(tài)位的分析結(jié)果,實證結(jié)果驗證了假設2:相比“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技術(shù)多樣型”企業(yè)有更高的長期績效,假設4:相比“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技術(shù)專長型”企業(yè)有更高的長期績效。
3.技術(shù)生態(tài)位對企業(yè)績效的影響:以“技術(shù)多樣型”企業(yè)為參照組
為進一步驗證“技術(shù)多樣型”、“技術(shù)專長型”和“技術(shù)平衡型”企業(yè)間績效差異,以“技術(shù)多樣型”企業(yè)為參照組進行FE-IV模型回歸,考慮到投資者反應遲滯因素,以TobinQ為被解釋變量的回歸中加入主解釋變量的滯后1期和2期,回歸結(jié)果如表5所示。
Kleibergen-Paap rk LM統(tǒng)計量和Hansen J統(tǒng)計量以及對應P值表明,四組FE-IV模型工具變量采用是適合的。以ROA和ROE為被解釋變量的FE-IV模型回歸結(jié)果顯示了“技術(shù)平衡型”比“技術(shù)多樣型”企業(yè)短期績效更高,系數(shù)分別為1.6%和2.5%,且在5%水平顯著,驗證了假設7:“技術(shù)平衡型”比“技術(shù)多樣型”企業(yè)有更高短期績效。無論是在技術(shù)生態(tài)位當期還是滯后2期情況下,以TobinQ為被解釋變量的回歸結(jié)果都不支持“技術(shù)平衡型”比“技術(shù)多樣型”企業(yè)長期績效更高,這一結(jié)果支持了本研究在研究假設中的討論,長期看,“技術(shù)平衡型”和“技術(shù)多樣型”企業(yè)各有優(yōu)劣。此外,回歸結(jié)果不支持“技術(shù)專長型”比“技術(shù)多樣型”企業(yè)短期和長期績效顯著更高,也支持了研究假設的討論結(jié)論。
(五)穩(wěn)健性檢驗
本研究做了兩個穩(wěn)健性檢驗:第一,使用ROE替代ROA作為短期績效指標進行回歸,回歸結(jié)果穩(wěn)健,結(jié)論不變。此外,使用TobinQ2替代TobinQ進行回歸,與TobinQ不同,TobinQ2=市值/(資產(chǎn)總計—無形資產(chǎn)凈額—商譽凈額),結(jié)論不變。第二,使用子樣本進行回歸檢驗。由于技術(shù)生態(tài)位是逐年計算得出,考慮到回歸中有滯后2期情況,不宜刪除太多年份,本研究剔除了2011年數(shù)據(jù),使用2012-2018年7年子樣本數(shù)據(jù)進行回歸檢驗,結(jié)論不變。

表5 技術(shù)生態(tài)位對企業(yè)績效影響的回歸結(jié)果:以“技術(shù)多樣型”企業(yè)為參照組
六、結(jié)論與對策建議
(一)結(jié)論與理論貢獻
本研究定義企業(yè)技術(shù)生態(tài)位為企業(yè)技術(shù)能力的相對位置與發(fā)展?jié)摿Γ霞夹g(shù)寬度和技術(shù)重疊度構(gòu)建了四個技術(shù)生態(tài)位,即“技術(shù)追隨型”、“技術(shù)多樣型”、“技術(shù)專長型”和“技術(shù)平衡型”企業(yè)。利用2011-2018年滬深醫(yī)藥上市公司面板數(shù)據(jù)展開實證,結(jié)果顯示,相比“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其他企業(yè)有更高短期和長期績效,相比“技術(shù)多樣型”企業(yè),“技術(shù)平衡型”企業(yè)有更高短期績效。本研究可能的理論貢獻在于:
第一,將企業(yè)技術(shù)能力劃分為四個技術(shù)生態(tài)位,有助于更全面準確地測量企業(yè)技術(shù)能力,更清晰地解釋技術(shù)能力對企業(yè)績效的作用機制。以往基于某一維度定義的技術(shù)能力對企業(yè)績效作用的研究多有爭議,以技術(shù)多樣化對企業(yè)績效作用的研究為例,Watanabe et al.(2005)分析1980-1998年間日本主導機電企業(yè)的技術(shù)軌跡數(shù)據(jù),認為技術(shù)多樣化和銷售收入間的良性循環(huán)是佳能公司可持續(xù)性發(fā)展的來源。然而Bergek et al.(2009)則發(fā)現(xiàn)技術(shù)領(lǐng)域更加聚焦的GE公司電力部門比技術(shù)更多樣化的ABB公司電力部門更具有發(fā)展?jié)摿ΑI鲜鰻幷撝屑夹g(shù)多樣性指高技術(shù)寬度,包含了不同技術(shù)競爭力(技術(shù)重疊度)的情境,僅從技術(shù)寬度(多樣性)一個維度刻畫擁有世界領(lǐng)先技術(shù)的日本佳能公司和技術(shù)競爭力相對弱的ABB公司電力部門難免會產(chǎn)生相矛盾的結(jié)論,從而削弱研究科學性和價值。近年來學者們呼吁使用多維度定義技術(shù)能力,如Pan et al.(2018)通過中國上市公司數(shù)據(jù)實證發(fā)現(xiàn)技術(shù)多元化和績效關(guān)系的不一致性情況,提出一個結(jié)合技術(shù)廣度和深度的技術(shù)多樣化定義才能解釋上述不一致的現(xiàn)象。
第二,為完善“技術(shù)戰(zhàn)略—結(jié)構(gòu)—創(chuàng)新績效”研究范式提供新思路。當前企業(yè)技術(shù)戰(zhàn)略績效研究多采用Chandler(1962)“戰(zhàn)略—結(jié)構(gòu)—績效”(SSP)研究范式,強調(diào)與技術(shù)戰(zhàn)略相匹配的組織結(jié)構(gòu)是產(chǎn)生高創(chuàng)新績效的基本條件,學者們多以專利數(shù)量、新產(chǎn)品銷售率等指標來測量創(chuàng)新績效(Liu et al.,2007;李笑等,2020),由于技術(shù)戰(zhàn)略制定過程考慮了企業(yè)間技術(shù)競爭情況,以專利數(shù)量來測量創(chuàng)新績效,不能全面體現(xiàn)企業(yè)間技術(shù)能力相對位置變化,以此來檢驗技術(shù)戰(zhàn)略實施效果存在邏輯上瑕疵。使用企業(yè)技術(shù)生態(tài)位變遷來檢驗技術(shù)戰(zhàn)略實施效果,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新思路。
第三,為理解企業(yè)技術(shù)能力演化過程提供新視角。四類企業(yè)技術(shù)生態(tài)位的劃分為刻畫企業(yè)技術(shù)能力由低水平平衡(“技術(shù)追隨型”)向高水平平衡(“技術(shù)平衡型”)的發(fā)展路徑提供了可能性。企業(yè)可以通過改善技術(shù)生態(tài)位來提升績效,成功企業(yè)的能力發(fā)展路徑存在多種可能,例如可能是“技術(shù)追隨型”——“技術(shù)多樣型”——“技術(shù)平衡性”的技術(shù)能力發(fā)展路徑,也可能是“技術(shù)追隨型”——“技術(shù)專長型”——“技術(shù)平衡性”的發(fā)展路徑,或者是“技術(shù)追隨型”——“技術(shù)多樣型”——“技術(shù)專長型”——“技術(shù)平衡性”的發(fā)展路徑等,取決于行業(yè)和組織的創(chuàng)新條件。
(二)管理啟示
以技術(shù)重疊度和技術(shù)寬度刻畫的技術(shù)生態(tài)位體現(xiàn)了組織對效率和柔性的戰(zhàn)略平衡,事關(guān)企業(yè)生存和持續(xù)性發(fā)展。一方面,企業(yè)提升現(xiàn)有技術(shù)能力(降低技術(shù)重疊度)以保持生產(chǎn)效率與短期競爭優(yōu)勢,另一方面,對技術(shù)發(fā)展趨勢保持知覺(提升技術(shù)寬度)以保持戰(zhàn)略柔性和環(huán)境適應能力。成功者如IBM在一個世紀跨度中,從一家生產(chǎn)秤、時鐘和制表機的小型企業(yè),歷經(jīng)電腦硬件制造商、軟件提供商,實現(xiàn)到技術(shù)服務型大企業(yè)轉(zhuǎn)變,成功處理了上述戰(zhàn)略平衡問題。現(xiàn)實中由于技術(shù)戰(zhàn)略平衡處理不當,短期成功導致長期失敗(如柯達公司)或者因為過分關(guān)注長期技術(shù)目標而在短期內(nèi)失敗(新創(chuàng)企業(yè))的例子比比皆是。管理實踐中,面對效率與柔性、短期技術(shù)能力和長期技術(shù)能力的平衡,基于有限資源和不同情境,在什么時候以什么方式提升技術(shù)能力是企業(yè)關(guān)注的核心問題。四類技術(shù)生態(tài)位劃分為解決上述問題提供了參考和依據(jù)。企業(yè)可以使用技術(shù)生態(tài)位測量方法更為準確地評估技術(shù)能力,設計適合企業(yè)情境的技術(shù)發(fā)展路線。
以“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技術(shù)生態(tài)位變遷為例,該類型企業(yè)處于產(chǎn)業(yè)鏈低端,知識基礎(chǔ)小、技術(shù)競爭力弱,互補資產(chǎn)匱乏,技術(shù)方向上追隨上游企業(yè)或者集成企業(yè)。由于企業(yè)技術(shù)能力發(fā)展具有累積性特征,關(guān)鍵性緘默知識尤其需要在產(chǎn)品設計生產(chǎn)的特定情境中獲取,因此該類型企業(yè)不太可能越過“技術(shù)多樣型”和“技術(shù)專長型”企業(yè)直接向“技術(shù)平衡型”企業(yè)轉(zhuǎn)型。“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技術(shù)生態(tài)位變遷通過技術(shù)與市場互動完成。首先討論向“技術(shù)專長型”生態(tài)位變遷。在外部環(huán)境相對穩(wěn)定情況下,面臨著技術(shù)、市場、組織資源約束,“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可以通過節(jié)儉式創(chuàng)新或成本創(chuàng)新,在已有客戶中發(fā)展出為特定客戶量身定做的具備基本功能的低成本產(chǎn)品(Ernst et al.,2015),為此,需要在原有產(chǎn)品組件知識基礎(chǔ)上針對特定客戶群體進行架構(gòu)創(chuàng)新,并在產(chǎn)品獲得市場回應后,通過生產(chǎn)和市場互動不斷積累該技術(shù)領(lǐng)域知識,特別是緘默知識,從而逐漸演化為服務特定客戶群的“技術(shù)專長型”企業(yè)。其次討論向“技術(shù)多樣型”生態(tài)位變遷。隨著已有客戶品味和愛好變化以及技術(shù)環(huán)境變化,新的客戶需求或技術(shù)機會將會創(chuàng)造新的產(chǎn)品技術(shù)需求,引導“技術(shù)追隨型”企業(yè)開發(fā)或獲取多樣化技術(shù),推動產(chǎn)品多樣化并獲取范圍經(jīng)濟優(yōu)勢,Pavitt et al.(1989)和Suzuki et al.(2004)研究表明企業(yè)需要更多樣化的技術(shù)來應對產(chǎn)品多樣性需求,在市場多樣化需求和技術(shù)多樣化互動中,逐漸完成向“技術(shù)多樣型”生態(tài)位變遷。
技術(shù)生態(tài)位分類有助于企業(yè)技術(shù)發(fā)展路線的設計,但是并不適用于所有行業(yè)。技術(shù)寬度和技術(shù)重疊度的測量基于企業(yè)專利申請的數(shù)量和類別,適用行業(yè)要求以專利為技術(shù)軌跡決定因素之一,不適用使用商業(yè)秘密、秘訣等方式為技術(shù)軌跡的行業(yè)。參考Pavitt(1984)產(chǎn)業(yè)分類,技術(shù)生態(tài)位分類適用行業(yè)包括以科學為基礎(chǔ)的產(chǎn)業(yè)(醫(yī)藥/電子/電力/化學品等)、專業(yè)化供應商(如機械、工具設備等)以及規(guī)模密集型產(chǎn)業(yè)(如鋼鐵、汽車制造等),不適用供應商主導性(如農(nóng)業(yè)和房地產(chǎn)等)行業(yè)。此外,從創(chuàng)新過程特征看,技術(shù)生態(tài)位分類更適用于知識累積程度高的熊彼特Ⅱ型產(chǎn)業(yè)。
(三)不足與展望
本研究存在幾方面不足:第一,技術(shù)生態(tài)位構(gòu)念有待完善。技術(shù)生態(tài)位構(gòu)念和分類有助于更全面準確測量企業(yè)技術(shù)能力,限于國內(nèi)專利數(shù)據(jù)庫未提供專利他引信息,因此使用了代表專利數(shù)量的專利分類數(shù)據(jù),未使用以他引次數(shù)來表征的專利質(zhì)量指標,對企業(yè)技術(shù)能力的反映可能存在偏差。第二,企業(yè)技術(shù)能力提升是一個長期演化過程,技術(shù)能力提升對企業(yè)長期影響可能持續(xù)存在,本研究采用了時間跨度為8年的非平衡面板數(shù)據(jù),依然不能保證研究結(jié)果能夠完全體現(xiàn)技術(shù)生態(tài)位對企業(yè)績效的影響。
結(jié)合上述不足,未來研究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展開:一是使用反映技術(shù)質(zhì)量的指標測量技術(shù)重疊度,可以借鑒Podolny et al.(1995)的做法,通過專利交叉引文率和共引率來衡量企業(yè)技術(shù)能力相似性,有利于發(fā)現(xiàn)企業(yè)間技術(shù)的共同源頭。當然,這一方法并非無懈可擊,使用引文方法具有引文順序依賴性特點,不能充分提供某一創(chuàng)新的技術(shù)基礎(chǔ)知識(Aharonson and Schilling,2016),此外,如果企業(yè)出于專利策略和競爭策略的考慮造成企業(yè)間專利引用的缺乏,也會導致該方法的局限性。二是可以采集更多行業(yè)和更長時間內(nèi)的數(shù)據(jù)展開實證研究,可以在不同情境下尋求不同技術(shù)生態(tài)位和企業(yè)績效之間的中介因素或者調(diào)節(jié)因素,例如組織學習方式、創(chuàng)新網(wǎng)絡(閆俊等,2018)等。也可以依據(jù)技術(shù)生態(tài)位分類,通過質(zhì)性研究方法,開展技術(shù)生態(tài)位變遷的應用研究,加深對企業(yè)技術(shù)能力作用機制的理解。
- 南方經(jīng)濟的其它文章
- 精英身份與農(nóng)民創(chuàng)業(yè):趨名還是逐利?
- 中國“三農(nóng)”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政策的歷史演進:基于中央一號文件的語料庫研究
- 稅收政策對居民消費的“異質(zhì)性”效應
——基于規(guī)模結(jié)構(gòu)雙重視角下的實證分析 - 自由貿(mào)易試驗區(qū)建設與地區(qū)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升級
——基于中國286個城市面板數(shù)據(jù)的實證分析 - 中國當前勞動力技能短缺與企業(yè)應對
- 工資對個人勞動供給的非線性影響:部門市場化程度差異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