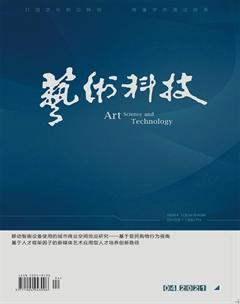電影《羅生門》的藝術美探究
摘要:《羅生門》講述的是一個日本武士被殺的故事,故事本身并沒有什么傳奇性色彩,但是卻開啟了日本電影的新時代。電影直面人性善惡,每個人物都從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發進行敘述,展現了人性的自私與悲哀。本文從電影賞析的角度出發,分析其獨具一格的藝術美。
關鍵詞:《羅生門》;電影;藝術美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1)04-00-02
0 引言
電影藝術自誕生以來,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斷完善與發展,實現了世界范圍內的文化互通。繼歐洲先鋒主義、意大利新現實主義之后,第三次具有世界性影響的新浪潮式電影運動爆發,宣揚以現代主義精神徹底改造電影藝術。而日本電影作為非歐美式的電影逐漸受到影響,在影片創作、形象構建等方面都展現出同構性,也進一步實現了新浪潮的模式化——反抗好萊塢的主流文化。因此,日本本土性的新浪潮電影模式被載入世界電影史冊。基于此,本文對黑澤明導演的《羅生門》進行簡要概述,從敘事藝術、細節表現等方面分析影片,旨在深入研究電影,引發人們的思考。
1 《羅生門》的歷史背景
二戰之后,人類對傳統歷史產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崩潰,對未來的不確定感到迷茫與彷徨,甚至陷入苦悶絕望的境地。這期間,大批青年導演站了出來,他們渴望重新認識現實,決定改變傳統電影注重導演資歷的陳舊制片方式,以一種極其大膽的拍攝手法,加上創新的電影藝術技巧,創造出了屬于新生代的現實主義電影,在電影界掀起了新浪潮運動。事實證明,這是一場運動,也是一場奇跡,不僅僅促進了歐洲電影的發展,更促進了全世界電影的發展[1]。
羅生門,即羅城之門。在這里,你可以看見戰亂紛飛,可以看見生靈涂炭,可以看見遍地尸野,可以看見陰森恐怖,可以看見人性鬼魅。羅生門是生死的分界線,是生死的大門,令人談之色變、遇之色變,它隔絕了人的生死、人世和地獄,其含義豐富而具體,而電影也聚焦人性的善惡,指向人性的生死,指向更深處[2]。自此,日本電影對現實主義思想發起了新的抨擊,無論是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批判,還是對好萊塢式電影主流文化的反抗,都是日本本土脈絡中的文化反思與文化再現。
2 《羅生門》的敘事藝術
2.1 倒敘發展,層次多元
在傳統的一元化思想下,真相只有一個,但在現實中,真相不止一個,有多少人見證,便能產生多少種主觀意識。事實經過個人主觀思維的運作,成為個人對真相的認識。一宗謀殺,在電影的敘述過程中并沒有多復雜,各位經歷者、見證者都陳述著自己的事實。每個人講述的事件都是對親眼看見的事件的個人意識的再現,故存在較強的主觀能動性,造成了眾說紛紜、真相難辨的局面[3]。導演黑澤明恰到好處地抓住了人類的主觀現實表現,平等地給參與敘述的七個人物分配鏡頭,使其在利益的驅使下面向觀眾、說服觀眾。世界總是荒誕的,說謊的究竟是誰,每個人的證詞各不相同,一個人一個故事,這正好印證了那句話:適合自己的才是最真實的[4]。荒山上的慘案陷入了一團看不清、猜不透的迷霧中[5]。
第一,強盜的供詞。強盜說自己只是見色起意,誘騙武士上山,襲擊了武士,然后又誘騙武士的妻子,決定對其實施強奸,但事實上強奸未遂。想要離開時,武士的妻子開始挑撥離間,武士與強盜爭斗,經過多個回合的斗爭,武士被殺,強盜獲勝[6]。在強盜的敘述中,殺人并不是他的本意,他只是一個勇敢無畏的角斗士,為愛決斗,一切都是那么理所當然。
第二,真砂的供詞。真砂直言被奸污后愧對丈夫,自己跪地祈求原諒,失聲痛哭,但丈夫給予的只有鄙視與冷漠,她不得已遞過短刀給丈夫,愿以死明志,然而換來的只有丈夫的拋棄。自殺還是同歸于盡?而后,她昏死,丈夫死亡……對于女人而言,廉恥、貞潔比生命更加珍貴,真砂認為自己不僅僅受到了強盜的極大傷害,還受到了丈夫冷酷的侮辱。她也承認殺人,但在敘述之中,她巧妙地強調丈夫可能是受羞恥心的驅使主動受死,試圖洗脫罪名[7]。
第三,武士的供詞。強盜不僅僅見色起意,強奸了自己的妻子,而且在奸污后對其進行言語誘惑,想要妻子跟從他,拋棄丈夫。妻子并沒有表現出痛苦與絕望,反而言聽計從,而且脅迫強盜殺了自己,毫不顧忌夫妻感情。面對妻子的冷酷與無情,武士痛不欲生,只能選擇告別這個荒誕與無情的世界,他拾起短刀,對準胸口,自盡而亡。他死后,一個人輕輕地走來,輕輕地拿走了短刀。在主觀敘述之下,武士否認了強盜所述的決斗失敗,維護自己作為武士剛正勇武的尊嚴,否認了妻子的哀求原諒,指控出妻子的兇殺罪行。
而本案中的樵夫則認為這三個人都在撒謊,從新的視角對整個案件的經過進行敘述。第三人稱增強了故事的客觀性,打開了故事講述的超敘述層次,但這是樵夫竊取短刀后,精心編造的新的主敘述層次[8]。作為敘述的受眾,我們在故事的發展過程中被不斷說服,不難看出,那一聲聲振振有詞的自我辯護,都是為了一己私利,都是在美化自我。
2.2 未知結果,判斷思考
當事人不同的供詞,讓我們深陷于迷霧之中,反觀世界,人類只有真正認識到自己的渺小、未知的偉大,才能因此而偉大。電影通過多重敘述構造了一個謎團,敘述人物、敘述情節、敘述形式等的差異,導致事件真相撲朔迷離,讓人不知何為真,何為假[9]。但細細想來,真相真的重要嗎?在現實社會中,人類通過簡單的對錯、真假的一元化思想,判斷事情的所謂真相,從道德、法律等層面對真相進行評價。也許事物的發展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果。一聲嬰兒的啼哭將迷霧吹散,雨過天晴,樵夫抱著嬰兒向夕陽深處走去,至此,電影散場,真相散場,人性散場,新的人性復蘇也在夕陽的深處重新入場[10]。無論是敘述者的言語行為,還是接受者的主觀認知,都在整體的構建之中相互融合、相互串聯、相互分散,要用心靈去反思認識,用心靈去尋找永生[11]。
3 《羅生門》的細節藝術
3.1 畫面表現
傳統電影大多以黑白影像的形式出現,現代電影以色彩語言的增強、以光影的變幻、以視覺上的沖擊,增添了愉悅的因素,用一種精神鴉片似的色彩習慣,吸引觀眾的眼球[12]。在彩色影片時代,很難看見純粹意義上的黑白電影。一部好的電影,色彩的表達會成為主題與人物的延伸,光和影的對照、黑與白的展現,都源于故事敘述與情感表達的需要。環境的變化能體現出心中的情感,影片的大部分畫面充斥著低垂的天空和灰蒙蒙的霧氣,將危險、黑暗、壓抑的主題展現得淋漓盡致,將受眾自然地帶入日本12世紀真實而黑暗的社會之中,帶入陰暗逼人的審訊室中。接受審訊時,人性曝光燈之下的每一個當事人,都展現了自己陰冷的一面,看似無比合理的解釋,進一步體現出了其靈魂的丑惡。燈光照亮了武士,照亮了強盜,照亮了妻子,照亮了樵夫,照亮了日本的普通大眾。二戰結束后,生活本該是充滿希望的,本該是充滿活力的,但是這些希冀卻與現實形成了強烈的反差。藝術來源于生活,也應該還原生活,以一種貼近生活的心理表達方式,奠定日本本土電影殘酷、陰冷的情感基調,但是內心的人性終將得到自我救贖,終將在現實之下走向溫情,走向人性復蘇的未來[13]。結尾黑白表現的落差再次直擊觀眾,究竟是黑暗取得了勝利,還是白色帶來了光明?電影走向高潮,走向落幕,走向未來,未來將是陽光燦爛的、美好的、有希望的[14]。
3.2 非語言符號運用
非語言符號是影視作品的重要內容,影片創作通過對視覺符號的藝術化處理最大限度地傳遞信息。《黑天鵝》通過女主人公服飾的變化展現其破繭而出的過程;《末代皇帝》從溥儀的視角出發回憶往事,以強烈的色彩凸顯出溥儀跌宕起伏、悲慘灰暗的人生[15]。回到《羅生門》電影本身,作者巧妙地利用黑白兩色,將觀眾與電影片段中刀的符號聯系在一起,恰到好處地使用了刀這個符號,實現了共性與個性的結合,由個性特征推及共性價值[16]。
刀,在電影開篇就成了影片的視覺載體和構成基礎,是故事的開啟者;刀,插在死去的武士身上又離奇失蹤,是案件的見證者;刀,在武士和強盜的纏斗中成為兇器,是社會的被害者;刀,在妻子奸污后被出現,引發決斗騷亂,是謀殺的導火索;刀,在武士死后被樵夫帶走,是罪惡靈魂的救贖者。刀在黑與白的光影中,從開篇到見證最后的救贖,通過不同場景的結合,構造出了具體的符號形象,成功推動了情節的發展,深化了主題[17]。與此同時,其對人物形象的塑造、影片整體節奏的把控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把刀反映了社會百態,以小見大,折射出了人文關懷,體現了影視中非語言符號的傳播策略[18]。刀,剖開的是自私本我的人類、撲朔迷離的人性、荒誕離奇的世界,影片從謊言重新回到真實,說明人與人之間還是存在信任的[19]。
4 結語
人性的考量沒有對與錯,正如黑澤明導演所言,世界很復雜,人把它想得太簡單了。人類在真真假假、有有無無中走向人性解放,唯有不斷對自身進行反思,保持善良的心,才能戰勝自己,走向更遠、更深處。
參考文獻:
[1] 許家睿.《綠皮書》:鋼琴鍵上的“黑白配”[J].藝術科技,2020,33(1):81-82.
[2] 姚佳.淺析小說日劇《絕叫》中陽子悲劇的原因[J].藝術科技,2019,32(09):105-106.
[3] 彭楠.從電影《賽德克·巴萊》看賽德克族人的血性[J].漢字文化,2020(04):88-89.
[4] 侍渝杰.淺論《罪與罰》的倫理觀[J].大眾文藝,2019(7):45-46.
[5] 徐亦鑫.從《驛路》看人性的復雜性[J].漢字文化,2019(11):97-98.
[6] 李曉薇.淺析《水形物語》的敘事策略及主題表達[J].藝術評鑒,2019(8):157-158.
[7] 陶野.從紀錄片《流亡的故城》看顧城和謝燁的愛情悲劇[J].漢字文化,2020(06):87-89.
[8] 顧亮.淺析《肖申克的救贖》中“關不住的鳥”——安迪[J].漢字文化,2020(6):99-101.
[9] 侍渝杰.《推拿》:模糊與清晰[J].戲劇之家,2019(20):100,102.
[10] 魏中華.淺析《局外人》中的荒誕世界與對本真的追求[J].漢字文化,2019(10):41-42.
[11] 顧雯清.淺析電影《夜宴》中的插曲《越人歌》[J].黃河之聲,2019(19):138-139.
[12] 余雅雯.淺談《小鞋子》里苦難生活中的人性之光[J].漢字文化,2019(16):102-103.
[13] 劉高揚.對電視劇配樂的幾點思考[J].中國電視,2019(02):97-100.
[14] 侍渝杰.《野草莓》:懺悔與重生[J].漢字文化,2019(08):37-38.
[15] 孫遠軼.淺析電影中鋼琴美學的特點與表達[J].黃河之聲,2019(19):137-139.
[16] 朱卉.由《樓下的房客》淺談人性的悲哀[J].漢字文化,2019(11):121-122.
[17] 宗楨,劉雪芹.影視作品中非語言符號的應用與傳播——以電視劇《都挺好》為例[J].漢字文化,2019(20):70-71,73.
[18] 劉新元.淺談電影《小森林》美食背后的生活智慧[J].戲劇之家,2019(26):97-98.
[19] 巢千麗.淺析電影《龍蝦》中的婚戀觀與人性的沖突[J].漢字文化,2019(11):91-92.
作者簡介:王志鵬(2000—),男,江蘇揚州人,本科在讀,研究方向:漢語言文學、戲劇文學。
指導老師:鄭仁霞